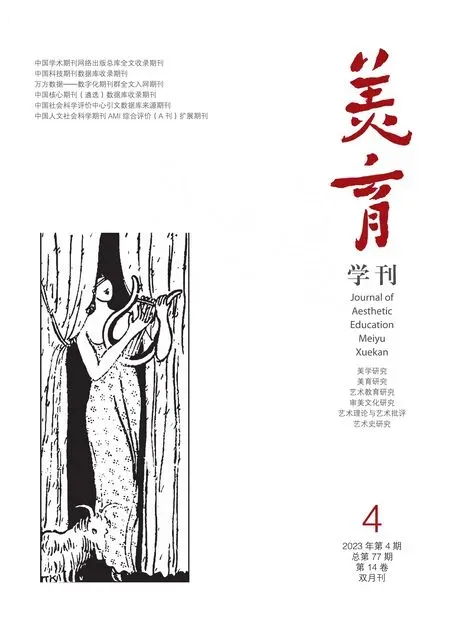风月繁华记盛时,欲将宝鉴警顽痴
——吴世昌《红楼梦》图咏论略
陈炜舜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 999077)
一、引言
《红楼梦》问世后,一直有以题咏诗歌的方式来评点此书者。民国以后,新红学诞生,不少红学家在撰写论著之余,仍喜以题咏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仅如此,由于《红楼梦》对人情世故的千姿百态曲尽描摹,兼以旧体诗歌本身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因此题咏者在表达对小说内容、人物之情感的同时,也可能在有意无意间带有一己身世的感慨。在芸芸红学家中,吴世昌便至少有四次题咏的经验。
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海宁人,著名学者,以诗词及《红楼梦》研究尤为知名。邓庆佑指出,吴世昌“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成就,甚至比他在文史领域其他方面研究的成就还大,知名度更高,是一位在中外享有盛名的红学家”。其首部红学专著,乃是1956年开始写作、196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的英文本《红楼梦探源》。1980年,他将从1962年到1972年发表在国内外报刊上的单篇红学论文收集成册,名曰《红楼梦探源外编》。此外还有若干单篇,后结集为《红楼碎墨》《吴世昌点评红楼梦》。[1]对于自己的红学观念,吴世昌如何以诗歌来呈现?这无疑是饶有兴味的。邓氏又云,吴世昌早在初中时期便已开始阅读《红楼梦》,但正式开始研究则在执教牛津以后。当时有指导的学生研究《红楼梦》,因此他不得不对此书的各种问题重新思考。此外,20世纪50年代《汉学要籍纲目》(巴黎、海牙联合出版)的编者约他为《红楼梦》撰写提要,限于篇幅,许多问题无法说透。他依据已发现的问题、已掌握的材料继续探研,因而有了1961年《红楼梦探源》英文本的面世。[1]1959年年底书成后,吴氏题以五首七绝,这是他首度创作的红楼题咏。1962年,吴世昌自英归国,此后至1980年间,三度为《红楼梦》图画题咏,共计三十篇次,皆为七绝。本文尝试聚焦后三度的图画题咏,讨论吴世昌如何透过诗歌创作与《红楼梦》文本、图像发生互动。
二、吴世昌《红楼梦》图画题咏考论
吴世昌三度为《红楼梦》图画题咏,三组诗作的数量多寡不一,而文字容或有重复互见之处。本节先通盘考察三度题咏的历程,再以出现于这三组诗作中的《宝钗扑蝶》一诗为中心,讨论吴氏如何修订此作,以呈现吴氏红楼题咏之来龙去脉。
(一)吴世昌题咏红楼图画的历程
增订版的《罗音室诗存》中收录了吴世昌《为徐平羽副部长题刘旦宅绘红楼人物图(十二首)》,其跋语云:
右为徐公题人物图十二幅,每幅一诗,裱成长卷,为郭老题端,俞平伯题七古一首,沈雁老题七律二首,我均录存。前年见徐公,则图已在十年浩劫中失去,我将所见各诗钞付徐公,而画则不可得矣。(1)吴世昌:《诗词论丛》,吴令华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99-400页。按:徐卷诸诗不见于香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罗音室诗词存藁》,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罗音室学术论著》第4卷《罗音室诗存》亦收录(第937-938页),文字同于《诗词论丛》。
据以上所言可知画家刘旦宅尝为徐平羽绘制《红楼人物图》十二幅(下文简称徐卷),而徐氏遂邀吴世昌逐幅题诗,装裱后又请郭沫若(1892—1978)题签,俞平伯(1900—1990)、茅盾(沈雁冰,1896—1981)赋诗。选择此三人参与题卷,盖因其身份之故:郭沫若时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茅盾时为文化部部长,俞平伯与胡适同为新红学之创始人。查《俞平伯诗全编》中有七古《红楼缥缈歌——为人题〈石头记〉人物图》一首[2],《茅盾集》中有七律《题〈红楼梦〉十二钗画册》二首[3]120,应当就是吴氏跋语提及之诗作。吴、俞、沈三人著作中皆未标示确切创作年份,考徐平羽于1960年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文物和艺术工作,曾因抵制江青对周恩来之攻击而遭关押七年之久,至1975年彻底平反。茅盾则于1949年至1965年担任文化部部长。而吴世昌于1962年自英归国,则其此番题诗之时间当在1962年至1965年间。再观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吴世昌发表《题〈石头记〉人物图(七绝四首)》,诗作实选自徐卷,而落款于1963年。[4]8这应当是吴氏题诗之确切年份。至于茅盾诗题虽有“十二钗”字样,但并非指涉传统的十二正钗。据吴世昌十二首诗作所见,绘画及题咏之标题依次为《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元春省亲》《湘云眠石》《探春结社》《凤姐设局》《妙玉祝寿》《三姐刎颈》《晴雯补裘》《袭人刺绣》《金钏投井》《平儿理妆》。据《红楼梦》原书第五回,黛玉至妙玉七人固皆居“金陵十二钗”正册,晴雯、袭人则在又副册。戚序本第十八回脂批论警幻情榜云:“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皆陪客也,《红楼梦》中所谓副十二钗是也。又有又副册三段词,乃晴雯、袭人、香菱三人而已,余未多及,想为金钏、玉钏、鸳鸯、素云、平儿等人无疑矣。”可见刘旦宅绘图时,并未选择正钗中的李纨、秦可卿、迎春、惜春、巧姐。盖因此五人中,李纨寡居有宣扬“封建贞节观”之疑,秦可卿颇有瑕行而故事难详,迎春懦弱无趣,惜春面冷心冷,巧姐晚辈,要到八十回后才正式登场,故刘旦宅另外选取了正钗以外个性鲜明且故事性强的五位女性角色。而俞平伯的《红楼缥缈歌》中有“芙蓉累德夭风流,倚枕佳人补翠裘。评泊茜纱黄土句,者回小别已千秋”之句,据其后来所言,乃阐发其“钗黛并秀”之说,且谓“芙蓉一花,双关晴黛。诔文哀艳虽为晴姐,而灵神笼罩全在湘妃”。[5]此未必与吴世昌之见相合,然亦可窥见徐卷中晴雯与钗黛并列之因由。惜画卷于动乱中遗失,所幸吴世昌当时抄录了自己及俞平伯、茅盾的题诗备份,这组作品方能流传至今。
1978年秋,红学家周雷(1938—2019)为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编辑《1979年红楼梦图咏月历》(后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同年11月梓行,下文简称月历)[6],同样邀请刘旦宅绘图十二幅,只是这次图画的主题是故事而非人物。据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中《茅盾与红学》一文记载,周雷原本拟请六位著名诗人或红学家每人题诗两首,然而:
一九七八年秋天,笔者(按:即周雷)为该杂志社编辑《一九七九年红楼梦图咏月历》,特请著名画家刘旦宅绘制了《红楼梦》故事图十二幅,并拟请茅盾、姚雪垠、吴世昌、周汝昌、张伯驹等六位著名诗人每人题诗两首。九月末的一天,我拿了刚从荣宝斋托好的画页,先到茅公府上,请他寓目。茅公一幅一幅仔细鉴赏,频频点头称赞。我拿出预先写好的十二个画题亦即诗题时,茅公兴致勃勃地提起笔来,一面胸有成竹地圈了四个题目,一面微笑着说:“好,我先来圈。《读曲》是一首,《葬花》是一首;《补裘》我最近给关良题过,也算一首,再来一首《赠梅》,是讲妙玉的,我来题好了。”九月二十八日,茅公就作好了另外三首,连同《补裘》一首,一并用他那工整秀逸的行楷写出。这些诗发表后,人们争相传诵。[7]16
如此一来,月历的题诗工作最后由五位诗人负责,计有茅盾四首,张伯驹(1898—1982)、吴世昌、姚雪垠(1910—1999)、周汝昌(1918—2012)各二首。兹将分工情况列表于下:

表1 《1979年红楼梦图咏月历》题诗分工情况
从表1可知各图的内容大抵与时令相关,如《葬花》在四月、《扑蝶》在五月、《咏菊》在八月、《补裘》在十一月、《赠梅》在十二月,等等。吴世昌在月历中负责的两首题诗,《射谜》为新作,《扑蝶》的文字则与当年题徐卷的《宝钗扑蝶》略有差异。再观1979年,新创立的《红楼梦学刊》于头两辑共刊登了吴世昌为徐卷所题诗作八首。第一辑所刊登的四首依次为《黛玉葬花》《探春结社》《三姐刎颈》《晴雯补裘》。四诗之内文与诗集所见基本上无大出入,唯三姐诗“谁知料理风流债”,“谁”改为“那”;晴雯诗“病里西施不耐秋,况教澈夜补金裘”,“耐”改作“胜”,“澈”改作“彻”。[4]8第二辑则为《宝钗扑蝶》《元春省亲》《湘云眠石》《妙玉参禅》四首。元春诗“片时相对泪滂沱”,“相对”改作“相见”。妙玉诗题由原本之“祝寿”改为“参禅”,内容则无变动。唯宝钗诗首联仍依徐卷本“山伯英台取次飞,轻罗小扇舞杨妃”[8],而非月历之修订本,可见吴氏于此诗文字有两存之意。
稍后,吴世昌再度为《红楼梦》图画题诗,这次是基于程十发(1921—2007)所绘的图册(额为《红楼梦人物图咏》,下文简称程画)。图册十六幅作品中,包括了《顽石难悟》《警幻司情》《兼美惊梦》《群艳射谜》和十二正钗的画像,其中《可卿失足》《迎春误嫁》《惜春出家》《李纨教子》《巧姐归农》的五位人物皆不见于1963年的徐卷。换言之,程画与徐卷题诗中重见之人物达七人,列表于下:

表2 徐卷与程画之重见人物及题诗
从表2不难发现,七人之中有六人的图画情节都不相同。实际上,其题诗也随之而异。但是,唯《宝钗扑蝶》不仅主题没有变更,文字也大体相同。再者,程十发在画册开端题曰:“余为《石头记》拟写十二金钗草稿,赠绍昌兄留念。”(2)吴世昌题咏:《红楼梦人物题咏》,程十发制图,收入魏绍昌集藏:《红楼雅集:当代名家红楼梦诗书画集》,上海:上海书店,2008年,第1册,第1页。绍昌即红学家魏绍昌(1922—2000),魏氏曾编纂《红楼雅集:当代名家红楼梦诗书画集》六册,于其身后出版。该图册汇集了众多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有关《红楼梦》的书画作品,吴世昌、程十发合作的画册《红楼梦人物图咏》编为册一。杜宣于2001年为《红楼雅集》所作前言云:
最近上海书店即将出版他珍藏的红楼梦书画库,其中包括:红楼梦人物图咏、石头泥塑集、红楼梦花名酒令签图册、红画集萃、红楼梦人物图咏诗意图等。
这真是一个伟大计划,一部旷世之书。时间是从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开始,到一九八零年前后为止,花了四五年时间,约请了七十名左右中国当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及红学家们作画题诗,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计划啊!他怀着这目标,奔走于京沪道中,叩开这么多大家的门扉,在他指定的命题下,临池泼墨,这又是多么艰巨的工作啊!所幸,当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书画市场停滞,大家都在守着清贫的日子,朋友间书画应酬,也都习以为常了。若按今日市场价值,这部画库,真可说价值连城了。[9]1-2
值得注意的是,魏绍昌开始《红楼雅集》的工作,是因为赵丹(1915—1980)、白杨(1920—1996)的《红楼梦咏菊诗意图册》。吴泰昌回忆道:
1979年春,我在上海,酷爱文艺史料收藏的魏绍昌先生在寓所给我看了一份《红楼梦咏菊诗意图册》原稿,赵丹绘菊花,白杨录书中诸人咏菊诗,共十二帧。绍昌先生珍惜地说,这是赵丹和白杨近年的合作,看过的人无不赞赏,作者已请了一些大家、名家为之题写。他特意给我看了茅盾先生的题诗。茅公素来吝于写诗,他为这本图册题写的诗引起我特殊的兴趣。1978年春赵丹来京看望过茅公,谈到他在“文革”时的遭遇,是年十月,茅公见到赵丹与白杨共同创作的这本图册,有感而发赋诗相勉,诗作赞扬他们“曾耐九秋冻,傲骨欺风霜”。绍昌先生希望我帮他们在京城请些文艺界老人为图册题写。我表示此事会放在心上,尽力去办。告别时,他交给我一个纸包,内有图册散页的复印件和多张有一定格式的空白宣纸。[10]
包括程画在内的所有作品都是作于这种宣纸之上。杜宣认为魏绍昌编纂此书在1976年至1980年间,然观白杨小引落款为“戊午春日”(1978年)[9]4,则其他作品面世必然更晚。周雷谓茅盾在1978年9月为月历题诗之后,“同年十月,茅公还作了《题赵丹白杨合作红楼梦菊花诗画册》长诗一章”。[7]16准此观之,程、吴合作之画册亦当成于1978年至1980年间。然而,程画与月历面世时间如此接近,吴世昌是先为何者题诗?笔者认为当以月历为先。从外证来看,茅盾题诗的次序,便是先月历、后《红楼雅集》。从内证来看,盖月历系由刘旦宅先画,再由周雷统筹,所以吴世昌之《射谜》《扑蝶》乃命题作诗,只是吴氏恰好有《扑蝶》旧作,故能稍作改动。而程画问世乃应魏绍昌之邀,虽以《红楼梦》为主题,却并无详细指引或限制,故此吴氏方能移录月历中两首现作,而请程十发依据诗意绘图。换言之,程画《宝钗扑蝶》题诗的文字虽与徐卷不尽一致,却应是取自月历而加以修订。
赵丹、白杨在文艺界享有盛名,不仅因为是影坛明星,还因在特殊时期备受摧抑而不屈不挠。赵善画、白善书,两人合作,文艺界有共同经历者自然一呼百应。吴世昌也曾下放到河南息县,至1971年方有机会返回北京。因为吴世昌敢说真话,他在浩劫中的遭遇可想而知。而他对《红楼梦》的研究、题咏,也幽微地折射出内心的抑郁不平之气。
(二)吴世昌对宝钗扑蝶诗的修订
蔡义江说:“自以钗、黛为情敌、贾母取钗弃黛的一百二十回程高刻本问世后,人们同情黛玉的不幸,贬钗议论便占了上风。近现代又大兴以封建叛逆者与封建卫道士划分正反面人物之风,更加强了这一褒贬倾向。认定宝钗最终嫁给贾雨村的吴世昌,便是贬钗派的代表。”[11]6吴世昌不喜宝钗一角,盖亦有个人经历与心理之阴影存焉。宝钗虽是《红楼梦》中的重要角色,但与她相关的艺术作品往往都以“扑蝶”为主题。宝钗年龄略长于宝玉、黛玉,性格稳重,处事得体,可谓八面玲珑。而二十七回所描写的扑蝶之举很罕有地流露出她童真的一面,脂批云:“可是一味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写宝钗无不相宜。”(3)[清]曹雪芹:《脂评本红楼梦》上册,脂砚斋重评,马美信校注,第350页。正因如此,扑蝶主题一直为后世艺术家所看重。不过,紧随扑蝶一举的就是为人诟病的“滴翠亭事件”:在亭中,丫鬟坠儿把贾芸拾到的帕子送还好友小红,小红又把自己的另一块帕子托坠儿捎给贾芸,隐然有交换定情信物之意。在礼法森严的贾府,如此行为自然大逆不道。宝钗碰巧因扑蝶来到滴翠亭,无意间听到二人的对话。以宝钗“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个性,她的实时反应乃是避免卷入是非,故而采取“金蝉脱壳”之计,说了一句:“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如此一来,不免令小红甚为担忧:“若是宝姑娘听见,还倒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风声,怎么样呢?”(4)[清]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校注》,里仁书局校注,第421页。吴世昌曾据而申论道:
小红后来变成了王熙凤的得力助手。在下半部书中商议宝玉的婚事时,凤姐当然参与大计。在决定黛、钗二人的选择上,如果由于小红平时说到黛玉的一言半语,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凤姐,因而间接地起了决定的作用。棠村在序中说“颦儿正文”要“借小红……之笔作引”,可见他是看到后半部书中小红有影响到“颦儿正文”的作用;而追溯其源,却是由于宝钗向小红诬告黛玉偷听了她们的私情话,以掩饰她自己的偷听。所反〔以〕决定黛玉一生命运的“正文”其实根源于宝钗。[12]
回观吴氏《宝钗扑蝶》一诗,1963年与1978年的两个版本列表于下:

表3 徐卷、月历及程画之所见《宝钗扑蝶》题诗
尾联“惊心滴翠亭中语,嫁祸无人识暗机”两句一字不易,可知他对宝钗的看法一向未变。但是,首联文字则颇有调整。与徐卷旧版相比,月历及程画新版的“窃粉偷香”“随风逐影”对仗自然更为工整,但七绝在体式上并无对仗的必要,且“到处飞”“舞杨妃”无论在词性或平仄上都不相对,那么,吴氏的修订当另有原因。今本《红楼梦》中,宝钗所见乃是“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所扑之扇则是“向袖中取出”。(5)[清]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校注》,里仁书局校注,第420页。既然蝴蝶是一双,故吴世昌将之比喻成梁山伯、祝英台。至于“取次”虽近乎语典,大抵却出自元稹悼念亡妻之作《离思》其四:“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13]有将蝴蝶比喻为宝黛,赞美二人爱情如梁祝般忠贞不渝之内涵。言下之意,宝钗扑蝶就可能有棒打鸳鸯之隐喻了。
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一辑中,吴世昌发表了《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一文。吴氏指出,曹雪芹诗友富察明义有《题红楼梦》七绝二十首。根据其诗所言,《红楼梦》稿子当时并未传出来,而诸首七绝中涉及的内容,有的见于今本《石头记》,有的则今本所无,有的虽有而情节不同,还有的因诗句意义不够具体而不易对出所指的是哪一个故事。将这些内容与今本比勘,可见明义所见原稿后来是被曹雪芹改动过的。[14]625-626对于宝钗扑蝶的情节,明义是有吟咏的:“追随小蝶过墙来,忽见丛花无数开。尽力一头还雨(两?)把,扇纨遗却在苍苔。”吴世昌进而阐发道:
这首咏“宝钗扑蝶”,明白无误。但据诗中所咏,则与今本颇有不同:如此抄本说宝钗用纨扇,今本则说她“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则显然是折扇,因纨扇藏不进袖中。题诗说“小蝶”,而今本则改为“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但最大不同是明义所见抄本有“过墙”、“遗扇”,而无今本中她到滴翠亭边听小红的私情话,又假装追寻黛玉的重要情节。明义题诗二三两句似乎说:宝钗见花,努力折了两把,因此把扇子忘在地下了。却没有说她听见小红与坠儿的对话,急智中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嫁祸于黛玉。[14]629-630
吴氏在后文且云“雪芹在增删加工的过程中作了大量剪裁配合的工作,使读者觉得全书是无缝的天衣,而不知作者是集锦而成此百衲”。[14]634也就是说,无论蝴蝶是一只或一双、宝钗用的是团扇或折扇,都是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构思。吴氏在1963年题徐卷时使用“山伯英台”“轻罗小扇”字样,显然是以今本为依据的;至1978年为月历题诗时,大概也在撰构关于明义《题红楼梦》绝句的论文,尝试将最新研究成果纳入诗中,故而出现文字修订的情形;稍后再为程十发题画,也依然采用修订后的版本了。
既了解吴世昌舍“山伯英台”“轻罗小扇”字样而不用的原因,吾人可再探讨他何以改为“窃粉偷香到处飞,随风逐影舞杨妃”。所谓“窃粉偷香”,出自欧阳修《望江南·咏蝶》词:“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天赋与轻狂。”[15]将“傅粉”“偷香”变为“窃粉偷香”,贬斥之意更为明显,也更契合《红楼梦》原稿所言其蝶乃一只而非一双:若是一只,自然不可言“山伯英台”,且也似乎与“偷”“窃”之举更为贴合;而“到处”也点出其偷窃之毫无原则。那么,这只浪子般的蝴蝶与宝钗关系何在?也许我们可以从下句中寻绎出一些信息。将“轻罗小扇”替换掉,自然避开了团扇或折扇的问题;而“随风逐影”四字则令人想起杜甫《绝句漫兴》“颠狂柳絮随风舞(一作去),轻薄桃花逐水流”的句子。[16]宝钗既“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6)[清]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校注》,里仁书局校注,第123页。,其随风追逐的蝶影,在如此语境中自然就成为名利的借代了。尽管名利看似美好,却也如梦幻泡影——蝴蝶不正是梦的隐喻么?在《红楼碎墨》中,吴世昌还依据贾雨村寒微时所吟一联“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为证,认为“钗”是宝钗,“时飞”即贾雨村的表字,此联预言了宝玉出家后,宝钗的归宿是改嫁贾雨村。[17]如此推测也许求之过深,但吴世昌心目中的宝钗既然如此,他将宝钗的“改嫁”视为热衷名利的证据,并斥之为“随风逐影”,就不足为奇了。正因如此,纵使吴氏论文发现曹雪芹初稿中并未将扑蝶与“滴翠亭事件”连接在一起,却也没有把这个发现呈现在诗作中,依然保留“惊心滴翠亭中语,嫁祸无人识暗机”之语。
不过在1998年出版的《罗音室学术论著》第4卷中,有增补版之《罗音室诗存》,其中即收录了《程十发绘红楼梦人物图咏》十六首。其《宝钗扑蝶》一首,文字又有出入:
窃药偷香到处飞,随风逐影舞杨妃。金蝉脱壳浑闲事,哪怕旁人说是非。[14]943
此诗将月历及程画版之“窃粉”改为“窃药”,尾联更是面目全非。如此改动,当因吴世昌晚年增订《诗存》,将程画题诗收入时,察觉扑蝶一诗重出,故而修订文字。不过,吴氏此举可谓“换骨”之法,文字不同而文意依旧,对宝钗的评价并未改变。“金蝉脱壳浑闲事”即谓宝钗如此伎俩已非常纯熟,“哪怕旁人说是非”则一语双关,一来称其无惧于得闻小红、坠儿所谈之事,二来称其不可能将是非惹上身,因此也不会贻人口实。至于首联上句将“窃粉”改为“窃药”,更是使用了嫦娥偷灵药的典故,暗指她即使与宝玉成婚,最终还是劳燕分飞,甚或改嫁他人。
三、吴世昌《红楼梦》图画题咏的诗画关系
本节讨论吴世昌《红楼梦》图画题咏的诗画关系,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系以前节《宝钗扑蝶》一诗的讨论为基础,进一步探析三次题咏之诗作间的关系,这些诗作所吟咏之人物和事件或为独见(仅见于某次),或为重见(互见于两次或以上);其二则为吴诗与画作之间的关系。为便于论述,本节先整体观照徐卷、程画所独见之吴世昌题咏,再探讨刘画与吴诗间的对话,最后以王熙凤之题咏为切入点,析论徐卷与程画之重见人物。
(一)徐卷、程画与吴世昌题咏
先秦两汉时代,人物画的技巧尚未发展成熟。如武梁祠的古帝王壁画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人,皆为戴冕旒、垂衣裳之像,面部特征很难呈现,若非一侧之文字解说,观者不太可能知道画中人物之身份。唯神农手持耒耜、大禹头戴斗笠,尚可辨识。再观《山海经》,其原本之配图虽早已亡佚,但玩味其文字,仍有描述配图的意味。如《大荒东经》谓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18]404,从一个“方”字便可寻绎出这段文字乃是在描绘一种正在进行的动作。又如《海外东经》云:“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18]305青丘只是竖亥从东极到西极的途经之处,竖亥“左手指青丘北”,大抵是配图仅描绘出竖亥经过青丘时的情形。的确,人物画像若能将其特殊身份与经历一并呈现出来,无疑更易于展示该人物的特征乃至情态。受此状况影响,后世绘画之主角若为历史或小说人物,往往选择以一个脍炙人口的情节作为主题。以所谓“四大美人”之仕女图为例,主题多为西施捧心(或西施浣纱)、昭君出塞、貂蝉拜月、贵妃醉酒(或贵妃出浴),使观者一览便知。晚清改琦所绘《红楼梦》人物,画中虽然仅标人物名字,但观者不难发现图画内容仍多以书中情节为背景,如宝玉则读《西厢》、宝钗则扑蝶、湘云则眠芍、李纨则教子、尤三姐则观剑、晴雯则补裘可知,再如警幻则观云烟可知,黛玉则观湘竹可知,凤姐、妙玉则观服饰可知,不一而足。然如秦可卿、邢岫烟、秦钟、贾蓉等人,却较难分辨。不过,改琦诸图对于《红楼梦》人物似有穷搜之意,那些次要人物自然不易于画笔下表现。
回观吴世昌题咏诸图,徐卷中十二位女性皆有情节配合,月历更以情节为主,程画除十二钗外兼及石头、警幻、兼美三人,又沿袭了月历中射谜场景,因此也不难了解各人物之身份与内容。徐卷十二首题咏中,有五首不与月历及程画重复,包括《三姐刎颈》《晴雯补裘》《袭人刺绣》《金钏投井》《平儿理妆》。不过玩味这五首诗作,似乎以描述为主,新见不多,如嗟叹尤三姐之死,指摘袭人的心术(针线密),将晴雯之死归咎于袭人(妒妇),将金钏之死归咎于王夫人(萱堂),乃至平儿理妆的因由,等等。而程画十六幅作品中,不计《群艳射谜》,尚有八幅的人物不与徐卷相重复,包括《顽石难悟》《警幻司情》《兼美惊梦》《可卿失足》《迎春误嫁》《惜春出家》《李纨教子》《巧姐归农》。纵而观之,警幻、兼美、迎春、惜春诸首依然述多于论,但其余诸首则颇能呈现吴氏一己之见。如可卿一诗中“天香楼静无人到”一句,虽然所言之“淫丧天香楼”之谜尚未全解,但“雾阁云窗手共携”点出了第五回中宝玉在可卿睡房中梦至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携住宝玉的手”向一众姊妹介绍,甚至更暗示可卿乃是宝玉“初试云雨情”的真正对象。巧姐一首云“程高不解曹公意,错把巧儿嫁富绅”,指出曹雪芹原意并非安排巧姐日后下嫁一乡村富绅之子,而是“最后来到刘的村庄嫁给刘姥姥的外孙板儿”,“这完全吻合警幻图册中透露的曹沾的原定计划”。[14]349因此,吴氏在诗中对程伟元、高鹗的续书作出了批评。至于李纨一诗,更从相反角度立意,谓李纨若坚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成见,是不可能培养出贾兰这般优秀的儿子的——纵然吴世昌认为“寡妇李纨本来应在其子贾兰官场发迹后不久死去”。[14]479笔者以为,吴世昌在英文本《红楼梦探源》付梓后所题五首绝句中便已呈现出不少新见,然在1963年题咏徐卷时却有所不及,此盖因刘画之作在先、吴诗之题在后,二人创作前无甚默契。兼以吴世昌正值归国之初,其英文著作未必为国人所熟知,故刘旦宅绘图之内容多依据其他学者之说,而吴世昌题咏又是奉徐平羽之命,故发挥空间较为有限。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吴世昌先后与刘旦宅、程十发再度合作,诸人早已成为旧侣,加上同为浩劫中之难友,因此诗画间的内容便更能契合了。
(二)刘画与吴诗的对话
刘旦宅虽是描画《红楼梦》人物的专家,但徐卷今已不存,因此本文将着眼于月历,以见吴世昌如何透过题咏与刘画进行对话。如前所言,吴世昌题咏之月历图画共有两幅,一为一月之《射谜》,一为五月之《扑蝶》。宝钗扑蝶的部分,前节已多有讨论,然此处还须再作补充。刘旦宅不止一次以宝钗扑蝶为绘画主题,就背景而言,或完全不画,或画柳丝数条,或画鲜花几株,或画曲径几折,一看便知是在户外。若以户外为背景,蝴蝶一般都绘一对,而宝钗所执皆为折扇,鲜有团扇之例。值得注意的是,月历的扑蝶图乃是以滴翠亭的檐廊为背景,廊后墙壁关门闭户,廊前花柳成阴,下方是一大片太湖石。整个画面被安排得密不透风,几乎没有留白之处,给人以窒息之感。宝钗伫立廊上,发髻上方仅有一只蝴蝶,然此时的宝钗似已无意于蝴蝶,而是折扇下垂、侧首睨目,有窃听之意。而吴世昌诗云“惊心滴翠亭中语,嫁祸无人识暗机”,试想如果题在纯以户外为背景的扑蝶画上,恐有离题之嫌,由是益可见月历中刘画吴诗之紧密切合。盖刘、吴二人十余年前已有合作经验,是次刘氏制图,当可能吸纳了吴氏的研究成果。稍后,吴世昌与程十发合制图册,其中《宝钗扑蝶》一图不设背景,蝴蝶则为两只,吴氏题诗文字与月历版本全同。程氏亦题字云:“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此自是原书警幻仙曲《终身误》的文字,预示了宝钗的命运,点出宝玉日后纵与宝钗成婚,心中却郁结难安。而就程画而言,“举案齐眉”与图中一双蝴蝶正有相应的关系。(7)吴世昌题咏:《红楼梦人物题咏》,程十发制图,收入魏绍昌集藏:《红楼雅集:当代名家红楼梦诗书画集》,上海:上海书店,2008年,第1册,第32-34页。吴世昌沿用旧作,依然表现出对宝钗一角的指责。而程画中,一双蝴蝶在左上角,而宝钗却背向双蝶,且将折扇持在身后,也可见她已被其他事情吸引,心不在蝶。这与吴诗还是有所呼应的,只是相去略远了。

图1

图2
至于“射谜”,内容则来自原书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当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妃“差人送出一个灯谜儿,命你们大家去猜,猜着了每人也作一个进去”,这些谜语也都贴在府内春灯上。曹雪芹安排身为家长的贾政逐一猜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四姊妹及宝钗的灯谜(此外制谜者还有宝玉、黛玉、贾环、贾母及贾政本人),最后感叹一众子侄“皆非永远福寿之辈”。(8)[清]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校注》,里仁书局校注,第350页。蔡义江认为这一情节的象征意义涵盖了全书。[11]2可以说,这个灯谜宴会乃是全书关捩,谜语暗喻了撰写者的命运,为各人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线。1979年1月28日乃农历正月初一,元宵节不在1月,而在2月11日。编者将“射谜”诗画安排在元月,有旧酒新瓶之意,不仅标示一年之始,也预示着《红楼梦》故事在未来的发展。不过,刘旦宅的画中纵然张灯结彩、富贵花开,却并未让贾政出场,而是以宝玉为中心。宝玉气宇轩昂,手指春灯,身前一女与之对视应答,又有二女侧立,年龄较小,三人当为迎、探、惜三春。最值得注意的是,宝玉背后尚有一女作鼓掌状,凤冠盛装,当系元春。原书中,元妃远在深宫,并不可能参加这次宴会。刘旦宅将她增入画中,却又安置在宝玉背后,有一二丝绦下垂,略如帘幕掩遮,似乎意味着她是这次宴会的发起者,有幕后角色的含义。宝玉及四姊妹皆为平辈,象征着贾府的未来,此盖刘氏不将贾母、贾政、宝钗、黛玉绘入的缘故。除背向观者的迎春外,其余四人皆有欢容,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制灯谜中的“凶兆”,进一步展示出画家对贾府命运的嗟叹。而吴世昌的题诗,也与刘画珠联璧合:
世态纷纭类转蓬,谁将隐语启愚蒙。他年往事成追忆,尽在今宵一梦中。
讽刺的是,宝玉与四春在诗、画中都成了“愚蒙”,全然没有料想到自己的家族会有“忽喇喇似大厦倾”的一日,真正读懂预言的竟是端方正直、失之迂腐的贾政。当厄运来临之时,宝玉诸人回想今宵盛况,宁不有恍如一梦之感乎!
稍后,吴世昌、程十发应魏绍昌之邀,合作绘制图册,其中前三幅分别以石头、警幻、兼美等神话人物为主角,唯第四幅题为“群艳射谜”,吴氏题诗文字与月历无差,盖其总冒之功能也别无二致。(9)吴世昌题咏:《红楼梦人物题咏》,程十发制图,收入魏绍昌集藏:《红楼雅集:当代名家红楼梦诗书画集》,上海:上海书店,2008年,第1册,第9-10页。由于宣纸面积有限,程氏不可能采用工笔画形式,其构图也与月历中的刘画有所不同。图中仅绘一贴有谜语之宫灯,灯前有女子五人(而无宝玉),中立者身披红袍,头上有凤钗,当为元妃无疑。其余四人较难辨识,然系贾府姊妹,庶几无误。可见程、刘二人画风虽异,却皆强调元妃之在场感,个中信息当是由吴世昌所传递。
(三)徐卷与程画重见人物之题诗
如前文所示,徐卷与程画中有七位重见人物,除宝钗扑蝶外,其余六位的情节与题诗都不相同。这六对图画也都有联系,如黛玉图一为葬花、一为焚稿,葬花预示着黛玉的消殒,焚稿则系黛玉去世前所为;元春图一为省亲、一为托梦,前者意味着贾府全盛之日,后者则意味着贾府的衰败;湘云图一为眠石、一为拾麟,前者象征着天真烂漫,后者隐喻着情窦初开;探春图一为结社、一为远别,前者体现其干练多才,后者嗟叹其究竟无法逃脱婚姻包办;凤姐图一为设局、一为贪贿,两者皆指向其精明贪婪却无惧冥诛;妙玉图一为祝寿、一为赠梅,两者皆表明其身在佛门而向往红尘。可见两两之间有呼应而互补者(如黛玉、凤姐、妙玉诸图),有比照或反衬者(如元春、湘云、探春诸图)。限于篇幅,兹仅举王熙凤题咏之例而讨论之,以作管窥。
吴世昌题徐卷之《凤姐设局》云:
别有奇才运妙思,千金入手葬情痴。瑞儿死去蓉儿笑,那管颦儿泪尽时。[19]
虽然年长于贾瑞的堂兄贾珍、贾琏也被称为珍儿、琏儿,但贾瑞载书中一般只称为“瑞大爷”。此诗为了将贾瑞与蓉儿、颦儿二者达到文字上的一致性而称其为“瑞儿”,或嫌牵强。但就章法而言,仍有可观之处。此诗以首句为总冒,其下三句皆为阐发之语。首句对于王熙凤的心窍称为“奇才”“妙思”,采用一个“别”字,可见赞誉之余却颇存贬斥。次句谓第十五回中凤姐弄权铁槛寺,贪图利益(千金入手)而拆散张金哥与守备公子的姻缘,致使二人双双自尽(情痴)。三句谓第十二回凤姐拒绝贾瑞三番五次的骚扰,因而在贾蓉的协助下“毒设相思局”,令贾瑞疯癫至死。末句谓第九十六至九十七回凤姐以调包计使宝玉与宝钗成婚,而使黛玉泪尽而逝。值得注意的是,调包计出现在高鹗续书中,未必是曹雪芹原文。吴氏也说“高的补作也写了贾府败落的结局,但因不少情节截然违背曹霑的原定计划而大为逊色”[14]293,但根据脂评,他也赞同:“林黛玉死后仍有许多故事,这说明黛玉之死发生在第八十回之后不会很久。作者想必不忍心让林姑娘死得太早,但他更不忍心让这位无辜的少女一起经受后来降临贾府的灾难。”[14]333-334兼以在现代学术语境中,题咏终非严肃之研究,故吴氏在诗中齿及调包计以凸显凤姐之机心,可以理解。
王熙凤所害性命多矣,何以吴氏在诗中仅举此数人呢?就诗作章法观之,尽管张金哥、贾瑞、黛玉皆因凤姐而死,三者的功能却不尽相同。依照故事发展,这几人去世的顺序依次为贾瑞、张金哥与守备公子、黛玉。但吴诗将张金哥置于最前,强调她与守备公子之痴情,一来承接首句而点出凤姐之伤天害理,二来为标示凤姐作恶之开端,三来张金哥与守备公子究非主角,可以在诗中达到提起与铺垫之作用。贾瑞可谓自寻死路,与张金哥、黛玉截然不同,而七绝第三句往往有承上启下的转折功能,故此处提及贾瑞最为适合。进而言之,贾瑞虽存心不良,但罪不至死,其结局依然可鲜明体现凤姐之机心,与前后文保持了一致性。此外,贾蓉作为凤姐的帮凶,虽然并未参与宝玉成婚的调包计,但就此诗的脉络而言,“蓉儿笑”三字却能开启末句,点出主角黛玉之去世不仅无人关心,更不乏冷眼嘲讽者。
至于程画的《熙凤贪贿》图中,程十发仅绘出凤姐身披红斗篷的端庄样貌,又题下“一场欢喜忽然辛”七字。而吴世昌题咏则云:
算尽机关祇为财,乃知凡鸟本庸才。阴司地狱卿无惧,哭向金陵究可哀。(10)吴世昌题咏:《红楼梦人物题咏》,程十发制图,收入魏绍昌集藏:《红楼雅集:当代名家红楼梦诗书画集》,上海:上海书店,2008年,第1册,第29—31页。
与徐卷题咏相比,此首不再列举例证,而是以议论为主。首、次、末句皆出自警幻仙曲,一为《聪明误》之“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一为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11)[清]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校注》,里仁书局校注,第87页。“凡鸟”固为凤字所拆,而所谓“哭向金陵”,吴世昌认为贾府败落,凤姐也因作恶多端而系狱。到她出狱回家时,她和丈夫贾琏已相互易位。一度惧内的贾琏占了上风,将性情和顺的侍妾平儿扶正,凤姐地位一度下降到与婢妾为伍,最后更被贾琏休掉,不得不“哭向金陵”。[14]338凤姐如此机敏,却只为钱财,贪图眼前之利而不顾后果,因此吴氏将其贬为“庸才”。且在铁槛寺中,凤姐对老尼静虚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12)[清]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校注》,里仁书局校注,第230页。此即诗中第三句之出典。由于不信报应,益发助长了凤姐作恶之念,无所忌惮,其结局之悲惨也不难逆料了。
补充一点,比对月历版中以凤姐为主题的作品为九月之《攒金》(图3),由周汝昌题咏:“侯门随日逐豪华,醵寿何妨效小家。打迭笙歌归院落,荒庵谁念塑朝霞。”此诗首联典出第四十三回:“贾母做主,让众人学小家子凑分子,为凤姐办生日,又将这事交给尤氏办,‘越性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受用一日才算’。尤氏往凤姐房中商议,打趣说:‘你瞧他兴的这样儿!我劝你收着些儿好。太满了就泼出来了。’”(13)[清]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校注》,里仁书局校注,第664页。尤氏所谓“太满了就泼出来了”,与秦可卿向凤姐报梦时所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同一意思,暗示凤姐乃至整个贾府的命运。尾联上句来自白居易《朝归书寄元八》中的文字:“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20]周氏用此联暗示贾府衰败乃至凤姐被休后返回娘家。下句则引出另一典故:凤姐与丫鬟金钏皆为九月初二生日,金钏因受王夫人责辱,投井自尽,成为水中之魂,宝玉遂在次年金钏冥诞前往郊外的水仙庵加以祭奠。第四十三回描写道:“宝玉进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赏鉴。虽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之态,‘荷出绿波,日映朝霞’之姿。宝玉不觉滴下泪来。”(14)[清]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校注》,里仁书局校注,第668页。而金钏之死,也预示同一天生日之凤姐的结局。不过就月历性质及买家心态而言,毕竟应以富贵吉祥为主题,这正是刘旦宅此次选择“攒金”主题作画的原因。因此,周汝昌诗虽有不吉之语,却深藏若虚,远不似吴世昌题咏凤姐二诗那般一读便知。

图3
四、结语
无端歌哭若为情,好了歌残破夙因。岂有华筵终不散,徒劳空色指迷津。百家红学见仁智,一代奇书讼假真。唯物史观精剖析,浮云扫尽海天新。[3]120
茅盾将唯物史观的辩证思想与“好即是了,了即是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相扣连,却也为那华筵般贾府盛世的咏叹与绘画找到了落脚点。正如书中第一回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对石头所言:“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15)[清]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校注》,里仁书局校注,第2页。华筵的结局是究竟散去,盛与衰恰好也是风月宝鉴的一体两面。故吴世昌诗云“风月繁华记盛时,欲将宝鉴警顽痴”,虽是题咏其《红楼梦探源》,却也点出了他后来三次为红楼图画题咏的心态。无论是对于书内的石头还是书外的读者来说,“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16)[清]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校注》,里仁书局校注,第2页。,毕竟还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1979年月历的制作最能说明问题。但就月历而言,无论是前文所举吴世昌《射谜》《扑蝶》,还是茅盾《补裘》、周汝昌《攒金》,主题、绘画都看似鲜花着锦,令“痴顽”的普通读者心生欢喜,题诗却都暗含不和谐的“凶兆”,仿佛隐藏在风月宝鉴背面的白骨。可以说,月历的问世不仅成为当时雅与俗、学界与普罗大众间的桥梁,同时也将徐卷与程画贯通一线——若谓徐卷仍蕴含着积极的政治理想,那么程画的生成则应和着魏绍昌编纂《红楼雅集》的动机,既为了记录创痛,也为了疗愈伤痕。在这贯通的时间线上,徐卷、月历、程画乃至整个《红楼雅集》竟相互辉丽,镜中有镜,光外有光,骨相应骨,花影生花,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