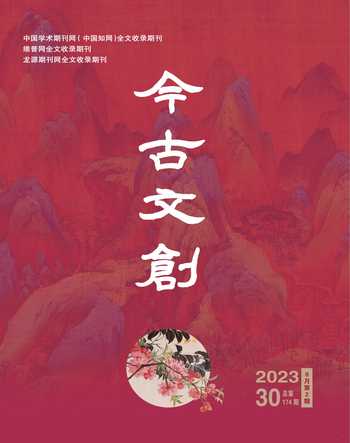《萍芃》 : 泰国帕罗故事演变的平民视角创作分析
【摘要】20世纪初泰国社会动荡,思想进步的中产阶级作家们以文学作品为媒介,表达对传统等级思想的抨击。雅各布把封建王朝时代的经典作品《帕罗赋》颠覆性地改编成短篇小说《萍芃》。他以平民视角创作,改变故事发生的场域,重构男、女主人公的三角恋,塑造出平民“爱神”,反映出关怀社会底层百姓、关注个体命运发展的新时代精神。
【关键词】泰国;《萍芃》;帕罗故事;平民视角
【中图分类号】I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0-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0.006
《帕罗赋》是泰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作品,大约在15世纪时由宫廷诗人创作。该作语言优美,感情细腻动人,1914年,被泰国文学俱乐部评为“立律体诗歌之冠”,在泰国文学殿堂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发现,早期的泰北社会早有与帕罗相关的民间传说,后来故事传入中部的王国阿瑜陀耶(1350—1767)宫廷,成为《帕罗赋》的前身[1]。该故事主要讲述了泰北颂国和松国之间延续了三代人的爱恨情仇,聚焦身为泰北颂国王子的男主人公帕罗与松国两位公主帕萍、帕芃之间的情爱纠缠,以三人皆为爱牺牲为结局。我国学者裴晓睿指出,《帕罗赋》作为一部伟大的爱情悲剧作品,它首创了以“爱情”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创作题材[2]。
后世许多作家青睐于《帕罗赋》这一文本,在其故事情节或人物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使之衍生出一系列变异的帕罗故事文本,其中就包括雅各布①(Jacob,1907—1956)的短篇小说《萍芃》。1932年,泰国政体从传统的君主制变革为民主制。雅各布是当时新兴的中产阶级职业作家代表。他思想进步,拥护民主制,善于创作讽刺文学作品,表达对社会不公的嘲讽。《萍芃》于1933年创作,深受读者喜爱,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本研究将对比《帕罗赋》,以《萍芃》中最为显著的改编切入,即故事发生场域,试图解析雅各布通过从平民视角对帕罗故事的再创作,以表达对传统等级体制的批判。
一、“乡间”的场域设定
《帕罗赋》的作者在诗中言明,其创作旨在献给国王,读者也不难读出该作的显性意义指向,即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泰国学者颂结·瓦塔纳(Somkiat Wanthana)指出,《帕罗赋》中包含政治意味,意在警示当朝者应恰当处理好两性关系,“爱情”可能是致使政权倾覆的危险因素,正如文中帕罗不听从母后的劝告,最终命丧黄泉[3]。左翼文学评论家因特腊育(Intrayuk)甚至认为,该作乃色情作品,诗人旨在为统治者进行情欲消遣而作[4]。虽然该作的深意仍值得探索,但无论如何,读者清楚地看到,故事场景主要设置在宫廷,讲述王公贵族的爱情故事。
《萍芃》则不同,故事场景转移到乡间,男女主人公的身份也转换成平民阶层的最底层——农民。男主人公罗长相英俊,老实肯干。他与叔叔一家共同生活。叔叔有两个女儿,分别是姐姐萍和妹妹芃。罗与萍有婚约,应萍的要求,发誓永不变心,否则不得好死。一个偶然的机会,罗发现原来芃一直深爱着自己。情不自禁的情况下,两人发生关系。为避洪水,罗出远门放牛。芃有了身孕,在分娩时去世。罗归家后得知,悲痛不已,为表真心,投河自尽。故事发生的场景是泰国民众熟悉的“乡间”:无论是家庭生活、田间劳作和人情世故的描绘,还是鸡啼狗吠、雨后的林间、入夜的田野等景物描写,均呈现浓浓的乡土气息。
就连爱情故事重要的桥段——男女主人公的合欢云雨,《萍芃》也展示出乡土文艺特点。雅各布在描写罗、芃两人发生关系时,采用的都是非常含蓄、隐晦的语言,但又足以让读者浮想联翩。他运用农村人容易产生共鸣的外部自然环境描写:乌云翻滚,风雨交加,雨停后一轮红月挂上梢头,静谧的村子传来幽幽的夹杂着些许忧伤的长笛声。这种含蓄的性生活描绘,在泰国古代民间文学作品中常见,叫作“风雨篇”(pob asajan),而宫廷文学则非常露骨[5]。雅各布高超的“乡土艺术”创作使这部改编的作品保留了《帕罗赋》的“色情”特质,也躲过了左翼文学评论家的批判。
《萍芃》的创作是对当时泰国社会和文学创作风潮变化的呼应。20世纪初开始,越来越多新兴中产阶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批判传统礼教,以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虽然雅各布为帕城第五任城主的小儿子,也有贵族血统,但是他本人并不以贵族身份自居。反而在文学创作中处处反映出对平民的关注与重视。他创作时所考虑的是社会独立个体的命运,他所描写的角色尽量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
故事场域被设置在乡间,迎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引导大众反思和批判封建等级观念。泰国政体刚转型为民主制,封建礼教的等级思想是民众的重要思想桎梏,人们需要面对现实,从思想上适应作为国家“公民”而存在的新观念。为了更好地让平民们吸收新思想,雅各布选择了泰人熟悉的帕罗故事进行改编,旨在利用家喻户晓的角色作为平民接触新事物的“润滑油”,描写中也非常注重突出乡村生活的场景。当时的思想家蓬得里·功蒙那拉提巴彭巴潘指出,“1932年变革的是政制,但是立刻就急着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传统风俗是行不通的。”[6]因此,《萍芃》相当于引导读者,使一贯以来以宫廷为中心的“向上”视线转为“向下”,关注人数最多的下层民众。
二、“平凡”的三角恋故事构思
从根本上看,《帕罗赋》中的三人恋情是封建父权制度下男性视角的叙事。该故事中,两位女主人公有主动求爱和纵享情欲的表现。有的学者认为,该作反映出女性有进步意识,勇于挣脱封建宗法的枷锁[7]。也有学者认为,该故事中的女性行为是泰国民间文学中原先就存的母权文化因子导致的。《帕罗赋》既然衍生自民间帕罗故事,帕萍、帕芃“放荡”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8]。无论如何,该作的故事叙述凸显男性中心主义视角,二女以帕罗为尊,和谐相处,毫不争风吃醋,甚至为帕罗英勇献身,呈现出传统父权社会的爱情故事叙事逻辑思维。欧拉泰·披亚育拉(Orathai Piayura)认为,文中充斥着把女性当成性工具的男性凝视视角,女性角色处于被动地位[9]。总之,坚贞不渝的帕萍、帕芃作为宫廷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模板被書写。
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书写的传统下,《萍芃》也逃不过女性角色沦为男主人公“陪衬”的嫌疑,女性角色是为了衬托男主人公的伟大而存在。尤其是芃,文中提到芃曾对罗说过,“我爱你没有任何原因,我生来就为了爱你”。这句话表面上展现了芃对罗的无限爱慕,但实质上与从未谋面就爱上帕罗的帕萍、帕芃两姐妹相差无几。二者都透露出一种共识,即默认女性生来具备满足男性种种需求的功能属性。在文本中,女性角色成为塑造男主人公光辉形象的工具。
但不能忽略的是,《萍芃》中明显透露出一种女性视角和新时代的女性意识,比起《帕罗赋》,其女性角色形象更为丰满,更“有血有肉”。萍在文中是敢于直面自我情感的女性。虽然20世纪初,一夫多妻制被废除,但男人偷情私通仍被看作是风流韵事,无伤大雅[10]。主流社会女性仍被要求接受丈夫有情人的事实,甚至要与“情敌”友好相处。但萍并没有按社会期待行动。当她察觉到芃暗恋罗,便立即要求罗与芃划清界限。她所追求的爱是现代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的爱。当她得知罗与芃发生关系后,她没有像传统女性一样选择容忍,而是质问和指责罗,表露出自己的不满与怒意。不可否认,萍也曾埋怨过芃,但当妹妹难产去世后,她除了怨恨罗,还为芃抱不平。萍需要爱,但并不是没有爱就活不下去。尽管萍并未接受现代教育,但她的行为却非常具有现代女性气质,体现出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而芃则不同。面对罗已经与姐姐在一起的现实,芃一直默默付出努力讨好罗,直至被姐姐发现。虽然芃可以被看作是插足萍与罗的第三者,但雅各布并没有把她塑造成传统三角恋中的“坏角”,而是让她实践真爱,震撼读者。《萍芃》虽是短篇小说,但细腻地展现出女性人物的感情变化,体现作者对女性人物的关怀。
罗、萍、芃的三角恋故事在今天看来颇为平凡,但在当时的爱情故事中是新颖的,在女性意识、两性关系的复杂性表现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实际上直到今天,这样的三角恋故事构思仍不过时。
三、“落俗”的爱神塑造
《帕罗赋》与《萍芃》在故事内容的设计上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两位男主人公均死亡的情节。本节将探讨作为“国王”的帕羅和“平民”身份的罗两人的死亡背后,究竟蕴含了何种深意。
关于帕罗为何死,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未有定论,但可以明确的是,帕罗的死亡是被作者歌颂的君王的伟大壮举。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统治者借鉴吴哥王朝的政治统治,印度教神王思想被大加利用,文人通过法律制定、文学创作等多种方式把国王塑造成“假想神仙”(som matitep)[11]。王权崇拜逐步形成具有泰民族特性的文化传统,贯彻在政治统治和礼俗文化中。1932年民主革命后,国王成为名誉国家元首,没有实权,但仍深孚众望,被视为正法的代表,左右政治的发展[12]。该作被命名为《帕罗赋》,其实就是帕罗王的颂歌。帕罗追求爱情,并为爱牺牲,他被塑造成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敢于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的“王中堪为尊”形象。但要注意的是,《帕罗赋》本质上是献给国王的宫廷文学作品,如诗中开头写道:“世间颂歌,无数妙曲,帕罗颂歌,无与伦比。丽藻加饰,沁人心脾,供呈圣上,吾王福祉!”[13]帕罗在文中被描绘成完美的男性形象,这是由他的身份决定的。作为文本中的“国王”以及作为要供国王赏读的“国王”,帕罗的形象不可能,也不可以不完美。该作塑造的帕罗王与泰国文化中“神化国王”的传统观念相符合,帕罗遂被当成“情圣”。
后世的各种帕罗故事改编版本,大体上都保持上述创作思维,但《萍芃》则独树一帜,罗的死亡并不是由外界因素造成的,而是一个小人物因违背真爱誓言而自戕的结果。该故事中,罗起初爱的是萍,芃在他眼里仅仅是妹妹。偶然间,萍发现妹妹似乎对罗有非分之想,妒火中烧。为了安抚爱人,罗便发誓永远不会背叛两人的爱情,甚至以死作证。可立下誓言不久,得知芃钟情自己后,罗被其纯粹的爱意打动,渐渐地也爱上了全心全意崇拜、爱慕自己的芃。两人情不自禁,在一个雨夜中发生了关系。罗因放牛需离村一段时间,归家后发现叔叔披对他不理不睬,爱人萍也恶言相向。这才得知原来他外出期间,芃怀了他的孩子,还在生育时不幸身亡。罗悲痛万分,面对萍的指责,他承认自己和芃产生真爱,但他会信守对萍立下的真爱誓言,因此,罗投河自杀。
由此看出,罗因爱情而死,但他的爱情与《帕罗赋》中帕罗的爱情不同。《帕罗赋》中的爱情在现代人眼中,很难被看成“真爱”。帕罗完全受到美色引诱,前往敌国求爱。反观《萍芃》,故事中的人物追求灵肉合一的爱情,比较符合现代人对真爱的认知。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他本人为自证爱意,对萍立下事关生死的誓言。在他立下誓言的那一刻,与萍爱意正浓的罗没有料想过自己会违背这个誓言,这也是为何他会用生命作证。但当罗真的背叛了萍之后,他并没有不负责任地远离这一切。而是选择直面支离破碎的爱情,并信守自己的诺言。
罗为爱而死的行为也是震撼人心的。原文提到,罗“以存心求死的方式死去”[14]168,是以一种可以说是残忍的、折磨自己的方式自杀—— “双脚蹬地借力,使得头部先划入水中”,这点足以证明罗的伟大品格。故事的结局是村民们为他立祠,附近的少男少女得知罗的事迹后大受感动,纷纷前往祭拜祈求爱情坚贞。文中写道:“死后的百年间里,罗已经成为附近村落无人不知的爱神,无论是哪对爱侣要订婚或订情,都一定会前去参拜……他是整个村落好男子的典范。”[14]168-169雅各布用“昭罗” ②即“罗王”来尊称罗,全篇都是对他男子汉气概的正面描述。可见雅各布本人是刻意要设置罗的死亡情节,目的是通过罗的“死”来实现他的“神化”,完成他的“阶级跨越”。通过直面内心情感,信守诺言,承担责任,罗从原本的“哎罗” ③变成了“昭罗”。
罗虽出身农村,没有知识背景,与上层阶级更是沾不上边,但他在文中的敢爱、敢做、敢当的形象,其实就恰好印证了雅各布的平民视角,揭示了雅各布本人对于在当时如何成为优秀公民的看法,即地位、出身等外在条件并不重要,只要敢于面对问题,敢于承担责任,布衣平民也能成“神”。
四、结语
雅各布所创作的《萍芃》,反映出其以平民的视角,对封建君王统治时代的文学经典作品《帕罗赋》进行颠覆性地改编,通过将场域从宫廷转向乡土,利用该作中的人名,重新构思了一个看似平凡的农民阶层的三角恋故事。但却反映出父权制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将平民的罗塑造成“爱神”,揭示出平民男子凭借自身的品格也可以封神。可以说雅各布成功地改编了帕罗故事,体现出他关怀社会大众,尤其是底层百姓,关注个体的命运发展,符合主体意识加强、追求平等公正的新时代精神。
注释:
①(泰)雅各布,原名???? ??????????(Chot Phraephan)。其笔名为西巫拉帕所起,源自英国报纸STRAND幽默专栏作家W·W·Jacob。
②????在泰国皇室等级中指的是君主或国王,还指拥有皇室血统的,王子和公主以上等级的贵族。
③????泰国东北方言里对长子或兄长的称呼前缀。
参考文献:
[1]裴晓睿,熊燃.《帕罗赋翻译》与研究(总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6.
[2]裴晓睿,熊燃.《帕罗赋翻译》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
[3](泰)颂结·瓦塔纳.《帕罗赋》中的政治教训[J].泰国研究杂志,2019,(1):47.
[4](泰)因特腊育.帕罗赋[A]//因特腊育.读古典文学有感[M].曼谷:阅读出版社,2016:73-90.
[5](泰)尼提·尤西翁.羽毛笔和船帆[M].暖武里:法调代出版社,2012:64-65.
[6](泰)蓬得里·功蒙那拉提巴彭巴潘.司法权[A]//谈皖文集[M].曼谷:帕东苏克萨出版社,1965:128.
[7]唐敏莉.《金瓶梅》与《帕罗赋》中泰封建制下的女性意识比较[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100-104.
[8]陈慧敏.泰国父权社会发展与帕罗故事演变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1:23.
[9](泰)欧拉泰·披亚育拉.力量、支配和性:泰国色情文学中男性气质的呈现[J].人类学社会学,2010,(3):34-49.
[10](法)斯科特·巴梅.女人、男人、曼谷:泰国的爱情、性和流行文化[M].清迈:蚕书出版社,2002:158.
[11]吴圣杨.婆罗门教信仰与泰人的礼法文化[J].太平洋学报,2007,(08):22.
[12]吴圣杨.泰国法王思想探源——兼评《“翻搅乳海”:吴哥寺中的神与王》[J].东南亚研究,2018,(2):109.
[13]裴晓睿,熊燃.《帕罗赋》翻译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0.
[14](泰)雅各布.萍芃[A]//真爱[M].曼谷:飘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黄静仪,女,壮族,广东佛山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亚非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泰国文学。(指导教师:吴圣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