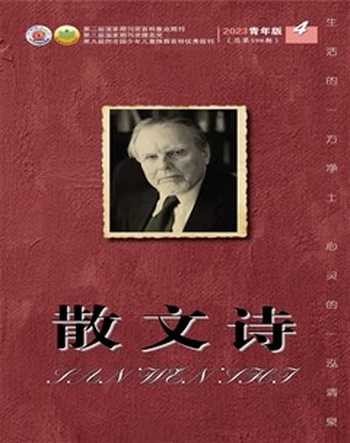神往的园地
曹尔
断想
来到博物馆,人声寥寥——
我看到草原上升起一轮深红的太阳,它的光芒铺洒在沙河之中。战靴、刀戟,不完整的头骨和器皿,一一搬了出来,搬出来的还有棺椁。一副骨架到底留有多少过人的胆识、超凡的才能、显赫的功名?我说不上来。但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为了一处神往的园地,我仍纵马驰骋。古道传来悠远的嘶鸣。
天下攘攘,人心离乱,我似乎看到一个英雄正策马而来。他一意角逐群雄,抗衡命运,天下黎民莫不尽人彀中;他一意构筑更宏大的蓝图,成就伟业。捻一把隔代的风尘,还原连天的碧草和混沌的长河,是无数个来到草原上的人所需要做的事情。
真正来到草原,我的心,平静得像清晨第一丝风儿吹开的花蕾。那是风和日丽的一天,是兴之所起而千里以赴的一天,是不遑多言的一天。我的工作无非是将煤矿研磨成粉,送去化验,日复一日。这与我所向往的草原出入颇大。我带着一怀热忱而来,落得一身自在而去,如同生长在草原低处的青草,牧羊人挥出的鞭影。
市井
微冷的春风,明媚的春光。
在人群里,我接住来自陌生人的目光,有时,觉得它像麦芒一样,上上下下扑棱到我的身上。有时,又觉出它所析出的璞玉似的澄澈。常常在街市、火车站、农贸市场这些地方打转,做一些不称手的活计,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人,这是我走出校园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喜忧参半的每一天,无不充满未知的可能性,虽说某些个日子意义非凡,而我觉得其中也没有什么可值得特别地供奉。
生活,有时出其不意,有时略作抵偿。
农贸市场,一个关涉到利益所指就格外不能容情的地方。一次,一辆小汽车与我的三轮车相撞,让人不解的是,某些冷眼的看客勿论黑白便都一口咬定地说错在我。这件事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让我知道人心是偏斜的,往往总偏向殷实的一方,而排斥贫弱的一方。唯有心存善念,心怀宽广,方能笃定前行。
不管在任何场所,我最是看重一个人有着怎样的襟怀,有着怎样的韧劲,我坚信每个人都有一颗倾尽全力的心。我坚信,与众多胼手胝足的人声息相通,活得才更具真实性。
出游
久别了绵远的公路,久别了凌风的跨河大桥。
记不得多久没有外出旅行了,只记得那里满是风浮动不止的油菜花田,缓坡上随意标识着几棵树。站在长路的凸起处,可望见一围湖泊之全貌,呈扁葫芦形。既得其形,就姑且想当然地赋其以貌,以为它很美便是了,至于它需抵御着什么样的风浪,四时陪护着什么样的山神和马匹,全不在本人的考虑之列。
我喜欢走马观花的旅行方式,喜欢轻描淡写的写作。
我写下,模糊的更加模糊,明晰的明晰起来。
2017年6月,我和朋友前往贵德,相约去看远处的山。那里的峰峦被起伏的山岚吐纳,那里的崖壁映射着褐色的光,那里的山脊线棱角分明,有章可循。若把山抛到一边,那里便颜面顿失。如果把山上诸多微小的植株和纵横交错的丘壑一并抛进我的心里,那便自是另一番景况。
回來的路上,我若有所悟:得失顺逆,接过世道人心的献礼,一尝其中甘苦交杂的滋味,我所寻求的目标,不外乎像这些湖、这些山一样地活着。
果园
水渠北侧睡着一座果园,已遭园丁搁弃了。
我曾一度想把它重建起来。低矮的夯土围墙,不成体统,其上点染着块状的苔痕,如矿山上的积灰。一条小路把园子分作两半,一头是灰溜溜的园门,一头是土坯房;路两旁分置栅栏,外加几种攀缘植物。地势略高的一半种苹果,低的一半种梨树,皆以碧桃为埂。
春天来时,花木繁复。冬天来时,围炉小坐。
来到土坯房,一应家什尚能对付,故可越俎代庖。待到冰消瓦解,便全身活络起来,及至一叶知秋,略有所得。房前种豆点瓜,弄草莳花。我想试一试,尽管我并不擅长饲养鸽兔。
这是梭罗给出的一个无妄的设想,后来与霜打的萨迪携手同行,他那直橛橛的胡茬,传布到了我的嘴边。昔日的果园,化作一长串音符,从我和他之间的歌声中飞散。我已久不入果园,已打消了再见它的念头。实质上,当我隐微地想起,我的双脚便触及到了它。
到底是我想重建它,抑或是它要重塑我,我已无心讨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