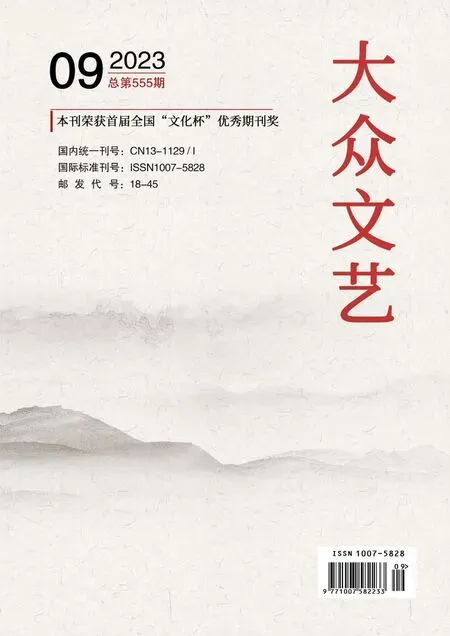论延安时期诗歌大众化的美学思想
李坚凯
(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1935年,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陕北后,延安文艺的序幕正式被拉开。各种文艺政策陆续推出,文艺活动竞相上演,文艺组织纷纷成立。街头诗、戏剧、歌舞剧等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送到前线军民的眼前,尤其是自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周扬、丁玲、艾思奇、何其芳等文艺理论家的到来,他们用优秀的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来支持着抗战。在各种文艺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和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是一方耀眼的花园。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发表之后,描写劳动大众生产生活的作品逐渐占据主流位置,具有“人民性”的诗歌作品源源不断地被创作出来,甚至由此形成了与“九叶诗派”“七月诗派”鼎足而立的诗人群体。按照龙泉明的解释,这一群体可以称之为“延安诗派”,即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不断吸引其他解放区诗人加入这个团体,从而促进工农的密切结合。因此从根本上讲,它“不是一个纯地域性的诗歌群体,而是一个诗歌流派。”[1]在这一团体下,聚拢了许许多多的诗人,如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萧三、贺敬之、艾青等;活跃于晋察冀的魏巍、田间等;活跃于太行山区的阮章竞、叶枫等。他们虽然所处地域不同,但是在诗歌创作上,都集中体现了“大众化”这一美学思想。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地域上的差异,间接使得各个诗人之间的文学思想相互碰撞,从而促进了他们在诗歌美学思想上达成一致。
一、形式的大众化传播
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857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在当时文艺界存在着对工农兵轻视的问题,因此他通过《讲话》所要传达的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意识。并且鼓励文艺工作者要亲近工农兵,同时引导文艺工作者开始思考“为谁而歌”的问题。针对毛泽东所指出的文艺创作中“人不熟”这一问题,许多诗人进行了反思,于是他们开始逐渐去贴近劳动人民的生活,甚至为了创作出老百姓真正喜闻乐见的作品,自发的去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艾青创作的《吴满有》,他为了能够创作出大众满意的作品,便住到了吴满有的家中,与他朝夕相处、平等交流。在创作出初稿后,又来到吴满有的家中读给他们听,当面听取吴满有的意见,不断修改,直到吴满有满意为止。这些行为表现出了“在主流政治文化尤其是毛泽东文艺美学的影响下,延安诗派形成了工农兵诗歌审美思想”,[3]即大众化的诗歌审美思想。
为了进一步将这一思想落实到底,延安时期的诗人们开始从诗歌创作最基础的“诗体”入手,各自在自己擅长的诗体上进行创作,古体诗、自由体诗、十四行诗等诗歌越来越多地被创作出来。不过在这一系列的创作探索过程中,自由体诗歌仍是许多群众最为喜爱的表现形式,而且因为诗人们需要用大众的情感来反映大众的心声,所以他们就必须以人民大众的思想和习惯去创作作品,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民歌体”诗歌,如戈壁舟创作的《边区好似八阵图》:“两山中间一道川,/两川中间一架山。/翻过山来又是川,/转过川来又是山。/边区好似八阵图,/敌人进来不得还!”[4]120又如贺敬之的《临男民兵》《过黄河》《果子香》等作品,这些诗歌都用大众最为熟悉以及最能接受的形式来教育影响百姓,使其真正成了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诗歌向民歌“取经”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的诗歌和实现诗歌大众化是当时延安文艺界的要求。萧三在《论诗歌的民族形式》中就指出中国新诗的创作必须要有中国情感,必须要用具有中国民族的形式来表达。要求诗人们在关注民族形式的同时亦要注意中国百姓的整体情况,即当时中国大众至少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朗诵出来的诗太洋化了的时候,老百姓一定不会喜欢的,一定不会被接受。”[5]同时,阮章竞也发现群众之所以对他们的“民歌体”诗歌抱有兴趣是因为用民歌形式“编写歌舞、活报剧,群众都较喜欢看。”[6]而人民群众的反映令文艺工作者们意识到只有创作出对群众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赢得群众的欢迎。
此外,形式的大众化不仅体现在创作形式上的“民歌化”,还体现在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上。1938年边区文协“战歌社”发表了《街头诗歌运动的宣言》,针对印刷和纸张的缺失问题,他们号召人们进行街头诗运动,其目的不仅在于利用诗歌做抗战的武器,而且也要使诗歌真正走上大众化的道路。由此,在诗人们活跃的区域随处可见“墙头诗”“岩壁诗”。同年,作为“街头诗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高敏夫将街头诗的种子带到了晋察冀边区,随后街头诗便在这里生根发芽,遍地开花。杨朔称之为:“(诗歌)绝不高坐在缪斯的宝典里……他们走进农村,走进军队,使诗与大众相结合,同时使大众的生活诗化。”[7]这些诗歌以其准确、生动、凝练而又形象的语言,传达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极其强烈的感情,使诗歌在鼓舞人心、愉悦性情、催人奋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真正做到了在实现诗歌大众化的过程中利用诗歌做抗战武器。
由此,我们可以从诗歌形式的大众化中看出,《讲话》之后“诗歌要为人民服务”已经印刻在了延安时期诗人们的思想中,他们已然意识到人民群众才是诗歌服务的主体。这表明在文化领域,文艺真正的主人已经由知识分子开始向人民群众转变。
二、语言的大众化流行
延安文艺工作者对于根据地人民生活情况的了解也是以《讲话》作为分界线的。在此之前,他们对于人民生活并不了解,有时为了创作甚至凭空捏造人民生活,这使得他们的诗歌无论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是从语言的使用上都不切实际,以至于创作出来的作品百姓们读不懂,也就谈不上接受。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就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工作者们的短处就是由于“语言不懂”,导致他们高高在上,与人民群众有距离感,所以有时创作的作品中生造了一些与人民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语句。并且指出要想做到文艺“大众化”,途径就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2]851曾经主张通过诗歌朗诵来实现诗歌大众化的音乐家吕骥也认为,诗歌朗诵要“接地气”,这不是为了给文艺工作者画“牢笼”,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正确选择。毕竟当一个地区只有“土语”时,那么“土语”就是通用的语言。
自此,诗人们开始与人民有了初步的结合,少量的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开始逐步进入到诗人们的诗歌中,就如艾青在《吴满有》中对吴满有的生活描写,无论是写吴满有之前的贫苦生活:“三个孩子挤在炕上,/不是赤着上身,/就是光着屁股,/脏的像猪子,/瘦得像猴子。”[8]54还是写他现在的幸福生活:“你的脸像一朵向日葵,/在明亮的天空下面,/连影子里都藏着欢喜。”[8]54这些诗歌无不是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来表达,并且都饱含真情,真正做到了为民而歌。
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学习人民大众的语言就成了一股热潮,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在将陕北方言拿来“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适用于自己作品的表达方式。可以说,相较之前,在语言的大众化运用上,延安时期的诗人们已经正式的“土”化,如萧三、田间、李季等,大量的陕北方言出现在他们的口中、作品中。在田间创作的长诗《戎冠秀》中,他就选取了许多群众的语言作为创作元素,如:“……戎冠秀心发软,/老鼠跳过她手边;/头一回减租,/闹了个糊糊。”[8]55这些诗歌通过运用群众的语言,不仅使作品更加符合群众审美,而且饱含了群众的情感和智慧。
此外,还有青年诗人贺敬之,他在《讲话》发表之后,积极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通过深入群众,学习群众语言的方式,将诗歌与陕北民歌进行了融合加工,如他创作的《行军散歌(开差走了)》:“崖下下来了老妈妈,/窑里出来了女娃娃/……把我们围个不透风,/手拉手儿把话明:‘水有源来树有根,/见了咱们八路军亲又亲’……”[9]376这一句句鲜活口语的运用,描绘出了八路军与边区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让人不禁分外感动。这都是延安时期诗人们在语言上接近民众,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结果。
纵观延安时期诗人们创作语言的变化过程,他们不再自视清高,和劳苦大众保持距离感,而是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努力汲取和提炼大众语言的精华,创作出了许多朴素的、自然的、口语化的、非矫揉造作的、民族的新诗。这也使得他们在实现“小我”和“大我”的有机融合中,让自己的创作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并且在推广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真正地表现出了只有符合大众的接受习惯和欣赏口味,才能真正赢得大众的喜爱。
三、内容的大众化显现
1943年,萧三对《讲话》之前的各种文艺思想进行过研究和总结,其中“有人认为,通俗、大众的东西,至多只是文艺的一种——而且是‘低级’的一种,那些主张及实行写通俗大众东西的作家,是写不出来真正‘高级’作品的”[4]60以及“写些通俗的、大众化的作品,只是为了抗战需要,是出于一时的不得已,而其实,那是文艺的降低,甚至那不是文艺”[4]60的观点可以说是和毛泽东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背道而驰。针对这些观点,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明确且有力的给予了回答:“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2]873这就使得延安时期诗歌大众化的另一表现就是内容的大众化。因为延安时期诗人们创作的诗歌归根到底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必定脱离不了人民的生产劳动,所以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作为诗歌的素材而出现。可以说,延安时期的诗歌不仅是人民生活的反映史,而且也是时代的记录史。所以针对当时的人民生活,诸如生产劳作、拥军支前,还有边区百姓的民主政治以及全新生活等,诗人们都用自己的诗歌去尽情描写,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体形象。
同时,由于延安时期处在战争年代,一切围绕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诗人们所作的诗歌作品除了描写战争、拼杀和牺牲外,大多数反映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生产建设的场景。如蓝曼《劳动的歌》:“我们紧紧地,/追赶着太阳和月亮,/我们把爱情,/全放在镢头上。/停停镢头向后望,/身后一片黑色的波浪。/土浪黑,我们汗滴,/正散发着阵阵清香……”[9]533戈壁舟的《烧炭》:“这是原始的森林,/这是无人的荒山,/纵横浩浩数百里,/知道古老的黄河边。/突然一支远征军,/出没在这无人的森林。/鸟儿在叫第一声歌唱,/人们就攀沿着荆棘前进……”[9]78这些诗就生动地表现出了边区人民生产劳作的真实过程,记录了广大劳动人民为了美好生活而不断奋斗的拼搏画卷。除此之外,还有陈学昭的《边区是我们的家》:“法西斯的第五纵队,特务分子,/勾结敌人要来破坏我们,/恶魔的黑手,/伸向边区,/试试看!/我们要用明快锋利的剑,/斩断那恶魔的黑手!/边区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生命属于它,/我们要拿头颅热血来保卫它!”[9]304张铁夫的《选民会》:“范五坐在那里灰溜溜地/低着头不言语。/老村长制止了骚动起来讲话,/他说范五是刚从白区过来的农民。/在国民党那里他活了半辈子,/甚至没有听说过自由和民主,/边区里人人平等他还没全解下,/要使他脑筋改转,/大家要慢慢教育他。”[9]333这两诗就凸显了当时身处边区的老百姓们为了守护边区,坚决对抗侵略者的坚定勇气以及边区农民参与民主政治,在政治领域翻了身的真实状况。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即使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人们依然没有放弃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许多诗歌中都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其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这部长诗以贫苦农民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为主线,描绘了农民与封建地主势力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曲折过程,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我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从大众化的美学思想来看,这种内容大众化的出现主要是广大诗歌作者在下乡入伍的过程中,完成了心理身份转换,诗人从思想到创作都实现了净化,能够主动、自觉地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也就是说,此时的诗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诗人,而是亲眼看到农民劳动甚至亲身参加农民劳动的诗人,他们的创作视角聚于工农兵身上,他们作品的内容也就是大众生活中的所有活动。如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描写了农民阶级在遭受苦难和压迫之下的一种成长过程;柯仲平《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生产》一诗,描写出了劳动人民进行抗战的巨大决心……
结语
总而言之,从延安时期诗歌创作形式、创作语言以及创作内容“大众化”的表现中能够看出,在《讲话》之前,诗歌大众化已经是一个大部分诗人们所共识的观点,但是就以何种方式去寻求“大众化”则产生了多种分歧,不过这种分歧在《讲话》发表之后便不复存在了。而且在经过这一实践过程之后,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已经不再是精英阶级的专属,而是表现出一种文化重心向普通大众下移的趋势。并且这一过程也使得诗人们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真正站到了大众的立场上去创作,努力追求作品的“大众化”成了他们创作的美学基础。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来说,依然具有借鉴意义。文艺工作者们应该时刻站在广大群众的立场上,将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机结合,以文艺特有的方式将之展现;而不是用机械的、古板的或者巧合的一种描绘来想象性的创作文艺作品。所以,文艺家只有真正站在群众之中,用文艺作品为群众服务,才能真正体现“大众化”的美学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