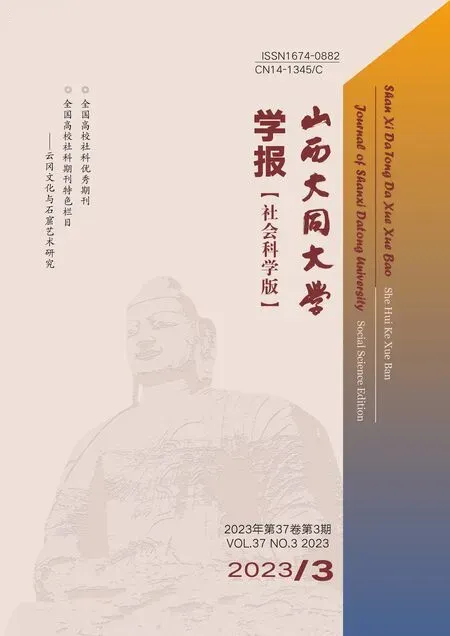契丹入汴与辽乐的崛起
董希平,邸晓平
(1.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2.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北京 100024)
后晋(936-947年)是五代仅仅持续了两帝十二年的中原王朝,契丹-辽(916-1125 年)则是持续了九帝两百余年的塞上王朝。前者对后者崛起与强盛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报答契丹在取代后唐战争中的帮助,石氏后晋不仅提供了契丹踏入中原的地理基础——燕云十六州,更继续提供了辽乐崛起的契机和物质基础。
契丹具有礼仪性和政治意味的国家音乐的形成,在与政治体制相比在时间上要滞后得多。从五代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 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族首领,到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 年)他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称帝建契丹国,契丹音乐一直保持原始味道,政治礼乐意味也不浓。直到太宗耶律德光帮助石敬瑭击败后唐建立后晋,取得燕云十六州,在与后晋的交往中不断获得中原音乐与文物,才奠定了契丹国家音乐的基础。而后947年耶律德光入汴,①灭亡后晋,并于汴京称帝,改国号“大辽”、年号“大同”,期间所用礼乐多就地取自石晋,其后耶律德光北归,所携带的战争虏获使辽的国家以及全民音乐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基于中原礼乐的音乐大发展,也为“北面官以契丹旧制治契丹人、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②的政策提供了礼乐上的合法性,并巩固了辽国胡汉分治改革的成果。试详论之。
一、契丹早期音乐的部落色彩
帮助石晋建国并与之建立密切关系、开始获得中原乐之前,契丹音乐是比较原始的,其内容与功能距离严格意义的国家层面,还有很大的距离。早期契丹音乐,从内容到形式,从曲调到乐器,简朴单纯,充满了原始部落意味,国家意识不强,在宋人的视野中,不过“吹叶成曲”而已:
胡人吹叶成曲,以番歌相和,音韵甚和。[1](P270)
契丹本土音乐,后来称为“国乐”,其所控制下的国家、部落之乐则称“诸国乐”,即便是后来国家礼乐完备,众人在国事礼仪活动中往往也不脱素朴本色。如清人王文清所论:“辽之未有古乐也,地限之也,然独能自成其乐,不如宋乐之纷更也。……辽制,上寿日,亲从双岐树下过身,象母生时苦状也,是日撤乐,此制殊令人生感。”[2](P868)辽国正朔日朝贺、元会,用雅乐、大乐,晚上皇帝燕饮,则用国乐;春飞放杏埚,皇帝射获头鹅,荐庙燕饮,也不过是用“乐工数十人执小乐器侑酒”。[3](P881-882)
诸国乐使用的例子举不胜举。太宗耶律德光会同三年(940 年),接见后晋和其它国家使者,直接在便殿饮酒歌舞,后晋宣徽使杨端、王朓亲自起身表演;这一年端午,百官与各国使臣朝贺,大家宴饮之余,回鹘、炖煌两国使臣被命表演本国舞蹈;即便在辽国末年,天祚帝耶律延禧时期,头鱼筵上,参与的各部落首领还是次第歌舞,天庆二年(1112 年)混同江头鱼酒筵上,女直阿骨打拒绝歌舞为乐,甚至引起了耶律延禧的杀机:
诸国乐太宗会同三年,晋宣徽使杨端、王朓等及诸国使朝见,皇帝御便殿赐宴。端、朓起进酒,作歌舞,上为举觞极欢。
会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国舞。
天祚天庆二年,驾幸混同江,头鱼酒筵,半酣,上命诸酋长次第歌舞为乐。女直阿骨打端立直视,辞以不能。上谓萧奉先曰:“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不然,恐贻后患。”奉先奏:“阿骨打无大过,杀之伤向化之意。蕞尔小国,又何能为。”[3](P882)
契丹祭祀类乐舞更具原始宗教色彩,甚至有排他性,如早期皇族受册立,汉人不得参与,只有本族人歌舞于现场“聒帐”;祭祀拜谒契丹圣地木叶山,其仪式也不过骑射唱歌,所用乐器仅仅胡琴而已:
凡受册,积柴升其上,大会蕃人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汉人不得预。有诨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将尽,歌于帐前,号曰“聒帐”。每谒木叶山,即射柳枝,诨子唱番歌,前导弹胡琴和之,已事而罢。[4](P2561)
契丹本土音乐这种质朴原始风格,既是与生俱来,也是契丹贵族有意识避免浮华的结果,据说耶律阿保机时期,乐官人数也很多,但后唐庄宗李存勖因为沉溺伶官而亡国,阿保机因之大生警惕之心,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一月户部尚书叶梦得《奏应诏大询状》中谈到这段历史,说:
昔后唐庄宗父事契丹阿保机,及庄宗之难,阿保机谓其使者姚坤曰:“吾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人、乐官千人,放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败也。我自闻其祸,则举家断酒,解放鹰犬,罢散乐官。我亦有诸部乐官千人,非公宴不用。”[5](P89)
阿保机因为庄宗李存勖的悲剧而“举家断酒,解放鹰犬,罢散乐官”,客观上延缓了辽乐向原始质朴向豪华风格发展的进程。
契丹日常乐舞活动,往往随游牧移动迁徙而行,独特的生存环境构成其独特魅力,宋词人姜夔曾在都城临安听降宋的金国将领萧鹧巴讲契丹风俗,萧氏原为契丹人,他所描述的契丹风俗,歌舞表演与车马、渔猎生活融为一体,显示出实用、狂野的风貌:
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儿牵车小儿舞,弹胡琵琶调美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平沙软草天鹅肥,健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鞴(bèi,臂上架鹰)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无,年年海上驱群胡。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之飞铁为翼,射生小儿空看得。腹中惊怪有新姜,元是江南经宿食。(姜夔《契丹歌·都下闻萧总管自说其风土如此》)[6](P13)
即便是到了辽国后期,契丹乐依旧保持适应性强、便于移动演奏的特点。宋人江万里《宣政杂录》载,宣和年间,宋金合作攻辽,流落到汴梁的辽国百姓,所进行的击鼓歌、投竿等表演,即是如此。其表演非常流行,以致于被视为稍后北宋灭亡的预兆:
宣和初,收燕,辽民居汴者,夜有臻蓬蓬歌,词曰:“臻蓬蓬,外头花花里头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满城不见主人翁。”此本辽谚,为宋北辕之谶。又有伎者投竿,念诗曰:“百尺竿头望九州岛岛,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亦辽人作,竟成宋谶。[7](P139)
契丹传统音乐形式内容简略,节奏旋律明快急骤,与传统的中原音乐颇不相同,因此契丹音乐往往被禁止外传,据宋人说是自愧不如在作怪,但有魅力的音乐是无法抗拒的,宋朝之时,以横笛、拍鼓、拍板为主力伴奏乐器的契丹歌舞,最终还是流传到宋朝和其他部落,并且得到极大欢迎,风靡于军中和宋朝士大夫之家:
臣观契丹视他戎狄最为强桀,然所用声曲皆窃取中国之伎,但不能和阐婉谐、弹丝擫管、趋于成音而已。耻其本俗所翫,禁止不传,而中国第得其蕃歌与舞,其制:小横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和之,其声喽离促迫,舞者假面为胡人衣服皆効之,军中多尚此伎。……然今天下部落效为此伎者甚众,非特无知之民为之,往往士大夫之家亦喜为之。[8](P727)
这是最正宗的契丹本土音乐,大约也是最有诱惑力的契丹国乐了。但是依旧被建国远远晚于辽的宋人瞧不上。
二、辽乐国家属性的基础和崛起的关键
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天福元年)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助石敬瑭击败后唐军,石敬瑭与耶律德光约为父子,十一月石敬瑭即皇帝位,改元“天福”,国号“晋”,将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
得到燕云十六州之后,随着石晋赠送各种音乐,辽乐有了国家属性的基础,并不断发展。
辽最先得到的是散乐。散乐主要以横笛、拍板、腰鼓乐器来进行伴奏或烘托渲染气氛的歌舞、杂耍,又称百戏,《旧唐书·乐志》描述其大概说:
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汉天子临轩设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化成黄龙,修八丈,出水游戏,辉耀日光。绳系两柱,相去数丈,二倡女对舞绳上,切肩而不倾。如是杂变,总名百戏。[9](P1072)
五代时候的散乐表演歌舞杂耍纷呈,继承的是汉唐遗风,后晋天福三年刘煦带到契丹的伶官,开了契丹人的眼界,也为契丹散乐打下了基础,《辽史·乐志》说:
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晋天福三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3](P891)
天福三年刘煦一行人是以为契丹皇帝和皇太后行册礼的使节身份去的契丹,所带散乐应该是为册立宴饮娱乐之用。
散乐恐怕是刘煦一行人所携带音乐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应该是雅乐与大乐。因为刘煦使团是去参加辽皇与皇太后的册礼大典的,既然带了音乐,仅仅是散乐恐怕是不够的。薛居正《旧五代史·高祖纪》言及使团的构成和目的:
八月戊寅,以左仆射刘昫为契丹册礼使,左散骑常侍韦勋副之,给事中卢重为契丹皇太后册礼使。[10](P1017)
是年为辽太宗会同元年(938 年),《辽史·太宗纪》记其事则直接说是给辽皇与太后上尊号:
九月庚戌,……边臣奏晋遣守司空冯道、左散骑常侍韦勋来上皇太后尊号,左仆射刘昫、右谏议大夫卢重上皇帝尊号,遂遣监军寅你已充接伴。[3](P44)
刘煦一行人既然是上尊号行册礼,以辽国当时的状况,相关礼乐器契丹不可能完备,而刚刚两年前耶律德光刚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前者帮助后者灭唐建国,两者关系正处于史上最好时期。一应礼乐器、卤簿、礼仪工人大部当是后晋所带,用完之后,直接留给契丹,《辽史·乐志》记其事说:
晋高祖使冯道、刘昫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3](P885)
这些声器、工官与法驾,又成为契丹太常礼乐的基础。
刘煦一行人所带去的,还包括大乐,大乐是用于帝王祭祀、朝贺、燕享等典礼的典雅音乐,有别于通常所言的太常宫悬雅乐。③唐代大乐有“七德乐”“九功乐”“文舞”“武舞”“景云乐”,中唐之后仅余景云乐舞,历经唐末五代之乱,辽国即存有大乐,且是晋代所传。《辽史·乐志》解释契丹大乐器说:
大乐器:本唐太宗七德、九功之乐。武后毁唐宗庙,七德、九功乐舞遂亡,自后宗庙用隋文、武二舞。朝廷用高宗景云乐代之,元会,第一奏景云乐舞。杜佑通典已称诸乐并亡,唯景云乐舞仅存。唐末、五代板荡之余,在者希矣。辽国大乐,晋代所传。[3](P886)
据《辽史》说明,用于杂礼的坐部乐工二百四人,都用景云遗工来代替:
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3](P886)
后来契丹一直使用石晋带来的大乐,如辽圣宗耶律隆绪朝,册立皇太后仪式上就用了童子、女子队乐:
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册承天皇太后,童子弟子队乐引太后辇至金銮门。[3](P885)
要知道那时候立国不久的宋朝,朝会时候根本还凑不齐一套礼乐,只能找些教坊乐工凑数。
后晋送往契丹的乐工,来源广泛,不仅仅限于京城一地,比如天福三年八月戊寅,刘煦使团出发之后,辛丑,河北三州就奉诏送六十七名乐官去契丹,这应当是使团带给契丹音乐的一部分:
(天福三年八月)辛丑,镇、邢、定三州奏,奉诏共差乐官六十七人往契丹。[9](P1018)
散乐、大乐的进献为契丹乐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但真正使契丹乐突飞猛进的,则是耶律德光灭晋入汴的劫掠。
晋高祖石敬瑭之后,石重贵即位,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契丹三次南下,最终于开运三年(946 年)攻入开封,俘虏石重贵。是年为契丹太宗会同九年。契丹入汴梁,大肆掳掠,人口财货之外,礼乐器物是最大的收获。第二年,耶律德光改国号“大辽”,年号大同。大同元年(947 年)在汴梁的耶律德光即用中原皇帝的卤簿仪仗,并习以为常:
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晋,备法驾,受文武百官贺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3](P907)
后来他的继承者更将所获唐、晋文物,全部拿来使用:
是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3](P907)
该年四月,耶律德光离开汴梁北归,提前于三月份首先掳掠而去的是后晋所用的太常雅乐一应器物:
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辽阙郊庙礼,无颂乐。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3](P883)
当然,整体而言,掳走的几乎是后晋或者说中原的精华:
三月丙戌朔,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赐将吏爵赏有差。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3](P59-60)
对于这场搬空后晋朝廷的迁移,《契丹国志》记录得更大气,说是“尽载府库之实以行”:
帝发大梁,晋文武诸司、诸军吏卒从者皆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实以行。[1](P45)
如此,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再加上天福三年刘煦使团所带册立礼乐,契丹已经几乎拥有当时中原雅乐的全部。
耶律德光当年死于北归途中,但是他对于中原礼乐的使用这种习惯却在契丹保持下来,契丹汉官舆服,后来就是以石晋遗制为标准:
五代颇以常服代朝服。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及五代晋之遗制也。[3](P900)
契丹拥有了完整的中原雅乐,可以将中原礼乐用于治理汉人的汉制中,这强化了其会同元年耶律德光(938 年)实行的南北两面胡汉分治改革,使得“北面官以契丹旧制治契丹人、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更具有礼乐上的合法性,也更加稳固。辽汉兼治,又使得契丹在与后来的中原政权交往中也更具法理性,姿态上也更显自信。
耶律德光入汴导致的中原音乐人、物的南迁,这种掳掠遍及各阶层,而不仅限于官方行为。出帝石重贵家族北迁,其乐工歌伎散播的过程,可以作为一个考察个案。耶律德光入汴第二年正月,石重贵即被押送黄龙府安置,耶律德光还算照顾他的面子,配备了全套侍从人员:
辽降出帝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迁于黄龙府。……于是太后与冯后、皇弟重睿,子延煦、延宝举族从晋侯而北。以宫女五十,宦者三十,东西班五十,医官一,控鹤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仪鸾司三六,军士二十人从,卫以骑兵三百。[1](P42)
有意思的是,所携带人员中的五十名东西班禁军乐队,先后被瓜分。到了辽阳,先是被阿保机长子耶律倍的儿子永康王耶律兀欲夺走十五人,剩下的又被永康王妻兄抢走:
汉乾佑元年(948)四月,永康王至辽阳,帝与太后并诣帐中,帝御白衣纱帽,永康止之,以常服谒见。帝伏地雨泣,自陈过咎,永康使左右扶帝上殿,慰劳久之,因命设乐行酒,从容而罢。永康帐下从官及教坊内人望见故主,不胜悲咽,内人皆以衣帛药饵献遗于帝。及永康发离辽阳,取内官十五人、东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并令随帐上陉,陉即蕃王避署之地也。有绰诺锡里者,即永康之妻兄也。知帝有小公主在室,诣帝求之,帝辞以年幼不可。又有东西班数辈善于歌唱,绰诺又请之,帝乃与之。后数日,永康王驰取帝幼女而去,以赐绰诺。[9](P1126)
引文中描述“永康帐下从官及教坊内人望见故主,不胜悲咽,内人皆以衣帛药饵献遗于帝”,可见石晋皇室的歌妓乐工,远在耶律德光大规模掳掠之前,也已经有被掠至契丹的了。
如此,耶律德光灭晋的掳掠,等于中原的乐工、歌妓、乐曲精华移至辽地,为契丹所用,并融合生长,辽乐藉此得到了迅猛发展,同州合阳县令胡峤,在契丹南下战争中做辽将萧翰的掌书记,后居契丹七年,于后周太祖郭威广顺三年(953 年)逃归中原,他对辽国上京情形的记录反映了后晋灭辽之后的各行各业包括音乐的迅猛发展,以及这其中显著的中原因素:
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1](P266)
胡峤说上京市集,各行各业多为中国人,且以并、汾、幽、蓟之人为多,这很程度上是世宗入汴所带来的战争福利。
三、宋辽交流成为辽乐兴盛的助力
960 年北宋建立,其音乐基础远不如已经获取中原音乐精华的辽,但是北宋据中原地理优势,又获得了西蜀、南唐、吴越、南汉诸国的音乐,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音乐体系。宋、辽音乐于是形成了交流与竞争的关系,两者的交流在“澶渊之盟”后进入高潮,在这一交流中,辽世宗入汴所获取的中原音乐无疑为辽人提供了强大的礼乐自信,礼乐也同样在这一交流中更加完善,走上其高峰。
宋辽音乐交流而影响于辽,使节间的来往是主要途径。宋对于辽使臣的接待,音乐表演是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且表演内容丰富,宋皇生日大宴中的教坊乐的宏大表演,契丹等邻国使节是重要嘉宾和观众,《东京梦华录》中有详细描述,兹不赘述。此外,专门接待契丹使节,根据从不同场合,既有教坊散乐,又有胡部诸乐:
圣朝宴契丹使于紫宸殿,敎坊应奉惟作小儿伎舞及杂剧而已,未尝专待以胡部之乐也。然用胡部乐以宴蕃使,宜于国门外玉津园作之,或在殿庭当一用雅乐焉,斯得古人内中国外夷狄之意也。[7](P924)
而辽接待宋使的歌筵,观其曲宴宋国使乐次,则正式得多,几乎是宋朝大宴的精简版,而且还多了宫悬雅乐,这可看出前者对后者的有意学习,或者者说后者对前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五行阙。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酒七行 筝独弹。酒八行歌,击架乐。酒九行歌,角觝。[3](P892-893)
辽接待宋国使臣的燕乐,比起辽皇生辰乐次还繁复,饮酒多了三巡,分别是两次歌唱、一次击架乐:
酒一行 觱篥起,歌。酒二 行歌,手伎入。酒三行 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四行 阙。酒五行 笙独吹,鼓笛进。酒六行筝独弹,筑球。酒七行歌曲破,角觝。[3](P891-892)
如此看来,在使节的招待上,增加歌唱内容的比例,又用上了宫悬架乐,辽人对于接待宋使的重视程度之高可想而知。这里边除了国事之外,显然又有音乐的交流和竞争了。
遇上特别的使臣,辽人往往还有特别的优待,这种特别优待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还体现在乐舞招待上。如宋仁宗至和元年九月(1054 年),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使辽,一行人于第二年即兴宗耶律宗真重熙二十四年二月(1055 年)被邀请参加了契丹头鱼宴。王拱辰使宋朝状元,且任职翰林十五年,耶律宗真不仅亲自劝酒,而且亲自弹琵琶为拱辰侑酒:
辛巳,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为回谢契丹使,德州刺史李珣副之。拱辰见契丹主于混同江,其国每岁春涨,于水上置宴钓鱼,惟贵族近臣得与,一岁盛礼在此。每得鱼,必亲酌劝拱辰,又亲鼓琵琶侑之。谓其相刘六符曰:“南朝少年状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待之。”[4](P4281)
国家之间的物品交换,则是音乐交流的又一途径。宋赠辽的物品中,音乐是其中之一,凡契丹皇帝生日,宋朝必送礼物,如“宋朝贺契丹生辰礼物”单中,“红牙笙笛,觱栗,拍板”这些常用乐器赫然在目,且排在礼单前列:
契丹帝生日,南宋遗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袭,金玉带二条,乌皮、白皮鞾二量,红牙笙笛,觱栗,拍板,鞍勒马二匹,缨复鞭副之,金花银器三十件,银器二十件,锦绮透背、杂色罗纱绫縠绢二千匹,杂彩二千匹,法酒三十壶,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盐蜜菓三十罐,干菓三十笼。其国母生日,约此数焉。正旦,则遗以金花银器、白银器各三十件,杂色罗纱绫縠绢二千匹,杂彩二千匹。[1](P226)
如此的交流发展,到契丹末期,辽乐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 年),辽国为金所灭之时,宋著作郎许亢宗为贺金主吴乞买登位使,他在金国上京会宁府所见金人所用契丹教坊四部,已经有两百余人,其歌唱水平之高,以许亢宗的眼光,也认为“声出众乐之表”,他在《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写道:
虏主所坐若今之讲坐者,施重茵,头裹皂头巾,带后垂,若今之僧伽帽者;玉束带、白皮鞋,薄髯,可三十七八许人。……食余,颁以散三节人。乐如前所叙,但人数多至二百人,云乃旧契丹教坊四部也。每乐作,必以十数人高歌以齐管也,声出众乐之表,此为异尔。酒五行,食毕,各赐袭衣袍带,使、副以金,余人以银,谢毕,归馆。[11](P40-41)
许亢宗见到吴乞买的第二天,又有百戏表演,这是当时水平很高的散乐,考虑到金人刚从白山黑水出来,这样先进、繁复的表演,不像是他们原本具有的,应该也是灭契丹的收获:
次日,诣虏庭赴花宴,并如仪。酒三行则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刀牌、砑鼓、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挝簸旗、筑球、角抵、斗鸡、杂剧等,服色鲜明,颇类中朝;又有五六妇人涂丹粉,艳衣,立于百戏后,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如祠庙所画电母,此为异尔。酒五行,各起就帐,戴色绢花,各二十余枝。谢罢,复坐。酒三行,归馆。[10](P41)
许亢宗所说的热闹百戏,与宋朝相似;持镜妇人为百戏表演提供背景和舞台效果,镜光闪烁,如祠庙所画电母,这应当是契丹乐中的西域乐舞成分。则中西融合,也是成熟辽乐的一个特征。
概而言之,辽乐的发展与完备,是在与中原、尤其是石晋政权交往中完成,并最终以国家音乐的姿态卓立于诸国之间,但历经百余年的演进,最终不脱历史循环,辽乐又为金所夺取,“楚人弓,楚得之”,随着金灭宋,辽乐又与宋乐在金乐的背景下又进入了一个百年融合循环。
注释:
①张其凡.五代都城的变迁[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4).五代政权更迭频繁,都城屡经变迁,后梁朱温以汴州为开封府,称东都,以唐之东都洛阳为西都,东都、西都又称东京、西京。后梁先都开封,两年后迁都洛阳,末年又迁开封;后唐都洛阳,改东京开封府为汴州宣武军;后晋初都洛阳,后建东京于汴州,复以汴州为开封府。详参张其凡《五代都城的变迁》。开封有汴州、东京、东都多种称呼,因其为战国魏都城大梁故地,故又称大梁、汴梁,这些称呼从五代开始,直到后来的北宋,一直混用,并不随时局变化而进行严格更改,后晋人亦如此。
②(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契丹汉辽分治,一国两制,起于太宗耶律德光:“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辽的大乐,即是由石晋传入的唐张文收所制《宴乐》四部乐舞,辽称其为“大乐”,是为了与“散乐”区别;宋宫廷则称雅乐为“大乐”,以与燕乐相区别;南宋民间则称宫廷教坊所奏燕乐为“大乐”,以与民间流行的、使用乐器少的细乐相区别。详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十八章“宫廷的鼓吹乐和燕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