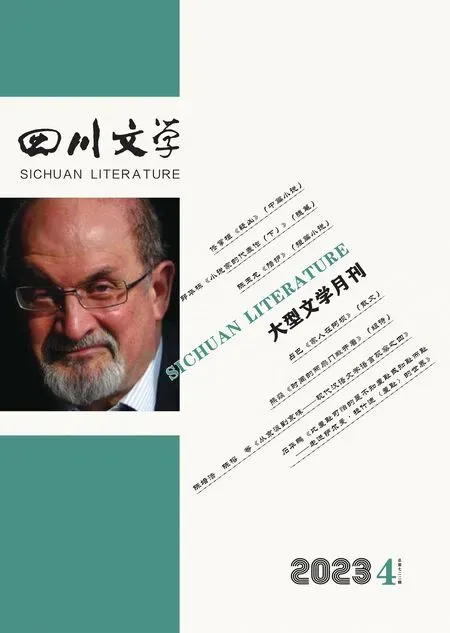陪护
□文/陈玉龙
介绍人指着前面一幢青砖绿瓦的房屋说,王姨,就在这里。
王秀梅稍作停步,伸手捋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嘴里应答一声,这里么。
房屋是平房,在众多漂亮的楼房之间显得有点简朴,像是在一群浓妆艳抹的女人之间走出一个男人,一个普通得让人无法记住的男人。
王秀梅胡思乱想之间已经走进小院子,介绍人熟练地推开大门,王秀梅跟着一只脚踏了进去,可另一只脚却留在了门槛外。因为屋里光线太暗,或是从外面进入一时适应不了屋里的光亮,介绍人双脚停住,王秀梅的身子就撞到了她的身子上,另一只脚艰难地插进来。这时,她们没留神一只大花鸡从门口角落里的鸡窝里飞出来,咯咯大叫着从她们头顶上飞过,一个爪子把王秀梅的头发也抓成了一个鸡窝,王秀梅只好双手梳理着头发,眨巴眨巴眼睛。介绍人这时已把大门全开,屋里这时才亮堂起来。介绍人叫了一声老胡,王秀梅才看清厅堂里的摇椅上半躺着一个清瘦的老人,穿着件灰色夹衣,头发没有全白,像是稻田里夹杂着一小撮稗草。他坐起身,目光直接扫向了介绍人身后的王秀梅,神情一亮,说了一句,来了,坐。说话简短,就像他那矮小的身材。
事情是早就谈好了的,也就没有了其他多余的话。介绍人再次在王秀梅耳边叮嘱说,一切就按说好的做吧,有什么情况就打我的电话,当然,最好是不要有一点小事就打,尽量自己先处理好。工资嘛每月尾打到你的账户上,这里的开销实报实销,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要乱花,他们也是相信你才放手让你这么做的,相信你会让他们放心。
王秀梅瞟了老人一眼,见他还在打量着自己,倒有点不好意思,便转过脸对介绍人说,放心吧,答应的事我会做到。
屋里有点乱,地上还留有鸡屎。王秀梅找到扫把正要打扫,老胡发话了,说先不要忙,歇一会儿吧。老胡的声音有些沙哑,王秀梅一听就知道是喝水少的缘故。但地上的鸡屎很碍眼,让一向爱干净的王秀梅不扫不快。把地上扫干净后,王秀梅看到老胡又半躺在摇椅上,便拿起桌上的热水瓶,却是空的。老胡说,茶几上有烧水壶,厨房里有自来水。
听着水壶滋滋响起来,王秀梅拉过一个矮凳子坐到了老胡身边,老胡有点不好意思,胳膊支撑在扶手上想坐起来。王秀梅却拉住他的胳膊,说,老胡,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陪护了,你躺着舒服就躺着吧,不要见外了,有什么事就吩咐我一声。老胡嗯了一声,竟听话地躺下了。
老胡的儿子在省城成家立业,老伴过世多年,儿子让他在城市生活,可老胡不干,就是要赖在乡下的老房子里不走,说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哪有乡下随意?儿子大了,孙子都上大学了,老胡也就老了。儿子不放心,只好给他找个陪护,起先老胡是不答应的,现在,不答应都不行,身体由不得他了。
对于老胡的家庭情况,王秀梅听介绍人作过介绍,就爽快地答应了。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屋子,水已烧开,给老胡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说实在的,王秀梅不但感觉到口渴,肚子里也早就饿了。中饭吃得早,从几十里的山村赶到这个紧邻乡街的村庄,王秀梅几乎不曾停下过脚步,好在她平常也劳碌惯了,倒也不觉得很累。王秀梅问老胡想吃什么,老胡说你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吧,冰箱里有儿子托人给他买好的菜,不过,他吃粥,早上已吃过,中饭还是粥,只不过是叫王秀梅热一下。王秀梅站在老胡身旁又坐下,说,老吃粥怎么行,营养跟不上,身体就不行呀。老胡半晌没说话,而后坐起身,想站起来,显然有点儿吃力。王秀梅上前扶住,老胡才离开了摇椅,王秀梅抓紧他的胳膊,问,老胡,你要做什么?老胡人本来就瘦小,站在高大的王秀梅跟前,仰起脸来正好碰到王秀梅的胸,女人倒没有什么尴尬,毕竟老胡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可老胡倒显得慌乱,推开王秀梅的手说,我自己可以走。说着,身子颤悠悠地往屋后的卫生间走去。
陪护的生活正式开始,对王秀梅来说可谓轻车熟路。前几年孙子出生,王秀梅本想去儿子的城市里带小宝贝,可儿媳妇说城里房子小,多一个人不好住。其实,这只是个借口,王秀梅索性找到县里的家政公司,做起了陪护和保姆的工作,挣的钱,存在了折子上,留到以后老了,住到养老院。指望不上儿子,她要留个后路。
村子不大,老胡的房子正在村中,王秀梅的到来吸引来了一些女人瞧热闹,她们挤挤挨挨进了院子。听到声响,王秀梅主动走出来,热情地招呼着说,进来坐坐吧。她们站住,一个个伸头瞪眼地打量着王秀梅,一个头上只有几根稀疏白发的老女人说,大狗真会享受哇,找了个这么年轻的女人。大狗?王秀梅心里问大狗是谁?老女人看出她的疑惑,说大狗就是你说的老胡,小名就叫大狗。一个短发胖女人问王秀梅,你真的愿陪这个八十多岁的男人呀。王秀梅知道她们是误会了,说,我只是老胡儿子请来的陪护,照顾他是我的工作。
女人们不相信地摇头,交头接耳啧啧声不断。王秀梅发现有一个大概六七十岁的瘦女人一直没作声,只狠狠地拿眼盯着她,但王秀梅与她的目光一对上,她却迅速躲开了。
她们也不进屋,就在院子里聊着。王秀梅也懒得理她们,进门做饭,肚子真的饿了。
夜晚的降临让整个村子安静下来,王秀梅白天里的忙乱似乎让这个小屋有点热气腾腾。许久没有这样的气息了,老胡茫然地看着眼前王秀梅高大的身影,竟然有恍若隔世的感慨。院子里一片黑暗,屋里的电灯亮堂堂的,在老胡的记忆中,近年来也只有过年时才有这么一种亮堂。老胡的住房里临时加了个床铺,那是王秀梅来之前介绍人给加的。老胡年纪大,每天只能吃稀饭或者汤汤水水之类的食物,否则咽不下去。晚上起来小解的次数频了,陪护的人需要同住一室,以防老胡出现摔倒之类的意外。
房间里的大灯关了以后,开了一个淡黄色小灯,这也是王秀梅特地准备的。初来乍到,忙了整整一个白天,王秀梅感觉真有点累了,躺下来就睡。本来她还想陪老胡聊聊,可看着老胡谨慎的表情,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老胡却睡不着,床还是自己的床,可房间里多了个人,而且还是个女人,使他脑海里出现一个错误的意识,好像自己睡到了别人的家里。当初儿子要请陪护的时候,老胡没有答应要住到一个房间里,可儿子硬是替他安排了,说这才是关键,老人往往出问题都是在晚上,他可不想担惊受怕。
一觉醒来,王秀梅看了看手机,两点过十分。这一觉睡得太沉了,梦都没做一个。她轻手轻脚爬起来走到老胡的床前。老胡侧身睡着,秃顶在一圈花白的毛发中安详地散发出淡淡的光影,密密的胡茬更清晰可见,盖的是一层薄被,一条胳膊紧箍在胸前,压住被子,似乎害怕有人突然一下子给掀开。
没有什么情况,王秀梅放心地躺下来。不一会儿,听到老胡翻身的声音,接着床吱呀一响,抬起头一看,老胡正在下床。王秀梅知道老胡要去小解,赶紧下床,说,老胡,我扶你去吧。老胡摆着手,说不用,你只管睡就好了。但王秀梅还是走过去给他披了一件外衣,老胡嘴里颤声说不冷不冷,手上还是把外衣拉正了。王秀梅坐在床沿上,尖起耳朵听着门外的响动,生怕传来老胡的惊叫或者摔倒的声音。还好,一切正常,几分钟过后,老胡推开门,身子慢慢移了过来,见王秀梅还在坐着,不好意思地说,你睡吧,我没事的。王秀梅走过去,把他的外衣给拿下来,又帮他拉好被子。老胡连忙说,我自己可以的,我自己来。
不时有女人来老胡家串门,说明老胡先前在村子里人缘还是不错的,当然,她们主要还是来看王秀梅。一个外村的女人专门来陪一个老男人,说什么在村里也是一件新鲜事。与王秀梅熟悉后,她们不再扭扭捏捏在院子里拉呱,而是大大方方坐在厅堂中,夸赞王秀梅把屋子收拾得干净,光亮堂堂的舒适,不像一个老人住的屋子。以前老胡一个人在家里总是关着个门,没进门就闻着一股霉气,虽是一个男人住着,却阴气重。
但有个女人不喜欢和她们一起来,总是瞅着机会一个人来。王秀梅后来也知道她的名字,叫秋菊。也就是一开始出现的那个瘦女人。
秋菊的穿着在村里来说比较新潮一点,尽管天气已转凉,可她竟然穿着城里女人才敢穿的裙子,梳得亮光的发边夹着一只黄色发夹,看着越发年轻。她进来时轻巧巧的没有声音,有时王秀梅干完活儿,一转身才发现老胡身边坐着秋菊,女人只微微对她点一下头,仍同老胡说着话。王秀梅略显尴尬,只好主动找事去干。显然,秋菊与老胡的关系不一般,或者说曾经不一般。好在秋菊每次来都不会坐很长时间,至于他们谈的是什么,王秀梅不愿意听,偶尔听到过一次小小的争议,好像是老胡有什么东西不愿意告诉她,秋菊有点儿恼怒。
老胡五十多岁时老伴就走了,而且他曾经吃过公家饭,与村里的某个女人有些纠葛也属正常。王秀梅不想打听老胡的隐私,她只是个陪护,管好老胡的生活,尽量让他开心过好余下的日子,做好这些就足够了。从那些老女人的闲聊中王秀梅也对老胡的过去有了一个粗线条的了解,感觉老胡这个人挺复杂的。干过十多年的民办教师,后来又做生意,生意失败后夫妻两人又到南方打工,拼死拼活地把儿子送上了大学。可儿子毕业那年,妻子却意外去世了,老胡不再外出打工,回到村子里陪着妻子的遗像闭门不出。后来儿子把他接到刚工作的那个城市住了一段时间,直到儿子结婚,老胡又回到了村子里。此时,老胡已变了个人,一个人自耕自足,倒也乐得自在。儿子带着媳妇孩子过年时热热闹闹地回到村子里,老胡也不惊不喜,由着他们热闹去,自己则孤寂地坐在他的小房间里不出来。老胡的性格越来越孤僻,身子也越来越差,儿子把他接到省城的大医院检查,医生悄声对他儿子说了一些什么话,然后当着老胡的面说,无须治疗了,回家好好静养吧。
老胡养了一只大母鸡,门角里的鸡窝几乎每天都有一个鸡蛋,只是那只大母鸡喜欢随地拉屎,王秀梅便把它赶到院子里,把鸡窝搬到院子中的一个角落里,这样厅堂里就干净多了。隔不了几天,王秀梅就要去乡街上买菜。她有一辆电瓶车,骑着车子十几分钟就到了,很方便。田野里的庄稼大都收割完了,凉气嗖嗖地灌进衣服里,骑在车子上的王秀梅感觉到深秋的寒意。
有一天早上,王秀梅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却突然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男人,光着脑壳,穿了一条看上去许久未洗的灰色裤子,神色有异。见了王秀梅,他一只手抓着光脑壳,一只手指着屋门说,我进去找个人。王秀梅想也没想便说,你是找老胡吧,他还没有起床哩。男人摇了摇头,说我不找老胡。王秀梅奇怪了,屋里除了老胡和她,还有哪个?就在王秀梅惊讶之时,男人大步闯进屋去,王秀梅顾不得满手泡沫,跟着跑了进去。
当男人推开老胡的房门时,王秀梅看到秋菊正坐在老胡的床前跟老胡说话,她见了男人,并没有什么惊讶,而是皱眉道,你到这儿来做什么?男人低声说,秋珍刚过来了,还在家等着哩,说事情急,钱今天就要送过去。秋菊站起身,瞪了男人一眼说,走吧。秋菊快步上前,男人跟在后面,脚步吧嗒吧嗒响。王秀梅这才发现,男人竟然穿着一双拖鞋,脚后跟的死皮白花花一片。
秋菊什么时候进来的呢?王秀梅疑惑地问着自己,回转身看了看老胡,见他半躺在床头,神情疲倦。王秀梅不得不开口问他,秋菊找你做什么?
老胡眼里闪出一丝慌乱,说,没事,就是来坐坐。
没事就好。老胡不愿说,王秀梅也不好追问,老胡的私事她不好管。她缓缓走出房门,随手关上了。
中午,老胡在省城的儿子给王秀梅发来了视频通话,让老胡接。天气渐凉,王秀梅把摇椅垫上一床薄被,给老胡身上盖了一床毛毯。父子俩没说上几句话,老胡就把手机递给了王秀梅,老胡儿子说,王姨,别的话我也不说,我爸的事还要你多耐心点。王秀梅说,放心吧,你爸很好。老胡儿子说,我看得出来,我爸的脸色比以前好多了,精神也不错,当初医生的话……老胡儿子猛然打住,说王姨你忙吧,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挂了视频,王秀梅愣了会儿神,心里在想,老胡的儿媳呢,怎不一起和老胡说句话?外面阳光灿烂,晒在身上有细小的汗珠儿冒出,王秀梅这时想应该给老胡洗个澡。卫生间里有个大浴缸,这是儿子特地为老胡准备的,人老了站着洗不方便,躺身浴缸,那才叫安全又舒服。老胡本来懒得洗,经不住王秀梅的劝,答应了。水放好后,王秀梅先帮着他把外衣脱掉,然后扶着老胡走进浴室,王秀梅轻声问老胡,要不要她进去帮他洗。老胡身子哆嗦了一下,摇了摇头说他自己会。
王秀梅不敢做其他事,她坐在卫生间门外,关注着里面的动静。里面先是有点响动,后来很静,难道老胡在浴缸里睡着了?王秀梅不放心,喊老胡老胡,你没事吧。听见老胡在里面哼哼几声,王秀梅感觉有异,立马打开玻璃门,看见老胡坐在浴缸旁边的地上,见了王秀梅,想挣扎着爬起来。王秀梅喊道,老胡,你不要动,让我来。
地上的老胡光着身子像个瘦猴一样趴在那儿,双手遮住裆部,嘴里说,地太滑,不小心跌倒了。王秀梅问他痛不痛,老胡说,现在不痛了,没事。王秀梅抱起老胡的身子,再轻轻放进浴缸,大大地喘了口气。
老胡紧绷着身体,让王秀梅帮他擦身子时不好操作。王秀梅就说,老胡呀,你都八九十岁的人了,可以当我父亲了,我也是过来人,做陪护也不是第一次,经见的事儿可多了,没有必要害羞。老人么,就像一个小孩子,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放松下来,舒舒服服地享受吧。老胡虽听话地把双手放开,闭上眼睛,但身体还是放不开。王秀梅没再说什么,而是让一双手轻轻地在老胡身上游走、游走,渐渐地,老胡感觉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舒服感,索性摊开身子,任由王秀梅的双手揉搓着他的每一寸肌肤。没想到,让人给自己洗澡,还真是一种享受啊。
有了那次洗澡的体验,老胡反倒主动要求王秀梅给他洗。从此,老胡不再对王秀梅避讳什么,两人之间的话语自然就随便多了。但是,对于老胡和秋菊的关系,老胡始终没有打算告诉王秀梅,有一次他们谈起家庭,王秀梅提起秋菊的事,老胡赶紧避开了话题,王秀梅也很识趣,不再提起。
天气转凉,老胡的身体差,王秀梅给他提前准备好过冬的衣服。衣柜里较乱,新的旧的塞满了整个空间,弥漫着一股陈腐的气味,甚至角落里还留下了一些干硬的老鼠屎。王秀梅一边整理一边感叹,家里长久没个女人还真不行。她把一些旧的整理出来,让老胡决定是否弃用。当一条淡黄色丝巾出现时,王秀梅愣住了。这是新丝巾,折线清晰可见,还有股樟脑味。老胡显然也发现了,脸色霎时苍白。王秀梅赶紧上前扶住老胡,老胡不住喘着粗气,慢慢地拿起丝巾,然后闭上眼睛对着王秀梅说,扔了吧。
看着老胡痛苦的表情,王秀梅说,要不我还是放在原处吧。她心里清楚,这条丝巾有些年代了,不同寻常,里面肯定藏着不可言说的故事。
这时老胡一把抢过来,揉成一团,来到厨房下,啪的一下打着煤气灶,蓝色的火焰一下子把丝巾给烧着了,火光冲起来,几乎碰到了顶板。王秀梅的脸都吓白了,急忙去关火,又拿起湿抹布盖住了丝巾的火苗,瞪眼对老胡说,太危险了。老胡显然也没料到这种情况,他只是急于让这件旧物消失掉,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色乌黑。王秀梅返回身拉住老胡,手掌不住抚着老胡的胸口说,老胡你别激动,现在没事了。
王秀梅把老胡扶到厅堂中的摇椅上躺下来,低头认错道,老胡,是我不好,不该把那些东西翻出来。老胡双眼盯着屋顶上的瓦片,那里有一只大蜘蛛正在结网,半晌他才说,不关你的事,是我做错了事。两颗泪珠从左右脸颊旁滚落下来,接着一串串地冒出。王秀梅用纸巾帮他擦掉,劝道,老胡,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对也好,错也好,都没有意义了,重要的是过好现在的日子呀。
那时我真混蛋呀!老胡坐起身来,王秀梅给他倒了一杯水,心里期待着老胡把心里的故事讲出来。然而老胡喝过水,又躺了下来,仿佛累了,闭上眼睛,不再说话。王秀梅拉过毛毯盖住他的身子,轻手轻脚地走开了。
外面天气阴沉,这么个天气,又是下午三四点光景,村里很少有人走动,只有风把路上的纸屑吹得乱飞乱舞,王秀梅心里有点失落落的。
许久没回过家了,不知大风是不是把她的院门给吹开了?那年大雨,她不在家,正在县里给人做保姆,要不是发宝帮她屋子排水,恐怕房子就被大雨给冲倒了。想起发宝,王秀梅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黑脸汉子来,心里便安稳了许多,脸色却有点复杂。
男人在世的时候,王秀梅几乎没怎么干过重活粗活,男人身强体壮,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女人受累。那时,王秀梅的身体不好,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瘦得一根木棍似的。可是,那么强壮的男人竟然经不得一病,走时死死地拉着王秀梅的手,大家都知道,男人是多么担心女人今后的生活。好在那几年王秀梅硬是挺了过来,直到儿子上大学参加工作,才松了口气。
农村里,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哟。王秀梅不由感叹一声,走进屋去。
下了一场雨,老胡咳嗽得厉害,王秀梅说去看医生吧,老胡说不要紧,是老毛病。王秀梅给介绍人打电话,介绍人说她给李医师打电话,让他去看看。果然,不到半个小时,门外开进一辆白色小车,一个背着药箱的男人走了进来,王秀梅第一眼看到的便是男人半米长的胡子,乍一看,还以为是个雄健的老人,待看清了,才见男人最多也就五十岁的样子。王秀梅叫了一声李医师,男人点了点头,正眼瞧了一下王秀梅,问,你是——王秀梅赶紧作答,我是老胡请的陪护。
王秀梅给李医师泡茶的工夫,李医师就把老胡的病给看完了。接过王秀梅端过去的茶杯,他没喝,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从身边拿出一只不锈钢茶杯递给王秀梅说,是今天烧的开水么,给我来一杯,里面有茶叶。说着,走出老胡的房间,坐在厅堂里的八仙桌旁,开始写单子。王秀梅给茶杯倒好开水,轻声问,李医师,老胡的病要紧么?李医师没有说话,龙飞凤舞地写完单子,交给王秀梅,抚着长须说,老毛病,也没什么大碍,先吃几服中药吧。王秀梅抓着手上的单子,问,去你那儿拿药么?李医师笑笑说,你是新来的,还不了解吧,老胡这病我都给瞧了几年啦,我的诊所就在乡街上的便民药房旁边,一服要煎两次,趁热服下。李医师又从药箱中拿出两种丸药,说,这个先给老胡服下,每种一次两粒、一天两次,配合着治疗,见效快些。
李医师走出门时,王秀梅问,这诊疗费和医药费——李医师一只手拿着茶杯,一只手轻抚长须,说,老胡的儿子会结账的,你先不要管。
老胡接连服了几次药,加上药丸的作用,咳嗽基本上停止了,神情也好了许多。阴雨过后,天气真正有点寒冷了,而正午的太阳还算强劲,王秀梅把老胡的摇椅移到屋外的墙壁下,扶老胡晒太阳。转身之间,秋菊的身影进了院子,也不看王秀梅一眼,直接来到老胡身旁,问老胡身子好点儿没有。老胡的身子还没有躺下去,点点头说好多了。阳光温暖地照在老胡的脸上,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望了王秀梅一眼。王秀梅进屋搬出一把小竹椅给秋菊坐,自己则打扫着院内的卫生。
对于秋菊的到来和冷漠的表情,王秀梅也习以为常,这个女人和老胡之间的故事有点神秘,虽不想长舌妇般去打听,总觉得心头的疑团越缠越紧,有点儿难受。秋菊对她有敌意,让她感到好笑,自己一个陪护,难道对老胡还有什么想法?况且老胡身体不好,八九十岁的人,说不准哪天不好就走了,自己能得到他的财产么?隔着不远,王秀梅看到秋菊从身边拿出一张照片给老胡看,高兴地跟老胡说了一句话,脸上突然变得比阳光都灿烂。但老胡没有笑,只是紧瞅着照片,心情复杂地躺下身来,也说了句什么话。王秀梅听不清,秋菊听清了,笑容收起,站起身,走出院外。她没有回头,也没有看一眼正在忙碌的王秀梅。看情形,秋菊生老胡的气了。
老胡心里也有气,这点王秀梅看得出来。打扫完院内,王秀梅转进屋内,大花鸡忽地从鸡窝里飞下来,炫耀地咯咯叫着,王秀梅一看,鸡窝里刚下了一个鸡蛋。
那天王秀梅买菜回来,听到屋里传来争吵声,吓了一跳,疾步赶进去,却见秋菊从老胡的房间里出来,满脸怒气。她见了王秀梅,哼了一声,大声对里面的老胡说,我知道,你是想把钱留给你这个新相好的。王秀梅还没有明白过来,她就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待王秀梅明白过来时,不由愤怒起来,跑到屋门口,对着外面大声喊道,呸,你这个下贱女人,亏你说得出口!再进屋看老胡,见他气得浑身乱抖,不住地咳嗽。王秀梅赶紧扶着他坐在床沿上,又倒了一杯热水递给他,轻抚着他的胸口说,消消气,别气坏了身体。转眼看了一下房间,愣住了——房间的衣柜大开,箱子被掀翻,抽屉被拉开,到处散乱地丢着旧衣杂物,像遇上了小偷一般。王秀梅不相信地问,老胡,这是秋菊刚才做的事?老胡喝了一口热水,点了点头。
老胡,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事,秋菊这么无法无天?王秀梅再次发怒。
那是一场噩梦!老胡唉声叹气,而后双眼盯着天花板愣神。
见老胡半天没说,王秀梅也不再追问,慢慢地收拾着地上的东西,尽量做到物归原位,气也渐渐消了。有些事,她也经历过,还有些事,虽没经历,但也听到过看到过,里面的缠缠绕绕,是很难说清的,甚至分不清谁对谁错。
一整天,老胡的情绪非常低落,王秀梅的劝说反倒让他抹开了眼泪,一个男人,竟然哭了,这让王秀梅不知所措。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秋菊晚上竟然又来了。这一次,竟然还带着她的男人。王秀梅想要阻拦,显然没有这个能力。秋菊对身后的男人使了一个眼色,没想到男人竟然抓住王秀梅的胳膊,把她拉出了房门,然后男人又把门关上了。王秀梅大喊,你们这是想对老胡做什么?门开了一条缝,男人半张脸露出来,说,放心,我们不会对老胡怎么样,只是找他商量一下事,负他应该负的责任。
负责任?王秀梅问了一句,可男人不再理她,狠劲把门给关上了。王秀梅去推门,推不开,她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里面的动静,倒也安静,只隐约听到秋菊的说话声,没有先前的火气,倒也温和。
屋外的院子静悄悄的,老胡房间里的灯光从窗帘缝隙中挤出来,散淡淡的没有一点能量。发生这样的事情,王秀梅怕出意外,还是给介绍人打了电话。没想到介绍人却说,没事的,他们之间是有点复杂,你注意点儿就是了。王秀梅忍不住问道,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电话里面的人沉默半晌,叹了口气说,这些事,如今说给你听也不要紧,都过去很多年了,要不是秋菊的儿子结婚急着要买房,他们也不会这么急着逼老胡。
秋菊的儿子买房怎么能逼老胡呢,难道老胡欠她的钱?王秀梅惊讶地问。
其实,秋菊的儿子也是老胡的儿子。
王秀梅被介绍人给说糊涂了。
手机里面的声音说,你还不明白么,秋菊在四十岁前一直没有生育,后来才有了一个独生子,据说她的丈夫与老胡曾有过协议。本来这事早就了结了,没想到现在他们被儿子给逼急了,竟然转来逼老胡,看来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哟,谁叫老胡有些家底呢。按理说,老胡帮他们一把,也说得过去,明面上是他们的儿子,实际上村里的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儿子长得跟老胡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想瞒也瞒不住。
这么说来,老胡老婆的死肯定跟这件事有关啰?
是哟,当时老胡老婆的娘家还大闹了一场。
这个老胡,还真是个糊涂人哪,怎么去做这样一件荒唐事。
有些事也只有他们当事人最清楚,村人口中传出来的故事也都是各自的猜测和想象。老胡和他们之间的事情你注意一点儿就是了,只要老胡不受伤就可以了。说完,介绍人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老胡的情况我还隐瞒了一点,老胡的病是不治之症,据医生判断,他大概只有半年时间了。
外面的风很凉,王秀梅走出来,此时,她的脑子很乱。重回屋里,见老胡的房门打开,秋菊和她男人先后走了出来,她没有理睬王秀梅,后面的男人倒是望了王秀梅一眼,被秋菊推了一把,说,磨磨蹭蹭做什么,难道你这个老东西还想吃嫩豆腐?男人浑身一哆嗦,赶紧走出门去。王秀梅心里窝着火,可她并没有赶过去和秋菊争辩,而是急忙来到老胡的房中。还好,老胡半躺在被窝里,脸上看不出悲喜,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异常。
王秀梅问,没什么事吧。
老胡点了点头,眼神复杂,不住咳嗽起来。
王秀梅坐在老胡的床边,不住地轻拍他的后背,又给他端来一杯热水,用勺子喂下。老胡的眼里涌出了泪,王秀梅给他擦掉,轻声说,老胡,不要想多了,千事万事,都没有身体要紧,该放开的就放开,只要活得轻松就可以了。老胡这时伸出手,似乎是想握着什么,想了想,又放进了被窝。
秋菊又来过几次,倒与老胡没什么争吵,王秀梅估计,是老胡妥协了。对于老胡和秋菊的故事,王秀梅心头渐渐也理出了一个头绪,但对秋菊那种带有敌意的目光,王秀梅还是感到不满。自己只是老胡儿子请来的陪护或者说叫保姆,又不和她争老胡什么东西,并不妨碍她和老胡的关系,对她为何有如此敌视?王秀梅向来是与人为善,她不想和秋菊发生什么矛盾,哪怕是她已经把她当成了敌人。
难得天气晴朗起来,趁着中午暖和,王秀梅给老胡洗了个澡,把身净气爽的老胡搀扶到墙壁下的向阳处晒太阳。王秀梅走出院门,一直走到了秋菊的屋门前。门前有一条大黄狗吠叫,秋菊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见了王秀梅,惊愕地问,你这是——
王秀梅向屋里瞄了一眼,果然看见秋菊窜了出来。见是王秀梅,她不觉一愣,说,你来得正好,我也有事正要找你。
这下王秀梅倒有些惊讶了,秋菊找她干什么,她可是个局外人。
秋菊转头对男人说,还不快让人家进屋坐。
男人拉过一条木凳,王秀梅没有坐,而是打量起屋子。屋子虽是个楼房,可修建的时间有点久,四周墙面斑驳陆离,几乎看不清是白是灰。看样子,秋菊家里确实困难,怪不得她要找老胡了。秋菊又把王秀梅打量了一番,说,你这人做事倒还可以,总不会除了老胡家就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了吧。
此话怎讲?王秀梅有些恼怒,这不是明摆着要她离开老胡家嘛,自己又不是她请来的,她有什么权利说这话。
你就不能辞职吗?秋菊咄咄逼人的样子让王秀梅感觉到好笑。辞职?她可是老胡儿子请来的,还签了用工合同的,自己又没什么过错,干吗主动辞职呢?
见王秀梅没有半点迁就的意思,秋菊的声音忽然软和下来。
你辞职吧,我现在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王秀梅大笑起来,转头又看了看男人,对他说,大哥,嫂子要去给老胡做陪护,你说好还是不好。
男人噌的一下站直了身子,脸色憋得通红,正要回答王秀梅,可这时秋菊也转过身来,狠盯了男人一眼,男人立马坐下来,把头低下,不敢发出一言。
王秀梅笑着走到秋菊身边,说,嫂子,我叫你一声嫂子是尊重你,我问一下你,如果我不干这个陪护,老胡的儿子会请你吗?你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对我如此敌意,我得罪了你什么,和你争过什么利益?你和老胡的恩怨我根本不想知道,更不想掺和,我只是一个陪护,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嫂子,你难道就不想让老胡过得安心一些?难道就不想让老胡多活些日子?
屋子里一片寂静。
王秀梅大步走出门,正午的阳光,让她浑身燥热得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