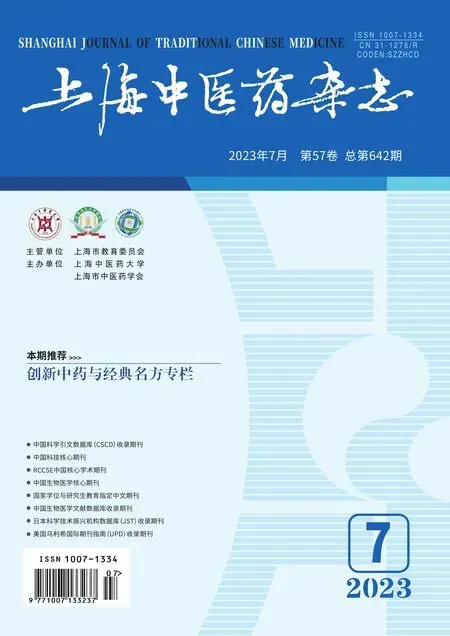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从络论治体会
薛纯纯,谢 磊,李晓锋,黄爱苹,谷 桢,孔舒祎,温馨林,李亚南,蒉文筠,王开强
1.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疼痛科(上海 200071);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骨伤科(上海 200071);3.施杞名中医传承工作室(上海 200071)
带状疱疹后神经痛(postherpetic neuralgia,PHN)为带状疱疹皮疹愈合后持续1个月及以上的疼痛,可表现为阵发性或持续性火烧样、针刺样、闪电样、刀割样疼痛以及麻木等多种形式,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活动及生活质量[1-3]。PHN 属于顽固性神经痛,尤其是年老体弱患者容易遗留后遗症,其皮疹虽然已消退,但疼痛仍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造成极大的痛苦。近30年来,我们通过不断的探索及实践,临床上采用从络论治的方法辨治PHN,收效显著。现将相关认识及临证体会总结如下。
1 中医命名
中医医籍中有关带状疱疹的描述最早见于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甄带疮者,绕腰生,此亦风湿搏血气所生,状如甄带,因以为名。”其将带状疱疹命名为“甄带疮”,其后历代医家还将带状疱疹称为“蛇串疮”“缠腰火丹”“蛇丹”等,但少见有关PHN 的记载。清代祁坤《外科大成·诸疮痛痒》载:“桑皮饮治皮肤痛不可以手按者……槐花散治皮肤痛,虽苍蝇飞上即痛者。”文中所述的“皮肤痛不可以手按”和“虽苍蝇飞上即痛”与PHN 特有的疼痛形式(触诱发性疼痛)非常一致,但并未将其定名。直到2006 年,河南中医学院牛德兴等发表论文《“蛇丹痛”说》[4],文中提出带状疱疹一病,根据中医历代医书记载称为“蛇丹”,而患蛇丹病在水疱结痂后疼痛持续超过1 个月者应定义为“蛇丹痛”。该中医命名虽然比较确切,但至今未被临床广泛应用。
2 PHN的络病内涵
络的定义始于《黄帝内经》。《灵枢·脉度》载:“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其认为络脉是由经脉分支横出、逐级分层,形成不计其数的细支,名为孙络。清代《医门法律·络病论》载:“十二经生十二络,十二络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络,缠络生三万四千孙络。自内而生出者,愈多则愈小,亦以络脉缠绊之也。”说明不同级别的络脉纵横交错,从大到小逐级细分,从而形成三维立体网络。随后通过医家不断的完善及发展,最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教授系统提出了“络病学说”,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络病并非一个独立的病种,而是广泛存在于多种内伤疑难杂病和外感重症中的病机状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致病因素伤及络脉所致的络脉功能及其结构损伤的自身病变[5]。
2.1 PHN 发病部位与络病相符 PHN 主要是由于前期脑神经或者脊神经感染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病毒活化复制导致相应神经支配区的神经损伤,随着病程的发展皮疹虽然逐渐消退,但神经损伤并未修复。《难经·二十八难》载:“其脊中生髓,上至于脑,下至尾骶,其两旁附肋骨,每节两向皆有细络一道,内连腹中,与心肺系,五脏通。”书中所述的细络意指从脑髓发出的脑神经及脊髓发出的脊神经,大脑和脊髓中枢发出各级神经形成遍布全身的网络神经系统,联络全身肌肤官窍,与呈网状分布的络脉系统相吻合[6]。也就是说从解剖学的角度,PHN 的发生部位与络相符合。现代大多数医家认为将PHN归属于“络病”范畴更为确切[7-9]。
2.2 PHN 病程与络病病程相似 PHN 病程较长,短则几个月,长则1~2 年甚至10 余年,病势缠绵,迁延难愈。《素问·百病始生》曰:“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在络之时,痛于肌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着孙脉,或着络脉。”疾病的发展过程一般由经到络、由气至血、由浅至深,而络脉是疾病的传变途径。另外,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认为“经年宿病,病必在络”。就病程而言,PHN 符合络病病程持久(久病入络)的特点。
2.3 PHN 临床表现与络病病机相应 PHN 疼痛形式多样,可表现为触诱发性疼痛(如皮肤摩擦痛)、自发性疼痛、火烧样疼痛、针刺样疼痛,以及皮肤烧灼感及麻木等。可以是一种疼痛,亦可多种疼痛形式并存。经脉为气血运行的通道,络脉从经脉支横而出,逐级细分,使得经脉中线性运行的气血流速逐渐减缓直至面性弥散渗灌至纵横交错的络脉,并在络脉的末端与脏腑组织相连,形成津血互换和营养代谢的场所[5]。络脉细小,络中气血运行缓慢,若邪留络脉,影响络中气血的输布环流(渗灌),易致瘀滞状态;另一方面,络脉的末端分支细小迂回,一旦邪气入络,则难以祛除,所谓“至虚之处,便是留邪之地”。络脉的特殊结构导致病邪具有易入难出及易虚易瘀的特点,PHN 不同的病机变化可以出现不同形式的疼痛,具体如下。
(1)火烧样疼痛。不同于急性带状疱疹的疼痛剧烈,火烧样疼痛以自觉烧灼样疼痛为主,往往呈阵发性发作,多因早期感染湿热毒邪,经治疗后湿去热存,余毒未清,郁久化热,燔灼肌表之孙络、浮络,从而引发络脉壅滞之疼痛如火燎。
(2)触诱发性疼痛。PHN 特有的皮肤或者衣物摩擦痛,多因结聚迟留不得发越,经络阻塞。若大量密集分散的孙络、浮络等屈曲蜷缩或拘急牵引,则遇轻微刺激便可产生阵发性的疼痛。
(3)针刺样疼痛。急性带状疱疹和PHN 均常见针刺样疼痛,其病机多为毒损络脉,气血运行缓慢,血行涩滞,脉络瘀阻而发。毒邪侵入十五别络、孙络、浮络,可破坏神经细胞,使其发炎、出血、坏死,进而导致络脉由滞到瘀,甚至不通,不通则痛。该类疼痛迁延缠绵,可贯穿于急性带状疱疹到PHN阶段。
(4)自发性疼痛。自发性疼痛多见于老年人或体弱者,其平素如常人,但又会出现阵发性疼痛,实则为卒然不通则痛,为络脉绌急,即屈曲拘急;多因久病不愈,气血虚衰,脉络失养,导致细小以万亿数计的孙络、浮络被破坏,同时一些毒邪的残余滞留不行,使得孙络、浮络处于绌急状态。
(5)牵扯性疼痛。多为湿热毒邪稽留不去,余毒未清,日久化热伤阴,阴血不足,脉络拘急,“小络急引故痛”(《素问·举痛论》)。
(6)疼痛及麻木并行。多为感受湿热毒邪,稽留不去,日久化火,伤及络脉,产生疼痛;或日久余毒未清,瘀阻络脉,导致气血运行失司,络脉失养,故疼痛、麻木不仁。
(7)瘙痒。部分PHN以瘙痒为主要表现,多由湿热毒邪损伤浮络、孙络所致,但此时的湿热毒邪均已衰减,且局限在患处,不波及全身。正如《素问》所云:“热甚则痛,热微则痒。”《诸病源候论》亦云:“风入腠理,与血气相搏,而俱往来,在于皮肤之间。邪气微,不能冲击为痛,故但瘙痒也。”
3 三期辨证,从络论治
PHN 患者经过前期的治疗,湿热毒邪基本消除,但疼痛仍顽固存在,主要原因为余毒未清,稽留络脉,络脉损伤日久不能修复,导致疼痛缠绵难愈。PHN 的病机关键为毒损络脉,络损不复。《临证指南医案·诸痛》曰:“然其独得之奇,尤在乎治络一法。盖久痛必入于络,络中气血虚实寒热,稍有留邪,皆能致痛,此乃古人所未言及。”因此治疗PHN 的关键在于以“通”为用,通畅络脉,使气血运行无碍。所谓“通”者,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使得气血流通,从而将络脉的损伤降低到最低程度。我们按照疾病发展过程将PHN分为三期。初期:毒损络脉,病程在1~3 个月;中期:络脉瘀阻,病程在3~6 个月;晚期:络虚不复,病程一般在6个月以上。
3.1 初期毒损络脉:予清毒舒络方以清热解毒,舒络止痛 带状疱疹皮损痊愈后疼痛持续1~3个月,这个时间窗对于治疗而言至关重要,需及时控制疼痛,以将络脉的损伤程度降到最低。该阶段络脉已损伤,湿热余毒未清,部分孙络及浮络可能还滞留残余毒邪,邪正交争,气血运行失畅,络脉绌急。余毒不除,则络脉的损伤就会继续加重,故宜以清除余毒为主。
初期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局部皮损色红,阵发性或者持续性针刺样疼痛,自觉皮肤灼热,时有麻木;伴心烦易怒,失眠,口苦咽干;大便干结或正常,小便黄;舌红、苔黄或腻,脉弦滑。治宜清热解毒、舒络止痛,予自拟清毒舒络方加减。
方药:羌活18 g,防风9 g,大青叶15 g,栀子9 g,泽兰9 g,酒大黄3~6 g,当归9 g,丝瓜络12 g,忍冬藤15 g。方中羌活、防风取自九味羌活汤,解表祛风胜湿。大青叶、栀子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现代研究[10]发现,大青叶可促进T 淋巴细胞活化,增强免疫功能。栀子入血分,既能清血分之热,又出于气分而清气分之热,气血两清。泽兰入肝、脾二经,辛散温通,不寒不燥,性较温和,行而不峻,能疏肝气而通经脉,具有祛瘀散结而不伤正气的特点。当归养血活血化瘀,又无破血药之峻烈,正是护络良品。酒大黄泄热除滞,兼活血祛瘀。丝瓜络既可清解余毒,又可通络止痛。
3.2 中期络脉瘀阻:予活血通络方以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经过前期邪正交争,余毒逐渐消退,但是络中气血因络脉的不断受损而运行受阻,发为气滞血瘀,导致络脉瘀阻。此证候在PHN 患者中最为多见,治疗时以化瘀通络为重点,以恢复络脉的气血运行。
中期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局部皮损色晦暗或黧黑,自觉阵发性刺痛或刀割样疼痛,疼痛位置固定不移,夜间较白天明显,伴或不伴有局部皮肤烧灼痛;入眠困难,饮食正常或食欲不佳;大便少,小便可;舌暗红,舌面多见瘀点或瘀斑,舌苔多薄白或腻,脉弦涩或细涩。治宜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佐以解郁安神,予活血通络方(以桃红四物汤为基础)加减。
方药:桃仁9 g,红花6 g,川芎9 g,当归9 g,白芍9 g,生地黄9 g,鸡血藤15 g,三棱10 g,莪术10 g,虎杖15 g,合欢皮30 g,首乌藤30 g,全蝎3 g,蜈蚣3 g。桃红四物汤养血活血、祛瘀生新、通络止痛,是叶天士“辛润通络”法治疗络病的具体体现。三棱、莪术破血祛瘀、行气止痛,两药合用,散一切血瘀气结。鸡血藤不仅养血活血、化瘀通络,配合当归还可以达到祛瘀生新的功效,共同修复受损的络脉。虎杖清热解毒、散瘀止痛,合欢皮、首乌藤疏肝解郁安神、活络止痛,全蝎、蜈蚣搜风通络止痛。诸药合用,共奏养血活血、行血化瘀、通络止痛、解郁安神之功。现代研究[11]表明,桃红四物汤具有调节免疫作用,可促进机体血液循环、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
3.3 晚期络虚不复:予补虚护络方以益气养阴,护络止痛 PHN 络脉瘀阻日久,气血运行受阻,致络脉失养而虚损;且患者经过慢性疼痛的伤害,耗伤气血,气血亏虚,络脉失养更甚,加重络虚。此证候多见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及素体虚弱者,病程多在6个月以上。治疗时应重视益气养血,慎用辛温燥烈、破血化瘀药物,以免伤正,加重络虚。
晚期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局部隐隐作痛,不可名状;伴坐卧不安,倦怠乏力,夜不能寐;大便不调,小便可;舌淡暗、苔薄白或少,脉涩无力。治宜益气养血、滋阴通络、祛风止痛,予自拟补虚护络方(以圣愈汤合芍药甘草汤为基础)加减。
方药:黄芪15~30 g,党参9 g,川芎12 g,当归9 g,熟地黄9 g,白芍30 g,甘草6 g,柴胡9 g,白术12 g,茯苓12 g。方中圣愈汤益气养血以补络脉之虚,黄芪、党参、白术甘温通络,川芎、熟地黄、当归辛润通络,柴胡调畅络脉之气机,白术、茯苓顾护脾胃,芍药甘草汤缓急止痛。诸药合用,益气养血以纠正络虚,滋阴养血以通络止痛。
4 常用止痛药对及引经药
4.1 止痛药对 针对PHN,我们在前述三期辨证、从络论治的基础上,根据患者疼痛的主要表现形式进行加减用药,主要以药对为主。①火烧样疼痛加水牛角和生地黄,二者为犀角地黄汤的主药,可加强清热解毒凉血作用,其中水牛角用量为30 g。②针刺样疼痛加失笑散(由生蒲黄与五灵脂组成)。《本草纲目》载:“失笑散,不独治妇人心痛血痛;凡男女老幼,一切心腹胁肋、少腹痛、疝气并胎前产后,血气作痛,及血崩经溢,百药不效者,俱能奏功。屡用屡验,真近世神方也。”③触诱发性疼痛部位多在胸腹部,加金铃子散(由延胡索与川楝子组成)。金铃子散出自《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具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功效。④刀割样疼痛加乳香、没药。乳香善透窍以理气,没药善化瘀以理血;对于疼痛部位在胁腹、躯干、四肢者,均可用其行气活血止痛。⑤自发性疼痛加熟附片和鹿角片,以通阳益元,阳气畅达则可恢复络脉出入自由、充盈满溢的状态[12]。⑥牵扯性疼痛加木瓜和伸筋草。⑦电击样疼痛多为肝风内动,加天麻和钩藤。
4.2 引经药 PHN 在胸胁部者,加柴胡3~6 g、桔梗3~6 g。《本草崇原》载:“桔梗,治少阳之胁痛。”《神农本草经》载桔梗“主胸胁痛如刀刺”。现代药理研究[13]结果显示,桔梗有抗炎镇痛、提高免疫力等作用。头部疼痛者,加升麻;颈项部疼痛者,加羌活、葛根;腰腹部疼痛者,加狗脊、杜仲;下肢疼痛者,加怀牛膝;上肢疼痛者,加桑枝。
5 刺络放血的应用及体会
PHN 经中药口服治疗后仍有部分患者效果欠佳,主要原因有两点:①络脉细小,用药力弱则不达,而攻伐太过又易伤脾胃,造成用药两难;②PHN 患者多年事较高或者年老体弱,其络脉易损难复,部分患者难以耐受长期用药。相较于内服药,外治法可减少服药之苦,也可减少药物对脾胃的刺激。《临证指南医案》载:“至虚之处,便是留邪之地。”对PHN患者而言,其细小以万亿数计的孙络、浮络被破坏,而且还滞留有残余毒邪,导致其不能行使网络循环的作用。而通过放血的方法,可使毒邪外出,新血再生,带来新的营养物质。一般而言,经过放血原来的主痛点会变为次痛点,但也会出现新的主痛点,此时宜根据以痛为腧的原则继续采用刺络放血疗法。通过临床观察发现,一般情况下经过2~3次的刺络放血,可基本上解决局部疼痛。
刺络放血止痛的方法最早散见于《黄帝内经》。如《素问·诊要经终论》载:“夏刺络俞,见血而止,尽气闭环,痛病必下。”《素问·血志形气》载:“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泻有余,补不足。”《灵枢·寿夭刚柔》载:“久病不去身者,视其血络,尽出其血。”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有更加具体的描述:“久病在络,气血皆窒……邪与气血两凝,结聚络脉……久病必治络,谓病久气血推行不利,血络之中必有瘀凝。”刺络放血是直接针刺病变处皮肤络脉使其出血,令邪毒随之外泄,继以拔罐使邪毒消散殆尽,则疼痛可止。刺血疗法可有效改善皮损部位神经末梢周围的血液循环,促进局部代谢产物及炎症因子的有效排出,进而使受损神经末梢得到必要的氧供,提高神经修复能力[14]。
6 结语
目前临床对于PHN 多从肝论治[15-16],抑或从六经辨证论治[17]。PHN 疼痛难治且缠绵,与络病的“久痛入络”和“久病入络”相似;另一方面,神经的节、根、干及末梢神经逐级分支遍布全身与全身络脉由大到小逐级细分网络相似;PHN 因感染病毒致感觉神经损伤出现受损神经支配区域的疼痛及感觉异常,因此病位在络脉。我们根据PHN的发病特点,从络的角度论治,遣方用药以通络为主,主张以叶天士提出的治络当以辛温通络、辛润通络、辛甘通补、解毒通络为法则,局部疼痛顽固者可联合刺络放血。
需要强调的是,治疗PHN的方法并非孤立应用,临证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可以一种治疗方法单用,也可针药组合应用。对于治疗时间超过3个月疼痛仍控制不佳的患者,也可以联合应用现代医学的微创治疗方法(如神经阻滞或射频消融等神经靶向性治疗),以尽早减轻患者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