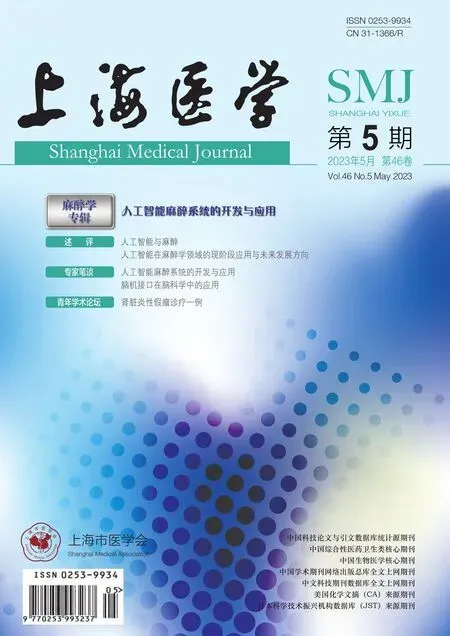肝脏自然杀伤细胞与肝损伤研究进展
吴宇泠 王宝珊 胡 晶 鄢和新 杨立群
肝脏是人体腹腔内较为独特的器官,可同时接受动脉血和静脉血的双重供应,其中门静脉来源的静脉血是供给肝脏的主要来源,经肝动脉进入肝脏的动脉血仅是一小部分。门静脉血不仅富含肠道吸收的营养物质,也含有由损伤的肠黏膜上皮细胞转移而来的病原体及其衍生物,肝脏必须耐受这些潜在的免疫原性物质,同时保持对病原体和恶性肿瘤的持续免疫监视。因此,肝脏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免疫学特性的免疫器官[1]。同时,肝脏也是一个固有免疫占据优势的器官,固有免疫细胞数目远远高于适应性免疫细胞。作为肝内固有免疫占比最高的细胞,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在清除细菌、病毒和癌细胞以维持肝内稳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
慢性肝病是全球主要的疾病负担之一,每年导致200万人死亡。慢性肝病的潜在病因包括病毒、酒精、代谢、自身免疫和遗传等因素。器官纤维化则是慢性炎症疾病进展的特征,占全球全因死亡率的45%。肝纤维化是以细胞外基质的过度产生和基质降解障碍为特征的病理过程[3]。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细胞损伤、死亡为肝纤维化提供了信号,其释放的细胞碎片和内容物,以及免疫细胞的浸润激活了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HSC)并诱导其增殖、分化、产生过量的纤维蛋白原和细胞外基质[4]。肝纤维化的进展决定了慢性肝病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若不给予有效治疗,将进展为肝硬化及肝细胞癌。在目前临床实践中,肝部分切除术和肝移植手术是肝癌及肝硬化等终末期肝病患者的有效治疗手段,但围手术期肝损伤[术中缺血再灌注损伤(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IRI)和术后移植物免疫反应等]影响着患者的预后。随着对肝纤维化和围手术期肝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的深入了解,研究[5]发现固有免疫在两者进展中起着关键调节作用。本文将总结固有免疫细胞中的NK细胞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过程和肝移植手术围手术期IRI,以及术后移植物免疫反应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
1 正常肝脏与NK细胞
NK细胞最初被定义为对肿瘤细胞具有天然细胞毒性的大颗粒淋巴细胞,来源于骨髓淋巴样干细胞,是机体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组分之一,在人体的大部分器官中均有分布[6]。NK细胞在人体中起到免疫防御与免疫监视的作用,不仅可以通过细胞毒性发挥杀伤能力,同时具有产生细胞因子的效应功能。NK细胞可以通过直接释放穿孔素、颗粒酶、颗粒溶素等裂解颗粒诱导细胞死亡,其表面表达的TNF超家族成员(如FasL和TRAIL)分别与其相应受体(Fas和TRAILR)结合,诱导细胞凋亡。NK细胞表面表达一些抑制性受体和激活性受体,这些受体可与靶细胞表面的相应配体结合传递抑制或活化的信号,而这两种信号之间的动态平衡调控着NK细胞的活性。抑制性受体可以识别各种形式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Ⅰ分子。靶细胞上MHC-Ⅰ分子表达水平下降或缺失可减弱传递给NK细胞的抑制信号强度,从而促进NK细胞的活化。此外,NK细胞还可通过其表达的IgG Fc段受体Ⅲ(FcγRⅢ,即CD16)与抗体Fc段结合,介导抗体依赖性的细胞毒性作用,以杀伤靶细胞。人常规NK细胞可根据其标志物CD56的表达水平分为CD56dim(即CD56低表达)和CD56bright(即CD56高表达)两个亚群[7]。不同亚群具有独特功能属性,在免疫反应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同。CD56dimNK细胞亚群相较于CD56bright亚群的细胞毒性更强,其FcγRⅢ的表达水平更高;而CD56bright细胞亚群分泌细胞因子的能力更强。NK细胞也可根据CD27与CD11b的表达分为不同亚群,CD27-CD11b+NK细胞更为成熟且呈现出更高的细胞毒性[8]。
NK细胞在肝内淋巴细胞中的占比显著高于其在其他脏器和组织中的比例。人血液循环中NK细胞在淋巴细胞中的占比大约为5%~15%,而肝脏中NK细胞在淋巴细胞中的占比高达50%。人类肝脏中不仅有通过血液循环迁移而来的常规循环自然杀伤(conventional circulating natural killer,cNK)细胞,也有特殊的肝脏驻留自然杀伤(liver-resident NK,LrNK)细胞。LrNK细胞首次在大鼠肝脏电子显微镜(简称电镜)检查中被发现,并被定义为Pit细胞[9]。后续的研究[10]结果表明,LrNK细胞是驻留于肝血窦中的高细胞毒性的NK细胞。血液循环中CD56brightNK细胞亚群占比较低,肝脏中CD56brightNK细胞占比与CD56dimNK细胞相当,同时CD56brightNK细胞群高表达组织驻留与活化标志物CD69、趋化因子受体(chemokine receptor,CCR)5和趋化因子CXC亚家族受体(CXCR)6,其中CCR可与肝血窦内皮细胞上的相应配体结合,从而选择性定位于肝血窦中。目前,主要通过转录因子Tbet和Eomes的表达水平来区分cNK和LrNK,EomeshiTbetlo(即Eomes高表达,T-bet低表达)LrNK细胞亚群占人NK细胞的50%,cNK则不表达Eomes而高表达Tbet。肝脏NK细胞的异质性及相对丰富性提示其在肝脏免疫微环境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这群细胞有助于了解其在肝脏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11]。
2 肝纤维化与NK细胞
肝脏具有高度再生能力,肝脏受到损伤后,可以通过再生恢复肝细胞数量和功能。然而,持续的慢性损伤导致肝细胞反复受损,再生功能发生障碍,致使瘢痕形成和纤维化。肝纤维化的病理特征是细胞外基质的过度沉积。持续的损伤因素刺激肝细胞和肝巨噬细胞(Kupffer细胞)等非实质细胞释放大量促炎因子,激活静息态的HSC,HSC进而转化为具有增殖性和成纤维性的肌成纤维细胞,产生大量纤维蛋白原和细胞外基质,导致肝纤维化的发生。因此,HSC一直是肝纤维化研究的重点。近年来的研究[12]结果表明,NK细胞有着抗纤维化作用。研究者对不同类型免疫缺陷小鼠进行慢性肝纤维化诱导发现,缺乏T、B、NK细胞的SCID BEIGE小鼠[即重度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小鼠与NK细胞缺陷(BEIGE)小鼠杂交的小鼠]相较于缺乏T、B淋巴细胞的SCID小鼠肝纤维化程度更高,且SCID BEIGE小鼠肝脏IFN-γ水平也明显下降,提示NK细胞具有抗纤维化的作用[13]。临床上,丙型肝炎(简称丙肝)患者尤其是纤维化晚期阶段患者的NK细胞出现功能及表型缺陷导致其活性下降,为丙肝病毒逃避NK细胞监视提供基础,且NK细胞功能与自身肝硬化程度呈负相关[14]。
NK细胞拮抗纤维化的具体作用机制主要与其表面活化性受体及抑制性受体传递的活化或抑制信号的变化相关。静息态HSC在肝内主要负责摄取、储存和释放视黄酸,纤维化早期活化的HSC(activated HSC,aHSC)产生更多的视黄酸,进而促进其表面NK细胞活化性受体杀伤细胞凝集素样受体亚家族K成员1(killercell lectinlike receptor subfamily K1,KLRK1)即NKG2D的配体视黄酸早期诱导基因-1(retinoic acid early inducible gene 1,RAE-1)的表达上调[15]。另有研究[16]结果表明,aHSC表面同时表达NK细胞另一活化性受体天然细胞毒性触发受体(natural cytotoxicity triggering receptor 1,NCR1)NKp46/NCR1的配体,NK细胞也可通过NKp46介导的细胞毒作用杀伤aHSC。除了NK细胞激活信号传递增加,抑制信号的减少更提高了NK细胞的活化程度。HSC在损伤信号刺激下,不仅活化性受体的配体表达上调,且抑制性受体配体MHC-Ⅰ表达下调,传递给NK细胞的抑制信号减少,杀伤能力进一步提升。体内、外实验结果均表明,siRNA敲低NK细胞的抑制性受体后,增强了其对HSC的杀伤能力并改善纤维化[17]。NK细胞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杀伤HSC来改善纤维化,其分泌的效应分子IFN-γ也可以通过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1依赖的方式抑制HSC增殖和诱导其凋亡干预纤维化进程[18]。尽管IFN-γ在小鼠肝纤维化模型中可显著改善肝纤维化,临床试验[19]结果表明IFN-γ疗法在乙型肝炎和丙肝患者中的疗效有限且肝病晚期患者并不能从中获益。HSC在肝纤维化过程中可以合成大量TGF-β,TGF-β是肝纤维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促纤维化因子,其可通过下调NKG2D的表达来抑制NK细胞的杀伤功能。体外HSC和NK细胞共培养实验提示,离体培养4 d(早期活化)的HSC可以通过NKG2D-RAE1机制促进NK细胞活化,而这一激活效果在离体培养8 d(中期活化)的HSC中明显下降,其原因在于离体培养8 d的HSC合成的TGF-β显著增多,抑制了HSC的激活。此外,NK细胞STAT依赖的IFN-γ的分泌也受到了干扰,活化HSC视黄醇代谢的增加激活了细胞因子信号传送阻抑物(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SOCS1),进而抑制了STAT1活性影响IFN-γ的分泌[20]。上述研究提示了NK细胞的抗纤维化作用集中在纤维化早期,随着疾病进展其抗纤维化作用受到抑制,IFN-γ治疗进展期肝纤维化的临床试验收效甚微的原因或在于此。
NK细胞对HSC细胞的作用可以作为治疗肝纤维化的潜在靶点,NK细胞活性的提升虽能杀伤HSC,但其对肝实质细胞的损伤也不能忽视。肝细胞本身也表达NK细胞活化性受体的配体,如FasL、MICA/MICB和B7-H6,爆发性病毒性肝炎中,NK细胞的活化反而会通过Fas/FasL、NKG2D/NKG2D配体方式损伤肝细胞,造成更严重的肝实质细胞炎性坏死,反而有利于病毒的持续存在[21-23]。以NK细胞为基础的疗法仍需更多的体内研究验证其安全性及可靠性。
3 围手术期肝脏损伤与NK细胞
3.1 肝IRI 肝IRI是肝部分切除术和肝移植手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病理生理过程,主要分为缺血期缺氧诱导的细胞损伤和再灌注后免疫炎症反应两个阶段。肝缺血使肝细胞缺氧、ATP耗竭、pH值变化,以及代谢应激而导致肝细胞损伤或死亡。再灌注后,肝脏代谢受到进一步干扰并诱发相关的炎症级联反应,导致细胞损伤加重。肝脏IRI可分为热缺血和冷缺血两种类型。热IRI主要与肝切除术、出血性休克、外伤、心脏骤停或肝窦阻塞综合征所致的肝组织血管闭塞相关。冷IRI则主要发生在肝移植手术中,供肝在移植到患者体内前保存于低温缺氧的环境中[24]。
肝脏缺血1 h、再灌注2 h后,肝实质中NK细胞浸润增多;而NK细胞清除后,肝脏CXCL-2表达显著下调,中性粒细胞浸润减少,肝脏IRI程度减轻[25]。肝移植模型中,同种异体移植物的NKG2D基因表达水平显著增高,提示NK细胞活化,而抗去唾液酸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预处理供体清除其NK细胞后,NKG2D表达水平下调时肝内细胞因子(TNF-α、IL-1β、IL-6和IL-8)和NK细胞分泌的效应分子(穿孔素、颗粒酶B)水平也均下降,早期中性粒细胞浸润亦随之减少[26]。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NK细胞在冷IRI和热IRI中均起到重要作用,损伤发生后NK细胞通过募集进入肝脏,活化并激活炎症反应的同时分泌炎症因子及效应分子,从而加重肝脏的IRI程度[27-28]。肝脏IRI的严重程度与肝移植患者早期同种异体移植物功能障碍(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直接相关,可降低移植物短期存活率[29]。
3.2 移植后免疫排斥与免疫耐受 NK细胞与免疫介导的同种异体移植物损伤有关,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NK细胞也可能促进同种异体移植物的免疫耐受性[30]。肝移植早期阶段,供体来源的LrNK细胞和cNK细胞同时进入受体的血液循环中,其中EomeshiLrNK细胞较为长寿,其可在移植物中停留长达十余年;而供体来源的EomeslocNK细胞则是停留在受体的血液循环中,移植数年后几乎无法在血液中再检测出这群NK细胞[31]。EomeshiLrNK细胞表面抑制性受体的表达水平较低,且分泌的穿孔素和颗粒酶B水平较低,呈低细胞毒性;EomeslocNK细胞则相反,其高细胞毒性表现使其在进入受体血液循环后首先攻击受体肝脏内浸润的淋巴细胞,导致早期异体移植物排异反应;EomeshiLrNK则由于其长寿特性得以长期停留在受体肝脏中,有助于肝脏产生更耐受的环境[31]。临床研究[32]显示,接受骨髓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回输的肝移植患者体内供体来源的NK细胞增多,促进了免疫耐受环境的建立。受体本身的NK细胞在移植后数小时内就进入移植物中,但其具体介导免疫排异还是免疫耐受反应仍存争议,还需进一步的体内实验明确其表型变化及响应移植后机体生理变化的机制。这将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如何靶向调控NK细胞以调节移植后的免疫反应。
4 总结与展望
慢性肝损伤导致的肝纤维化是慢性肝脏疾病的共同病理过程,也是慢性肝病向肝硬化进展的必经之路。有效的病因治疗可以减轻甚至逆转肝纤维化,但特殊原因(如自身免疫因素、代谢因素等)导致的慢性肝病仍缺乏可行的抗纤维化治疗方法。进展至肝硬化或肝癌的终末期慢性肝病患者的治疗手段则更为缺乏。肝部分切除术和肝移植等手术治疗是目前最为有效的方法。然而,基于慢性肝病的肝脏手术还面临着围手术期肝脏损伤与术后移植物免疫反应的巨大挑战。NK细胞作为肝脏淋巴细胞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慢性肝病患者疾病进展阶段还是肝脏手术的术中和术后阶段均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免疫疗法的兴起,NK细胞在慢性肝病及肝移植围手术期的作用更不容忽视。NK细胞在肝脏中的特殊亚群及其在纤维化、IRI、移植物免疫反应中的作用及其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以NK细胞为靶点,尤其是其在肝脏中的特殊亚群,或许能为不同阶段的慢性肝病患者提供新的疗法和个性化治疗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