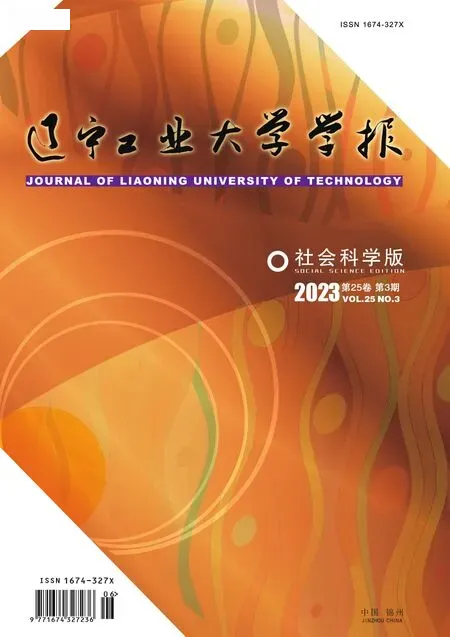女性自我的不断追寻
——《觉醒》的二元对立解读
叶小军,瞿小月,谢庆庆,潘璇
(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部,安徽 安庆 246052)
结构主义批评理论是文学批评方式之一,在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中,文学批评的中心不再是作者生平、作品的时代背景,不再依据他们去探讨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而是转向探讨作品本身以研究组成文学作品的成分结构,从而揭示文学作品构成的一般规律。
作为结构主义重要的批评手法之一,二元对立理论认为一系列对立矛盾的结构存在于语言本身,也存在于以语言为媒质的叙事文本之中。正是这一系列的对立矛盾结构组成了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从而使得它产生了价值和意义。在进行叙事文本研究时,研究者将其分解成一系列的细微结构,将其中具有对等、并列、对立等逻辑性的结构理清,正是这些具有逻辑性的细微结构呈现出了相互对立位置的两个事物,显示出了明显的比较和对照,从而引申出彼此的另一层含义,因而研究者可以位于一个新的视角来诠释和把握叙事文本的复杂结构。因此,在读者看来,一个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对立项有机系统地构成了一部文学作品。二元对立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文本解读方法,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系统地探寻文学作品的内涵和美学价值。
《觉醒》是女性主义作家凯特·肖邦的代表作,是一部经典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小说大胆而又直率地探讨了女主人公艾德娜面临着独立主体和自我缺失的他者境遇,揭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和男权社会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存在于整部小说之中,极致地展现出了作家肖邦矛盾的思想和二元对立观点。本文将从传统与自由、文明与自然、灵之生与形之死三对二元对立项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传统与自由
法国作家爱米尔·左拉曾说:“人不是孤立的,他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环境中。”[1]一方面人总是受到一定的社会传统规范及价值观的约束,另一方面人又总是在和社会抗争,挣脱其束缚以获得自由。《觉醒》中主人公艾德娜·庞特里耶是一位已婚妇女,她所居住的新奥尔良城商业发达、制度全面、规范完整。男性们在这里纵横打拼天下,主导社会传统和秩序,一切规范制度和传统都是为男权服务,这里是父权制文化的一个缩影。为了构建独立的“自我”意识,在男性社会里男权会压制、异化一切异于“自我”的特征,并将她们视为“他者”。在新奥尔良这个以男人价值观为准绳的男权社会里,女人附属于男人,并长期被男权社会的价值观所洗脑。面对抉择,艾德娜严重缺乏主体意识,即便在婚姻这样的终身大事上,在她看来,与礼昂•宠特里耶结婚完全是一个巧合,只不过为了在现实社会可以“有尊严地占据一席之地”[2]22。尽管人们认为庞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2]8,但艾德娜完全是为了获得舒适的生活而表现贤淑温柔,听命并满足于丈夫。她从未因她的婚姻而发自内心地开心过。虽然艾德娜与丈夫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不满足于现在的婚姻,但她选择隐忍,未做出任何反抗之举。其实,在丈夫和社会面前,艾德娜已经缺失了自我,处于一种失语的他者境地,唯一能够维持其婚姻稳定是内化的男权价值观。每次遇上丈夫的抱怨和指责,艾德娜只能通过哭泣来宣泄内心的压抑。由于主体意识的缺失,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痛苦的真正原因,只能感受到一种抑郁感隐约让她整个人非常痛苦。很明显,父权文化已经剥夺了艾德娜的发言权,禁锢了她的主动性,她已经成了一名被动、无声的沉默女性。然而,格兰德岛度假之旅改变了艾德娜,罗伯特的出现使她的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萌发。就在她去大海独立游泳回来的那天晚上,她平生第一次拒绝丈夫的意见。她要挣脱社会传统规范及价值观的束缚以获得自由,体验个人生活和自由生命的意义。艾德娜经过反复的沉思和自省,在意识到自己被困于有性无爱的婚姻牢笼后,对于丈夫提出想过性生活的需求坚决回绝。她怒砸婚戒后狠狠踩踏它,这表明了她想要摆脱约束自我、压抑个性的传统婚姻的决心。她打破每周二招待家庭访客的常规惯例,卸下繁重的家务活,循着自己内心的真实感觉去探寻未知的城市生活空间。饱受可悲婚姻的折磨和辛酸后,她对妹妹的婚礼置之不理。艾德娜卸下迎合传统男权的刻板面具,再也不是一尊任由他人摆布的木偶,她反抗传统、追求自由。可是,当她最终觉醒竭力反叛社会时,她遭到了失败。她是孤单的,孤军奋战的,心爱的人逃跑了,没有人帮助她,最后她只能绝望地选择了走向大海自杀而结束了自己反抗传统、追求自由之旅。
二、文明与自然
19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在经历内战后,开启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社会和经济迎来了巨变。作为肖邦的出生地,圣路易斯几乎处于美国的几何中心,地理位置重要,当时各方面都发展迅速。此外,在南北战争的带动下,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女性的经济独立性有了一定的提高,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亦有一定的身份。即使这样,女性的声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仍基本处于淹没状态。女性作家们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对女性的经历有深刻的体验,对女性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遭遇进行了深刻大胆的反思和披露。这些因素影响了肖邦的创作思想,在其小说创作中体现为人类社会文明与主人公追求自然的生存状态之间的冲突。在西方文明发展中,女性和自然相联系,她们在男权社会里都被视为被压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长期处于失语和边缘地带[3]。小说中艾德娜一家来到美国南部的格兰德岛度假。这个海岛周围是大自然的荒野,远离繁忙喧嚣的城市,仿佛世外桃源,让人的心灵返璞归真。艾德娜在这遇见了善解人意、温柔多情的罗伯特,这重新点燃了她内心被世俗婚姻湮灭了的爱情之火,开始思考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她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她开始了释放个性,追寻自我的觉醒之旅。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望无垠的大海意象意味着自由自在的大自然,是她追求和向往的,让她感到十分亲切。亲近自然是女性非暴力抵抗男权社会的一种方式。在大海面前,艾德娜摘掉束缚的面纱,敞开心扉地向拉提诺尔夫人倾吐心声,自然地流露真情实感,勇敢地展现真实的自我。在大海那绵绵不断的无穷力量召唤下,她循着内心的真实无畏地摸索着未知的新世界。
经历了格兰德岛之旅后,艾德娜深受大自然的洗礼和熏陶,意识到了男权社会里所谓的种种道德、习俗和文明与其所追求的女性自我势不两立。于是,她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提到女人为家庭牺牲时,她坚持为了孩子放弃金钱、舍弃生命,但绝不可以放弃自我。艾德娜回到城市——这个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物,对周围的一切感到无趣、麻木,甚至反感,她决心不再沦为她所不爱的丈夫的所有物。她通过怒摔玻璃花瓶,摘除、丢弃并踩踏婚戒等方式表达内心的愤懑和不满。精神觉醒的同时,艾德娜在物质上也进行了反抗。她决然地从丈夫的高级住宅搬进一间粗陋的“鸽楼”居住,因为她深刻地觉悟到要想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就必须同它划清界限。然而,艾德娜摆脱男权束缚和摧毁世俗文明的努力是苍白徒劳的,被她打碎的玻璃花瓶很快就被清理干净,被她竭力踩踏的婚戒依旧完整无缺,并且她还要继续戴到手指上。更为严重的是,面对艾德娜对女性自然生存状态和自由生存空间的勇敢追寻,一直深爱她的罗伯特没有选择理解和支持,反而遗弃了她,甚至扮演起了男权社会和文明世俗的维护者的角色。此时的艾德娜极度痛苦绝望,孤独无援,只能向大自然寻求抚慰、汲取力量。只有在那,她才能获得精神的慰藉和肉体的自由。就像人类文明发展给大自然带来的毁灭性破坏一样,人类文明的巨大压力压得艾德娜喘不过气来,她只能静静地消融在自然之中。
三、灵之生与形之死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4]121庄子《逍遥游》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和一种超然返璞的态度。他倡导的“天人合一”境界可以用来形容小说主人公艾德娜人生所追求的境界。随着艾德娜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她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充斥着激烈的二元生死矛盾和斗争。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可以归结她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惑,即主体意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对独立、自由和爱情强烈渴望的自我意识战胜了理性,使她本能地顺从了阿罗宾。一位有夫之妇接连出轨,这与当时的社会习俗完全相悖,实属大逆不道,是要浸猪笼的。然而,艾德娜未被社会现实所压倒。她从大海、罗伯特以及雷西小姐的音乐获取了无限的力量。住进“鸽子屋”,以绘画独立谋生表明她逐渐觉醒,挣脱人妻、人母的附属角色。尽管在社会地位上她有下降的感觉,可在精神世界里她得到了随之而来的提高。她洞察和熟悉生活的最深处,用她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她不再满足于随声附和,而是循着心灵深处的召唤。艾德娜没有在阿罗宾的关系中迷失自我,反而增加了她对事物的理解。遮天蔽日的乌云已经消散,她更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她不属于任何人,她只属于她自己。显然,艾德娜的精神与肉体此刻是分离的。尽管她有着云游四方的精神,但也有着委曲就范的肉体。凯特•肖邦与中国的先古哲人庄子处于完全不同的时空,但她这种矛盾的主体意识与庄子的“心灵与形体的分裂”[4]116并无二致。她逃避罗伯特的爱情,因为她发现他和自己的丈夫都只是个墨守成规的人。她完全认识到现实社会中已没有她值得留恋的任何东西。社会的现实压抑着艾德娜的自由和个性,而她未能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情况,更没有寻得脱离困境的获胜方法。她艰辛、痛苦地求索,荒唐无聊、乌烟瘴气的生命对她来说似乎是毫无价值的,人就像站在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的山顶上的盲人,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毁灭。但是,艾德娜不甘向注定毁灭的命运屈服和妥协,始终不渝地追寻着理想的自我存在。不过,她不喜欢听命于丈夫、顺从于孩子的阿黛尔,因为她失去了自我;她也不欣赏不修边幅、性情孤傲的雷西小姐,即使她给予了她激动和勇气。“存在在思维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5]艾德娜爱好绘画,绘画也可算她的一种言语了。然而,她不太擅长作画,拉提诺尔夫人看完艾德娜为她作的画像感到非常扫兴。她自己在认真地端详这幅肖像画后,将其涂抹并揉碎扔掉。很明显,形体的生与死的矛盾在她那已经无法调和了。在现实的社会中,她已经没有了半点她想要的空间,形体的存在已经没有了立锥之地,本能的需求已经微不足道。形体存在的消亡,必然是全新自我的释放与重生。在大海向她发出大自然的召唤下,她褪去人类社会束缚的外衣,人生第一次一丝不挂于青天白日之下。此刻,她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里睁开清澈的双眸,“多么意趣盎然!”[2]147显而易见,此刻艾德娜的全身融入自然已经完全解构了生死的二元对立矛盾。生亦是死,死亦是生,生生不息。她与自然相通统一,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四、结语
从以上二元对立项的分析可以看出,艾德娜在追求自由、追求理想的自然生存状态过程中面临了灵与肉、生与死的矛盾斗争。通过其女性自我的不断追寻,她终于认清了她的精神世界与外在的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最终与自然相统一,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整篇小说表达了作者对回归自然生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理想的颂扬,蕴含着深刻的自然美学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