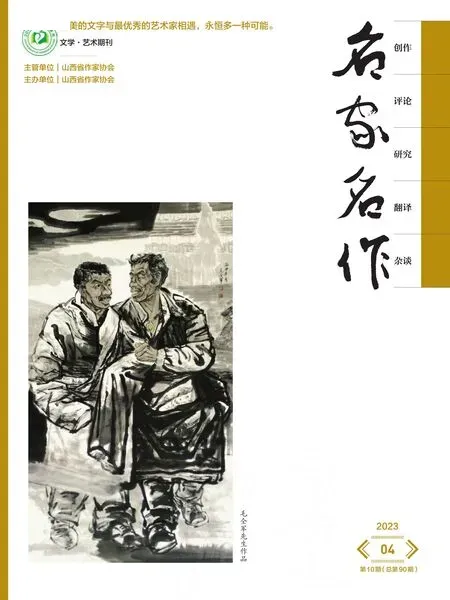诗人的荣光
顾笑奕/译
我的魔鬼兄弟,我的同类,
我看着你褪去血色,同黎明的月亮一般高悬,
晦迹于空中的一朵云后,
匿伏在可怖的群山之中,
魅惑而狭长的耳朵后,艳火状若繁花,
如同吟哦午祷词的孩童,
在无知的幸福中亵渎神明,
残酷地讥笑和凝望着我对尘世的厌倦。
但不是你,
我不生不灭的爱,
不该是你把幻想、无能和堕落当作笑料,
因为我们是同一团焱焰燎起的火花
同一次吹息将你我抛入
一场诡谲造物的冥暗涌潮,众生于此
攀过他们的困苦岁月,像火柴般燃尽。
水泡日晒后
你的肉体同我的一样切盼同暗影厮磨;
我们的言语焦渴于
在五月和暖中敛起芬芳和秀色
花枝一样的男孩;
我们的眼渴望一成不变又千汇万状的大海,
回荡着灰鸟溃于暴风雨的哀鸣,
我们的手渴求向世人的轻蔑报以奇文瑰句。
人类你是晓得的,我的兄弟;
你看他们如何扶正那了不可见的冠冕
搂着自己的女人模糊了踪影
自鸣得意却浑然不觉,
胸脯间又保持着恭敬的距离,
俨如天主教司铎对待他们悲悯之神的形体,
苟合产下的子女,那逃离睡梦的片刻
都挥霍于床榻,浓得化不开的鸾凤深暗
在他们的兽穴,交颈缠绵。
你看他们迷失在了自然中,
看他们如何在娇俏的栗树或者沉默的香蕉树丛间苦熬,
如何贪婪地抬起下巴,
感受着黑魆魆的恐惧啃食脚跟;
你看他们如何想当然地在第七日从工作中出逃,
库房,柜台,诊所,事务所,政府办公室
任凭风捎着缄默的杂音掠过那寥寂之境。
你听他们接连不断地蹦出
蛮横昭昭的话语,
要为被铁链拴在那圣洁烈日下的幼童讨一件外罩
或是一杯温吞的水,那会温柔体贴地呵护
他咽门的温度,
自然水过分的寒凉可能会冻伤它。
听听他们关于有用、正常和美丽的
大理石般的训诫;
你听他们对世界发号施令,为爱定下清规戒律,
把无可名状的美打入框框条条,
却听任自己在醉舞狂歌中恣情纵欲;
观察一下他们古怪的头脑吧,
一代,又一代,试图搭起一座庞杂的沙厦
以惨白森然的屋面拒绝星辰闪耀的和平。
我的兄弟,他们
是我孤身走向死亡时的同路人,
是幽魂,有朝一日催生出伟大学者
他在陌生学生面前说出我这些话中的神谕,
由此声名鹊起,
外加一间在紧挨着首都的恼人山峦上的小农舍;
而你,隐于斓斑的雾气,
抚弄着你卷曲的碎发
漫不经心地从高处睥睨
这片扼杀了诗人的秽恶之地。
然而你知道我的声音属于你,
我的爱欲属于你;
这漫漫长夜就让,哦,就让
你炙热而黝黑的胴体,
同鞭子一般轻盈,
滑到我——埋在无名墓里的忧悒枯骨——的身下,
就让你的唇舌,那无穷尽的泉源,
将我们之间至死不渝的狂热浇灌在我身上;
因为言语的徒劳叫我心力交瘁,
就像对于孩童,玲珑的小石子儿
投入湖中,看那份平静
震颤着晕出神秘巨翅的倒影。
时辰到了,是时候用你的双手
将诗人渴望的繁丽的匕首
递给我的荣光,
是时候利落的一刀,把它刺入,
这铿然而激昂的胸膛,同鲁特琴一样,
此处唯有死亡,
唯有死亡,
才能唤起那应许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