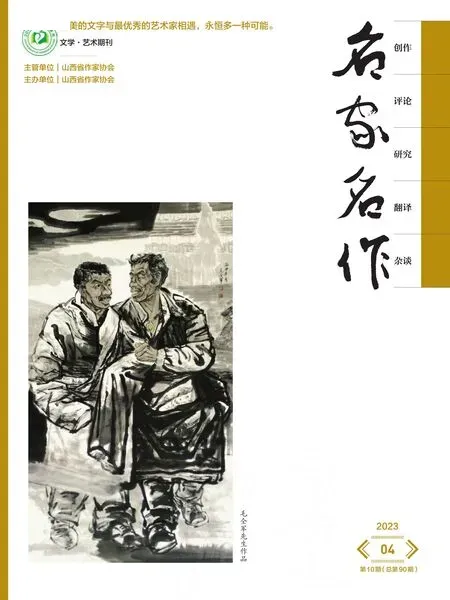浅析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学与诗文创作中的理性因素
苏源宸
兴起于18世纪晚期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对僵化的理性主义做出了激烈的反叛,在该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青年才俊,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热情及全新的、异质化的思想,为浪漫主义的产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我们与其说浪漫主义是哲学家的事情,倒不如说它是诗人、艺术家和“天才”人物的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者虽对理性持批判态度,但理性精神仍作为一种恒久存在的神话,存在于浪漫主义美学与作品之中,并深刻影响着它们的思想内涵。
一、美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
当我们追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论时,便会惊奇地发现理性精神在其中仍旧占据着重要地位。纵然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对人的本质(理性还是感性)、国家的构建(契约还是文化)、历史的进程(普遍还是各异)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是我们不能仅以此便将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比作一根绳子的两端,将二者彻底分离,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早期浪漫主义尚不能脱离理性而立足。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浪漫主义者在诗学与美学层面仍旧认可理性对人的启蒙作用,充分继承了自古希腊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即将诗歌作为连接尘世生活与彼岸的精神桥梁,积极地运用艺术审美的方法去关照人类,赋予艺术关注人类命运的母题,承担起尘世启蒙者的角色。毋庸置疑,这是贯彻了启蒙主义对文学的主题要求,即对人类命运的普适性关注,并启迪民众扫荡思想中的封建残余。作为浪漫主义者,虽然他们将这种责任感隐埋在诸如上帝、自然等宏大的、超越的理念里,但我们仍可从这些缥缈的意象之中窥见他们对世俗的关照。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浪漫主义更是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审美人文主义的基石。
这种与理性的暧昧还体现了对绝对主体——“自我”的承认,只不过在启蒙思想家那里“自我”被理性一以贯之,他们虽然自觉地认识到人自身作为一种主体的存在地位,但他们把“我思”前置于“自我”这一自然主体之前,运用二元论对问题进行考量,将人类理性化的思考视作更重要的存在。而浪漫派在此基础上还强调人作为一种感性动物,他们充分继承了费希特的自然哲学,费希特追溯了“我思”之前的“我”,用“自我”这一实存的、主客统一的绝对主体代替了“我思”,使浪漫主义者的思考出发点从传统二元论的“我思”转向以“我是”为优先思考的最高原理,如蒋孔阳在《德国古典美学》指出:“费希特‘解放’了浪漫主义者主观世界,强调‘自我’的独立性与自由。”[1]由此,在浪漫主义者的哲学之中,“自我”便是蕴含着各种感情与内心的不确定性,而心灵永远是包含着激情与个性的统一整体,并不能划分为各种机能,强调每个个体的多元性和无规律性。而这是逻辑与理性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此他们提出要了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意趣,更倾向于关注真实的“自我”。
此外,浪漫派也分享了启蒙运动的线性时间观,他们对民族历史和过去的沉湎正是预设了“现时”,只不过他们与理性主义者对“现时”的乐观不同,浪漫主义者更多表现出的是对现代的不信任;浪漫主义者也没有抛弃历史的进步观,相比于理性主义者对现代化的自信,他们更注重历史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辩证眼光,他们虽怀念中世纪的精神,但却为了在历史中探寻理想世界,“在回家的路上,寻找父亲的宅子。”呼吁人们关注过往孕育现代性的东西,让民族的传统照亮堕落的现代,从而实现精神世界的“返乡”。
由上可知,也许我们可以将早期浪漫派确立的信念称之为“新理性”,他们承认理性的存在和价值,坚持启蒙思想中对人类自由、平等和进步的理想,但同时又认为理性不能完全主导人类的认识和文化,而应与感性一道,共同促进人类进步。实质上,浪漫主义者是继续了康德等人对理性批判和界定的工作,高扬独立思考,体现人的自主性,敢于去除神话与迷信的启蒙运动宗旨。与此同时,他们将感性的地位拔高,试图将理性和感性统一起来,他们认为只有当理性和感性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时,人类才能获得完整的认识和真正的自由。而正是由于他们的观点,使唯美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震荡代替了理性的一统天下,在启蒙运动后用理性为人类在经验世界中祛魅,但他们又将理性神话了,傲慢的理性主义便从这时逐渐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仰,大众逐步对由理性的盲目崇拜造成的冰冷的历史和工具的人性进行不自觉的抵制。而在艺术创作领域,浪漫主义者认为,人类内心的情感和感性体验的重要性是相当的,甚至理性的方法可能更为重要,例如要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恰当地运用理性的形式,以此让诗更富张力。由此可见,浪漫主义还没有将理性主义的太阳彻底拉下地平线,他们让太阳还保留着余光,让理性神话得以延续。这正是在理性与感性、光明与黑暗交替的时节,也正是这一光明与黑暗参半的情形又为理性塑造了强大的张力,促进了富含理性的浪漫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二、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理性乌托邦
在尚未与理性完全分道扬镳的浪漫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浪漫主义者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具有理性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义者们所强调的浪漫精神与感性精神其本质上就是“诗”的精神,对事物的浪漫化就是对事物的诗化,并非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经验世界更深层次的思考,而这种感性的理解是与理性的认知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若要具体找寻理性在浪漫主义中的余韵,就必须要深入诗中寻觅答案。
浪漫主义者认为诗是高于哲学存在的,其拥有救世之功用;在这个层面上,诗歌与启蒙运动后所宣扬的理性精神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在浪漫主义者眼中,诗又可以被分为有形之诗与无形之诗。有形之诗即是我们通常认识的诗歌,其作为文学作品,是由诗人心中的灵性感受“无形之诗”创造出来的,拥有诗所应具备的内容与形式。而无形之诗则是一种诗化哲学,即“宇宙之诗”,其连接着有限与无限,将个体与整体完全统一,是自然与宇宙创造力的显现。当然,作为诗人,浪漫主义者自然是通过有形之诗来反应无形之诗,展现“天才”的思想与情绪;而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新理性主义,其诗文便不由自主地蕴藏着理性的光辉,其中以诺瓦利斯的诗文最为典型。
诺瓦利斯作为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夜颂》组诗充分反映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的特点。诗歌中通过对自我的剖析,对万物自由的想象代替了对客观世界的摹仿,而自然作为诗歌表达的主要依托,寄托了诗人无限的幻想,又通过自然这一神秘的景象将诗人的主体情感转移到客体的心灵。其内容通过超验的手法充分表达了浪漫主义式的追求。而在这些显然的美学特征背后,诺瓦利斯在诗歌主题的塑造过程中亦继承了德意志民族重思辨、重内涵的传统,并由此展现出理性的光辉,即对世界的期待与怜悯之情与对乌托邦式理想世界的追寻。正如其写道:
你是那个少年,
他长久以来
就站在我们的墓地上思考;
黑暗中出现一个令人宽慰的信号——
更高尚的人类已经欣然起步。
让我们陷入悲伤的,
现在让我们生出甜蜜的渴望。
死亡中预示着永生,
你的就义换得我们的健康。[2]
在此,他将一位少年作为重点叙事的对象,如后世新批评学家艾略特提出的情感表达应有“客观对应物”的观点,少年就是整段诗歌的“客观对应物”。在艾略特看来,“在艺术作品中,艺术家要表达某种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寻找一种客观对应物。一组事物、一连串的事件等都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客观对应物。艺术家借助作品结构使情感客观化,批评家也就能够根据这种客观化的对象形态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3]在此,诗人借少年的意象展现出一种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情感,这位少年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做了深入的思考,并得出一个欣喜的结论:“更高尚的人类已经欣然起步。”而通过这一思考所要表明的思想内容与新古典主义诗歌中出现的主旨是一致的,即对人类发展的自信与期待。在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者对人类理性抱有极大的信心,其认为人类的判断力是优秀的,即便犯错,也可以在后天通过学习训练进行改善,由此来达成认识世界的目的,并成为更加完善的人,也就是诺瓦利斯在诗中所言的更高尚的人类。
通过少年的救世之举不仅能反映出诺瓦利斯本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即通过死亡回归夜晚,获得某种意义上通向彼岸世界的永恒。而且这种以自身之死换取的人类健康的要求,以近乎“诗”的形式来拯救客观世界,构成了一种全体人类都能达到幸福的理想乌托邦式的场景。通过这种建构更能体现出他对于物质世界的怜悯与关注,反映出启蒙主义者式的对世界充满理性的关照之情。
同样是在《夜颂》之中,诺瓦利斯通过将私人化的宗教经验进行诗性的处理,以此来寄托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设想:
你,夜之灵感,天国的瞌睡降临到我的头上。
四周的地面慢慢地高起——在地面上漂着我的解放了的新生的灵气。
丘冢化为云烟,透过云烟,
我看到我的恋人的净化的容貌——她的眼睛里栖息着永恒。
——我握住她的手,眼泪流成割不断的闪光的飘带。
千年的韶光坠入远方,像暴风雨一样,
——我吊住她的脖子,流下对新生感到喜悦的眼泪。
这是在你、黑夜中的最初之梦。
梦过去了,可是留下它的光辉,
对夜空和它的太阳、恋人的永远不可动摇的信仰。[2]
部分浪漫主义诗歌中浓厚的基督教式的对神明的崇敬在诺瓦利斯的诗句中被消解了。宗教不再是世俗所理解的一个现世的基督,而变成了一个寄托人类心灵情感的栖息之所,一个承载着泛神论幻象的极度美好的环境。这与在理性思维指导下的乌托邦文学有极大的相似之处。18世纪的乌托邦小说大多运用想象构建出一个远比现实社会美好、幸福、自由、和平、富足的未来社会,即正面乌托邦,通过构建一个以理性王国所主导的完美社会来批判现实生活中尚不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作为一种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价值取向,达到了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这与诺瓦利斯诗中提及的以基督教为根本环境,但却蕴含着人性光辉的环境类似,二者虽在指导思想上有着差异,但其在存在性与指向性上是相似的,二者于现实世界都是一种恒久的“缺席”,亦为人类未来的幸福指明了道路。总而言之,当人类在现实世界陷入困境、遁入想象之中时,便描绘出理想世界的文学创作方向作为一种共性,并兼容于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现象。
三、浪漫主义诗文中的反思理性
诺瓦利斯在《夜颂》组诗中构建出与理性乌托邦近似的浪漫世界,与此同时,在他的其他作品创作中,如短诗与长篇散文之中,亦能充分体现出蕴含其中的理性精神,在这些作品中,他对浪漫主义思想本身进行了反思与再创造。如他的一首小诗《致一只蚊子》写道:
你这小虫,不要飞得过分靠近这明亮的烛光
它使你眼花,你飞进去,它会烧掉你的小翅膀……许多聪明人也常像这样,
当他被迷误的假象所欺,盲目地奔了过去,
就会意料不到地跌倒在那里。
许多青年人也是如此,
碰到亮光,情欲的温暖,
就受到迷惑,高高兴兴地投入那烧焦他的火焰。[4]
在这首小短诗中,诗人先从蚊子扑火这一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引入话题,而聪明人、青年人等在浪漫主义者眼中象征着天才与美好的形象在某些方面却与蚊子无异,当他们面对假象或诱惑时,也会如昆虫般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即便被灼烧也不自知,他们正是被“本我”冲昏了头脑,导致悲剧的发生。这与浪漫主义者所提倡的对自由、感性不顾一切的酒神狂欢式的想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于过度浪漫的反思与批判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是不常见的,反而是一种启蒙主义者理性的反思性思维的体现。
无独有偶,诺瓦利斯在他的小说《塞斯的弟子们》中亦构建了运用感性手法对理性做深刻关照,并通过理性的思辨对浪漫化的想法进行深刻反思的典型意象。其讲述了男主人公夏青特在得到一本难以解读的书后,为了寻找“伊赛斯”——生命圣洁女神,与自己的爱人洛森绿蒂告别,踏上了漫长征途。历经诸多磨难之后,最终找到了这位象征着自然的女神。而揭开女神面纱的仪式性行为成为故事的高潮,面纱下等待着夏青特的既是自然女神伊赛斯,也是他的伴侣洛森绿蒂的形象。女神与爱人合二为一的戏剧性结局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式的对“爱”的美好想象。
而故事的反思理性又从何处体现呢?故事主人公夏青特(Hyazinth,即风信子石)与女主人公洛森绿蒂(Rosenblüte,即盛开的玫瑰花)之名形成了矿物与植物的鲜明对比。在不少浪漫主义诗歌意象中,矿物可以反映为坚硬、不可动摇的理性,而植物则是象征着自然、生命与热烈的感性。这与诺瓦利斯的想法不谋而合:“男人代表认识与追求、理性、分裂、隔离,相反,女人则体现真理的所在、全面的智慧、整体与自然。”[5]男性对女性的追求,从深层语义的角度加以分析正是理性对智慧与真理的追求,这与其他浪漫主义诗文中对理性的批判大不相同,这就体现出诺瓦利斯对浪漫主义的反思。由此,我们便可将故事中夏青特对洛森绿蒂的个人情爱上升到启蒙主义式的对真理与知识的爱方面,而夏青特对洛森绿蒂起初的离开亦可以被认为是诺瓦利斯对浪漫主义思潮中过度浪漫化现象的反思。总之,在诺瓦利斯的创作过程中,自我被“浪漫化”地抬升到了与自然平等的地位,但其思想内核依然没有脱离18世纪所规定的启蒙目的论与通过理性改造世界的思想框架,浪漫化的表达中仍是对真理的渴求,是运用理性对浪漫的反思性思考,是对理性及客观世界不断完善的愿望,并以此让自我获得在现世的幸福。这是诺瓦利斯诗学的意趣,更是启蒙主义者对现实生活想法的真实反映。
诺瓦利斯作为德国浪漫主义诗派的代表人物,他试图通过诗歌的形式探索人类内心的感性体验和存在的意义,同时也关注逻辑、语言和思维的问题,将理性的知识与浪漫主义的情感和想象相结合,从而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个人创作特点。其在诗歌创作中多样的意象选取与复杂的情感,充分体现出德意志民族重思辨、重内涵的理性思想内核。此外,他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德国诗歌的转向,其深入“心灵”进行深刻剖析的创作方式,将描述客观世界的诗歌导向内心与自我,拓宽了诗歌的主题,并对浪漫主义进行了反思,将诗歌与理性充分结合在一体,形成了德国浪漫主义的独特风格。
四、结语
由上所述,德国浪漫主义诗派并不是同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与理性分道扬镳,而是对理性进行批判地继承。他们对福柯所言的“理性即酷刑”中的单纯的工具理性进行猛烈反抗,而对理性中的合理科学成分进行了充分吸收。浪漫主义者虽然将理性的太阳拉下了神坛,让感性重新回到了人们眼前,但他们仍旧让二者得以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让充满理性思辨的浪漫主义文学在历史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时至今日,德国浪漫主义的回响仍在我们耳边萦绕,其呼唤着我们对感性世界的追求和对工具理性霸权的警惕,而这对今日的社会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