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科技强国,必须重视系统工程和技术科学(上)
梅永红
最近,许多人都在关注美国对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加码限制的问题。对于一个每年进口量达数千亿美元,信息产业规模早已跃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来说,这种限制无异于在一个疾行者的前路挖了个大坑。其实何止芯片,中国高校、科研单位、医院和企业里,但凡高端仪器设备和核心软件,至少90%都是进口的。多年前有人曾发出“谁来装备中国”的诘问,庞大制造业大厦的底座掌握在他人手里,这个问题至今在许多领域仍然未解。
“卡脖子”是否因为我们基础落后、人才经费不足
应当承认,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本地化、商业化开发,是后发国家绕不开的发展路径,今天不可一世的美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于现实中的“卡脖子”问题,我主要有两点思虑:
第一,这些年来类似的问题始终存在,信息产业面临的风险更是令人揪心。某种程度上说,产业规模越大,被“卡脖子”的可能性也越大。但产业界的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们认为西方国家不会放着到手的钱不赚,所谓“毁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蠢事不可能出现。而“以市场换技术”,从“技工贸”到“贸工技”的转轨,是把中国产业大厦牢牢建构在他人底层技术基础之上。今天,当美国决意以国家安全名义开展“在岸生产”,以意识形态名义开展“友岸外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以商业思维谋划国际竞争战略,是进行路径选择,还是战略短视?
第二,芯片技术理论早已定型,甚至看起来并不深奥,我们又有那么多的专家,为什么一直做不出来?荷兰ASML的专家说,即使把光刻机的图纸交给中国,中国也造不出来。中国台湾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也说,中国大陆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高端芯片。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形,比如同样被别人“卡脖子”的航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高端医疗仪器,甚至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的乘用汽车、农用拖拉机等,中国许多专家早就对其理论烂熟于胸,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造不出稳定可靠的高质量产品,究竟原因在哪里?
更多的人将原因归结于中国科技人才匮乏,科研能力和水平不行。于是,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科技教育经费预算,围绕教育、人才和科技的国家级行动和计划不断推出,985、211、院士、杰青计划、千人计划、知识创新工程、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专项、大科学工程等层出不穷。若论经费,中国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早已位居世界前列。在高端人才方面,中国绝对在世界第二方阵中。地方政府也穷其财力引人才、建平台、搞园区,试图一举突破产业瓶颈约束。据说,仅高端芯片产业就已投入上万亿,投资百亿级的芯片项目接连冒出,效果究竟如何?
我无法苟同将产业问题简单归咎于科技问题,因为理论是一码事,工程实践是另一码事,两者虽然密切关联,但形成规律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是,理论也许可以共享,技术也许可以引进,物化的技术产品也许可以用钱买到,但技术能力必须是内生的,是十年磨一剑和久久为功的结果,从来没有速成之说。以芯片为例,台湾总共只有2000多万人口,无论是人才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可能比大陆强多少。资金方面更是沒有可比性,广东、江苏一个省的实力都能超过台湾。在市场应用方面,别说台湾市场,整个欧洲国家市场加起来也不如中国的大。有人有钱又有市场,却无法在芯片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上挺直腰杆、赢得尊重,看来不仅是板子打得不够重,下力不够猛,而是可能打错了地方——方向和路径错了。
最近有两份材料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个是MIT前校长苏珊·霍利菲尔德的新书《生命科学——无尽的前沿》,从科学的视野出发,阐释了生物技术和工程学的结合,在不久的将来如何“为改善我们的世界提供非凡的手段”(哈佛前校长福斯特荐语);另一个是重温原国务委员宋健同志2015年发表在《前沿科学》上的一篇文章《还原论和系统论》,在充分肯定还原论对于近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奠基性作用外,文章特别指出其理论的局限性,包括对信息的忽视,而信息恰恰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宇宙“三基元”;对系统层级结构的忽视,难以回答“总体大于子和”;还原论描述的自然过程都是可逆的,但生物进化不可逆,时光不会倒流。
这两位东西方学术大师的中心思想,都是指向基于系统和工程化的技术科学。我们知道,科学是发现,完成从0到1的过程,具有唯一性;而创新是对理论的产品化、工程化和系统化,完成的是从1到100乃至无穷的过程。实践证明,这个工程化过程并不只是线性的理论成果转化,而是学科交叉融合、系统整合配套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大量缄默知识,具有对特定情景的高度关联性,并且具有典型的“非公共性”。哈耶克认为,在人类的知识中,除了有Knowthat外,还有Knowhow,显性知识只是人类知识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说一切知识总体是一座冰山,那么显性知识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而缄默知识则是隐藏于水下的绝大部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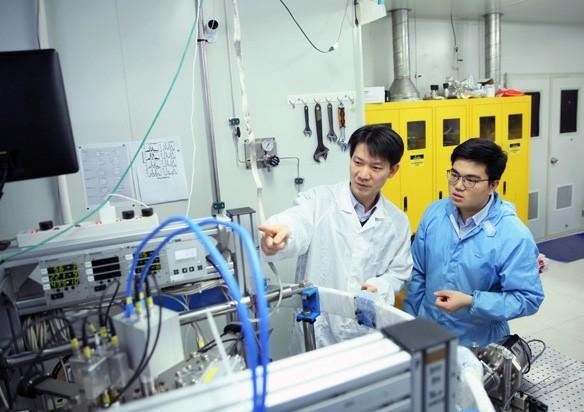
这种缄默知识来自于工程化实践。由此,我结合中国目前的学术生态、科技体制以及相关资源配置情况,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卡脖子”问题,关键不在于还原论基础上的经典科学差距,而在于系统工程的缺失,技术科学、系统科学是最大的短板;第二,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更多地突出市场和需求的引领,突出企业和企业家的组织功能,然而用解决学术问题的思路无法解决复杂应用场景下的系统组合问题;第三,政府的作用需要精准定位,要着力解决创新生态,特别是政策的碎片化、资源配置的低效化以及对颠覆性创新的体制性扼制。
我国科技布局缺乏对工程科学、技术科学的重视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引用两位杰出华裔科学家的论断。一位是杨振宁先生,他在1981年就曾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倾向于走两个极端”,即基础研究和产品研究。“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经费多得多。事实正相反,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我理解的发展性研究,就是指的工程科学、技术科学。
另一位是李政道先生,他在1999年说过:“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基因组织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而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不光物理学如此,这也许还会影响到生物学和其他科技的发展。”显然,经典意义上的还原论无法回答大多数系统问题、宏观问题。
引用以上思想,主要是试图说明一个问题:隐藏在水面之下的知识冰山究竟有多大,形状如何,运行轨迹如何,才是决定露出水面部分之功能关键所在。如果只有理论研究,而没有基于完整、持续发展研究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但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诸多“卡脖子”问题,而且也失去通过工程化手段探索和认知极限状态、系统状态下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可能。在我国目前的科技结构中,基础理论科学固然亟待加强,而技术科学、工程科学是更大的短板。一方面,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的,我们历来关注两端的基础研究和产品研究,各种资源配置及政策集中于这两个方面,工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主体也不够清晰;另一方面,学术界对工程科学和技术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能工巧匠的层面,并未登上学术“大雅之堂”,以至于工程科学和技术成为教育、科研和就业的偏门冷门,真是谬以千里!
以荷兰ASML为例,它从1984年起步,至今已近40年。加上对菲利浦之前20年技术开发基础的承接,可以说是集60年之力而成就的。为了保证全球工厂每秒以比头发丝千分之一还细的精度准确刻出上千亿个晶体管,他们不但开创性地利用全球“智识”为我所用,进行全球性的产业链布局,而且在时间、精度、速度、成本、强度、稳定性、成品率等多维度下求得最优,是数学、材料学、光学、化学、力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为一个数据往往需要经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试错与否定的过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是系统性思考、互动性分析、创新性思维的成果,是对各子系统互动规律的全新发现和认知。
这样的世界性企业还有不少,美国的特斯拉、韩国的三星、中国台湾的台积电都属于此类。他们能够走到世界领先乃至一骑绝尘的位置,成为国家倚重的战略力量和国际政治角力的关键筹码,其成长过程和规律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赢在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上,赢在通过不断实践和迭代所积累的丰厚缄默知识上,赢在与市场应用场景及上下游关联企业的互动与协同上。归纳而言,第一,十年磨一剑,与急功近利无缘;第二,应用场景和市场结果导向,构成完整价值闭环;第三,开放合作,实现全链条合作共赢。
目前我国无论是在科技结构布局上,还是资源配置上,都没有对工程科学和技术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时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排斥。我曾与一位知名科学家交流工程技术对现代科学发展的价值,但被其完全否定。言谈之间,明显表现出对于工程技术的不屑,认为只是工匠和苦力,不是原创,不具有前沿性。我不知道这种思维在学术界是否为主流,但以在CNS等顶级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为大确属事实。最近几年,医学界不断曝出学术不端行为,一个成功做了上千例手术的临床医生,居然必须以发表学术文章获得职称晋升。这鼓励的是什么?申请课题,发表文章,获得奖励,这种“三点一线”的学术路径,让不少学者陷入陷阱,这种机制怎么能支持创新性的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是成功孵化出全球无人机领导者大疆创新、“水上特斯拉”逸动科技等一系列明星科技创业公司的知名科学家。他曾分享创业成功的核心思维模型——工程意识:“以前招学生,都是找最好的学校、成绩最好的,最后发现错了,工程意识比成绩更重要。未来的工程师要学会跟跨学科的团队合作,学会从设计到制造的快速迭代,学会把艺术、工程跟设计融合,去面对全球的市场”;“你需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知道如何动手,如何学习,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不断迭代。我们所熟知的创业者,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皆是如此”。脚踏实地才能解决问题,这既是经验之谈,更是规律使然。
不少学者认为工程科学、技术科学不是原创,那什么才是原创?原创并不是经院中的奇思妙想,是牛顿、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灵光,更多的是在长期和大量工程实践中打磨而成的经验性知识、平台型模式、开拓式思维。ASML、台积电、三星做原创都是在几十年工程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厚重,令后来者望尘莫及,望而生畏。马斯克的电动汽车、火箭回收、星链计划、真空管道交通和脑机链接,其实都不能算是原理创新,但人们却认同其原创性、颠覆性。集成,并由此积累起缄默知识和产品门槛,这就是技术和产品层面上的原创,其复杂性、探索性绝不在原理发现之下。
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学立国”,并且取得了骄人成就,其发展路径同样发人深思。陕西科技厅原厅长孙海鹰教授认为,日本的科学技术进步不是搞什么“遴选拔尖人才”“苗子经费资助”“面向国际前沿”“基礎科学计划”“帽子、票子”等,也不盲目追随西方,而是在产业应用中深入科学研究,敢于进入“无人区”。在日本已经获得的23项诺贝尔奖中,有6项属于基础科学(基本粒子等),有17项属于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是日本科学研究的重点。
事实上,当代最热门的新兴学科,几乎都是科学、技术和工程一体化的产物。比如计算科学,当人们认识到计算机本质上是对符号的操控,更高级的编程语言、更能控制程序运行的操作系统以及基于软硬件结合的算法不断被开发出来,并且奠定了人工智能的科学基础。再比如材料科学,过去更多的是基于大自然已有材料的功能发现与利用,而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等的出现表明设计特定功能的材料成为可能,深圳光启实验室就是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的探路者。技术乎?科学乎?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