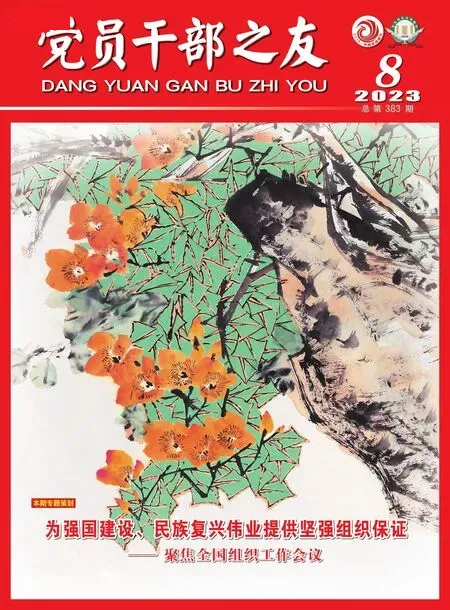浅色调
2023-08-11 21:54:04杨福成
党员干部之友 2023年8期
□ 杨福成

孙大勇/图
傍晚,树停下摇摆,斜阳给大地和天空铺上一条浅浅的色调后,准备歇息去了。
我搬个小椅子,坐在平房顶上朝远处望,庄稼和树木混沌成一片,地头和地头厮磨的小路,也是浅色调的,浅浅的如一条细线,一头牵着岁月,另一头牵着日子。
岁月长短,日子深浅,这一刻,或者一个世纪,都是浅色的。
你也甭以为自己怪能,可以把它们染重了或者涂抹掉了,都不可能。
浅是世界的元色,根子里骨子里血脉里的颜色,是亘古的童话,调皮任性好玩,改不了。
我曾经试着用墨水把自己的手涂黑,以方便在夜晚将月光偷进我的房间、年轮或者故乡。可是我办不到,一是月光它压根儿不跟我走,就算把它装进口袋里,也是漏了一地,绊得我半生踉踉跄跄;二是容易露馅,一有东西过往,我就心虚,那点墨水也吓得颤颤巍巍,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我还是我,浅浅的色调,在地上爬行,在风间游走。人的一生,都是浅色调的。如风吹过沙漠,即便积沙成丘,也不会改变它的颜色。如草吻过清晨,即便朝露含羞,也不会浸染它的霓裳。如水淹没村庄,即便草木枯了,也不会冲走砖色瓦色。
村头有一棵紫槐,色调也是浅浅的。我曾经和几个小孩爬上它的枝头,瞭望春天和秋天。枝头的风突然有了色调,浅浅的,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浅浅的。我的心被风掠过,我的曾经被风掠过,我的未来也必将被风掠过。
我看到,风的色调和我的色调重合了,我不知道该到风里去寻找自己,还是就那么着任自己随风而去。
浅色调是我,浅色调是故乡,浅色调是四处游弋的风。谁也别想着把自己浓涂重抹,否则,风会说你的悄悄话,风还会将色盘打翻,给你涂个大花脸。
这时候,花脸猫也会跑过来,对着你笑,笑着笑着它就哭了,褪去了自己的花哨,只留下一抹浅色调,与风闲聊。
猜你喜欢
红领巾·萌芽(2022年6期)2022-06-27 07:15:34
小学生优秀作文·时尚版·中年级(2022年2期)2022-02-18 01:13:59
小资CHIC!ELEGANCE(2021年25期)2021-07-29 06:40:27
小天使·四年级语数英综合(2021年4期)2021-05-10 14:37:51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7期)2019-08-13 00:54:06
童话世界(2019年14期)2019-06-25 10:11:46
摄影之友(影像视觉)(2019年2期)2019-03-05 08:27:12
时尚北京(2017年4期)2017-05-02 13:20:30
Coco薇(2016年4期)2016-04-06 02:00:19
小学阅读指南·高年级版(2014年5期)2014-09-18 02:5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