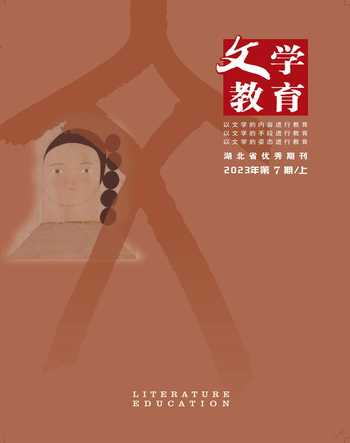王鲁彦《菊英的出嫁》:无价值的桃源之地
袁孟启
内容摘要:《菊英的出嫁》是一部民俗书写的乡土文学作品,以冥婚为线,展现出了一个以母爱和民俗为主题的女子“出嫁”的故事。王鲁彦作为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作品中展现出了一个独立于现代文明社会之外的封建农村世界,这个以浙东农村为原型的落后水乡拥有着纯粹的人性美,像一个悬崖边上的桃源之地。作者以温和的笔调展示出真实的封建农村中触目惊心的陋习以及带给人民的灾难,人性之美在封建民俗的压迫下消解成为了无价值的存在。《菊英的出嫁》目的是为了引起生活在旧制度下中国老儿女们生命意识的自觉与苏醒。
关键词:王鲁彦 《菊英的出嫁》 乡土文学 母爱 民俗
20世纪2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写乡土文学的年轻作家。乡土文学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乡土文学的思路之一,即在批判乡土中国的迷信落后之外,抹杀不了对来自泥土的最纯真也最朴实的爱的动容与恻隐。王鲁彦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中称之为"乡土写实流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菊英的出嫁》中就明显反映了乡土文学的这种思路。小说被收录在王鲁彦于192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柚子》中,以浙东农村的特殊习俗—冥婚为线,描写了菊英的母亲如何尽心尽力地为女儿操持人生大事,送女儿风风光光地出嫁。菊英母亲的爱热烈而真挚,浓稠得化不开,但是母爱越强烈就沦陷在陋习中越深。冥婚毫无疑问是荒诞的,但其中包含着的母爱是不容辩驳的。美、恶的对立反而造就了两者的和谐统一。茅盾在《王鲁彦论》中提到“奇怪的《菊英的出嫁》,无疑的也是一篇好小说。”其中用到的“奇怪”一词,确实能很好地形容这部作品中所充斥着的氛围。王鲁彦在文章中的各种描写与回忆,显示出《菊英的出嫁》中人性美与风俗陋的合二为一,虽然纠结,但两者确实是无法剥离开。看似平静的环境下隐藏着种种触目惊心,美丑的彼此消融使丑的寄生更加猖獗,而美的力量越来越没价值。
一.平静桃源中的人性美
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人,土地承载着人们所有的寄托,故乡永远是人们用以慰藉的精神家园。20世纪20-30年代,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一批作家远离故乡,寓居在北上,继承了鲁迅现实主义的笔法和“为人生”的态度去描写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他们见证过现代化过程中都市的虚假与繁华,反而更怀念有着纯粹人性美和自然美的故乡。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去呈现乡村,思考着乡土有无参与到国民改造的行动中来的可能性。王鲁彦,一个在五四时期走出故乡,来到北京的新知识分子,对于鲁迅是十分的崇拜与敬仰,他在北大旁听鲁迅讲课,到鲁迅家中进行拜访,即使在为了谋生而四处辗转的时期,也时刻与鲁迅进行着书信联系,甚至其名字中的“鲁”字也来自于鲁迅的“鲁”。受到鲁迅影响颇深的王鲁彦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向鲁迅靠近。但是,相较于鲁迅“一针见血”似的犀利的批判与讽刺,王鲁彦的创作更显得“温水煮青蛙”。《菊英的出嫁》中所展现的农村,以作者本身的浙东农村老家为原型,描绘出了一个平静的水乡农村,被水包围着的这片土地,有着不可思议的祥和,像是一个独立于喧嚣外的桃源之地,蕴含着质朴原始的人性美。
故事以冥婚为线,但冥婚的描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反而是着重描写了菊英母亲的沉重的爱。《菊英的出嫁》的故事分为两个部分,小说的前半部分以举办婚礼为中心展开,叙述菊英母亲如何操持婚礼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变化,小说后半部分进入回忆,讲解了菊英在八岁得了白喉之后,因迷信保守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而救治不当最终去世的过往。整篇文章以菊英母亲的视角为主,充满着母亲对女儿的爱意,散发着母性的光辉。首先是出嫁的部分,出嫁是农村女性不可缺少的,也可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是所有女性从有意识开始就被灌输的观念。菊英母亲是典型的封建农村传统淳朴的女性,她对女儿的爱是无私的,她深爱菊英,当菊英成长到了出嫁的年龄,她“毅然的把女儿的责任照着向来的风俗放在自己的肩了。”文章总体篇幅不长,却也是费了一些笔墨着重描写到了菊英母亲为菊英准备的嫁妆之丰厚,“她现在正忙着办嫁妆,她的力量能好到什么地步,她便好到什么地步”,“尽她所有的力给菊英预备嫁妆,是她的责任,又是她十分的心愿”。“大略的说一说:金簪二枚,银簪珠簪各一枚。金银发钗各二枚。挖耳、金的两个,银的一个。金的,银的和钻石的耳环各两幅。金戒指四枚,又钻石的两枚。手镯三对,金的倒有二对。自内至外,四季衣服粗穿的具备三套四套,细穿的各两套。凡丝罗缎如纺绸等衣服皆在粗穿之列······没有一件不精致、新奇、值钱。”一个丈夫长年在外的“留守妇女”,自己没有收入来源,却尽自己或超出自己最大的能力只为给女儿一个风风光光的出嫁,菊英母亲对菊英的珍视可见一斑。小说直至描写到出嫁的场景,才令人意识到原来菊英早已去世,参加婚礼的只是一副棺材罢了,母亲的操劳与心血在此刻显得是如此的无力和悲凉。其次是回忆的部分,小说的后半部分以菊英如何去世为落脚点,回忆了菊英生前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种种细节。“菊英幼时是何等的好看,何等的聪明,又是何等的听娘话!她才学会走路,尚不能说话的时候,一举一动已很可爱了。”“。第九天,她跟着祖母回来了。娘是这样的喜欢:好像娘的灵魂失去了又回来一般!她一看见娘便喊着“阿姆”,跑到娘的身边来。娘把她抱了起来,她便用手臂挽住了娘的颈,将面颊贴到娘的脸上来。”天真懂事的女孩形象和慈爱善良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菊英得了白喉之后,母亲带着菊英四处问药,“娘看起来,心要碎了!但是娘肯甘心吗?娘肯看着她死吗?娘肯舍却心肝儿吗?不的!娘是无论如何也要想法子的!娘没有钱娘去借了钱来请医生。”菊英母亲的奔波求医和备办嫁妆,都是一位母亲天然的,出于本能地对子女的爱护和责任,菊英母亲的爱并没有因为任何外因而有所改变,她把菊英当作自己的灵魂,最终却迎来了令人撕心裂肺的结局。
王鲁彦打造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故事,展示了作者對质朴、纯良人性的赞颂,他凭借简洁的语言,真实的画面感,创作出独立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地域空间,这里像一个世外桃源一般,没有物欲横流,没有针锋相对,却有着人性最自然流露出来的美,这种最原始的美便是母爱。母爱是其笔下的浙东乡土世界中最原始的、最纯粹的、最不容置疑的人性美。但是,在这种美的环境中,最致命的一点便是感受不到生命力的存在。
二.畸形民俗下生命、个性的无价值
小说开篇便是“菊英离开她已有整整的十年了”。这里的“离开”显得模糊不清,既可以是物理空间上的“离去”,也可以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法,这就为菊英和母亲之间制造了“生离”和“死别”两种可能性,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冥婚的揭示便显得顺理成章,更是加深了文章的总基调,带给读者一种“虽死犹生”的感觉。冥婚是浙东地区特异的婚俗,给已经去世的人做婚配本身就带有着一种诡异的色彩,认为死去的人仍在生长且灵魂不灭。“生死同质”便是冥婚最本质的特点,这种充满人性想象因素的习俗本义是建立一种生与死之间可以继续互通的纽带,以慰藉活着的人对死去之人的怀念,但如果死可以被当做生,那么生便会被变得毫无价值。
“生死同质”导致生的无价值。虽说是在讲菊英的出嫁,但其实是在讲菊英娘的故事,这是一个劳苦的女人,丈夫在他的生活中一直是缺席的状态,经常“半年六个月没有家信,四个月没有回家”,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目光都投注在菊英身上,菊英是“娘的心头肉,是娘的唯一的心肝儿”。菊英在世时,母亲为她而活,菊英去世十年,母亲仍然为她而活。菊英母亲从未为自己活着,她活在对菊英的回忆中,活在为菊英的忙碌中,女儿是她生命的全部和价值的凝结点。死去的人无法活着,活着的人却为了死去的人而活,一个人无法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她的生命空间便会变得越来越狭小。活着的人本应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死了的人理应得到永恒的平静,可是《菊英的出嫁》中活人的痛苦与孤独,死人的不得安宁,恰恰是冥婚文化所带来的悲剧。对死的重视便是对生的轻视,对鬼的重视便是对人的轻视,菊英给已经死去的女儿找了一个在阴间的“女婿”,置办嫁妆,敲锣打鼓,风风光光地送女儿出嫁,周围见证了这场冥婚的人们也是平静和严肃的,对冥婚的虔诚同时也是对活着的人生存价值的漠视与抹杀。当菊英的出嫁完成,菊英母亲活着的动力与方向便也随之出走,其作为母亲的权利不再拥有,留给菊英母亲的结局只剩“生不如死”。作者通过冥婚这一畸形民俗的事象,反映出封闭状态下,中国农村儿女的卑微和麻木。
父母意愿的强加导致个性的无价值。菊英去世十年后,母亲认为年龄到了,便为菊英寻摸婚事。菊英母亲认为“无论男子或女子,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想要一个老婆或老公,她相信是必然的。她确信——这用不着问菊英——菊英现在非常的需要一个丈夫了。菊英现在一定感觉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孤单。菊英所呼吸的空气一定的沉重的,闷人的。菊英一定非常的苦恼,非常的忧郁。菊英一定感觉到了活着没有趣味。或者——她想——菊英甚至于想自杀了。”一切的种种都是“她想”且“一定”的。菊英的具体情形对菊英母亲来说只能是“天可知”,但她却坚信菊英迫切地需要一个丈夫,没有丈夫甚至会让已经死去的菊英寂寞地再度自杀。一方面,菊英的母亲完全抹掉了生死的界限,把菊英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对待,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封建伦理观念带给女性的枷锁是永恒的。无论是死是活,女性的命运总是与婚姻相辅,菊英对自己的出嫁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倘若她还活着,她对于婚姻的态度也无外乎菊英母亲假设的两种,要么是她即使想要也“绝不至于说”,要么则是“当真的不晓得自己的苦恼是因何而起”于是就更加需要母亲替她打算。中国传统封建婚姻观念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偏偏没有考虑到男女双方本人的意愿,此时的两个新人完全没有话语权,在个性的意义上没有存在的价值,生和死也就没有区分的意义了。
五四时期许多现代乡土小说作家都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到了地方民俗上,民俗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能够鲜明准确地体现出一个地方的文化特点。婚礼,乃人伦之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婚礼是十分重要的民俗之一。《菊英的出嫁》中关于冥婚这一陋习的书写,把死人当活人看,把活人当死人看,“生死同质”,生与死都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体现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封闭的农村中乡民意识上的野蛮、落后与愚昧。王鲁彦对此抱持着一种反对的态度,敏锐地发现这种丑恶的封建思想因素已经潜移默化在人们无意识当中,并通过民俗的形式展现出来,试图凌迟人们麻痹的灵魂,在直面痛苦中使其觉醒。
三.奇诡的平衡
诞生于五四的中国乡土题材小说,一方面,作者要始终保持着理性意识,用冷静的眼光去审视中国农村中所存在的种种错误,试图用语言驱逐国民灵魂中的麻木,使人们摆脱封建思想和伦理纲常带来的禁锢。另一方面,中国民众的天性中带有着淳朴的一面,农村社会中也有着美的呈现,作者无法抛弃对故乡的眷恋,无法割舍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深情。即使是批判,从作者的笔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温情所在。《菊英的出嫁》虽然让我们看到了底层社会荒谬、丑陋的一面,但作者的批判力度并不如鲁迅等人的强烈,王鲁彦怀着的更多的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真实地写出了发生在浙东农村的母爱故事。人性美与风俗陋的碰撞在王鲁彦笔下竟形成了一种奇诡的平衡状态。
这种平衡来自于作者的乡情与理性的情感矛盾。随着鲁迅首先意识到了“吃人”的本质是封建礼教,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和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知识分子自然担负起了改造国民性的责任,乡土作家通过表现民俗来揭示封建宗法的害人本质。王鲁彦对于菊英母亲为菊英筹办冥婚的做法绝对是不赞同的,活人为了死人掏空自己是十分愚昧的行为。而菊英母亲对婚礼的操办那么疯狂的态度,那么虔敬的用心、那么事无巨细地考量,形成了惊心动魄的戏剧张力,一如其他庄重的民俗遗迹一样,它不会使人发笑,而是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诡异的恐怖感与压迫感。但在这可怕的风俗之下,菊英母亲对孩子的爱也是纯粹的、浓烈的,超越生死的,是不容置喙的。《菊英的出嫁》中的民俗书写大体上指向一种对封建民俗糟粕的批判,同时对底层人物的同情和隐晦的原谅在这种民俗书写中闪现出来。谁都无法去认定批判与温情那一项更加重要,更无法将两者剥离开,所以只能将对立的两者放置在天平的两侧,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
但同时,这种平衡也代表着作者对打破平衡的呼唤。五四时期的乡土作品较多受到鲁迅现实主义行文风格的影响,小说创作者的思路不断开阔,思想内涵不断加深,对创作方法的探索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王鲁彦同鲁迅一起,将中国农村的弊端展示到人们面前,让国民清楚地看到心中美好的乡土已不再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满着渣滓的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力量,试图以此唤起国民的良知,进行对国民的启蒙。只有启蒙人们从内部自发、自觉地去打破平衡,才算是对这片寄寓着浓厚情感的土地真正的、彻底的改造。
讽刺中透着同情,同情中又怀着憎恶,憎恶中又有真切的悲哀,这正是离开故乡的“老中国儿女”写故乡的“老中国儿女”的故事时,无法剥离自身的“历史中间物”属性而产生的复杂感情。菊英的离去以及离去后母亲为菊英举办冥婚的一系列操作,背后都有腐朽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文化对这位女性的影响。不同于离开故乡北上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一生无法接触到新潮思想,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一片土地,生活在自己理想中的世外桃源,被抹杀了所有存在的价值,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已然成为时代的破坏者和牺牲者。五四时期接受过进步思想的王鲁彦,明确指出了底层民众生命的悲凉背后的根源来源于无知且自满,试图将真实的图景展现在大众面前以引起国民的重视与反思,带给农民新的出路,给予时代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薛熹祯.批判与缅怀:疗救“乡土中国”的思考与实践[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04):112-123+192.
[2]朱棟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第一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61-167
[3]吕帅栋.论《菊英的出嫁》的冥婚民俗事象[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21,23(04):84-87.
[4]蔡登秋.“菊英的出嫁”的风俗隐喻[J].三明学院学报,2011,28(04):14-18.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