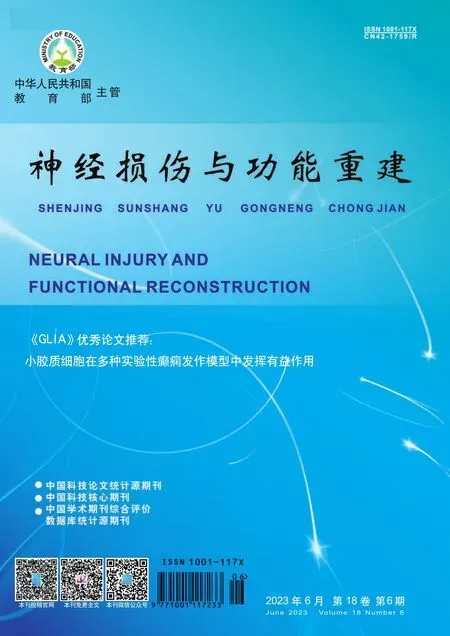复发性抗GQ1b抗体综合征1例并文献复习
林冠,王丽,孙霞,刘莎娜,肖君
抗GQ1b抗体综合征是一类由免疫介导的以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损害为主要表现的自身免疫性疾病[1]。其致病机制是由于空肠弯曲菌、流感嗜血杆菌等微生物感染后,诱导机体产生抗GQ1b抗体,该抗体与动眼、滑车、展神经,肢体的肌梭和脑干中的GQ1b抗原结合引起相应的神经损害。其特征性表现为眼外肌麻痹、共济失调和意识障碍等。抗GQ1b抗体综合征指的是一类连续的疾病谱,主要包括Miller-Fisher 综合征(Miller-Fisher syndrome,MFS),伴有眼外肌麻痹的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GBS),Bickerstaff’s 脑干脑炎(Bickerstaff’s brainstem encephalitis,BBE)和急性眼肌麻痹[2]。该病多为单相病程,预后较好,但有部分患者可出现复发。复发性抗GQ1b抗体综合征在文献中少有报道,如何预防复发更是鲜有提及。本文报道1 例复发性抗GQ1b 抗体综合征,伴血清抗GQ1b 及抗GT1a 抗体阳性,复习相关文献,探讨引起该病复发的危险因素,复发后的治疗及预后。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历资料
56 岁女性患者,因“复视伴行走不稳1 周”入院。1周前患者晨起时突然出现视物成双,头晕,行走不稳,症状持续且进行性加重。发病前6 天曾有咽痛、流涕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病程中无发热、头痛,无意识障碍,无吞咽困难及饮水呛咳等症状。既往:体健,无药物过敏史。神经系统查体:意识清楚,认知功能正常,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3 mm,光反射灵敏,眼球活动不受限。双手指鼻试验欠稳准,双下肢跟膝胫试验欠稳准,四肢肌力5 级,腱反射(+),其余无阳性体征。辅助检查:血、尿、便常规、凝血功能、生化、甲状腺功能、风湿全套、狼疮全套、女性肿瘤标记物均未见异常。腰椎穿刺脑脊液常规及生化均无异常;血清及脑脊液寡克隆带阴性。血神经节苷脂抗体:抗GQ1b抗体IgM(++),抗GT1a 抗体IgM(++),脑脊液神经节苷脂抗体阴性。头部MRI平扫同时增强未见异常改变。
根据最新的分类标准[3],患者诊断为抗GQ1b抗体综合征。临床分型为Miller-Fisher 综合征(MFS)。诊断依据:亚急性起病,有前驱感染史,有眼外肌麻痹,共济失调,腱反射减弱等MFS 的关键性临床特征。血神经节苷脂抗体:抗GQ1b 抗体IgM(++),抗GT1a 抗体IgM(++)。确诊后给予静滴人免疫球蛋白5 d[0.4 g/(kg·d)],出院后口服醋酸泼尼松片(20 mg/d)继续治疗。1 个月后患者门诊复诊,症状完全恢复,遂停用激素。距离首次发病7 个月后患者再次出现上述相同症状及体征发作,遂来门诊复诊。此次起病前无前驱感染症状。患者因经济原因未住院治疗,在门诊给予醋酸泼尼松片50 mg/d 顿服[1 mg/(kg·d)]。2 周后患者症状好转,逐渐减小激素剂量;1 个月后患者症状完全恢复,遂逐渐减停激素。距离首次发病15 个月后,患者再次因相同症状及体征发作住院治疗,此次起病前亦无前驱感染症状。复查腰椎穿刺提示:脑脊液常规未见异常;脑脊液生化总蛋白485 mg/L。复查血神经节苷脂抗体:抗GQ1b 抗体IgM(++),抗GT1a 抗体IgM(++);脑脊液神经节苷脂抗体阴性。复查头部MRI 未见明显异常。再次予以静注人免疫球蛋白5 d[0.4 g/(kg·d)],同时给予醋酸泼尼松片1 mg/(kg·d)治疗10 d 后症状好转出院。醋酸泼尼松片逐渐减量至20 mg/d 维持,出院1 月后患者复诊,症状完全恢复,继续随诊监测抗GQ1b抗体。
1.2 方法
使用Pubmed 数据库,输入关键词“recurrent anti-GQ1b antibody syndrome”或“recurrent Miller-Fisher Syndrome”,搜索时间截止2022年8月3日。检索获得的复发性抗GQ1b抗体综合征病例,从性别、首发年龄、发病次数、前驱感染情况、体征、神经节苷脂抗体检查情况、治疗及转归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获得7篇病例报道文献[4-10],总计7例患者,男女比例3∶4,平均首发年龄31.86 岁(18~63 岁),平均复发次数2.57 次。临床分型:6 例为MFS,1 例首发为MFS,复发为GBS。所有患者经积极治疗后均预后良好,详见表1。
3 讨论
抗GQ1b 抗体综合征抗是一类自身免疫相关的谱系疾病,其诊断标准目前尚无统一界定。比较公认的推荐是在临床上具有部分或全部MFS/BBE表现,如眼外肌麻痹、共济失调、腱反射改变、意识障碍等,同时伴有抗GQ1b 抗体阳性,充分排除其他疾病的情况下方可诊断[11]。
目前认为分子模拟假说是其发病机制。大部分患者起病前有上呼吸道感染、腹泻等前驱感染史。主要致病菌为空肠弯曲菌、流感嗜血杆菌。因其外膜组分脂低聚糖与GQ1b 抗原表位之间存在分子模拟。而GQ1b 抗原在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和外展神经、四肢肌梭和脑干网状结构中高表达。感染携带GQ1b 表位的微生物可诱导易感患者产生抗GQ1b 抗体。抗GQ1b 抗体与相关脑神经和肌梭表达的GQ1b 抗原结合进而致病,抗GQ1b 抗体也可能进入脑干并与GQ1b 结合,从而诱发BBE[12]。GQ1b 抗原以不同苷磷脂复合物的形式在不同部位表达,该病表现为不同的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受累的症状[13],这也是抗GQ1b抗体综合征具有不同症状组合及复杂分型的原因。
抗GQ1b抗体综合征多数表现为眼内外肌麻痹、构音障碍、共济失调、意识障碍、腱反射减弱/亢进、四肢无力、周围性面瘫和四肢感觉异常等。也有孤立性眼内肌麻痹为首发症状的报道[14]。因此在临床中出现首发表现为眼内外肌麻痹的患者,必要时需考虑完善血清神经节苷脂抗体检查,以鉴别抗GQ1b 抗体综合征。在本病例中,患者表现为眼外肌麻痹、共济失调、腱反射减弱等经典的MFS临床特征,诊断较容易。
免疫治疗是该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推荐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0.4 g/(kg·d)],连续使用5 d。亦可使用血浆置换治疗。如无条件使用上述2 种治疗,激素治疗可能是一种备选方案。免疫抑制剂治疗尚无公认的数据报道。本病例第1次使用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治愈后,第2次发作使用激素治疗,第3次发作使用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联合激素治疗,3 次治疗均取得良好疗效。但患者抗GQ1b抗体及抗GT1a抗体阳性,考虑患者症状反复,且抗体持续阳性,遂给予小剂量糖皮质激素(醋酸泼尼松20 mg/d)口服治疗随访,后续仍需随访监测患者的抗体水平及复发情况,以决定后续治疗方案。
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MFS 或BBE患病率和发病率的流行病学数据。目前已有的数据都是从现有的GBS 患者人群研究中提取的。在西方人群中,MFS 的发病率约为GBS 病例的1%~5%。而日本(约为GBS病例的25%)等亚洲国家的发病率明显较高。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BBE 的流行病学研究,但临床经验表明BBE的发生率较低[12],针对MFS的复发率更是少有文献提及。有研究表明复发性MFS 的患者首次发病年龄相比无复发的MFS患者更年轻,复发时的症状和体征较初次发作时更严重[15]。Neshige S[16]回顾性分析了93例GBS及MFS患者,其中MFS 的复发率为10.8%,且复发患者均检测出抗GQ1b 抗体阳性。有研究表明,在MFS复发的患者中,抗GQ1b抗体阳性的比例为80%[17]。导致抗GQ1b抗体综合征复发的机制尚不明确,有研究认为年龄小于30岁,表现为MFS的发作形式,是高复发风险的危险因素[18],也有研究认为,高滴度的抗GQ1b抗体持续存在,与患者持续的临床症状相符合,而临床症状的恢复,往往意味着抗体的逐渐消失。但如果患者再次出现前驱感染及接种疫苗等诱发免疫反应的因素,则会导致患者出现高复发风险及更重的临床症状[8]。在本病例中患者出现了2次症状复发;第2次复发时检测的抗体提示抗GQ1b 抗体及抗GT1a 抗体阳性。这说明抗GQ1b 抗体的持续阳性,与患者症状的复发有密切关系;及时随访,监测抗体水平变化,对于研究抗GQ1b 综合征的复发可能有一定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年轻患者、表现为MFS 样症状、持续的抗GQ1b抗体阳性可能是抗GQ1b 抗体综合征复发的危险因素,复发时其临床症状可能较初次发作更重。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及血浆置换对该病复发后的治疗均有良好疗效。本病例的报道有助于了解该疾病复发的危险因素,复发后的治疗及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