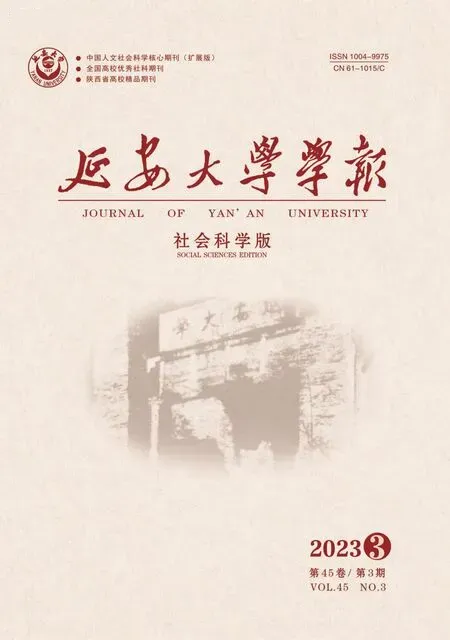元代陕北地区僧官机构与基层社会治理
——以“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为中心
杜林渊,邹 楠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现存于钟山石窟景区三号窟内,至元二十五年(1288)立石。碑高270厘米、宽87厘米、厚14厘米,座高35厘米、宽98厘米、厚63厘米。碑阳右部刊刻“重修大普济禅寺记”正文1370余字,左部为州县各级官员结衔题名;碑阴上部刻录“总昭方号之图”,详录龙泉禅师及4代门人120余名僧人的世系、法号,碑阴下部为管理各项社会事务的官吏和乡村里乣首、社长及有关功德主姓名。“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不但详细记述了大普济禅寺的兴衰变迁及成为陕北地区中心禅林的盛况,还展现了元代陕北地区州县地方政权官员设置和佛教僧官系统的大体情况。目前学界有关元代州县地方政权的研究主要是将其置于行省制度下考察,(1)相关研究著作有: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中华书局2011年版;张金铣《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而对于元代佛教僧官系统的研究,则多从制度史的视角就中央僧官和地方僧官机构的设置、演变,人员构成、沿革等方面进行讨论。(2)参见张晓桐《元代僧官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鉴于此,本文以“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文资料为中心,结合相关文献,对碑文中所反映的元代延安路州县地方政权及州县佛教僧官系统进行初步讨论。
一、“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志录文
碑阳左部州县各级官吏结衔题名:
都功德主前安定县长官:刘珍。进义副尉延安路打捕鹰房提领:刘克温。维那:张孜、冯玉。本路匠人所大使:杨外剌女。本县两务提领:魏公德。前安定县达鲁花赤:速怱都,次官:张初、马琇。丹头县官:史瑞。白洛县官:乔彦祐。前保安州太守:边再荣。前本县捕盗官:胡伯春,学录:魏守恩。从仕郎安定县尹兼诸军奥鲁劝农事:张邦献,典史:刘珦,司吏:张安智、井元、皇甫谦、魏克明。陕西前管山西失散民户提领:史裕,长官:史珪,前打捕提领:史良。敦武校尉安定县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劝农事:塔剌海,盐司提举:魏公道。绥德州前吏目:赵彧。安定务官:张卞、刘玉。丹头前务官:史琚、李德、武义。延州判官:冯绅。宣授延安路都僧录司弘教大师:伟吉祥。安定县都纲善惠普安大师:赞吉祥。中部县都纲立宗普通大师:揀吉祥。鄜州洛交县令:苏瑞。
碑阴下部有关功德主题名:
前本县务官:景仲良、魏公美、刘克良、冯智、马谦。投下长官:缑伯通,次官:张文顺、景德山、景珍,招抚:黎昌。延川监官:董瑁,百户:张志玉,屯田次官:闫宝、闫志才。延长管军弹压:贺福,征行弹压:边亨。本县库使:呼延顺,乘发司:曹德、胡山。泰安村:曹义、宜秀、折永忠、(男)折彦良、折彦温、屈秀、康迁、(弟)康玉、(男)康得禄、康福、(社长)曹顺、曹元、刘子忠、高秀、高稔、曹忠宝、曹忠玉、曹忠贵、史世皋。常乐村:(万户)李玘、(男)李伯全、韦伯通、(男)(社长)韦广、(孙)韦文贵、石子山、(弟)石子珍、石子川、(男)石忠显、石忠贵、何全、乔顺和。泰安村:冯珪、冯广、冯贵、冯德安。广积村:张勇山、王福得、何义、李秉、张贵、吴进、王君、李仲。永宁村:(社长)弥恩、张再立、张庆。普济村:刘友、高伯青、高显、(社长)韦得用、刘志荣、刘志才、杨顺、乔思明、张安礼、刘孜、雷显、乔思忠。丰盈村:吴恩、高七、李文彦。延寿村:韦伯全、何秀。利民村:张友。延川乐人提控:张耍和、张君美、杨世和、刘小快活、刘市乔、张小眼。医公管勾:魏玉、金资禄、强子文。丹头务都监:冯彦通。本县宣差:李惜剌。本寺助工:杨万、王觉护、管千。纠首都维那:张钦,善友:王德、刘克恭、冯亨、顾助绿。
二、碑文所见元代州县文官系统官员及长官属吏
《元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五·百官一》载:“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1]2120元代地方行政机构设置有行省、路、府、州、县五级。每省设丞相及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一至二名,均为一二品大员,属官有郎中、员外郎、都事以及掾史等。[1]2305各路置总管府管理军政民政,长官称为总管或都总管,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提控案牍等。元代府的行政级别有两种情况,一是直属于省,一是隶属于路。府的长官称知府或府尹,属官有同知、判官、推官、知事等。州也可分为两类:一种直隶于省,一种是属州,隶于路或直隶府。州的长官,在路级者为尹,属州的长官称知州,属官有同知、判官、知事、吏目、提控案牍等。县是最后一级行政区,县的长官称尹。如碑文中“从仕郎安定县尹兼诸军奥鲁劝农事:张邦献”。碑文中提到的县级较重要的官员还有“敦武校尉安定县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劝农事:塔剌海”。元代官制特殊之处,就是在路府州县长官之外,还设置一名达鲁花赤。比如“前安定县达鲁花赤:速忽都”。“达鲁花赤,亦做‘答鲁合臣’‘达鲁噶齐’,蒙古语,意为‘镇守者’。”[2]64汉语文献也称“监”,监某州、监某府、监某路,他们负责监督各级地方官,权力极大。“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1]2120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1]106由此可知,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掌控地方各级政权的实际权力。
此外,碑文中还记载了“鄜州洛交县令:苏瑞”“丹头县官:史瑞”两个官职。据《元史卷六十·志第十二·地理三》载:“鄜州,……旧领洛交、洛川、鄜城、直罗四县。至元四年,并鄜城入洛川,又并洛交、直罗入州。六年,废坊州,以中部、宜君二县来属。领三县:洛川,中部,宜君。”[1]1426至元四年(1267),洛交县已撤县入州,但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立石的“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中还有“鄜州洛交县令苏瑞”的记载,这可能是中央下达的政令到达地方落实有一定的时间差,抑或是过去的行政建置在当地民众心中影响深远,为了凸显人物身份而故意为之。再如,“安定,……元壬子年升为安定县。至元元年,析置丹头县。四年,并丹头入本县”。[1]1425至元四年(1267)丹头县被并入安定县,查阅陕西地方志丛书《子长县志》,其中也记载了“至元元年析置丹头县,至元四年撤丹头县并入安定县”。[3]67但在碑文中还出现了“丹头县官:史瑞”的记载,此情况可能也是上述原因所致。
碑文除记载上述官员之外,还涉及州县长官的部分属吏。
判官:辽金元时期,于府州设同知,作为主官的副职。其下又设判官,上州一人,正七品;中州一人,从七品;下州一人,正八品。[1]2317其职责为协助州尹或知州、同知处理政务,兼捕盗之事,“州判官在正官中品秩最低,但同样能对州政施加影响”。[4]708
司吏:“司吏设置在路、府、州、县和录事司等地方基层衙门。”[5]42宋代称手分,金代改称司吏,元代沿置。县司吏从贴书等见习书吏和巡尉司吏中选充,如安定县“司吏:张安智、井元、皇甫谦、魏克明”等。路府州的司吏依次从低一级的衙门中选充,考满出任典史、吏目等流外官。元代流外官的级别,由低到高依次为典史、吏目、都目、提控案牍,提控案牍考满,方许入流。[1]2047
典史:元代县典史是指县级官府中负责统辖文职吏员以及案牍等事务的首领官,是对宋、金旧制的承袭和发展。[6]50如“典史刘珦”。按《元史·百官志》,上县、中县的典史员额为二员,下县为一员。[1]2318如由路府州县司吏考核充任,一般可升为吏目,县典史的迁转主要是担任吏目或仓库官。
吏目:元从金制,于中、下州设吏目一至二人,为知州的直接属员,如“绥德州前吏目赵彧”等。“州千里之地,建其牧,有长有贰。而案牍之寄,则有吏目。所以达民吏之情,而受成于长贰者也。事之然不然,可不可,长贰不得独决于上,必于吏目折中焉。于是,狱讼簿书始于吏手之拟度,而成于吏目之笔削。”[7]27凡由吏目升入者,则为提控案牍,掌管衙内文书等日常事务和管理吏员,为衙署吏员首领,故又称都目。都目和吏目,常被统称为都吏目,官秩均未入流。
学录:元代地方学官名,置于路儒学内,协助教授教育所属生员。诸路各设儒学教授一员,及学正一员、学录一员。[1]2316由此可知碑文中“学录魏守恩”系延安路儒学学官。“直学考满,又试所业十篇,升为学录、教谕。……谕、录历两考,升正、长。”[1]2033学录由任满并经考核合格的直学中选任,之后可升任学正或山长。元代始终常设的地方学官,一是专司儒学管理、主管地方学务,设于各省儒学提举司的儒学提举、副提举等;二是兼有教师职务,在路、府、州、县学或书院主持教学日常事务的教官,有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和主管学校或书院钱粮、房产、书籍的直学。[8]83
县务官:于元代职官志中无考,可能为县尹属官的统称,如碑文中的“前本县务官:景仲良、魏公美、刘克良、冯智、马谦”等。
两务提领:元大都留守司所属各司局属官多以提领为名,如“上都、大都貂鼠软皮等局提领所,提领二员”。[1]2255路一级行政机构也有掌管某一方面事务的提领一职,如“保定等路打捕提领所,秩从七品。提领四员,典史一员。至元十一年,收集人户为打捕户计,及招到管丝银差发税粮等户,立提领所”。[1]2252元代县级行政机构复杂,权责明确,管理人员较多,碑文中“本县两务提领:魏公德”职责应是县衙掌管俸禄或赋税事务的官吏之一。
捕盗官:元朝掌管缉捕匪盗的衙役头目称为捕盗官。《元史·陈祐列传》载:“所拟事条,皆切于时用。于是严督有司,捕得盗贼甚众,皆杖杀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选捕盗官及弓兵,密授方略,示以赏罚,使追捕之”,[1]3947对于逃亡至他境的盗贼官府选任捕盗官及弓兵进行追捕,“如限内不获,其捕盗官,强盗停俸两月,窃盗一月”。[1]2595这里的“盗”主要包括强盗和窃盗,碑文中的“前本县捕盗官:胡伯春”也应属此。
盐司提举:食盐是关乎国计民生及古代朝廷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备受重视,历朝历代均设置管理、运输盐务的专门机构和官员。元代重视盐课,盐业组织管理严密,机构庞大,大体分为盐运司、分司、盐场司三级制。[9]20元朝在河东陕西设盐运司,延安路地接盐池,也特设专管盐务的官员,如“盐司提举:魏公道”。
乐人提控:中国古代以乐人为贱业,从业者称乐户。其中有犯罪官员或家属充当此役者,称充乐,世代皆为乐户。元时设天乐署,初名昭和署,管领河西乐人,至元十七年(1280)始置。其官有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协音一员,协律一员,书史二人,书吏四人,教师二人,提控四人。[1]2139碑文中的“延川乐人提控:张耍和、张君美、杨世和、刘小快活、刘市乔、张小眼”即为延川县管理乐人的官吏。
医公管勾:元代管理地方医药事务的小吏,如碑文中的“医公管勾:魏玉、金资禄、强子文”等。
匠人所大使:元代在大都及各路均设有管理军器、民匠、织造、毛毡等诸色匠人的总管府、提举司、匠人所等机构,以总管、提举等官员统之。“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二员,经历、知事、提控案牍、照磨各一员。至元二十年,为管领织染段匹匠人设总管府。”[1]2262碑文中“本路匠人所大使:杨外剌女”应当是延安路管理诸色工匠的官员。
碑文中还涉及元代州县管理官府财物仓库的官员库使,如“本县库使:呼延顺”;负责发送文书、告示的吏员乘发司,如“乘发司:曹德、胡山”。除了记载州县文官系统官员及长官属吏,碑文还提及元代州县武官系统官员。陕西行省一直是元朝西部边地的军政大本营,充当军需供应基地,在有效治理控驭西部北部边疆,维持元帝国百年统治方面,功莫大矣。[10]53如此重要地位在碑文中关于州县武官系统及州县屯田系统官员的记载中也可反映。
三、碑文所见元代延安路州县武官及屯田系统官员
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贵族分别执政,军队主官几乎完全由本族贵族担任,军队按原部落组织编制,战时与平时的军事组织相一致。《元史·兵一》载:“若夫军士,则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1]2508元代军队的主体则是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蒙古军以蒙古族人为主。探马赤军地位仅次于蒙古军,是独立于蒙古军之外的一个军种。探马赤军中的民族成分复杂,早期探马赤军中曾有蒙古人和汉人,其主要则是由色目人组成,当时有三十多个民族被称为色目人。“探马赤军军中来自西北的民族,有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阿速、哈剌鲁、唐兀等。”[11]83元朝军队以户口多寡组成万户所、千户所、百户所,军队主官万户、千户、百户多由蒙古人担任,各级军官均可世袭。作战时,领兵出征的大将可以称元帅,但无将军之类名号。另外,屯田的军民也以户口多少组成万户、千户、百户。
“元代屯田遍布全国各地,其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12]115元朝实行屯田的时间很早,又分为军屯和民屯。军屯是驻防在全国各地的军队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民屯则是由地方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屯田。元代在西北屯田的全盛时期主要为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这一时期的西北屯田主要分布于当时陕西行省和甘肃行省境内。在此背景下,至元二十五年(1288)立石的“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中也记载了部分屯田系统官员。据《元史·卷一百·兵志三·屯田》可知,陕西行省所辖军屯7处,为陕西等处屯田万户府和贵赤所属;民屯9处,主要为陕西屯田总管府所属。[1]2567
元代在陕西行省的军民屯垦,不但部分满足当地驻军的需要,而且还为巩固西北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元政府在陕西行省主要设陕西屯田总管府、陕西等处万户府和贵赤延安总管府三个机构分管屯田,在“地处僻远的屯田设经略司、提举司,或直接由路府县管辖,说明元代屯田管理机构比宋要严密得多”。[13]99“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文中涉及元代州县武官系统及州县屯田系统相关的官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万户:金元时期的武官名。元代以万户设万夫之长,隶属于中央枢密院。而驻于各路者的,则隶属于各行省。同时规定:统兵7000以上者,称上万户府;5000以上者,称中万户府;3000以上者,称下万户府。诸路万户府各设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副万户一员;其官皆世袭,有功则升之。[1]2310碑文中的“常乐村万户:李玘”可能是由汉人组成的下万户府之长。
千户:元代设千户为千夫之长,隶属于万户,驻于各路者的,则分属于诸路万户府。统兵700以上者称上千户所;500以上者称中千户所;300以上者称下千户所。各千户所设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1]2311碑文中的“总管千护(户):王文见”可能是由汉人组成的千户所之长。元代千户所下设属官弹压,“上千户所弹压二员俱作从八品,蒙古人一员、汉儿人一员;中千户所弹压二员俱作从九品,蒙古人一员、汉儿人一员;下千户所弹压二员俱作从九品,蒙古人一员、汉儿人一员”。[14]140弹压分掌各种事务,如碑文中的“延长管军弹压:贺福,征行弹压:边亨”。
百户:元代设百户为百夫之长,隶属于千户所,为世袭军职,驻于各地。上百户所设蒙、汉百户各一员,下百户所设百户一员。[1]2311碑文中的“百户:张志玉”则是由汉人组成的百户所之长。
奥鲁:元代军制,军人在军前入军籍,军人族属留住之所称奥鲁,奥鲁官的职责是管领军户家属,故军士“军前明有军籍,奥鲁官有奥鲁籍”。碑文中的“从仕郎安定县尹兼诸军奥鲁劝农事:张邦献”“敦武校尉安定县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劝农事:塔剌海”即属此职责。
打捕提领:根据《元史·百官二》载,“延安屯田打捕总管府,秩从三品。管析居放良人户,并兀里吉思田地北来蒙古人户。至元十八年始设,定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属官打捕屯田官一十二员”。[1]2169碑文中的“前打捕提领:史良”,即为延安屯田打捕总管府“打捕屯田官一十二员”中的一员。
陕西前管山西失散民户提领:此官应是负责招徕、安置、管理山西流民事务的官员。元灭南宋后,许多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流动人口,各地流民问题成为社会隐患。龙泉禅师长期住持普济禅院,广授门徒,普济禅院的辖理远及晋豫。[15]127或许是由于普济禅寺的影响,吸引了山西的部分流民前往陕西,所以朝廷在此专设陕西前管山西失散民户提领。
屯田次官:碑文中的“屯田次官:闫宝、闫志才”,应是延安屯田打捕总管的副手同知或经历、知事。
投下长官,又作头下长官:元袭辽制,对战时获得的俘户和私家奴隶称投下户,其管理者称投下管民总管,俗称投下长官。如“投下长官:缑伯通,次官:张文顺、景德山、景珍,招抚:黎昌。”据此可知投下长官应有协助其公务的副手次官以及负责招抚降众的招抚等属官。又如洛川出土至治二年(1322)“乡丈王公墓志”载:王公“又次子曰彝,今为投下管民总管”,[16]52其职务即为投下长官。
另外,还有打捕鹰房:据《元史·百官六》,“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总管府,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同知一员,副总管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至元十七年置”。[1]2302至元十八年(1281)延安屯田打捕总管府始设,碑文中的“进义副尉延安路打捕鹰房提领:刘克温”,应是延安路打捕鹰房提领的属官。
四、碑文所见元代村社制度
我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国家行政权与地方自治权相结合的方式。传统社会中,在国家最低一级行政区划县级以下,会有一些地方性的基层行政单位乡、里、亭等,其掌事者统称乡官。这些乡官一般由民间公推“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并经过县官认可而担任。历朝大体沿袭秦汉乡里制度,只是名称与编制不同。如唐代以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五保为里,五里为乡。一里之长为里正,一乡之长为乡长。元代承袭前代之制,如洛川出土元代“乡丈王公墓志”说王公之父王用“当金季扰攘之后,徙于鄜城县修回里居焉。公亦以耕自隐,不求闻达”。[16]52“乡丈”也可能是“乡长”之尊称。元代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是社,社的编制是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结成的,故称为村社。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社”一方面具有以自然村落为基础而结成的民间自助组织的性质,同时也长期被统治者利用,成为乡村基层行政组织。因此,“它具有农村民众互助和政府基层行政组织的双重性质,在中国古代乡村制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17]35“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文中就记载了泰安村、常乐村、永宁村、普济村社长一职任职人员的名单,这些信息对于了解元时的村社制度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元朝统一前,北方处在金朝统治之下。金代自然村落称为“村”或“社”,泛称“村社”,在乡村即以村社为编制,置里正、主首司其职。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置主首以佐里正禁察非违。[18]1031南方在南宋的统治下,实行的是保甲制度,但都保组织只是在乡的范围内编排,不能跨乡,因此形成了乡、都保、大保、保的乡村组织系统。蒙古入主中原初期,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元朝统治者采取了大力恢复农业生产,将农民控制在土地上的措施。基于实际需要和汉族社会“出入相扶,守望相助”的传统及民间自发结社互助意义的影响,元朝统治者沿袭金制,建立了旨在加强地方基层统治的村社制度,在农村设置里正、主首管理事务。在恢复农业发展的同时,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将民间自发的互助结社纳入政府的统治轨道。
至元七年(1271)颁布立社法令,始在北方各农村推行村社制。“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1]2354南宋灭亡后,元朝又将村社制推行到南方地区。其初衷是希望使“社”成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1]2355因此,担任社长的条件不是考虑资产,也不规定任期,而是需要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1]2355因此,作为村社的第一个职能,社长劝农的职责十分明显,需要检查监督社员的种植情况,因为村社的中心任务是从事农业生产。“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与科差事。”[1]2355甚至官方也规定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使得社长能够专一劝课农桑,不致惰废。
村社的第二个职能是教化。“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仍大书其所犯于门,俟其改过自新乃毁,如终岁不改,罚其代充本社夫役。”[1]2355对于不服从管教的籍其姓名,候提点官责之;对于不敬重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也是先听从社长教导,如遇不改,于门首大字粉壁书写其所犯过错。如本人改过自新,可以毁去粉壁。如终是不改,罚其充当本社合著夫役。由此可见,村社的教化职能对元代基层统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汉时设立的掌教化的三老制度颇有相似之处,都促进了乡村基层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
村社的第三个职能是互助。“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1]2355乡里互助是中国民间的优良传统,村民自发的结社也具有互助性质。“仁宗皇庆二年,复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许耕其半。盖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地中,蝗蝻遗种皆为日所曝死,次年所种,必盛于常禾也。……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莳桑苗,以社长领之,分给各社。”[1]2356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也因为村社制的存在而有所缓解,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村社的第四个职能是催征赋役。由于元代的社在组织上远较金代严密,在具体运行中常作为政府征调赋役的工具,社长的职责也从劝课农桑扩展到催征赋役,因此,社成为元政府征调差科的基本单位。
此外,据《元史》载:“诸伪造宝钞,首谋起意,并雕版抄纸,收买颜料,书填字号,窝藏印造,但同情者皆处死,仍没其家产。两邻知而不首者,杖七十七。坊[里]正、主首、社长失觉察,[一]并巡捕军兵,各笞四十七。”[1]2668如果社长没有察觉到村社内违法行为的发生就会受到处罚,据此可知村社还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19]452可见社长还具有解决一般诉讼纷争的职责。
元代的村社制度见于“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的有常乐村“社长:韦广”、永宁村“社长:弥恩”、普济村“社长:韦得用”等。可见元代村社制的实行范围与落实程度,村社制加强了元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碑文中关于安定县村落建置的记载也可增加我们对元代地方村落设置及政区变迁的了解。
五、碑文所见元代州县佛教僧官系统
有元一代,实行前所未有的宗教宽容政策,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在元朝得到发展。自成吉思汗以下,元朝历代统治者对汉传佛教及其重要的僧人都奉行礼遇的政策。“自世祖忽必烈始,藏传佛教受到空前尊崇。”[20]6无论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反映了佛教在当时的优崇地位。佛教的兴盛必然促进元朝僧官制度的完善。《元史·世祖三》载:“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仍于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1]106释教总统所是元代设置最早的一个中央级的僧官机构,其职能包括僧官的选任与管理、组织讲学和禅会等。“至元初,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1]2193释教总统所之后,忽必烈于至元元年(1264)又创设总制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如大征伐,则会枢府议”。[1]2193这时的总制院除全盘接替了释教总统所在中央的职能外,还需处理吐蕃境内政、教、军、民诸项事务。“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院。”[1]2193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宣政院“置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参议二员、经历二员、都事四员、管勾一员、照磨一员。”[1]2193这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设置情况,此后官员的类别和数额都在不断变化之中。
元代地方上的佛教事务除在宣政院的统一管辖之下,还先后设立了诸路释教总统所和行宣政院管理地方佛教事务。元代设置的地方性僧务机构主要有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的设置基本与路、府、州、县行政建制相适应。路、府设有僧录司,僧录司的主要僧官为僧录、僧判;州设僧正司,僧正司的僧官称僧正;县设都纲司,都纲司的僧官称正、副都纲。这些地方性的僧务机构根本职责是处理并督导各路、府、州、县的佛教事务。此外,朝廷还在个别时期设立过白云宗总摄所、头陀禅录司、崇教所、江淮诸路御讲所、广教总管府等机构,这些僧务机构性质或职能都比较单一,设置的时间也不长。元代地方僧官的选任还需通过试经,“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1]106可见元代负责处理佛教事务的官员佛学造诣都非常之高。
陕北地区作为古代中原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绳结”之地,在历年的多民族交融之中,民众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逐渐提升。金元时期,道教在延安地区发展迅速,得到当地官府与百姓的支持。[21]55北朝时期,佛教便沿着葫芦河、延河流域传入陕北,宋夏金时期,信佛风气弥漫,大量石窟造像纷纷涌现,直到元代达到鼎盛。位于今延安子长市安定镇境内的钟山石窟(石宫寺)是宋代陕北地区开凿的最大佛教石窟,也是宋代以来北方地区佛教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承载了丰富的宗教思想内涵和历史文化信息。从“总昭方号之图”来看,其所统辖的下院多达17座,分布于陕北各地和关中长安、泾阳邠州之地,甚至远在蜀东的瑞严禅师善淮也是龙泉大师的弟子。由此可见,金元时期石宫寺在陕北地区佛教地位之崇高,而“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文中涉及的部分僧官及职事僧内容则进一步加深对于元代僧官制度的了解。
都僧录司:元代利用佛教维持其统治,政事中以佛事为首,设宣政院,官阶从一品,掌管佛教僧徒及吐蕃之境政务。在原南宋区域设立释教总管。“戊申,立广教总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凡十六所:曰京畿山后道,曰河东山右道,……曰四川诸路,曰云南诸路。秩正三品,府设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员,宣政院选流内官拟注以闻,总管则僧为之。”[1]776至顺二年(1302年)在全国十六道设立广教总管府,各路设都僧录司。“宣授延安路都僧录司弘教大师:伟吉祥”即由朝廷任命的延安路最高僧官,主管延安路的佛教事务。
都纲:元代在各县设立都纲司,由僧官都纲主持该县佛教事务,如“安定县都纲善惠普安大师赞吉祥,中部县都纲立宗普通大师:揀吉祥”。
维那:维那是梵语的音译,意为“悦众”。其职责是“纲维众僧,曲尽调摄”。“维那:张孜、冯玉”就是负责寺院僧众的进退威仪,监督众僧执行佛律和寺规,遵照清规维持寺院日常秩序。
碑阳右部“重修大普济禅寺记”正文最后一句:“至元二十五年岁次戊子三月,姑洗朔乙酉二十四日戊申,大普济禅寺住持沙门:惠赞,院主僧:善远,副院:善缘等立石。”此处提到立碑人的身份为“住持”“院主”。
住持:寺院的最高僧职,一院之主,是寺院的总管。原意是“久住护持佛法”。[22]16元代在前人编修的僧制基础之上,修成《敕修百丈清规》,寺院组织实行寺主、上座、维那“三钢”制度。并将寺主改称住持,义为安住而维持佛法。住持又俗称方丈,意谓所住只有一丈见方之地,地方虽狭窄,但容量无限。“大普济禅寺住持沙门:惠赞”即为主管全寺佛事的寺主。
院主:又称监院、都监寺、主首。寺院在不设总监寺的情况下,院主就作为管理寺院内部日常事务的负责者。“在未有都寺以前,总管一寺庶务;增设都寺之后,在都寺领导下分管寺中部分庶务。”[22]223碑文中“院主僧:善远,副院:善缘”即为此僧职的正、副职。
“重修大普济禅寺记”题铭中的大量元代州县地方政权的军政机构、屯田机构及官吏构成的记载,有的可见于《元史》,有的于文献无考,这些内容不但可补史籍阙漏一二,同时还刊录了元代延安路地方村社制度以及州县佛教僧官系统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对碑铭内容的考释可知:元代地方行政管理系统较为完善,州县地方官及其属吏的行政管理覆盖了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通常所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还具体到社会治安、医疗、手工业等方面,并通过进一步完善村社制度实现了对乡村地区的紧密控制,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碑文中的达鲁花赤一职也印证了元时地方官制的特殊性,即地方各级最高长官均由蒙古人担任,通过该职,元朝统治者把地方控制权集中到蒙古贵族手中,保障了蒙古贵族的特权,实现了对广大疆域的严格管理。此外,碑阴上部刻录的“总昭方号之图”,详录龙泉禅师4代门人120余名僧人的世系、法号及遍布各地的下院,勾勒出一个庞大的僧团体系,表明当时大普济禅寺(今子长市钟山石窟)在此已成为延安路(今陕北地区)僧侣教育培养和宗教传播的中心,同时也体现了元代对地方佛教寺院严密地组织管理。在元朝中央政府内,设置有掌管佛教的机构宣政院、掌管道教的机构集贤院、掌管基督教的机构崇福司,地方则形成了与路、府、州、县各级行政建制相匹配的僧务机构系统,实现了国家对宗教的全面管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