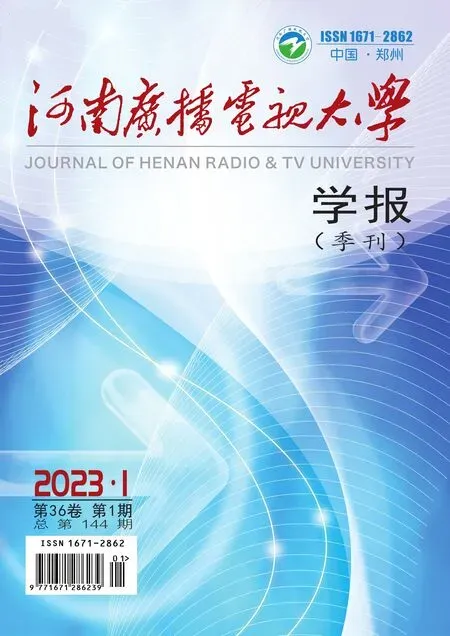《俗女养成记》:镜像结构下的女性出走与归来
刘 影
(安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女性”是重要的书写立场,女性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嬗变折射出现实社会价值观的判断,也反映着中国当代社会女性观念的变迁。近年来,女性作品蓬勃发展,塑造了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21世纪初台湾青春偶像剧诞生,以《流星花园》为代表塑造了一系列“傻白甜”式的“玛丽苏”形象,构造了灰姑娘嫁给王子美梦成真的“甜宠”戏路。2010年《杜拉拉升职记》展现了普通女性从职场小白奋斗到精英的逆袭人生,成功开创“玛丽苏2.0”版本的当代“大女主”。“甜宠剧”满足戏内外观众感情挫败的内心幻想,“大女主”戏强调“强”“爽”给生活于困顿中的职场女性提供了“乌托邦式”的想象,在众多的女性作品中,其银幕形象没有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我们始终也没能在屏幕上找到那个普通又平凡的“自我”。脱离了“甜宠”“强”“爽”影视作品能否给我们带来新的期待,2019年导演严艺文带着她的《俗女养成记》走进大众的视线。
一、镜像结构:女性自我的全新表达
《俗女养成记》从编剧、导演到主演都是40+大龄单身女性,其所传递的“俗女”精神内核更是一部彻底的女性题材电视剧。故事采用第一人称自传体的叙事,从两个故事线展开,一条是39岁的陈嘉玲回到台南重启人生,另一条是生活于台南的童年陈嘉玲的故事,将童年时的认知和当下的人生对照讲述,将大龄女青年的都市困境与五彩斑斓的故乡回忆交织起来,在温暖的散文式结构中探讨现代女性追求独立自我的可能性。近年来,女性题材电视剧一般以都市生活为背景,而《俗女养成记》则是一部地道的乡土剧。开头“我叫陈嘉玲,一个住在台北不过永远不是台北人的台南女儿”的自白,就交代了台北和台南两个地域时空,在一组相互对话与碰撞的时空与文化语境中,讲述一个女性做出大量反叛传统观念的行为,这是此前女性题材电视剧所不曾具备的立意与深度。
拉康镜像理论认为,完整人格的自我意识确立需要两个层次:想象界和象征界。“想象界”是自我意识的萌芽阶段,婴儿与自己镜像产生认同,这种自我识别标志着实体的“我”首次出现,但其尚不具备现实的认同意义。“象征界”是自我身份真正确定的符号世界,个体进入文化环境与“他者”建立联系,从而确立自我“主体化”,并彰显主体的价值[1]。第一季通过精心设计的镜像式结构,在相似的主题叙事中进行互文观照,让40岁的陈嘉玲作为“俗女”的特质逐渐变得清晰。第二季中陈嘉玲回到台南乡下开始人生下半场,熟悉的家人、朋友重新走入她的生活,在逐渐与自己、他人和世界的对话与碰撞中,陈嘉玲依然是“俗女”,只是此时她已经蜕变成自在自为的独立主体。自此陈嘉玲完成了拉康镜像阶段的跨越,关于女性自我、成长等命题也表达得流畅自然、清新脱俗。
“想象界”是通过镜像式结构认识自我的过程,《俗女养成记》中童年生活就是镜像式的对照存在,在不断追溯童年中,陈嘉玲重新确认自我。邻居家阿娟姐姐和男生谈恋爱,读小学的陈嘉玲和蔡永森负责当情书邮递员,导演设计了一组旁观式的镜头。一边是小嘉玲懵懂地听阿娟姐姐讲爱情的甜蜜,另一边是奶奶拿走了小嘉玲弄丢的情书,在整条街当丑闻来传阅,和少年真挚的情感比起来,大人们的嘴脸在此刻变得那么市侩。残酷保守的环境对情窦初开女孩“荡妇羞辱”式的残酷惩戒使陈嘉玲对爱情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成年的陈嘉玲在接受男友求婚之后,又遇到了令其心动的男性,她对着镜子先是傻笑,又骂自己无耻。镜像内外的陈嘉玲犹如童年时期与阿娟姐姐的对视,不被允许的爱情一定是痛苦的,陈嘉玲打消了她的念头。正是在这样镜像式的结构中,陈嘉玲逐渐建立起完整的自我意识。
“自我”在对“他者”的辨认过程中,走出镜像阶段,完成“自我”与“他者”的认同过程,从而生成“主体”[2]。如果说第一季重在发现自我,第二季则重在建构自我。更年期带来的恐慌使她加深年龄焦虑、容貌焦虑,表姐的到来使她意识到“淑女”的人生也有不为人知的痛楚,爸爸出轨使她第一次担当起妈妈坚实的依靠,弟弟面对恋爱时的犹豫不决使她更加坚定“决不妥协”的人生态度,阴差阳错的孕检使她第一次听到孩子的心跳声鼓起当妈妈的勇气,众多的“他者”让陈嘉玲在追求自我的道路上勇敢地聆听自己的声音,成为自由人生的选择者。
拉康关于“镜像阶段”的理论直接影响了当代电影“银幕/镜”的观点。观众所“凝视”的银幕形象,是自我幻想在银幕中的替代品,当观众在银幕中找到自我定位时,镜像阶段的凝视与认同就变成了电影观众的自我认同。原著作者江鹅认为,“俗女”就是普通女孩,那种没有成为世俗意义上好命女人的普通女孩,陈嘉玲就是这样一个俗女,她像极了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故事大量电影化的表现手法与细腻的生活场景足够跨越时代与地域,仿佛你我曾经历过的故事,让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都能体会共情的温馨。“你是被捡回来”式的离家出走,“别人家的孩子”式的攀比竞争,“学钢琴半途而废”式的不成材,强烈的人物与场景真实感,引起观众与剧中人物共鸣与共享,于是陈嘉玲的逆袭之路同样也是观众认同自我、重构自我的反思之路。
二、出走的“她者”:彰显女性意识
人类文明史是不断发现“他者”和追逐“自我”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男女之性别固然是指一种先天的、生理上的差异,但更重要的表现为一种后天形成的‘性属’上的差异”[3],女权运动的兴起正是源于对“他者”身份的抗争。“生命是对生成的肯定,它是一种生成之在[4]。在德勒兹关于生命的论述中,强调生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发现新的可能性,由此他认为“出走”便是某种意义上的生成,它意味着对过去的舍弃及逃离生命的桎梏。讲述“她者”的出走故事,是当代女性题材的“元叙事”,出走的女性也成为文艺作品中的叙事焦点和舆论热点,而《俗女养成记》就其根本来说就是一个“她者”出走的故事。
阿嬷,一个市井老太太,她的一生都在为家人操劳,在晚年之时帮朋友照看房子,她拥有了短暂的“出走”,感受前所未有的自由。当陈嘉玲步姑姑后尘黯然归乡,阿嬷不再讽刺而是羡慕这样勇敢洒脱的女性。小时候被喊“阿月”“月英”,嫁人后名字变成“陈李月英”,外人叫“陈太太”“老板娘”“医生娘”,家里叫“妈妈”“阿嬷”,她只是好久没听到自己名字了,走到生命尽头,她想与大海为伴,做回原原本本的自己。当最后她的骨灰撒向大海,阿嬷完成从身体到灵魂的“出走”。她的“出走”并不轰轰烈烈也不算彻底,但是她以细微躬体力行,为童年的陈嘉玲积攒勇气,赋予她“超凡脱俗”的勇气。
陈妈妈,一辈子任劳任怨的东方母亲形象,不成熟的丈夫、叛逆的女儿还有同性恋的儿子,让她为这个家庭操碎了心。当遭遇到爸爸背叛后,她愤然离家出走开始一段公路旅行,原来小学毕业的陈妈妈会开车、会游泳、会英语,她有那么多隐藏技能只是为了给男人留点面子。“出走”的陈妈妈在旅行中疗愈释放她的愤怒,然而,脱离了家庭的琐碎之后,她突然陷入无所事事的空虚,第一次拥抱一个人的世界,她发现草地很软、天空很蓝,一个人荡秋千的闲暇时光让她感受到乏味生活中自由自在的气息。
陈嘉玲是“俗女”,那么洪育萱便是社会语境中的“淑女”,在淑女与俗女之间是世俗实用价值观与自我意识的碰撞。在故事开始陈嘉玲也并非一无所有,她拥有即将步入婚姻的男朋友,助理的工作也做得游刃有余,只要顺着这个方向努力一下,她马上就要拥有在别人看起来还不错的人生了。然而故事动人之处在于最后关头她主动选择了“失败”,从岁月静好中“出走”,开始她披荆斩棘的新生活。洪育萱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小孩,可即便如此“好命”依然面临生活中的疾苦。她犹如金丝雀一般精致,哪怕被家暴,也要精心抹去痕迹,她永远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似乎假装不是自己,那些痛苦的真相就不属于自己了。洪育萱从淑女式的阔太生活中“出走”受尽现实的碾压,都以为她要放弃挣扎了,她却选择一切从零开始。
“出走”意味着一种深沉潜在而又呼啸澎湃的生命内驱力。《俗女养成记》中的女性,无一不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违背观众“政治正确”预期的另类选择。如果说阿嬷的“出走”是在多重社会身份中对纯粹自我的追忆,陈妈妈的“出走”则是家庭生活对女性身份桎梏的反思,洪育萱的“出走”是对婚姻中女性被压抑被摧残的反抗,陈嘉玲的“出走”是恋爱中追求独立自我的选择。对于恋爱、婚姻、家庭、社会不同阶段女性生活的内在剖析,我们看到女性生存永恒之困境,这些女性又何尝不是铿锵攀爬于时代风口女性的共同背影,她们以“出走”的方式摆脱对“他者”的依附,在不断碰撞的历练中,逐渐建立用独立精神大写的“她者”形象。
三、重构自我:追寻个体价值
生命进程中所有的转变都包含着缺失,在这主观欲求和客观镜像分裂的处境中,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年龄焦虑、多重社会角色的束缚等都是女性不得不面临的基本事实,如何超越女性永恒的困境,再次建构一种想象中的圆满和坚实的自我形象,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时代命题。蒋勋在《孤独六讲》中说女性要挣脱多重身份的枷锁,是一场伟大而不易被理解的革命。相较于和外部的对抗,陈嘉玲正在进行一场个人革命,通过两季的讲述,主创似乎在缓缓地告诉观众,任何女性都可以追求理想的自我。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作为女性话语权与主体性建构的隐喻,为女性主义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房间”不仅是女性赖以生存的物质空间,也是自我身份确认和内心审视的精神栖园。偶然的机会使阿嬷短暂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她坐在门口听风声、吃鲜奶油,还有独属自己味道的番茄炒蛋,在片刻的时光里,享受属于自己的孤独,被纷繁复杂的生活掩藏的自己好像回来了,就像她久久凝视着自己的名字“李月英”,又像她深情唱给自己的《纯情青春梦》,这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是对自我身份的再确认。阿嬷这代人在庸庸碌碌的生活中逐渐丢失了自我,她的生命是遗憾的,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她的世界安静下来,在孤独中还原一个纯粹的自我,这是一场伟大的自我完成。
“房间成了一个特定的称谓,意味着区别于男性主流世界的边缘与个人之地,它以其幽闭性与隐秘性构成了女性世界隐喻与隐语的空间,成为女性自立与自闭同在、自我保护与自我繁殖双重意义上的一个空间符码和意识符码。”[5]40岁的陈嘉玲在台南乡下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她买下荒废多年的“鬼屋”并亲手改造成理想中的样子。这个房子具有了“家”的意义,它是一个充盈姐妹情谊的女性空间,是遭遇着不同困境的女性彼此安抚、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心灵疗愈地,它记录着每个人的蜕变痕迹。陈妈妈遭到老公的背叛后来到“鬼屋”,丢掉了妻子、母亲的枷锁,一个独立的自己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当她收拾好心情再度归来时带来一份“新同居公约”。“鬼屋”迎来了洪育萱,在陈妈妈、陈嘉玲的陪伴下她逐渐揭开被出轨、被家暴得遍体鳞伤的婚姻事实,当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时,来自陈嘉玲和女警察的拥抱一样那么可贵,她开始抛弃过往,开启艰难坎坷的新生活。陈嘉玲在她的“鬼屋”中遭遇了更年期的恐慌,也迎来了怀孕后的一系列挣扎,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原来自己想要的只是一个治愈自己的家庭。在这间“鬼屋”中上演了太多女性的相互支持与温暖,就像台风夜女儿与妈妈那个时空叠加的拥抱,无论多么糟糕都会有人可以被依靠。像洪育萱拥抱陈嘉玲的那场痛哭流涕,有一个地方能让她卸去坚硬的铠甲,袒露自己的心声。这个女性联盟阵地没有明显的对女性主义振臂高呼式的呼喊,但是能看到她们在传统的规训中审视自我、确认自我、追寻自我的反抗力量,也许最朴素的女性主义就是如她们般能够独立选择自己的人生,并有承担后果的勇气。
当前,大量女性题材作品讲述“北漂”“沪漂”女孩需要在都市和故乡之间做出抉择,她们或许迫不得已回到故乡,然而她们面对的是“回不去的故乡”,《俗女养成记》却告诉我们“故乡一直都在,只要你自己不迷茫”。陈嘉玲一直都在追求独立,19岁从台南到台北读大学、开始工作,39岁失业失恋回到台南,这300公里的距离她走了整整20年。在那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故乡,有给她无限支持和包容的家人,生活中充满了质朴的小确幸与小欢乐,那是一个天然乐园的象征。故事最终导向的还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家园回归,她买下了那间“鬼屋”将它变成自己的天然乐园,她更想与童年的自己见上一面,告诉她进来看看吧,未知并不可怕,在一场精神归乡的旅途中我们看到她找到自己、接纳自己的人间清醒。
四、结语
《俗女养成记》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个普通女性的成长蜕变,陈嘉玲并没有脱离俗女的人生,依然选择回归家庭生活,回归是其自我意识自主选择的结果,她清楚认识到自我的价值与意义,从而按照自己的意愿潇洒生活。女性意识的探求没有终点,当女性带着突围过程中的全面体验再次回望时,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启示,从而启示女性成为更真实的个体自由存在。
媒介形象与现实的关系经历了从形象反映现实到形象创造现实的变化,当代女性题材电视剧只是个工具,是创作者表达对这个世界认识的载体,人们期待文艺作品于女性的生存境遇要有指涉。在创作中以真诚的态度反映现代女性追求独立自我的生存样态,同时又通过成功形象的塑造赋予荧屏内外的女性以清醒独立面对生活的勇气,这是电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使命所在。只有在“他者”与自我的对话中,才能塑造出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艺术形象,成为当代女性时代面貌的真正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