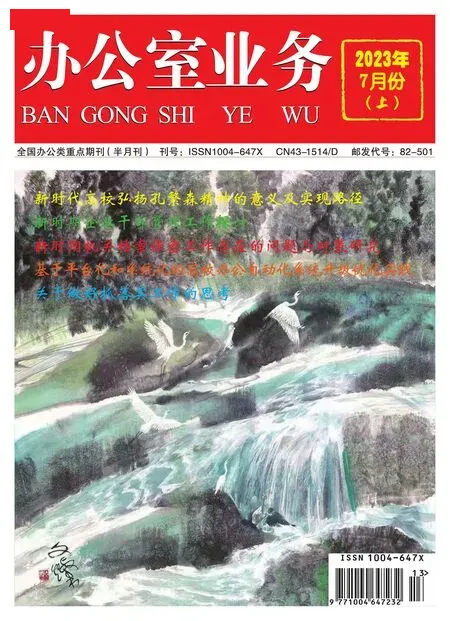对西方雇员群体及其工作的认识
文/陕西国际商贸学院管理学院 杨茜
近年来,企业雇员这一庞大的群体成为社会学、管理学各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从以往的研究看,美国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Mright Mills)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一书中,对新崛起的中产阶层进行了描述。他指出,由于手中仅有知识,没有货币资本等资源,这一社会阶层是极易出现向下层社会流动的社会阶层。
近年的西方译作,也从不同角度将全球其他地区的企业雇员群体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表明,雇员群体有着强烈的社会焦虑感和无力感以及职业的不稳定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间极具相似性。关于这一点,先后见于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阿莉莎·夸特(Alissa Quart)、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等人的著作。比如阿莉莎·夸特在《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中描述了美国雇员群体失业与再就业的艰难;海因茨·布德对德国中产阶层社会焦虑感的陈述;沙尼·奥加德对英国企业雇员恶劣工作状况的观察等等,为我们描述了不同时期的雇员群体,他们不同于杜拉拉般中产阶层雇员的生活图景。而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通过对雇员及其工作的认知,使人们正视雇员面临的艰难境地,毕竟这将影响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为我们提供新的动力,去探索新时代“人的发展”问题。
一、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雇员“画像”
在《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一书出版之前,先后有多位德国学者对魏玛时期的雇员问题进行过研究。如19世纪末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写的《德意志历史中的雇员们(1850-1890)》一文;又如瓦尔特·德尔克斯(Walter Dirks)在1931年写的《论德国雇员的处境》一文;还如汉斯·思拜尔写的《国家社会主义前的雇员们:1981年至1933年德国社会结构理解论》等等。克拉考尔在《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一书中,以店员和速记打字员所代表的雇员阶层,为德国魏玛时期雇员这个群体进行了画像。他是从以下角度来描述的:
(一)对“雇员”概念的界定。在这本书中,“雇员”包括了当时社会的公务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办公室文员、技术人员和部门领导,他们大多服务于商界、银行业和运输业。这些雇员们的工作,大多为脑力工作。他们来自市民阶层和小资产阶层,大多数人初、高中毕业。当时的雇员规模为350万。其中,女性为120万,服务于商业的雇员为225万左右。从群体规模增长速度来看,当时的工人人数尚未翻倍,而雇员人数翻了近5倍,即每5名工人对应1名雇员。
(二)公司里的人力资源状况。在公司招聘中,人事主管优先考虑他的外观。外观不是迷人或者漂亮,而是其“品性良好的红润肤色”。他们的谈吐、衣着、体态和面容相得益彰。他们常常借助摄影来塑造让人赏心悦目的外观。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在社会关系的压力下进行的选择。因而,当时柏林的整容业很繁荣。在薪酬方面,其薪酬会随着职位的升降而调整。文章还通过记录一个打字员的成长过程,来展示其新员工的培训过程:“老师们摇动着留声机的手柄,学生们则跟随着留声机发出的声音在键盘上敲字。留声机里有欢快的军队进行曲,他们通过升高唱盘转速,这群姑娘们在不经意间就会敲打得越来越快。”
(三)雇员的职业生涯。在组织管理方面,由于组织计划周严,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生疏,高职位者几乎没有机会了解底层雇员的状况,而底层雇员的目光无法向上穿透。雇员们几乎爬不到最高职位。对于雇员的个体发展,他们的机会实在很少。其中层管理者,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负责接收和传达指令。往往仅有具备才干的中层管理者敢于对抗糟糕的管理措施,但他们很少有凭业务能力升至高管层的;公司高管们的成长与选拔,往往其对象是受庇护的年轻人,他们会被安插进企业,以便为将来的掌权铺路。公司高管的选拔,往往出自这群人,他们多半是自我补充,其收入往往也很高。倘若他们想隐退,很多闲差的位子就是他们的。
(四)裁员。由于公司的岗位数量是一定的,倘若有新员工被录用,老雇员就必须被赶走。当公司面临合并、部门解散或整合时,老雇员被解雇的数量往往较多。他们一旦被解聘,将不再被雇用。当时,这些作为雇员的父母们,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选择一份轻而易举就有可能再被撵走的职业。
二、德国当代中产阶层雇员的“画像”
据德国学者海因茨·布德的观察,今天的德国社会,同样是一个充满焦虑感的社会。在《焦虑的社会》一书中,他将当今的德国社会,包括中产阶层和社会底层民众的焦虑感进行了描述。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曾经的德国中产雇员的画像,也能够窥见当今中产雇员的焦虑。
从中产阶层的构成上来看,以往的德国中产阶层,通常从事财务、运输和客户管理工作,或者在劳动规划、生产运营和企业发展等部门工作。而今天德国社会中产阶层构成中,一部分是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一部分是汽车、机床和出口型的、具有高生产率的设备制造业的专业工人;还有政府机关的中级和高级官员;最后一部分是自由职业者,其主要从事金融服务、医疗卫生和法律服务等工作。
海因茨·布德在该书中对中产阶层进行了“画像”。曾经的中产阶层,他们是奢侈品广告的主要广告对象。比如,符合环保要求的小汽车、品味高雅的家具装饰、定制旅游等等。在广告中,他们的形象是具有自我能力的人,他们自负其责,并且拥有独立自我。他们享有时间的自由支配。他们享受着二战后长期的和平稳定,因而社会福利增加,社会保障条件良好。据此可以看出,曾经的中产,他们拥有舒适的生活,享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和个人发展机会。
如今的中层阶层,包括法、英、荷、意、西、美、俄等国,其社会中产阶层在不断分化和减少。如今的中层阶层是一群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思想解放,易于接受更优化的生产方法。从阶层构成来看,他们通常是互联网电商的创立者、律所合伙人、营销公司创始人。从数量的变化来看,工程师的数量在增加,银行业、保险业、报社记者的数量在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分布于教育、咨询及其他社会服务行业的个体创业者,这一群体经常会朝不保夕。这群人既不缺少文凭,也不缺乏对其职业的兴趣。而造成其困境的,却是他们选择了错误的发展方向——自由职业者。
据统计,2014年的自由职业者人数为440万。他们是理发师、报亭商贩、小酒馆业主、律师、建筑师、自由创作艺术家、翻译、大学临时讲师等。这些人里有四分之一的人,其小时工资低于8.5欧元。正如该书所言,中产阶级其心理有着对其地位的恐慌。他们无法确切知道,现在为他们提供丰厚收入和高人一等地位的那些事物还能持续多久。
综上所述,综观全球中产阶层,其构成及所从事的职业,都相继遭遇着调整。随着全球产业的调整,曾经的中产阶层中,一部分人的处境变得糟糕,沦为“新穷人”,这在《乡下人的悲歌》中就有反映。面对这种变化,社会情绪不应该是负面的。正如汉迪在《饥饿的灵魂》一书中所讲的,雇员需要持续保持其自身的“可雇佣性”。往往在经济发展中,随着旧有职业的没落,新兴的职业便会出现。汉迪认为,新的就业机会往往来自新建的公司。这些小公司更关注“客户”而不是“就业职位”。所以,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小公司,而小公司的业务往往在向家庭服务的方向发展。
三、对当今社会雇员与工作的新认识
随着全球产业及其布局在全球的持续调整,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像消费者社会。这是西方雇员所置身的外在环境。
(一)对消费者社会的界定。所谓消费者社会,是相对于生产者社会的一个概念。根据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观点,生产者社会把人置于一个传送带与另一个传送带之间。这种社会要求工人们习惯例行的、单调的工作。其工作伦理是韦伯笔下清教徒般的生活,即工作是一种救赎,一种使命。人们之所以工作,一定程度是为了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而消费者社会,其工作伦理和工作意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消费者社会,人们以消费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依照“消费者”角色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在消费者社会里,更多的人属于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由于技术进步、工厂裁员,“精简”是这类社会新的行为准则。对于西方雇员来讲,其工作不再是终身的,而是暂时的、灵活的,且兼职工作的数量愈来愈多。从职业生涯来看,在生产者社会,人们终生去建构其社会身份,他的社会身份是相对平稳的、持续的。相较而言,消费者社会,具有不确定性。即消费者社会里的雇员,其职业不是终身的,也是不稳定的。用齐格蒙特·鲍曼的话来说,工作就像一件轻盈的斗篷,雇员们换一个工作,就像扔掉一件斗篷,工作随时准备着被扔到一边。他们追求的,是即刻的、即时的满足。他们的乐趣是获取对未知生活的体验。他们生活在一个接一个的诱惑之下,就像他们的先辈生活在一个又一个的传送带之间一样。
(二)消费者社会中的雇员及其工作。依据鲍曼的观点,在消费者社会,“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这里的“消费美学”使雇员对工作有了来自美学的审视。首先,雇员们具有良好的品位、足够的修养、独到的眼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优秀的教育。其次,他们赋予了工作艺术性的体验,即他们的工作是多样的、令人兴奋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里往往具有一定的风险和崭新的体验。在这里,娱乐式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幸福的人,可以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的工作时间是7×24小时专注的工作。而能够从事此类工作的人们,是幸运的。而曾经的“工作伦理”是,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做的工作,是单调的、重复的、例行的、缺乏冒险精神的、不允许创新的,这些工作没有调整,无法带来提升和自信。这样的工作,在前者看来,是无聊的工作。它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间的界限。消费者社会里,工作不再是个体自我构建或者社会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救赎的必由之路。其个体对于工作,不再是清教徒式的价值观,而是其在工作中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换句话说,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社会的雇员与工作,面临着社会结构调整后的新挑战。雇员中多数人的工作,从终身职业、不断完善的技能、连续的职业生涯,变成了暂时的、灵活的、不断变化的工作。这里的“灵活”,即没有任何持续性的保障,也就谈不上永久就业,往往兼职、外包工作更多一些。西方中产阶层雇员群体,在新的全球产业布局中,面临着分化和改变,这将是全新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