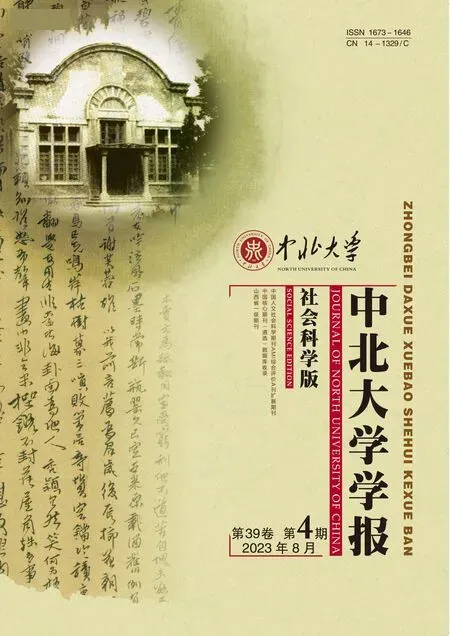南北融合诉求与“北方文脉”立场
——元儒张之翰文化观念辨析
刘成群, 李琳枫
(北京邮电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876)
1 张之翰的“取料”主张
从籍贯上来说, 邯郸人张之翰属于北人无疑, 不过在平宋之后, 张之翰作为行台监察御史颇有南方为官的经历。 由于张之翰“文声政绩辉辉并著, 有古循吏风”[1]372, 因此, 南方士大夫多愿与之交接。 在其文集当中, 常常看到他与南方士大夫唱和的作品, 其中, 就包括与江南文坛代表人物方回、 舒岳祥、 钱选、 赵孟頫酬唱的诗文。 南方士大夫对张之翰评价颇高, 方回称张之翰为“松江太守今贤侯”, 并颂扬云:“左手持螯右杯酒, 文章政事第一流。”[2]454戴表元称张之翰为“玉堂仙伯”, 也颂扬曰:“玉清篇脍炙惊吴下, 古迹探寻到雨余。”[3]770白珽则将张之翰比喻为“云间陆士龙”, 并赞美云:“人品中原说此翁, 雄文直气耿心胸。”[4]16杨载赞扬张之翰“长才当用世”, 又云:“落落蟠英气, 飘飘发壮图。”[5]卷三叶二十胡炳文也谦逊地向张之翰表示:“深衣大带, 先教为释菜之仪; 斗酒篇诗, 当共君观梅之乐。”[6]158张之翰在南方文化圈里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长期游走于江南文化阵营当中, 张之翰对南方文化也较为认同, 他非常尊崇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不仅拜谒文公祠, 而且在得到文公帖后奉若至宝:“我思昔贤全才何所不可施。 白云在天恨莫追, 空抱遗墨中原驰。”[7]30张之翰对南宋的词坛领袖辛弃疾也是推崇备至, 如其云:“乐府以来, 继吾坡公, 惟有稼轩。”[7]226此外, 张之翰对南宋理学家刘子翚以及诗人杨万里、 陆游、 刘克庄也均有较高的评价。 张之翰虽然身系北人, 但他对南方文化的推重, 有异于当时很多的北方儒士。
张之翰认为:“北诗气有余而料不足, 南诗气不足而料有余。”[7]208所谓的“料”, 大抵是指素材而言, 而“料有余” 乃是指素材的丰富性。 南方文学作品中素材的丰富性首先体现在自然风物层面。 南方山水奇秀多姿, 颇能激发起文学家对浪漫和美的追求。 张之翰在南方山水中徜徉, 写下了很多动人的诗篇, 如描写无锡三茅峰曰:“山形曲如字, 屋瓦青如鳞。”[7]9写西湖曰:“湖面好风将暑去, 山头落日送阴来。”[7]79写焦山曰:“金山东畔一峰青, 长与江流作画屏。”[7]80写蒋山云:“泉声时带松声落, 云气常兼海气来。”[7]80江南山水的旖旎风光在张之翰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张之翰到访过很多江南寺院, 留下了许多的精美诗句, 如写淀山寺云:“只今田亩纵横际, 畴昔波涛汹涌间。”[7]84写清隐寺云:“一县香灯供古佛, 数声钟磬落荒村。”[7]84写龙华寺云:“风软松江鲈欲上, 月明芦浦鹤初鸣。”[7]84写松江道院云:“潮落潮生分早晚, 云来云去弄阴晴。”[7]85写资福寺云:“迟迟白昼香烟冷, 寂寂绿阴牕户深。”[7]85写青霞观云:“月户云窗足潇洒, 翠鸾白鹤自蹁跹。”[7]86这些描写南方寺院的诗歌禅意氤氲, 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张之翰还写了大量的题画诗, 有学者统计“张之翰撰写了113首题画诗, 占其诗歌总数的五分之一”[8]。 宋代江南画风颇盛, 李唐、 刘松年、 马远、 夏圭曾经引领一时之潮流。 这种盛况到了元代无减而有增, 赵孟頫以及黄公望、 王蒙、 吴镇、 倪瓒更是烜赫一时。 张之翰对书画的探讨大抵与江南一带的文化氛围有关。 不仅如此, 张之翰在吃食、 器具、 文玩等层面也有非常深的研究, 写进诗歌的内容也非常多, 如写杯子的诗文就有《湖顶杯》 《谢郑小溪螺杯》 《同王简卿赋莱石瓢杯》 《吸月杯诗引》等。 张之翰上述题材的诗歌, 都可以算得是向南方文化取料的凭证。
在南方文化中浸淫已久, 张之翰的诗歌也具有了“清新逸宕”[9]1436的风格, 像张之翰一样勇于向南方文化取料的北方诗人也还是有的, 如卢挚就是其中一位。 卢挚在南方为官期间, 写下过很多赞美南方山水的诗歌, 显示出清新的韵致, 如《游茅山五首其二》曰:“涧边瑶草洞中花, 细水流春带碧沙。”[10]34即便是其散曲, 也明显透露出一种清丽的风格, 如散曲《中吕·喜春来·和则明韵》云:“春云巧似山翁帽, 古柳横为独木桥, 风微尘软落红飘。 沙岸好, 草色上罗袍。 春来南国花如绣, 雨过西湖水似油, 小瀛洲外小红楼。 人病酒, 料自下帘钩。”[11]107程钜夫评价卢挚诗文曰:“疏翁意尚清拔。”[12]157苏天爵亦曾指出:“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13]495卢挚这种“清新”或“清拔”风格的出现, 也可以视作是向南方文化取料的结果了。
张之翰与卢挚相友善, 前者曾写词“四海而今浑有几相知”[7]139赠与后者, 其交情可见一斑。 都喜欢向南方文化取料, 或许是他们交游的共同话题。 但在元代初年, 像张之翰与卢挚之类还是少数, 大多数北方作家固守质朴刚健的诗风, 没有加以变更的意识。 对于因分裂而导致北人缺料的问题, 张之翰是颇为遗憾的, 他看到山阴府乡中所得《止轩诗》后谈到:“余谓中州诸名辈, 如此老天假之年, 得见混一, 使之登会稽, 探禹穴, 其所作岂止此耶?”[7]202而对于将要到浙西赴任的阎复, 张之翰则激动地写道:
窃尝思公由东平入燕, 处深严十余载, 一旦渡长淮, 越大江, 过浙闽诸名山, 如党承旨诗所云‘平生梦寐不到处, 乃以王事从私游。’ 肃清之暇, 伸纸落笔, 发挥熊中所有, 亦南游之奇绝也。[7]170
对于南方有料的作品, 张之翰十分乐意向北人推介, 如读到徐择斋诗文后, 张之翰“因录藏行囊, 传归中原”, 其目的就是带给北方那些“名公巨卿”看, 让他们了解“东南文物”, 使他们认识到“自欧阳詹以来, 勿谓泉无人也”[7]204。 其实也是在提示北方儒士, 要眼界开阔, 要洞悉向南方文化取料的重要性。
2 张之翰的“取气”主张
如上所述, 张之翰认为:“北诗气有余而料不足, 南诗气不足而料有余。”[7]208什么是“气不足”呢?张之翰对此有具体论说, 如其指出:“宋渡江后, 诗学日衰。”[7]202诗学日衰的原因在于:“近时东南诗学, 问其所宗, 不曰晚唐, 必曰四灵; 不曰四灵, 必曰江湖。 盖不知诗法之弊, 始于晚唐, 中于四灵, 又终江湖。”[7]201“四灵”即“永嘉四灵”, 系徐照、 徐玑、 翁卷、 赵师秀4位诗人的统称, “江湖诗派”代表人物有姜夔、 刘过、 戴复古、 刘克庄、 方岳等人。 无论是“永嘉四灵”, 还是“江湖诗派”, 都有以学习晚唐矫正江西诗派之弊的取向, 他们忌用典而推崇白描, 诗风野逸舒长, 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掉书袋的毛病, 但却也出现了贾岛、 姚合身上那种气韵狭小的问题。 张之翰眼力颇佳, 他所谓的“诗法之弊”, 大抵是指“气”丧失, 恰是晚唐-“四灵”-“江湖”这条诗学发展路径所导致的。
当张之翰看到俞娱心的作品后评论说:“如娱心所作, 其欲兼之者欤!故喜为之书。”[7]208所谓的“兼之”, 当然是指互补的处理办法, 即北诗应该向南诗取料, 而南诗应该向北诗取气。 至于如何取气, 张之翰并没有直接说, 但是在他的文集中可以常常看到他鼓励南方儒士北游的诗文, 如《题长沙喻清仲纪行编》曰:
长沙喻清仲赴京, 有《纪行》一编, 朝廷诸老, 皆谓得洞庭清淑之气, 带湘江欸乃之音。 此固妙论, 以余观之, 清仲年方强仕, 抱负不浅, 北走数千里, 由岁贡而观国光, 见中原之河岳, 万方之衣冠, 九衢之鞍马, 必有得于胸中, 将发挥所藏, 随意落笔, 恐不止此。 他时荣归, 请倾囊自较, 当验斯言。[7]200
喻清仲作为南方诗人具有南方的特色, 所谓“洞庭清淑之气, 带湘江欸乃之音”[7]200是也。 但是, 张之翰认为这是不够的, 要想得到大力度提升, 必须得到“中原之河岳, 万方之衣冠, 九衢之鞍马”[7]200等中原风物的熏陶。 与《题长沙喻清仲纪行编》类似, 在《跋草窗诗稿》一文中, 张之翰也写道:
余读建安刘近道《草窗诗稿》, 见其风骨秀整, 意韵闲婉, 在近世诗人中尽不失为作家手。 然中原万里, 今为一家, 君能为我渡淮泗, 瞻海岱, 游河洛, 上嵩华, 历汾晋之郊, 过梁宋之墟, 吸燕赵之气, 涵邹鲁之风, 然后归而下笔, 一扫腐熟, 吾不知杨、 陆诸公当避君几舍地, 但恐后日之草窗, 自不识为今日之草窗也。[7]202
喻清仲也好, 刘近道也罢, 都非知名人物, 而白珽则不然。 白珽工诗赋, 与仇远齐名, 世称“仇白”; 又曾与当时名士结“月泉吟社”, 名动一时。 白珽曾向张之翰提出北上的设想, 张之翰记载曰:
梅花欲开雪欲落, 问君胡为北驱燕。 君言南北久分裂, 混一光岳气始全。 平生眼界苦未宽, 要看中原万里之山川。 恨余无文宠赠盖邦式, 喜君有志愿学司马迁。 渡江踰淮入泗汶, 指日可系都门船。 昭王一去年几千, 黄金台上荒秋烟。[7]28
在张之翰的意识中, 观南方旖旎之风物固可取其料, 而看中原万里之山川也可以取其气, 正所谓“吾州山川之气复还矣”[7]212。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有云:“太史公行天下, 周览四海名山大川, 与燕、 赵间豪俊交游, 故其文疏荡, 颇有奇气。”[14]381按照苏辙的说法, “周览四海名山大川”的确有为文章取气的成效。 在离张之翰时代较近的元好问那里, 也是非常强调山川所蕴含的气, 如《双峰竞秀图为参政杨侍郎赋》曰:“两峰突兀何许来, 元气淋漓洗秋碧。”[15]607, 同时, 也特别强调气对文章的激发, 如曰:“荡元气于笔端, 寄妙理于言外。”[16]1151总之, 山川对创作的影响是要靠气来打通的。 明白了这一点, 也就可以理解张之翰为什么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南方儒士要北上游览了。
按照苏辙的意见, “与燕、 赵间豪俊交游”也是文章“颇有奇气”的原由之一。 张之翰主张南诗向北诗取气, 不仅要游历山川, 同时也要接触北方人物从而接受陶冶以便实现升华。 在《书吴帝弼践行诗册后》一文中, 张之翰写道:
盱江吴帝弼近由建学提举得主安仁簿, 以燕都诸公饯行诗见示。 由鹿庵、 左山二大老而下, 如宋秘监之浑厚, 王礼部之圆熟, 阎侍讲之典雅, 李谕德之警戒, 徐参省之情实, 魏侍御之雄拔, 马刑部之精切, 夹谷郎官之感慨, 杨修撰之古秀、 王仪曹之巧丽, 皆余所素知, 南来所未见也。 君携此册, 试令向之好雌黄及谓不识字者一读, 余不知以为何如。[7]204
张之翰认为南方文风萎弱“亦由南北分裂, 元气间断, 太音不全故也”[7]202。 他所推荐的人物如王博文、 阎复、 李谦、 徐琰、 魏初等, 大多是元好问的学生, 自然主元好问元气之论, 如魏初就认为:“抑海内一家, 山川脉络同一元气。”[17]379又云:“古今一天地也, 人物一元气也。”[18]728张之翰对北方诗文“浑厚” “圆熟” “典雅” “警戒” “情实” “雄拔” “精切” “感慨” “古秀” “巧丽”等风格的赞誉, 其实都是展示给南方儒士看的。 张之翰的潜台词就是, 阅读上述诸人的作品, 掌握这些相对具体的风格, 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并习得北方文坛那种淋漓酣畅的元气了。
3 “取料”与“取气”背后的大一统心态
元代不似金代, 向有大一统之夙愿。 有元浩瀚的疆域, 赫赫的武功, 使得元代诸帝都产生了明显的一统心态。 元世祖在建元中统的诏书里就有“见天下一家之义”[19]65的表示; 而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大元, 也是在彰显“舆图之广, 历古所无”[19]138的一统气象。 一统心态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和军事层面, 在文化上同样会表现出恢宏的气度与非凡的自信。 元世祖时期, 就开始编纂极具象征意味的《大元大一统志》, 至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正式告成,前后历经两位皇帝, 为的就是“六合同风, 九州共贯也”。 时人皆以为, 元代在一统层面是超越汉唐的, 至于宋与金, 就更不在话下了。 许有壬为《大元大一统志》所作序言虽系后出, 但可以代表整个元代儒士的共同观念:
汉拓地虽远, 而攻取有正谲, 叛服有通塞, 况师异道, 人异论, 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 无以持一统, 议者病之。 唐腹心地为异域而不能一者, 动数十年。 若夫宋之画于白沟, 金之局于中土, 又无以议为也。 我元四极之远, 载籍之所未闻, 振古之所未属者, 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 则是古之一统, 皆名浮于实; 而我则实协于名矣![20]180
《春秋》大一统自古就十分符合儒士们的价值预期, 在元代则更别有一番滋味。 北方儒士虽受金源文化润泽, 但在金源那里却无法获得一统气象的满足感, 然而元朝却提供给了他们这种可能性。 如王恽论德运时就亟论“大一统之道”[21]3489, 姚燧也信心满满地说:“视秦、 汉、 晋、 隋、 唐、 宋六代之一家天下者, 若皆惭德于吾元。”[22]130就像一些少数民族知识人, 也为有元之广袤而倍感鼓舞者, 如贯云石就曾经赞叹曰:“赛唐虞, 大元至大古今无。”[23]72
从大一统角度来说, 南方区域固是有元广大疆域的构成部分, 而南方文化也不应该被排斥。 出于大一统的心理, 北方儒士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接纳并整合南方文化的一面, 所谓“今海宇混一, 方息马论道之时”[21]3753, 所谓“士生文轨混同之时, 亦千载之旷遇”[22]92。 “海宇混一”是指疆域一统, “文轨混同”是指文化一统。 疆域一统和文化一统自然少不得南方文化的参与, 唯有如此才能营造出盛世一统的气象。 在这一角度, 张之翰与当时很多北方的名公是一致的, 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南方, 可能这种大一统的心态要比他人更为强烈。
在张之翰的文集中, 有不少他对疆域一统和文化一统的赞誉, 如“今国家混一”[7]209“至国朝而混一”[7]171、 如“今南北混一”[7]158“自国家混一以来”[7]160、 如“圣朝南北混车书”[7]51、 如“今四海为家, 蔑三分之曹魏”[7]168、 如“吾元奄四海, 一意期升平”[7]4、 如“往年光岳分南北, 今日车书混文轨”[7]23、 如“九州岛四海颂声作, 万口一辞和气来”[7]59、 如“天教上寿非无意, 混一车书要正传”[7]88……。 在元初时代, 虽然疆域一统, 但国家制度层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南、 北因素的并存博弈”[24]的状况, 文化层面同样存在很多彼此隔膜的声音, 如“江南士人曩尝谓淮以北便不识字, 间有一诗一文自中州来者, 又多为之雌黄, 盖南北分裂, 耳目褊狭故也”[7]204。 张之翰和当时很多儒士一样, 明显持有大一统心态, 因此, 整合南北文化变成了他的夙愿。
张之翰认为:“北诗气有余而料不足, 南诗气不足而料有余。”[7]208为了真正实现文化的大一统, 北诗必然要向南方文化取料, 而南诗必然要向北方文化取气。 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促进南北文化的融合。 张之翰在促进元代南北文化融合层面所起到的作用, 已经得到了学界的重视, 如辛昕认为:“北人而长期仕宦于南方的张之翰, 具有促进南北诗风融合的自觉意识和明确的诗学理论, 并以其创作实践, 在这一融合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25]241而任红敏指出, 张之翰“在任职东南期间, 广交东南文士, 与方回、 白珽等著名诗人赠答唱酬, 相与论诗, 在南北诗风融合中起着重要作用”[26]509。
4 张之翰的北方文脉立场
虽然张之翰认为北诗要向南方文化取料, 而南诗要向北方文化取气, 看似不偏不倚, 但实则是存在一个立场问题的。 对于南方诗文, 他则多以近乎苛刻的言辞进行抨击, 如“宋渡江后, 诗学日衰”[7]202; 如“南北分裂, 元气间断, 太音不全故也”[7]202; 又如“盖南北分裂, 耳目褊狭故也”[7]204。 尤其是《书吴帝弼践行诗册后》一文赞美了北方名公后, 强调类似北方名公的诗文“南来所未见也”[7]204, 几乎要将南方文化全盘否定。 在那些鼓励南方儒士北游中原的诗文中, 张之翰将其北游行为称为“观国光”, 曰:“见中原之河岳, 万方之衣冠, 九衢之鞍马。”[7]200显然是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
尽管张之翰认为北诗料不足, 但他并没有过多地批评北方诗文, 相反还对其“浑厚” “圆熟” “典雅” “警戒” “情实” “雄拔” “精切” “感慨” “古秀” “巧丽”的风格赞誉有加。 除了《书吴帝弼践行诗册后》一文的集中赞誉外, 张之翰集中称颂北方文章名公的篇章几乎俯拾皆是, 如赞美郝经曰:“我从少年见陵川, 笔力扛鼎思涌泉。”[7]30如赞美魏初曰:“共爱文章有典型。”[7]68又曰:“喜君从来文擅场。”[7]25如赞美李谦曰:“前朝诸老已凋零, 翰苑须公共主盟。”[7]99如赞美胡祗遹曰:“文章勋业乘除里, 太白渊明伯仲间。”[7]100如赞美徐琰曰:“政事文章谁似之。”[7]64如赞美阎复曰:“天山文星是知己。”[7]65总之, 在北方文章名公那里, 张之翰几乎是不吝美好言辞予以赞美的。
张之翰这种立场大抵与其北方儒士的出身有关, 由于传记资料的缺乏, 现在很难具体了解张之翰的家世了。 不过, 张之翰对自己家乡文化颇为自矜, 正所谓“广平旧名邦, 自昔多善类”[7]13。 其乡贤中对张之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累官参知政事的何荣祖。 张之翰集中有不少写给何荣祖的诗歌, 其中《寄何右丞二首》曰“年少追随鬓欲霜”[7]62, 即是他早年追随何荣祖并获其提携的明证。 除了何荣祖, 张之翰还曾多次提及王内翰。 王内翰, 即王磐, 王磐也是张之翰的同乡, 但他们之间的交游关系, 还有待于考证。
在学术上, 张之翰与栾城人李冶具有师承关系。 在《元氏中秋不见月呈敬斋》一诗中, 张之翰提及“黄卷青灯记昔游”[7]114, 在《故昭义军节度副使王公碑铭》一文中, 张之翰提到“昔在封龙同登敬斋之门”[7]212。 敬斋即李冶, 系金末著名学者, 尤长于数学。 李冶与元好问、 张德辉游封龙山, 并称“封龙山三老”, 其人乃是元好问最好的朋友之一。 张之翰《敬斋先生寿二首》云:“四贤堂上无余子, 三老山中只此仙。”[7]87此诗有自注云:“又先生有封龙山三老会。”[7]87可见其对“封龙山三老”是熟知的。 按照张之翰自己的说法, 他与王构同在元氏封龙山从学于李冶, 又记载王构父亲王无咎与李冶、 元好问游, 可能在封龙山求学期间, 元好问也是其常常见到的前辈。
在张之翰的文集中, 并不乏元好问的身影, 如“元遗山所谓‘野狐岭上一回首, 不信君心如石顽’”[7]163“元遗山有椰瓢之语, 近时士夫多相效用”[7]188“‘我尝相夫君, 峩峩称天官。 玉树临春风, 绿发颜渥丹。 不珥银黄貂, 亦当切云冠。’ 此非遗山《题秦山图》之诗乎?”[7]212“九原不可作”[7]16这样的句子, 明显也是化用元好问“九原如可作”[15]155的原句。 另外, 元好问清雅豪壮的诗歌风格在张之翰的古体诗中也留下了许多影子。 如上所述, 张之翰交游和赞美过的北方文章名公, 如郝经、 王博文、 阎复、 李谦、 徐琰、 魏初等人, 都是元好问弟子。 张之翰虽然不是元好问亲炙的弟子, 但总归是颇有渊源。 张之翰之所以倾心赞美元门弟子, 是可以从北方学术传承的角度来理解的。
元好问传承金末儒学重估思潮, 同时, 又将这一思潮推崇治道和文辞的精神凝练升华, 整合唐宋文派, 并拈出“文统”二字与南方“道统”相抗衡, 如“文统绍开”[16]1053、 如“自文统绍开”[16]1218、 如“正赖天民有先觉, 岂容文统落私权”[15]1477。 总之, 形成了独特的“文统”之说。 元好问身负文章盛名, 追随者众多, 杰出者也不在少数。 有学者统计过元门弟子“十三人事迹见载于《元史》, 十一人有专传, 均系忽必烈开创元朝的有功之臣, 活跃于政治舞台, 建树颇巨”[25]。 这些人物在元初大多进入忽必烈政权当中, 相当一部分人还位在元初名臣之列。 元门弟子多在翰林国史院或监察机构任职, 他们在一起互通声气, 以唱和为乐事, 乃至逐渐形成了一个价值观趋同但在形式上松散的儒学群体。 这一群体传承元好问“文统”之衣钵, 乃至形成“北方文脉”这样一个传承体系。
所谓“文脉”, 乃是长时段内某种文学观念传承的历史轨迹。 “文脉”并非后人创建的概念, 在元初时代已然有之。 如家铉翁追忆南北异壤时文化的隔阂状况曰:“迨夫宇县中分、 南北异壤, 而论道统之所自来, 必曰宗于某; 言文脉之所从出, 必曰派于某。”[26]道统、 文脉的分判, 并非仅发生在南北异壤的时代, 即便在实现大一统的元初, 也依然如此。 北方的文脉之所以成为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 十分得益于元好问弟子群体的执着与坚守。
张之翰作为一位与元好问等金源遗老颇有渊源的儒士, 对“北方文脉”是非常认同的。 首先, 张之翰对于金源儒学十分赞同, 尤其是对金末儒学重估思潮的中坚人物赵秉文倾慕有加, 他称赞其曰:“平昔文章亚韩柳。”[7]119金末儒学重估思潮追求治道与文辞相表里的“文”, 其本质类似于唐代或宋代的古文运动, 因此可以说, 张之翰“文章亚韩柳”的评议确是切中肯綮的。 元好问倡导“文统”, 也是以继承赵秉文, 光大金源儒学而自居。 “北方文脉”的开端, 如果进一步追溯, 也可以延伸到金末儒学那里。 赞同金源儒学, 可是说是认同“北方文脉”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 金末儒学重估思潮与唐宋古文运动一样, 强调以文辞为载体, 以展现治道为旨归, 也就是所谓的“文以载道”。 金亡后, 元好问倡导“文统”, 这里的“文统”其实就是元好问的道统, 或者说是“文以载道”观念的传承。 在元好问弟子那里, 也有很多人持有“文以载道”观念, 如王恽曰:“文乃道舆, 经天纬地。”[21]2625如郝经曰:“文即道也。 道非文不著, 文非道不生。 自有天地, 即有斯文。”[27]739在这一层面, 张之翰也有相同的认识, 如其云:“文耶道耶果二物, 名虽不同实同矣。”[7]23又云:“言非文不行, 道非文不载。 二者本一途, 谁作彼此界。 道固我所乐, 文亦我所爱。”[7]6在“文以载道”认识层面, 张之翰与元门弟子并无不同, 此可谓认同“北方文脉”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后, 无论是元好问, 还是元门弟子, 都将金末以来“文以载道”的价值诉求理解为一个传承体系, 元好问就频繁申述“文统”正传之意, 如“文章有圣处; 正脉要人传”[15]911、 如“文章正脉须公等”[15]1515、 如“文章, 圣心之正传”[16]1326。 元门弟子也都认同金源儒学乃至元好问传承下来的文章观念, 并以之为正统。 如王恽云:“党赵正传公固在。”[21]756魏初云:“百年文柄遗山在。”[18]704郝经云:“俾学者归仰, 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 系而不绝。”[27]908张之翰的理解与元门弟子类似, 他评价魏初云:“学从正派篇章古。”[7]86并且多次强调文章之学的传承, 如“斯文一线竟何如”[7]59, “前辈诸公谁健在, 斯文一线要维持”[7]64。“斯文仅如缕, 愈久则愈衰……尚赖数名笔, 极力相维持。”[7]9从传承体系处着眼, 此可谓认同“北方文脉”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正是因为认同“北方文脉”, 张之翰才与元门弟子们交游密切。 在张之翰的文集中, 可以看到许多赠答郝经、 王博文、 阎复、 李谦、 徐琰、 魏初、 张孔孙等人的诗文。 与元门弟子交游密切, 并认同“北方文脉”, 这也使得张之翰的文学立场明显偏向了北方。 虽然张之翰在国家大一统的感召下呼吁南北文化融合, 但在某种程度上, 他还是抱有以“北方文脉”诗文观念整饬南方文化的愿景。 在这一层面, 张之翰与当时一些南下的北方文章名公们如姚燧、 卢挚等人并无多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