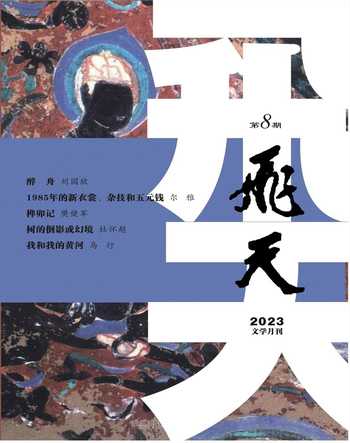喜鹊
吴永胜
一
小荷出现在拦河堰堤时,春明正起伏在堰角终年涌泉不息的泉眼里。堰水深只及胸。春明伏下身子,只把脑袋露出水面。堰角本有棵高大的苦楝树,树冠投下的阴影却遮蔽在堰中央。整个堰角就暴露在阳光下,春明脑袋上倒扣一张藕叶遮蔽阳光。脚下是碗口粗的泉眼,愤怒的泉水汩汩喷涌,细沙子激烈翻滚,合成一股力,一齐把春明往上推,好像努力要将这个阻碍者发射出去。春明不停践踏双脚,双手左右划动,才能与激烈的推托抗衡。凫立水的沉浮感和一身的沁凉,让春明心情惬意。下垂的藕叶有些蜷曲,边沿已经泛白,从藕叶与水面的空隙看出去,几十米外横亘的堰堤路上,似乎飘浮着半尺高迷蒙的烟尘。
阳光太用力,把堤路上的尘灰都拍得纷扬起来了。这时,一圈醒目的白从堰角烟尘中浮上来,跟着,一个穿淡红细碎花连衣裙的女孩头顶醒目的白出现在堰堤上。那白色的物体春明从未见过,它具备草帽的形体,边沿缀着一圈蕾丝花边。阳光拍在蕾丝花边上,折射出眩目的白光。跟着,高瘦的长生表叔出现在女孩身后。长生表叔戴顶泛黄的草帽,蓝色衬衫敞着襟,袒露出汗津津的胸膛,手里提着只军绿色帆布包。他们在堰角踅身,顺着堰堤往山崖走。烟尘被脚步搅动,向上纷扬旋舞。
“长生表叔,回来啦。”春明挺了下身子招呼。
“春明,你又在耍水哈。看你老汉晓得了,怎么收拾你。”长生表叔脚步停了一下,看看春明,撩起衬衫抹汗。那女孩也停了一下,左手拈起粘在胸前的连衣裙不停抖动,右手往脸上呼呼扇风,她扭头朝春明扫一眼又迈步向前走了。她朝春明看时,稍微仰了仰头,原本遮蔽在帽沿下的脸闪了一下,现出红彤彤的脸蛋。春明缩了下身子。他觉得女孩的目光既不耐烦,也饱含漠视。
“快些回去,不然我告你老汉。”长生表叔也走了。
“哎。”春明漫声应承。目光追随堰堤,那女孩脚下像垫着弹簧,明明低抬腿小迈步,可怎么看都像在蹦跳着前进。她头顶的那圈白,于是悠扬起伏在春明的视线里,直到转过保管室看不见了。
一只红蜻蜓飞过来,在春明面前停住,似乎在研究藕叶上能否栖落。若在以往,春明一定会平心静气,等蜻蜓安心栖下来了,悄悄伸出两个指头捉住它尾巴,或者猛然晃动脑袋,惊吓得它落荒逃走。可今天春明没有心情,他只在电影和连环画里,见到过戴遮阳帽穿连衣裙女孩的画面。现在,戴遮阳帽穿连衣裙的女孩居然去了长生表叔家,这让他有些恍惚。他不想再泡在泉眼里了,挥挥手臂赶走蜻蜓爬上了岸。
二
屋旁的竹林里,裸着上身的婆婆躺在竹凉椅上。左手握着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往胸膛扇风,好像全身最热的是那两只空荡松驰的褐黄色乳房。右手捏着的两枚核桃,还在掌心里寂寞地咕咕作声。春明才刚走进竹林,婆婆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她把春明上下打量,吧嗒着干瘪的嘴唇嘟囔说:“你又耍水了?”
春明不回答婆婆,他把嘴朝长生表叔家的房子努努说:“长生表叔家来了个城里的小女子。”
“我就说嘛,今天早晨喜鹊闹喳喳的。”竹林外阳沟边有棵高大的桉树,大桉树上有个喜鹊窝。每逢喜鹊早晨喳喳喳叫得欢畅,婆婆就总说有客到。往往就是那天,不是舅舅姑妈来了,就是姑婆舅公来了。可那女孩是到长生表叔家里的,跟春明家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是长菊的女。这女子,好些年没回娘屋了。”婆婆又说。蒲扇往胸膛上拍了两下,陡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嘴里念叨着,“这么热的天。”从椅子上爬起来,挪动小脚走上阶沿,从堂屋门侧的墙上取下竹篓子,竹篓子里装着晒干的草药,都是些夏枯草、车前子、牛尿蒿、冬桑叶,她挑拣出一大把递给春明。“给你长生表叔送去,让他泡水喝。城里人可娇贵。炎天暑热的,还不得中暑。”
春明接过草药走出了竹林,走了几步,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停下脚步,转身往回跑。婆婆刚躺回凉椅,欠起身子问:“你去呀,咋的又回来了?”春明不搭话,他跑进屋里,从柜子上翻出红色背心飞快套在身上。这背心,是春明上学才穿的。
春明走进长生表叔家,屋里没有那女孩的身影。长生表叔坐在屋中方桌上方,赤裸着上身,手里呼呼摇动蒲扇。水清坐在旁边的马扎上,挺着黢黑的脊梁打呵欠。他瞌睡未消的目光落在春明身上,立刻惊醒似地问:“你箍起来不热?”他指指春明身上的红背心。
春明原本不觉得热,水清一说,立刻感觉背心遮着的部位热起来了。那种热带着喷薄之势,既黏又稠,在身体外形成粘膜。入夏以来,他和水清一帮孩子,上身都寸纱未着过。春明咽了口唾沫,把草药放到桌上。“长生表叔,我婆说给你们泡水喝。”他记得婆婆说的是让他泡水喝,可他却怕长生表叔真的只是自己泡水喝了,又羞于说出怕那城里的女孩子中暑,于是把那们字咬音特别重。边说边用耳朵用力搜索,却没有听到女孩的声音。
长生表叔谢过婆婆,喊水莲拿过来一只搪瓷盅子,放几株草药进去倒满开水,再盖上盅盖。水莲看着春明的红背心,也像哥哥水清一样现出诧异的表情。那表情让春明心里慌乱。他有些进退两难,想走又有些不甘,想留却没有理由。他朝水清说:“来,我们下六子冲。”
水清挠着黑肚皮,撇撇嘴懒洋洋说出的话,让春明恨不得冲过去一脚踢翻他屁股下的马扎。“这么热,不想动。”好在水莲立刻响应了。“我跟你下。”就在屋角泥地面上画出格子,各捡了石子下起来。才走几步,水莲朝春明使眼色,头往春明跟前凑,几乎耳语般低声说:“我表姐来了。城里人假眉假眼呢,这么热的天要我给她烧热水,要洗热水澡。”
春明有些惊愕。“洗热水,不越洗越热么?”整个夏天,春明们洗澡洗头,都是用井里的凉水。
水莲嗤笑一声。“还有更怪的,她姓何,叫小河。”水莲的头几乎贴在春明脸上,春明突然发现水莲头发的汗馊味不绝如缕。他往后仰一仰身子,蹙着鼻子说:“你莫挨那么近嘛,头发好臭哦。”
水蓮愤怒地瞪大了眼,翕动的鼻翼泛起潮红,挥手猛地一扫,棋格里的石子蹦蹦跳跳撞在墙壁上。“你以为你香么?不下了!”她猛地站起来,差点撞在刚进门的女孩身上。女孩的脸还有些红,却不再是堰堤上时那般彤红。那红春明无法形容。他突然想起婆婆过七十岁生日时,大姑送来的增寿馒头雪白酥泡状如蟠桃,桃尖一点红,红向下晕染。女孩这时脸上的红,就像那被晕染的部分。
三
“我叫何小荷,不叫何小河。是荷花的荷,不是河流的河。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小荷。”小荷解释说。“你们背得这首诗么?”见春明水清都摇头,小荷有些惋惜地叹了口气。“那你们晓得小荷是什么吗?”
“荷叶莲花藕。”春明脱口而出。念出上句了,突然惊觉下一句的粗野,硬生生把下一句闷在喉咙。水清嘴快,立刻接上了:“鸡巴卵子球。”
小荷厌恶地剜一眼水清,挥手在鼻头前扇了扇,好像要把那句话的气味扇掉。嘴里鄙夷地说:“无聊。这么粗野的话你也说得出来。我要告诉舅舅,看他不收拾你。”
水清不置可否地撇撇嘴。春明知道水清在想什么。这对子本来是长生表叔在院里锯大木时,讲给其他人听的。水清和自己听到后记住了。长生表叔如果因此收拾水清,那就真的有些冤。他暗自庆幸,自己及时刹车忍住了。
小荷背着手,目光从水清、春明、水莲脸上环视一圈,“宋朝杨万里的诗题目叫《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一边一字一顿背诗,一边轻轻左右晃头,黑亮浓密的头发在脑后扎出个马尾巴,马尾巴左右晃荡。
春明和水清面面相觑。他们和小荷都是十二岁。小荷最小排在年末,却已经上五年级了,春明和水清才上三年级,没有读过这首诗。十一岁的水莲上二年级,就更没有读过了。水莲戳戳春明的手臂,提议说:“我们下六子冲。”说着开始在地上画格子。
春明还没有说话,小荷蹙了蹙眉头,说:“我们下军棋吧,我有军棋。”
水莲说:“我们下六子冲。”她探出手拉春明,春明趔趔身子,躲过水莲的手说:“我想下军棋。”
水莲的脸涨红了,鼻翼旁的雀斑格外分明。“你会下军棋么?你好久下过军棋?”
“不会就学呗,我教你们。”小荷说完,进屋去拿军棋。水莲狠狠地盯着水明,踅转身走到门口,抬脚要出门了,脚尖却用力踢在门槛上,转身回来,气鼓鼓地坐到桌前。
小荷将棋布铺在桌上,讲过了棋子的职位大小功能,又讲棋布上的框子圆圈的作用。“我们轮流下,谁输了就让。”
第一盘是水清和小荷下,水清很快就输了。轮到春明,走了几步,他有些举棋不定。手里的棋子是军长,前面两步,已经捉了小荷一个连长和一个旅长,小荷躲了个棋子进圆圈,另提了个棋子挡在前面。现在春明要么退回圆圈,要么就往前再捉。春明把棋子捏在指间,一边捻动一边盘算。水莲两肘支在桌上坐在中间,她往左探下身子,觑一眼小荷的棋子,两肘在桌面一滑,头凑到春明耳旁:“她是个炸弹。”
小荷瞪一眼水莲,水莲脸朝向大门假装没看见。春明咬咬牙继续捉子,果然是炸弹。水莲忽地站起来,跺了下脚就往门外走,嘴里狠狠地说:“给你说了是炸弹,真是个猪脑壳。”
四
春明在屋檐下写作业。接连几个晚上,他都没再用凉水洗澡了,也用了热水,热水浇在身上虽然有些烫,可洗过后好长时间皮肤都是凉爽的。凉水不一样,刚洗过片刻后皮肤又滚烫了。这时水莲走过来,手往春明面前一摊,赫然是块冰糖。水莲的手汗津津的,冰糖的边沿都濡湿了。春明拈起冰糖放进嘴里,汗水的咸后是浓郁的甜。看见春明吮咂着冰糖,水莲脸上浮现出笑意。她摊开手掌,伸出舌尖渍渍有声地舐着掌心。水莲凑到春明面前,头几乎碰到春明的头了,刚洗过的头发,散发出肥皂气味。有些幸灾乐祸地低声说:“哈,小荷给泥蜂子蜇了。”
春明停了手里的笔,腮不鼓了舌不动了,滑动的冰糖张皇地卡在了腮帮。
“我们天天从那过,都好好的。她走那过,泥蜂子偏偏就蜇了她。”水莲抿着嘴,眼里笑意盈盈。从竹林往上进水莲家,靠路的那篷竹子下,一窝泥蜂子把泥土絮出个洞筑了巢。它们总是嘤嘤嗡嗡忙忙碌碌地飞进飞出,从来没有蜇过人。婆婆说,只要不去招惹它,它不会主动蜇人。“那些泥蜂子怕是喜欢吃香喝辣,那女子天天用香皂洗澡,洗几桶水呢,一身香皂味。”水莲扑哧笑出声。
春明恼怒地瞪水莲,水莲却没看见。她正低了头,撩起碎花布衣裳下摆,松紧带裤腰上,夹着两本连环画。她把连环画掏出来,放到春明面前。连环画的背页被汗水濡皱了。
“莫让那女子晓得了。”
“你偷人家的?”春明把连环画拨落在地上。“偷的东西我不要。”
水莲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冰糖也是我偷的,你啷个抿得焗焗响?”她捡起地上的连环画,怒冲冲往外走。“我再也不理你了。真是狗咬吕洞宾!”冰糖在春明嘴里咕嘟一响,一下滑进喉咙,差点把他噎住。他用力咽下冰糖,作出了个决定,要去烧了那窝土泥蜂子。
那窝蜂子,少说也有几百上千只。打定主意要去燒了,春明心里又有些胆怯。抬头,看见屋檐下晾着一张薄膜,那是母亲晒玉米芡粉用过的。于是脑子里有了主意。从柴房里拿捆麦草,取出柜脚下的煤油瓶,往麦草尖上倒了一汪,煤油迅速在麦草尖濡开了,煤油的气息泛滥四溢。他想了想,又倒了一汪,再倒了一汪。装过223农药的瓶子,只剩下小半瓶煤油了。拿上火柴,扯下薄膜,夹了麦草就往长生表叔家旁的竹林走。婆婆翕动鼻子,盯着春明责怪:“你又要搞啥鬼迷花样哟?煤油糟蹋了,晚上咋照灯?”春明不理婆婆,径直从她身边走过。煤油在麦秆上不易被吸附,星星点点往下滴。他把麦草捆尽量竖立,让油顺着麦秆往下浸润。
泥蜂子仍忙碌飞进飞出,洞口外有许多小泥球,相互粘连向外突出。春明将薄膜缠绕在身上,只露出两只眼睛。然后点燃麦草,炽热的火焰立刻腾起来。火把抵在洞口,麦秆作响的声音和泥蜂子身体爆裂的声音混杂在一起。火焰吞噬了洞口,却有许多泥蜂子从泥球的缝隙爬出来,它们飞舞着愤怒地朝春明冲刺。薄膜厚实,它们蜇不穿,可交接处豁开了口子,泥蜂子扑进了口子,在薄膜内跌滚着近身下蜇。春明只觉刺痛尖锐灼热此伏彼起。扔掉燃烧的麦草火把,春明转身就跑,边跑边锐声尖叫边拍打撕扯薄膜。春明的脚下也像垫了弹簧,他连蹦带跳跑下竹林,跑过保管室,一直跑到拦河堰。愤怒的蜂子轰鸣追逐,直到春明跳进堰里,潜了一段,又潜了一段,躲进藕叶深处,那些蜂子仍盘旋不去。
春明被蜇了好几十处,每一处都鼓起红肿的包。爹用了一个小时,才把嵌在包里的蜇挤出来。水莲小荷水清都来了。春明眼睛肿得只剩下条缝,他看见水莲的脸愤怒地扭曲,鼻孔里喷出沌重的气息,鼻翼两侧的雀斑不停跳跃。小荷眼神怜惜又关切,她拿出盒清凉油,给春明蜇处涂抹。小荷的手指很软,好像没长骨头。触到蜇处,痛立刻奇异地烟消云散。
五
小荷进屋时,婆婆刚给春明蜇处涂抹完清凉油。春明只穿了个裤头,看见小荷,他有些忸怩不安。他从身后晾衣的铁丝上扯下蓝布褂子披在身上。小荷递过来两本连环画,一本《西沙儿女》,一本《保卫延安》。“送给你。本来我有好几本的,却不见了,多半是水莲拿了。”小荷说。
春明当然知道是水莲拿的,咧了下嘴想说出来,却忍住了。
“乡下真不好玩。”小荷低垂了头,语调忧伤,目光投向脚下,长长的睫毛向下卷。“我们家旁边就是人民公园,遇到星期天节假日,公园里人多得很,人山人海呢。公园里有个大湖,湖边都是柳树,顺着湖边走,柳条总是不停在你头上身上扫来扫去。湖里有小船,两毛钱就能坐一个小时。湖上有座桥,桥洞像月亮样圆。”小荷抬起头,眼里闪烁轻盈的亮光,“爸爸带我去,每次都要打气球。从湖上的桥下去,墙边有个打气球的,墙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气球,隔几米远用气枪打,瞄准气球,扣一下,打准了,气球就爆了。我爸爸一般都不打,有次被我和妈妈劝,他打了十发,就爆了十只气球。我不行,最多打中三个。”
春明没去过县城,最远只去过金华。那是个小集镇,那里没有公园,那里来来往往的,更多是些四里八乡的赶集人。他突然有置身泉眼的感觉,冰凉浸骨的泉水漫涌而上,把他整个人都淹没了。他勉强咧嘴笑一下,有些敷衍地说:“你爸爸真厉害。”
“嗯。”小荷点点头,眼里飞扬的神采突然有些黯淡,“可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能陪我打气球了。”她摇晃下头,好像要把什么念头抛出去,抛得愈远愈好。她站起来,说:“走,我们去下军棋。”
水莲坐在门槛边,面朝着院子正织草辫。她的手指灵巧翻动,洁白的大麦草秸窸窸作响,看见肿着眼泡的春明跟在小荷身后走过来,水莲撇撇嘴角,猛一折身子,把脸朝向房间过道。
打开棋盒,发现本来该整齐排列叠放的棋子乱了,一清点少了三枚。“我明明是数得清清楚楚,怎么就差了。谁拿了我棋子?”小荷尖叫。春明把狐疑的目光投向水莲,水莲闻声扭头,正面对春明。“你看我做哪样?我可没那个闲空。”水莲翻了个白眼。
小荷脸色绯红,胸脯一起一伏。“我们两个人一个房间,进进出出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的几本连环画不见了还没说呢,现在棋子也不见了。”
水莲把手里的辫子往大腿上一拍。“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拿了?”她冷笑一声,“嗯,可能是老鼠子吃了。我昨晚一晚上都听到老鼠子跑来跑去,啃得咯咯嘣嘣响呢。”
“好,就算是老鼠啃了。难不成老鼠自己把纸盒子打开的?”小荷拍拍完好的纸盒子说。长生表叔从屋里走出来,瞪了水莲一眼,“放在哪里了?快拿出来!你们是表姐妹,要互相让着。”
“没拿就是没拿!”水莲梗着脖子嚷。
长生表叔黑了脸,他伸手抓住水莲的头发,把水莲从凳子上提拎了起来,响亮地在水莲背上拍了一巴掌。水莲哇地哭出了声。她跑进睡房,很快跑出来,把几枚棋子往桌上一扔,转身就往屋外跑,一边跑一边哭着咒骂:“妖精,狐狸精,马屁精……”春明脸有些发烧,他知道水莲既在骂小荷也在骂自己。小荷也抽抽搭搭哭起来。长生表叔跺跺脚,从屋檐下的柴山抽了根桑条撵了出去,院后很快响起水莲尖厉的哭嚎。
春明手足无措,他把散落的棋子一枚枚拾起来,第一层整齐铺排了,再把第二层整齐铺排进去。小荷手捂着脸,仍在哭泣。春明把铺开的棋布对折一下,手掌用力抹平皱褶,抹得平平展展了,再对折一下,又抹。再折一下,又抹。直到棋布刚好纸盒大小,放进棋盒扣上盖子,小荷耸动肩膀,仍在低声啜泣。水清睡眼惺松地从屋里走出来,趿着的拖鞋扑踏扑踏响。他看了看小荷,又看了看正往门外蹭的春明,说:“走啥子嘛,我们下两盘。”春明摇了摇头。他无限忧伤地走出门。天好像突然阴了,一大团黑云遮住了太阳。
六
小荷找到春明,把棋盒往春明怀里一塞,“送给你。你保管好,再不要让猫狗老鼠偷了。”
春明捧着棋盒,有些慌乱,“你送给我了,你要下怎么办呢。”
小荷咯咯笑出了声,“我要下可以找你呀。”说完,小荷有些遗憾地摇摇头。“我有台上发条的火车,红色车头,有两节绿皮车厢。把发条拧紧放在地上,立刻嗒嗒嗒地跑。一直跑到發条松了才停。可惜太大了,不好带回来。”小荷走了。双手交剪背在身后,仍然像脚踩弹簧,马尾巴在脑后调皮地晃荡。春明看清楚了,小荷和水莲走路不一样,水莲的足掌是平展踏出去的,小荷却是脚尖向下先触了地,然后脚跟才落地,所以脚步轻盈如跳舞。小荷舞蹈般的脚步,把春明的心都踩乱了。他双手捧着棋盒,突然有种喘不过气的窒息感。他想,我一定得回送小荷件礼物。可是送什么呢?他却想不出来。
天气一如既往地热,春明溜到拦河堰,突然发现几乎是一夜间,堰塘里就开放了五六枝荷花。粉红的花挺拔在绿色藕叶间,有风从上沟吹下来,花就风姿绰约地摇曳。春明不泡澡了,他选了三朵开得正盛的荷花,连着尺把长的茎折下来。来到长生表叔家时,看见小荷居然和水莲坐在门旁,水莲正教小荷织草辫。他有些茫然,两三天时间,不知道她们的关系已经变好了。有水莲在,春明不好意思把荷花递给小荷,就把三支花往前一送,停在两人中间。“塘里的藕花开了。”水莲撇撇嘴,接过花往桌上一扔,“开得好好的,你折下来做啥?”
小荷抿嘴笑,眼睛里亮晶晶的。“人民公园里有很多荷花呢。红的粉的白的,湖里都是,只准看不准摘,摘一朵罚款五角。我以为人民公园荷花就多了,哪知道前年我跟爸爸到成都,去了新都桂湖,那里荷花才真是多呢。我爸说全国有八个荷花观赏湖,西湖洪湖大明湖,桂湖要排第一。”
水莲剜一眼春明,狠狠地说:“好好的藕花,瓜娃子才摘。”
春明气得攥紧了拳头。他不明白水莲咋就忘记了去年前年,她都缠着他摘荷花,他摘过最少好几十朵给她。他猛一跺脚,嘴里嚷:“我是瓜娃子,你就是呱婆子。”他踅身往回走,边走边嘀咕:“呱婆子。你是呱婆子。”走出竹林,走到自己屋角,婆婆手里的核桃仍在寂寞地咕咕响,屋檐旁的核桃树树影婆娑,一枚核桃啪地掉在脚前。那是枚谎核桃,它没有老实长桃仁,于是瘪了萎了,被风从枝丫间吹了下来。一道亮光炫目地从春明脑里划过,春明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他决定做个“呱婆子”送给小荷。
春明从屋檐下抽出根竹竿来到核桃树下,他高举竹竿目光在核桃叶间睃巡。婆婆狐疑地瞪大了眼,“春明,你害娃了么?核桃米米才一包嫩水呢。十月核桃九月梨,现在才八月。”春明不理会,他敲下了好几枚核桃,却发现哪怕最大的,里面的核桃仁刚成型,一掐就破。最要命的是,核桃壳像纸壳样薄脆。看着在一堆核桃壳前垂头丧气的春明,婆婆咂着薄嘴皮說:“说了你不听,真像害娃了。可惜了几个核桃。”婆婆又闭上眼睛躺在凉椅上,手里的核桃咕噜咕噜响。
七
春明把写作业的凳子搬在阶沿靠近竹林的地方。以前他不会搬在那里,虽然婆婆不识字,可只要春明在身旁写作业,她一定探长脖子看,春明架了二郎腿,或者把脚盘坐在屁股下,婆婆都要嘀咕,说春明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如果春明在本子上画画儿,或者盯着对沟的山好久不动,婆婆就会说,又在打王广,我要告你老汉。春明真是烦她,总想躲她远点。今天春明不躲了,他打开课本,专注看。婆婆说:“春明,你不写作业?”
“今天没作业。今天读书。”
“寂静风隐,哪叫读书?读就要读出个声音嘛。”
“默读嘛,就是不出声地读。”
春明把语文书一页一页慢慢翻,支棱着耳朵听婆的动静。一本语文书都翻完了,婆还是躺在椅子上没动静。中午喝的玉米糊,春明已经上过两次茅坑了,他不明白同样喝玉米糊的婆婆,咋就不蹲茅坑。他想也许是婆婆干瘪的皮肤,把玉米糊的水份都吸收了。正这么想,斑竹杖笃笃触地的声音欣喜地响起,婆婆走过院子,绕到院后去了。院后茅坑出粪口用石板盖着,怕鸡崽掉进粪坑,只留了道缝。不知道是哪一年开始,婆婆夏天一热起来就不穿上衣,大白天屙尿拉屎,也不避人,脱下裤子就往出粪口撅起屁股。那两枚核桃,分明排放在凉椅上。春明抓起一枚塞进裤兜,重新回到凳子前,他看了看鼓出一个包的裤兜,拍了拍,支棱耳朵仔细听,婆婆的竹杖声音还没有响起。于是飞快收拾书本,喊一声:“婆婆,我书读完了,出去耍了。”跑下竹林,婆婆在吆喝:“春明,看见我核桃没有?”春明说没有。
保管室后面的牛棚空荡荡的,只有苍蝇和牛虻在嗡嗡飞。那三头水牛,这时候正泡在牛滚凼里。保管室后有个竹子环绕的大水凼,凼低淤积着厚厚的软泥。牛下去了,侧身来回滚几滚,就粘上了厚厚的泥。屈膝卧倒,只眼睛鼻子露出水面,一直到天阴了,再拉出水。
春明来到牛棚与保管室连接的那堵墙前,扒下块泥砖,现出个洞,里面放着钉子小刀、竹片白线。春明把核桃立放在檐下石板上,他看见那只核桃硕大无比,原本黄褐色的表皮黑得油亮,深刻的槽纹全都磨低了。他用两块石头把核桃夹住,用钉子慢慢钻了个对穿的孔。横在眼前看看,那孔两边一般大,孔壁完全没有破损。侧面的壁上,也钻出一个孔。选块坚硬的石头,一只手拿着核桃模放在石板上,另一只手扬起石头顺着横纹轻轻敲,敲过一圈,横纹裂一道缝,轻轻一辦成了两瓣。掏掉发黑萎缩的果仁隔膜,刮得光光的竹签上,白线打一个结,然后一圈圈缠绕,直到竹签鼓出了肚子,两扇开孔的核桃套进去,线头从侧面的孔拉出来,合上。上方,刮削得薄亮的竹片楔进竹签,一个“呱婆子”就成了。线头绑一截短竹片,捏着竹片往胸前一拉,白线出来了,竹签顺势转动,顶上的竹片也跟着转。手里竹片一松,竹签立刻反向转动,竹片立刻逆转方向。不停拉放线头,竹片一反一正快速转动,在空气中擦刮出呱呱呱的声音。
小荷接过“呱婆子”,按春明的指点玩起来,在呱呱声中,她咯咯咯笑。
八
春明天黑才回家,爹黑着脸坐在屋中间,语气冷漠地朝春明说:“把板凳端过来,条子自己拿。”尽管春明早有准备,知道少不了挨打,可心里还是有些害怕。他把那根笨重低矮,却有三掌宽凳面的长条凳端到爹面前,然后踅身走到屋后柴房,他选中根尺五长小臂样粗的桑枝,进屋递给爹。爹把桑枝在手里掂掂,虚挥一下桑枝,作势要落在春明身上。只挥一半却停住了。“骨头敲断了,想让我继续白养你?换根细的。”
婆婆说:“不是他拿的。我多半是放失了手,唉,可能掉茅坑里了。”
“妈,你不用老是护着他,三天不打,上屋揭瓦!那天烧蜂子窝我没有收拾他,今天又偷核桃。不是他是哪个?你看他满手粘的啥子?”春明剥嫩核桃时,核桃液粘在掌心,两个手掌都乌黑乌黑的。
“婆婆搓了五年的核桃呢,你弄到哪去了?婆婆手不好,搓核桃活动筋脉。这下哪去找合适的?”娘说。
春明有些难受,也觉得有些对不起婆婆。狠了狠心,抽了根柔韧的黄荆条。出来爬在凳子上。爹用黄荆条点点春明的短裤,“裤子打烂好买新的?脱了。”
春明不作声,两只手从凳下穿过去,紧紧抱住凳子。“脱裤子!”黄荆条在春明屁股上拍了一下。春明不作声,手抱得更紧,脸贴在凳面上,凳面温润光滑。“脱裤子!”黄荆条抽在屁股上。火辣辣的灼痛立刻漫延,春明打了个哆嗦。手抱得更紧了。爹暴怒了,黄荆条雨点般抽下来。春明紧紧抱着凳子,脸几乎贴在凳面上,他的腿从凳面绕下去,脚踝勾住张开的凳脚。第一回,春明不哭不喊,他紧紧闭着眼。他依稀看见,小荷咯咯笑着,“呱婆子”在她手里,竹片往复旋转呱呱地叫。
黄荆条是婆婆从爹手里抢下来的。她扬着手掌,一下一下拍打爹裸露的肩膀。“不就个核桃呀,你想打死娃儿?”爹颓然跌坐在板凳上,大张着鼻孔呼呼喘气。“是个核桃的事么?不是,不是个核桃的事。”他喃喃着自问自答。
吃晚饭时,爹脸色和缓了些。筷头点点春明说:“明天一早,你去三舅爷家要点核桃。”三舅爷是婆的堂哥,远在四十里外的王家山。那里高山绵延,有许多核桃树。春明去过几回。三舅爷家里,随时都有隔年的核桃。问过春明还记得路不,又说:“对路去,对路回。好好戴罪立功!”
九
春明从三舅爷家回来,是第三天下午。走近自己屋旁,婆婆扑打着蒲扇,“喜鹊喳喳叫,真是有客到。这喜鹊子一早就闹喳喳的,半上午长菊就来了。”
春明突然涌起不详的预感,他颤声问道:“哪个长菊?”
“还有哪个长菊?你长生表叔家当官的姐姐呗。”
春明放下核桃,就往长生表叔家跑。跑过竹林,跑进院子。他看见长清坐在屋檐下,正蘸着唾沫翻连环画,他光光的膝盖上,叠放着好几本连环画。水莲坐在旁边,嘴里吸溜着什么,手里拿着“呱婆子”,正一拉一放。看见春明了,露出欣喜的笑容,停下拉线的一端,从裤兜里掏出两粒糖。“大白免奶糖呢,大姑给的,我给你留了两颗。”
春明不接糖,他有些瑟瑟发抖。指指“呱婆子”问:“怎么在你这里?小荷呢。”
水莲翻了个白眼,“她走了,再也不来了。她不要了,就给了我。”
水清停下翻书。“大姑专门来接小荷,她们明天都要跟姑父走。”
“去哪里呢。”春明失魂落魄。
“好像是新疆。”水清说。
春明觉得全世界在一瞬间轰鸣着炸裂了,他没有理会水莲的招呼,转身就往家里走。走进院子,婆仰着头,看着头顶的桉树。两只喜鹊喳喳喳叫着,围绕着桉树巅盘旋飞舞,它们的叫声喜庆欢欣热烈清脆。
“狗日的喜鹊!叫你妹!”春明拾起块瓦片,抡圆胳膊用力朝树巅掷去。愤怒的瓦片才飞到树身一半高,就无力地擦着树干飘出去了,歪歪斜斜落到那边的水田里,“咚”地一声,溅起一簇浑黄的水花。
责任编辑 赵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