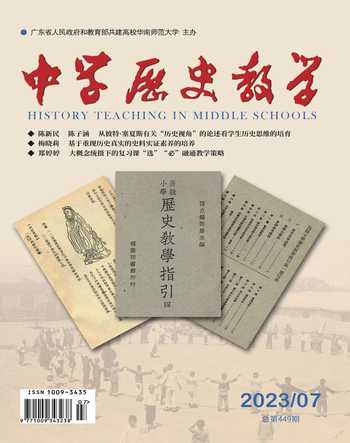直面争议、据史反驳
冀强
“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与方法。”[1]以史论证和论从史出是史料实证较为常见的模式,在日常教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史料实证模式——据史反驳。
据史反驳是史料实证的一种特殊模式。[2]它以史料为基础,通过一系列论证方式反驳或质疑原有观点,进而捍卫原有认知或形成新认知。对于这种模式,教师的关注度并不高。实际上,据史反驳的过程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思维。在批判、反驳和质疑中,学生获得的不仅是历史知识,更有辩证思维和批判意识的养成。
据史反驳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可以从概念入手,明晰概念内涵;可以从论证方式入手,检验逻辑过程;也可以从史料入手,分析史料内容。
一、明晰概念内涵:据史反驳的前提
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形态,是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本质特征,即使再相近的概念,也有细微的区别。因此从概念入手,明晰概念内涵是据史反驳的重要手段。
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已使用纸莎草纸,它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制成。纸莎草纸是多种语言文字的载体,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之一。因纸莎草纸出现的时间早于中国的蔡侯纸。一些人据此认为,古埃及人最先发明了纸。中国纸的发明权受到了挑战。面对外界质疑,我们应积极反驳。如果从纸的概念入手,这一问题将得到很好解决。
材料一:纸莎草茎高可达3米多,粗细与人的手腕相当,茎部富含纤维,用它为原料制造出来的书写材料就是纸莎草纸。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黏液,使草片相互黏結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
——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3]
材料二:蔡伦发明的造纸工艺流程是: 原料—沤、煮—漂洗—切锉—舂捣—打浆—加入纸药—抄、捞—压榨去水—分纸—烘、晒干燥—整成纸捆……舂捣,现代造纸术语称之为打浆,它的作用是经过沤、煮、锉切短了的纤维变得开裂、溃变,也就是现在造纸工艺所说的纤维分丝帚化,使纤维在水中形成有较大表面积的丝絮状,抄捞去水后,纤维之间结合得更紧密……打浆是区别纸和其他类纸物的关键。
——华玫、廖福龙《从现代造纸生产工艺看蔡伦发明造纸术》[4]
从时间来看,古埃及的纸莎草纸比中国汉代的纸要早3000年。但从工艺来看,古埃及纸莎草纸的制作流程与现代造纸业的工艺流程差异很大,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纸。汉代蔡侯纸的工艺流程则与现代造纸工艺基本类似,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最先出现于中国并没有问题。
火药的发明权也面临类似的争议。对中国火药发明权的争夺主要有两个:“希腊火”和“海之火”。从文献记载来看,“希腊火”和“海之火”确实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火药武器很像,且时间更早。但经过后人对其化学成分的分析和考证,发现其与火药的化学成分差异很大。
材料三:“希腊火”。据记载在公元前5世纪已用于战争,11—13世纪十字军东征,阿拉伯军队和十字军双方都曾用“希腊火”进行火攻作战。但这只是一种燃烧剂,其配方中没有硝石成分,这意味着它不能满足“自供氧燃烧”,因而不可能是火药。“海之火”。7世纪出现,是一种用于海战的、以虹吸管喷射的燃烧剂或烟火剂。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堡保卫战中,多次用“海之火”焚毁敌人战舰,故视之为天赐神物,对其配方严格保密。至18世纪,“海之火”的配方被考证出来,其中有硫磺,但是没有硝石成分,所以也不可能是火药。
——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5]
据材料可知“希腊火”和“海之火”实际上是一种燃烧剂。燃烧剂在燃烧时需要外界供氧,而火药则是“自供氧燃烧”,即火药本身就能供氧。在火药中,硝石就用于供氧。火药和非火药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存在硝石。
如果说明晰概念是据史反驳的前提,那么论证方式体现的则是据史反驳的过程。
二、检验论证方式:据史反驳的过程
任何结论都是经过论证后得出的结果,其间包含着各式各样的论证方式。因此从论证方式出发,找出其论证时的逻辑漏洞,也是据史反驳的重要手段。这里以印刷术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对中国印刷术发明权的争夺主要来自于韩国。近年来,韩国学者、媒体和官方对此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韩国学者的论证是否充分有力?我们以以下材料说明。
材料一:1966年在韩国一个庙里发现了一卷《陀罗尼经咒》,这是一份汉字的雕版印刷品。它的年代比刚才我们说的王玠印造《金刚经》的公元868年要早。这个《陀罗尼经咒》印刷的年代,可以肯定是在公元704—751年。因为704年这个《陀罗尼经咒》才被译成汉文,而公元751年是韩国这个庙落成的年份,这个东西是在庙落成之前埋下的,所以可以确信是公元751年之前。于是韩国人在世界上造舆论,说他们发现的《陀罗尼经咒》比大英博物馆藏《金刚经》要早。
——江晓原《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思考》[6]
材料二:它(《陀罗尼经咒》)使用了武则天在位期间的特殊汉字,而且“严格符合中国印刷的模式和方法”,它很可能是庆州佛国寺建成时从中国带来的贺礼——众所周知,唐代中国的佛经、书籍等,经常是朝鲜半岛上层社会热衷于搜寻和购买的珍品。
——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7]
据材料可知,在韩国发现的《陀罗尼经咒》,其刊印时间应为公元704—751年之间,确实比现存最早的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印刷品《金刚经》(公元868年)早了一百多年。韩国学者据此坚称韩国最先发明了印刷术,但韩国学者的论证并非没有漏洞。《陀罗尼经咒》上有武则天在位时期创制的特殊汉字,其印刷风格也非常符合唐代的印刷模式和方法。这说明这部经书来自于中国的可能性很大,但我们还不能就此下结论,还需要相关史料的支撑。
三、分析历史史料:据史反驳的基础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基于对史料的应用和解释。因此据史反驳也可以从对史料的分析和辨明入手。这里我们还以印刷术问题为例。
材料一:到目前为止,印刷术韩国起源说只建立在庆州发现本一个孤证上,再无别的证据证明新罗朝有印刷活动。有记载表明,半岛的印刷始于11世纪初。若706—751年新罗朝就已印刷佛经,为什么此后的200—300年间既无印刷记载又无实物遗存,而直到1007—1011年才迟迟出现?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新罗朝时没有印刷。
——潘吉星《印刷术的起源地中国?韩国?》[8]
材料二:1974年西安市西郊柴油机械厂出土梵文陀罗尼咒单张印刷品,出自唐墓中。出土时经咒揉成团置入铜腭托中,呈方形,印以麻纸……此印页中央有一7*6厘米的空白方框,其右上有直行墨书“吴德福”四字,从书法风格观之,为唐初流行的王羲之(321—379)体行草……同时出土的还有铜腭托和规矩四神铜镜……四神铜镜径19.5、厚0.3厘米,具有隋末至初唐墓葬铜镜形制特征,其铭文书体与贞观年(627—649)等慈寺碑文极其类似……我们认为其刻印年代为650—670年前后,因而是现存世界最早印刷品。
——潘吉星《论一九六六年韩国发现的印本陀罗尼经的刊行年代和地点》[9]
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在历史研究中应使用多种史料。文献史料在教学中经常使用,但实物史料也不容忽视,多种史料相互印证可以使反驳论证更具说服力。通过对上述材料的分析,可以提取出如下信息。韩国雕版印刷品的出土缺乏连续性,存在着几百年的空白期。中国境内出土了更早的陀罗尼咒印刷单页。经过比对和考证,其印刷时间应为唐初,比韩国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更早。这充分说明1966年于韩国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应由中国传入。
这里我们再以火药问题为例。根据对上文的分析,可知火药和非火药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存在硝石。如果要证明中国火药发明的优先权呢?关键是要找到含有硝石的火药配方。众所周知,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丹时无意发明的。这里可以呈现唐代的丹药配方。
材料三: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里,最先载录以硝石、含炭植物皂角及生、熟木炭为硫磺“伏火”的方法。……又过了大约一二百年,成于中唐的炼丹书《真元妙道要略》,即以非常确定的口气告诫说,以硝石、雄黄(三硫化二砷)、硫磺和蜜(着火后会释放二氧化碳)相合点燃,会引发强烈的火焰,乃有因此而“烧手、面及烬屋舍者”。这段记载,被认为是已知的第一个“原初火药”的配方单。
——刘东《中华文明读本》[10]
材料显示,在唐代的炼丹术著作中,已有了以硝石、硫磺、炭为主要成分的丹药配方,并出现了硝、硫合烧会爆燃的文字记录。这说明至迟于唐代晚期(公元九世纪),中国炼丹家已发明了火药。在宋代的时候,火药已被广泛用于军事。为了使论证更具说服力,还可以向学生呈现北宋时期的火药配方。
材料四:庆历四年(1044)曾公亮、丁度等编纂《武经总要》,堪称中国第一部古典军事百科全书,该书前集卷十二《守城·火药法》中,完整记录了三种黑火药配方。以其中“蒺藜火球火药方”为例,配方中硝、硫、炭的比例依次是50.6%、26.6%、22.8%,还有少量其他配料。
——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11]
《武经总要》是北宋时期一部官修的军事著作,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该书完整地记录了火药配方,这标志着火药的发明研制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中国火药的发明权难以动摇。
四、培育学科思维:据史反驳的归宿
历史学是一门注重逻辑推理和严密论证的学科。对历史的探究应以史料分析为基础,以逻辑论证为手段,以求真求实为目标。但受制于篇幅限制,中学历史教材多以结论性话语为主,对结论形成的过程则很少涉及。但就教育价值而言,过程性价值往往更为重要,也更能培育学生的学科思维。据史反驳就是一种典型的过程性思维。它的论证模式基本如下:反驳已有观点——依据史料史实推理论证——形成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明确求真求实的历史研究目的,理解论从史出的历史研究原则,掌握史料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据史反驳的过程中,学生经历了一次历史学科思维的深刻洗礼。
【注释】
[1] 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5页。
[2] 冯一下、张利娟:《试论史料实证的运作模式》,《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1年第5期,第47页。
[3]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第107頁。
[4]华玫、廖福龙:《从现代造纸生产工艺看蔡伦发明造纸术》,《造纸信息》2021年第5期,第68页。
[5] [7] [1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5、42、24—25页。
[6]江晓原:《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和思考》,《科技导报》2012年第2期,第16页。
[8]潘吉星:《印刷术的起源地中国?韩国?》,《今日印刷》1997年第2期,第6页。
[9]潘吉星:《论一九六六年韩国发现的印本陀罗尼经的刊行年代和地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6期,第8—9页。
[10]刘东:《中华文明读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