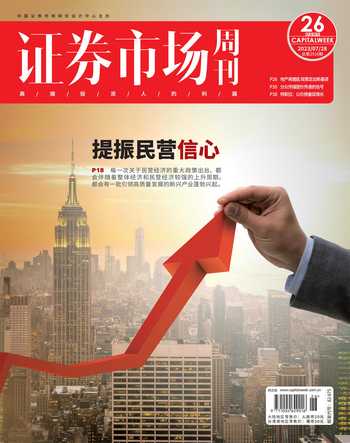如何看待城中村改造
秦泰

本轮“城中村改造”对特大超大城市地产需求具有一定的结构性稳定作用,但总量意义上的需求扩张效应相对比较合理,更多是着眼长期的房地产市场新发展模式的一种探索。
7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这是对4月底政治局会议指出的“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要求的呼应。
“城中村改造”不禁令人联想起八年前如火如荼的“货币化棚改”,彼时房地产市场迎来了一轮阳春,供需循环明显改善,甚至一度在多个城市出现了房价上涨过快、居民恐慌式购房的地产泡沫化现象,此后的2016年底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进入新一轮地产调控周期之中。本轮“城中村改造”与当时的“货币化棚改”存在诸多明显差异,对于我们分析展望后续房地产市场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
据2015年6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相关工作的意见》,当时的改造对象包括城镇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农村危房,其中城镇棚户区和城市危房都指的是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区域,本身已经是国有土地,改造过程中比较有利于在政策的鼓励下加快推进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等前期工作。
而城中村的土地權属涉及到区域内全部或部分仍为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复杂权属情况,在纳入城镇规划、进行改造建设之前,需要首先确定土地权属和性质关系,还涉及到人口城镇化后的工作安置等一系列前置性的问题,推进速度可能明显慢于城镇棚户区。
此次会议还提到“把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结合好”,目前已经出台城中村改造地方政策的城市,更多关注在城中村现有房屋改造后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方向。加之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同决定了城中村改造的情况更为复杂,地产需求预计难以短期内出现类似2015年的“爆发”。
本轮“城中村改造”沿袭了4月底政治局会议聚焦超大特大城市的要求,明确“城市政府负主体责任”,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可能优先于增加总体地产需求的目的。城市发展越成熟,城中村往往越少,本轮涉及区域范围明显小于2015年。除个别特殊历史或地理原因所致之外,城中村密度往往与城市规模和发育成熟度呈负相关关系,特大超大城市中除深圳、广州等个别城市之外,普遍来看城中村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本次实施城中村改造的范围限制较为严格。
市一级政府而非省级政府负“主体责任”,可能意味着并不会重新鼓励专项债资金用于城中村改造,对市一级财政自循环能力的要求更高。
与2015年明确要求 “积极推进货币化安置”不同,本轮城中村改造未明确提出货币化要求,而是改为“积极创新改造模式”,努力发展各种新业态,实现可持续运营。货币化安置的突出特点是完全可以实现地产需求的跨区域迁移。本次国常会中没有明确提及货币化安置的要求,意味着一二线城市地产需求集中大幅膨胀、房地产市场新一轮泡沫化的风险相对货币化棚改时期有比较明显的减弱。
货币化棚改期间要求人民银行给予政策措施配合,一年半时间内MLF、PSL合计新增投放超过4万亿元。本轮并未明确要求央行配合,而是要求“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预计本轮“城中村改造”对特大超大城市地产需求具有一定的结构性稳定作用,但路径范围决定了总量意义上的需求扩张效应相对比较合理,更多是着眼长期的房地产市场新发展模式的一种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优化目标的意义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