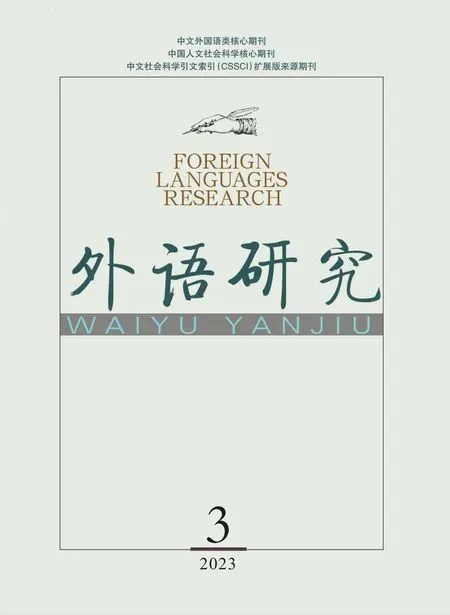朗吉努斯美学思想的四个维度与启示*
覃承华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广西崇左 532200)
0.引言
著名的美学论文《论崇高》①(On the Sublime)对后世的审美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其作者至今尚未明确,“《论崇高》最有争议性的一个方面就是其作者的身份”(Richter 2007:95)。一种说法是,它是由古罗马文艺思想家卡西乌斯·朗吉努斯(Cassius Longinus)所著。另一种说法是根据从大约10 世纪流传下来的手稿,《论崇高》的作者是狄俄尼索斯·朗吉努斯(Dionysius Longinus)。然而,这个名字的真实性有待考证,这是因为这个名字的两部分正好与古希腊罗马时期哈利卡那索斯的哲学家狄俄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和卡西乌斯·朗吉努斯有关联。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认为这个朗吉努斯就是生活于公元前3 世纪的古希腊演说家和哲学家朗吉努斯。但根据各种细节,这两种推断至今都还无法完全令人信服。首先,学界对作者是狄俄尼索斯持怀疑态度的主要依据是《论崇高》与他的其他作品的文体风格和写作方法不一致。其次,批评家对18 世纪以来普遍认为《论崇高》是由朗吉努斯所著的观点也持怀疑态度。理由是《论崇高》第四十四章谈论的是太平盛世时期文学衰退的缘由,这暗示《论崇高》的写作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1 世纪,而朗吉努斯所在的公元前3 世纪正是古罗马帝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与文中所提及的“天下太平”的时代特征相矛盾。据此排除了《论崇高》的作者是公元前3 世纪的朗吉努斯的可能性。根据古罗马帝国的征战史和立国史,英雄主义是该帝国最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向往崇高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表征。太平盛世可以消磨一个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而丧失对崇高的追求。从内容看,《论崇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复兴崇高”,即通过创作具有崇高风格的文艺作品重振古罗马帝国的民族精神。因此,从《论崇高》的文体风格和历史语境判断,其作者极有可能生活在公元前1 世纪。为方便起见,学术界至今仍认为《论崇高》是朗吉努斯所作(Leitch 2010:134)。虽然其作者身份尚存争议,但《论崇高》的作者极有可能是一位犹太人或者他非常熟悉犹太文化,一是因为第九章引用了《旧约·创世纪》的开篇,将无所不能的上帝当作一个与“崇高”有关的例子②,“这样一种参考具有明显的所指:没有其他知名的异教徒作者会以这样的方式对《圣经》进行引用”(ibid.)。再则因为“在西方,崇高源于希伯来文化”(张世英2001:57)。
1.心灵:《论崇高》的立论基石
美学论文《论崇高》以书信体写就,是朗吉努斯的美学思想的主要体现,其中心意旨是驳斥凯齐留斯(Caecilius)的同名文章,向贵族友人特伦天努斯(Postumius Terentianus)阐述对崇高风格的看法,提出其对伟大文学作品的全新认知。在批驳的同时,朗吉努斯也对凯齐留斯否定天赋与技巧关联性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强调崇高与情感之间具有关联性。“崇高需要情感,但情感不等同于崇高,只有崇高的情感才是真正的崇高”(李冰洋2022:4)。朗吉努斯认为,创作主体的天赋——“崇高的思想”(high thoughts)是崇高风格的来源和基础,“艺术家的伟大思想造就了艺术的崇高风格”(Day 2008:47)。艺术技巧是表达崇高思想的途径,二者相辅相成。思想肮脏的人不可能写出伟大作品。只有“崇高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strong passions)等天赋的有机结合,并辅之以近乎完美的艺术技巧,才可能造就伟大作品,即具有崇高风格的作品。不难看出,“崇高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均源自于人的心灵,均和人的内心有关。“崇高源于人的心灵,进而反观人的心灵和自然,产生一种豪迈和惊叹。这样,朗吉努斯把审美直接与人的心灵联系了起来”(朱立元2005:98)。在当时的语境下,朗吉努斯能认识到这一点极为可贵。
心灵是产生崇高思想和强烈情感的源泉,因为崇高风格本质上乃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缪灵珠1998:84)。赋予人物崇高情感的不是自然,而是诗人内化于自然的创造力,是诗人自我的力量。虽然崇高和情感相互独立存在,但强烈的情感是到达崇高的基础,必须通过崇高的写作风格加以实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崇高,首先是因为其思想崇高。《论崇高》的一个极其显著的特征就是朗吉努斯对思想在写作、演说以及阅读中的作用的充分肯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形成伟大思想的能力”放在了崇高风格五要素的首位,认为这是“第一且最为重要的”(Richter 2007:100)。这种思想是“一种崇尚伟大理念、仰视真理的能力”(温晓梅,何伟文2017:71)。可见,对“心灵③”的直接观照是朗吉努斯《论崇高》的立论基石。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对凯齐留斯的批驳,朗吉努斯试图重新确立以心灵为核心的“崇高”审美标准。
创作主体的心灵是知识能力的承担者。创作主体“拥有进行理性思考、感性认识和创造性重构的能力;他对生活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他的思想和情操,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规范着想象活动”(同上:72)。在行文中,朗吉努斯援引荷马(Homer)、色诺芬(Xenophon)以及柏拉图(Plato)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作为崇高风格的典范,对不重视创作主体心灵、脱离诗性真实而一味追求绮丽文风的不良现象提出尖锐批评。朗吉努斯指出:“文学中出现的这些丑陋、寄生增长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新奇的思想表达,这可视为是当今的时尚”(Richter 2007:100)。作家如果不重视心灵崇高和情感倾注,只在修辞上下功夫,那就无异于诡辩或存心欺骗读者。作为一名修辞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朗吉努斯在第一章就从美学的高度指出具有崇高风格的语言与传统的修辞语言存在显著区别:“崇高语言不是‘说服’(persuasion)听众,而是使他们‘神移’(transport)或者‘狂喜’(ecstasy)。使我们心荡神移、惊叹不已的东西远远不是只说服我们、或只让我们满意”(ibid.:97)。与“说服”不同,令人神移、狂喜的崇高语言具有排山倒海般的力量,令听众不可抗拒,并使其心灵受到震撼。可见,朗吉努斯所说的“崇高风格”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特殊品质,是一种以崇高为旨归的美学主张,而不是一般的修辞效果。
朗吉努斯是一位历经数个世纪才被认可的文艺理论家。《论崇高》对于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家及漫长的中世纪均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尼克罗·D.费高罗(Niccolo Da Falgano)将其翻译出来才引起关注。尤其是1674 年法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尼古拉斯·布瓦洛(Nicolas Boileau)的法文译本出版后,《论崇高》才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8 世纪以后,《论崇高》成为欧洲文学批评界的重要文献,受到包括爱迪生(Joseph Addison)、伯克(Edmund Burke)及康德(Immanuel Kant)等人的高度重视。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极大地丰富了论文的内涵。“正是如此,朗吉努斯和《论崇高》成为各个领域的学者不断汲取营养的宝库”(温晓梅2017:74)。尤其是随着康德著名的美学著作《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在1790 年的付梓,“崇高”再次成为重要的审美范畴,并达到了新高度。对此,陈榕(2016:94)中肯地指出,“五百年来这一概念被反复解读,它的阐释者中有一长列重量级的名字。他们都曾经发表著作来阐述对崇高的理解”。
2.《论崇高》美学思想的四个维度与启示
作为一篇文艺美学论文,《论崇高》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从理论上为后世勾勒了崇高不同于一般的美的基本特点,而且着重以文学作品特别是以诗为例,从文章风格和修辞学的角度探讨了崇高风格所应具备的因素”(张世英2001:53)。紧扣“崇高”主题,《论崇高》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它重新论述了文学作品“崇高”的审美判断标准,更在于它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蕴涵。概言之,这些思想内容包括倡导作者、文本与读者的良性互动,重视以古典作品作为崇高风格的典范,崇尚说服与神移的艺术效果,以及提倡文艺作品的整体布局观。朗吉努斯这些审美思想是开创性的。正因为如此,有人指出他在历史上“首先注意到了在分析文学作品时美学欣赏的重要性”(张萍,刘世生2003:92)。总体来讲,《论崇高》的思想内容超越了传统修辞学的范畴,达到新的美学高度。时至今日,这些美学思想蕴含仍是文学批评的重要观测点,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2.1 作者、文本与读者的良性互动
本质上,朗吉努斯的崇高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品质”(quality)。因为从字面含义看,崇高美(sublimity)指的是“某人或者某物所具有的极其杰出或者优秀的品质”(薛小惠2004:64)。《论崇高》开篇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具有崇高美的作品都必须具备两种属性。“第一是对主题的陈述,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说明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和手段”(Richter 2007:97)。朗吉努斯指出,凯齐留斯的《论崇高》虽然列举了许多关于“崇高”主题的范例,但仍然忽略了如何实现崇高风格的方法和手段。朗吉努斯所指的“方法和手段”,就是表达“崇高”主题的语言艺术。崇高的语言对观众的影响力不是“说服”,而是“神移”或者“狂喜”④。这里所说的“神移”或者“狂喜”,是指深深触动听众灵魂、精神高度振奋、欲拒之却不能的一种心理或情感状态。这与修辞学家认为修辞术旨在“说服”听众的观点具有本质区别。在第二章,朗吉努斯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即“是否存在崇高的艺术”,接着他阐述了对经典艺术作品的认识。他认为,崇高是一切伟大作品所共同具备的一种品质或风格。荷马、西塞罗(Cicero)以及德漠斯旦尼斯(Demosthenes)等人的作品都具有伟大、庄严、超凡等特征,与当时辞藻华丽、缺乏阳刚、追求愉悦的审美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他断言,具有崇高美的艺术作品是存在的,它们就是那些公认的古典作品。
崇高是人类心灵的一种独有的认知能力。无论是艺术的创作主体,还是艺术的审美主体,崇高都是构成他们心灵审美特质的基本要素。如前所述,崇高风格是伟大心灵的回声。“一个崇高的思想,在恰到好处时出现,便宛如电光一闪,照彻长空,显出雄辩家的全部威力”(ibid.)。在朗吉努斯看来,崇高的思想能在刹那间迅速地影响读者的心灵,在其心中产生“回声”,使其为之震颤、甚至狂喜。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源自心灵的崇高美,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不仅仅是视觉上或是句法形式上的优美,而是道德文化层面上的深刻之美”(张萍,刘世生2003:92)。再者,人类的心灵具有与生俱来的感知“伟大”和“崇高”的能力。
天之生人,不是要我们做动物;它带我们到生活中来,到森罗万象的宇宙中来,仿佛引我们去参加盛会,要我们做造化万物的观光者,做追求荣誉的竞赛者,所以它一开始便在我们的心灵中植下一种不可抗拒的热情——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所以,对于人类的观照和思想所及的范围,整个宇宙也不够宽广,我们的思想往往超过周围的界限。(缪灵珠1998:14)
也就是说,人生来就有一种对一切伟大的、神圣的事物的向往和超越周围的界限即“无限”的愿望。这是人类心灵的应有之义,是人之为人的天性。朗吉努斯同时对伟大、庄严和神圣事物的范围做了界定。现实中的财富、荣誉、特权、责任与义务等都不是崇高,因为崇高“是超越性情感的产物”(朱鹏飞2011:81),只存在于心灵中。
由于“心灵”是连接读者与作者的纽带,朗吉努斯认为“崇高”的产生是创作主体、艺术品与审美主体良性互动的结果。作者的心灵首先产生崇高,再通过作品进行传递,最后通过读者的心灵对崇高进行感应和引起回响。换言之,创作主体是“崇高”的缘起,艺术品是媒介,审美主体是感应者。因此,在论述了崇高主题之后,朗吉努斯继而以相当多的篇幅论述达成崇高风格的修辞手法,目的就是强调作者要与读者心灵相通,以引起其心灵震撼。由此可见,朗吉努斯非常重视作者与读者之间借助作品的互动交流。需要指出的是,他所指的“交流”,不仅仅局限在常规意义上对于“意思”的掌握,而是要借助想象力去感知文字之外甚至文本之外的含义,因为“作品庄严、雄浑、气势磅礴之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想象(phantasia)”(Longinus 1965:159)。“想象”是《论崇高》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
想象作为构建文学艺术崇高风格重要途径依赖于创作主体崇尚伟大理念、仰视真理的思想以及真挚强烈的感情;想象的介入可以美化作品并激发读者和听众的情感;从而使文学文本呈现“诗性真实”的同时也拓宽了其艺术的审美维度。(温晓梅,何伟文2017:68)
因此,伟大的作品要通过崇高的风格激发读者的想象以产生情感共鸣,而远非简单地用文字传情达意。显然,朗吉努斯非常重视读者与作者基于文本的互动交流,尤其是想象在读者参与建构文本意义过程中的作用。在当代,这一观点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创作是以心接物,即作家用心灵观照社会人生”(龙协涛2004:2)。在文学作品的接受、消费环节,读者同样是用心灵阅读、感悟作家用心灵观照过的社会人生,是一个以心接心,高度抽象的思维和认知过程。因此,文学创作必须顾及作者、文本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朗吉努斯对作者、文本与读者良性互动关系的论述是开创性的。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就如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作家的创作可以看作是产品的制作过程,他写出的作品就如制造商生产的成品。如果没有流通,没有被读者阅读和接受,再好的作品也不会产生价值和影响。因此,作品只有在读者大众的流通中产生影响,就如商品必须在交换中实现价值。但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对文学(研究)存在种种偏见。柏拉图认为,艺术创作仅仅是一种“模仿”活动,艺术家只是“模仿者”,艺术品是“复制品”,模仿的过程是简单、机械的过程,不涉及模仿者的思维、认知活动。虽然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的很多思想家对艺术的看法比柏拉图进步了许多,但各种偏见依然存在。即使是作为西方文学理论史上第一个强调“文学性”(literariness)并明确提出建立一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流派的形式主义批评,也仅仅把文学批评的首要目标锁定在“程式”上。因此,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总是在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循环往复。“整理归纳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脉络,可发现文学读解理论经历了三个明显阶段,即由作者中心论发展到文本中心论,乃至读者中心论”(同上:3)。这表明,文学读解理论的焦点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创作主体、艺术品与审美主体的内在关联看,文学批评中对作者、文本与读者三要素的任何一种的过度强调都是很不合理的。
2.2 古典作品作为崇高风格的典范
古典作品历来是后世学习和摹仿的对象。同为言必称希腊的古典主义者,朗吉努斯和贺拉斯在对古典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贺拉斯强调从古典作品中学习教条和规则等,朗吉努斯则主张从古典作品中汲取崇高思想、强烈情感和表现手法。由于对太平盛世的文坛现状深表失望,朗吉努斯提倡借鉴古人以获得崇高的思想,进而掌握崇高风格。他同时指出,摹仿古人、学习古人不是对他们的盲目崇拜,而是要超越他们。他以希罗多德(Herodotus)、斯忒萨科罗斯(Stesichorus)以及柏拉图对荷马的摹仿,尤其是柏拉图试图对荷马的超越为例,充分肯定了摹仿和超越的必要性。朗吉努斯甚至断言,柏拉图的成就就是源于他对前人的摹仿。“如果没有与荷马一决高下的抱负,那么柏拉图就可能没有如此完备的哲学思想,也不可能在很多情况下找到他诗歌的主题和表达形式的途径”(Richter 2007:106)。他还援引赫西奥德(Hesiod)的诗句“这场争斗对人类是有益的”(ibid.)对此加以肯定。由此可见,朗吉努斯十分重视古典作品的示范作用并呼吁人们超越它们。但他也强调,摹仿古典作家不是简单抄袭古人,因为摹仿“就像是从美丽的形式或修辞或其他艺术作品中获得印象”(ibid.)。因此,朗吉努斯秉持的是一种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摹仿论。他所指的摹仿“是艺术家对古人的一种精神性摹仿,并由此赋予摹仿概念全新的含义”(何伟文2012:84)。
源远流长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西方历史上的新柏拉图主义、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等思潮,本质上都是以重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信念,都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艺术为目标。因此,如何对待古典也是古往今来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在与此相关的探索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以批评家的立场对古典的阐述。蒲柏生活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并且他本人也是一名新古典主义者。他通过广泛阅读古典作家如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尤维纳利斯以及杰弗里·乔叟、威廉·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新古典主义诗人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艺理论家。他的长诗《论批评》(An Essay on Criticism)就是一篇较为系统地阐述美学思想的重要作品,被公认为是体现新古典批评思想的典范之作。在这篇著名的美学文献中,蒲柏论述了其对待古典的态度,提倡将古典作为创作和批评文艺作品的标准。由于对古典作品尤其是荷马作品推崇备至,蒲柏甚至极端地认为荷马就是诗人的“自然”,主张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他深情地写道:“最佳的艺术品源于对自然深入而又合理的研究。对过去伟大作品的研究,引导人们明白自然本身教给他们所依赖的稳固的和谐与秩序原则”(Leitch 2010:347)。“自然”在艺术审美中是极为重要的。《论批评》这样写道:
遵循自然最重要,做你的评价要依其准则,始终正确又一样。永远正确的自然,你神色光明、放诸四海,是永恒不变的明灯。你给予众人生命、力量以及美,同时是艺术的源泉、终极与量杯。(Richter 2007:200)
显而易见,蒲柏将自然当作了艺术鉴赏的最高原则,认为通过遵循自然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审美趣味。同时,“自然”则主要指的是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尤维纳利斯以及乔叟、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蒲柏认为能提升审美趣味,并且能使读者感知艺术和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蒲柏看来,古典文本就是一种方法化的自然,是评判艺术品的标准和尺度。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当下很多批评家没有趣味、没有原则,甚至没有德行。因此,他又进一步论述了自然和荷马之间的关系:
让荷马的诗篇成为你研赏的大作,白天品读、夜晚思索,由此形成鉴赏力,并带给你格言;继而探寻其缪斯,直到其根源……他(维吉尔)发现,自然与荷马竟不谋而合。所以,对古人法则要心存敬畏;抄袭自然,就等于抄袭了他们。(ibid.:201)
借维吉尔(Virgil)之口,蒲柏在这些诗句中对荷马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一方面,人们的审美趣味是通过阅读和思考荷马的作品形成的;另一方面,荷马的诗作就如同自然,就是诗人模仿的对象。如果艺术创作的确如柏拉图所说是对自然的复制和模仿,那么如今抄袭自然就是抄袭他们(荷马等人)的作品,因为“自然和荷马竟不谋而合”(ibid.)。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蒲柏所指的自然,不是供艺术家模仿的对象,而是为批评家建议的一项评判标准。这是因为,蒲柏的《论批评》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以自然为标准评判艺术品,而不是如何进行艺术创作。
蒲柏强调,通过学习古典作品,既可以提升自己的知识学问,又可以形成自己的审美趣味。蒲柏认为,尚在人世的作家,大多尚未接受时间的检验,因此不宜成为审美活动的趣味标准。在这一方面,20 世纪著名作家海明威与蒲柏是一致的。海明威认为,评价一位作家写得好不好,唯一的办法是将其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好作家多数并不存在,其名声都是批评家造势出来的。因此,海明威总是将看齐对象锁定在那些已经逝去的、举世公认的著名作家上。他曾数次以拳击隐喻和那些著名作家的较量:“我先试了屠格涅夫先生,不太难,又去试了莫泊桑先生,四个短篇才打败他。他被打败了。有些家伙是没人能打的,比如莎士比亚先生和无名先生”(海明威2019:809)。众所周知,这些作家都写出了举世公认的经典作品。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也十分重视经典作品的重要作用。布鲁姆指出经典具有陌生性(strangeness)、普遍性(universality)、竞争性(completeness)和焦虑性(anxiety)等特征,他同时认为经典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作家、艺术家与作曲家自己确定了经典,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者联系了起来”(布鲁姆2011:433)。经典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产物,是由作品自身特有的美学和审美价值决定的。一般来说,经典作品都具有崇高的美学特质,而崇高又赋予经典一种特有的美学尊严。“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是无法借鉴的”(同上:29)。因此,朗吉努斯对待古典作品的态度是客观的、可取的,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
2.3 说服与狂喜的艺术效果
说服与狂喜,简言之,就是文学的“教化”(teach)与“娱乐”(delight)作用问题。自古以来,文学便被赋予“教化”的功能。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通过学习经过严格审查的文学艺术,人们可以成为理想国中懂得“善”的公民。贺拉斯(Horace)在其《诗艺》(The Art of Poetry)中对柏拉图的观点做了补充,认为诗的最终目的是“教化”和“娱乐”,诗人应该“要么娱乐读者要么启蒙读者,或者写些既有趣又有用的东西”(Richter 2007:91)。贺拉斯认为,不同读者群体的目的各不相同,如骑士阶层追求“娱乐”,上层社会则更看重诗的“有益的教化”(ibid.:83)。道德主义者但丁(Dante)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则更为看重文学的“教化”功能,“娱乐”充其量不过是实现“教化”的一种途径。菲利普·悉德尼(Sir Philip Sidney)和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等人则与但丁和约翰逊相反,认为诗的主要功能是“娱乐”。当然,这些批评家对诗的功能的定位是和他们关注的读者群体密切相关的。比如,柏拉图和贺拉斯将读者群体限定在上层人士,悉德尼和德莱顿所说的则是大众化的读者。
朗吉努斯认为,向往崇高是人类的天性。虽然崇高的思想是一种天赋,但仍可以通过升华的语言体现出崇高的风格,进而激起读者对崇高思想的共鸣。因此,朗吉努斯十分重视崇高和情感的关系,认为崇高与情感并非像凯齐留斯所说那样是同一个东西,而是相互独立、相互影响的关系。朗吉努斯指出,有的情感是卑微的,而有的崇高篇章又没有情感,所以有助于崇高的莫过于恰到好处的真情。他还以荷马诗句为例做了说明。正是因为崇高和情感都和心灵密切相关,而且可以互相分离,朗吉努斯特别强调文艺的情感效果,对文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狂喜(ecstasy)。如前所述,狂喜是一种高度兴奋的心理或情感状态,是一种强烈艺术效果的表征。既然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是“近乎神的伟大心灵的境界”,只有在听众的心灵中产生情感上的反应,引起了共鸣,那么崇高才可能被最终认可和接受。因此,崇高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服观众,更在于使人心荡神驰即狂喜。凡是令人惊叹的篇章总是有感染力的,往往胜于说服。朗吉努斯所说的“一个崇高的思想,在恰到好处时出现,便宛若电光一闪,照彻长空,显出雄辩家的全部威力”(ibid.:97),强调的就是崇高的艺术所产生的一种巨大的情感效果,一种征服性的思想力量。崇高风格本质上不是一种修辞艺术,而是一种可以震撼心灵的强烈情感。这种强烈情感源于具有崇高主题和崇高风格的作品,作用于它的读者,“使之达到高远的意境,仿佛使之孕育着高尚的灵感”(缪朗山2011:71)。因此,《论崇高》结尾处再次如此强调:“强烈感情在一般文学里具有重大作用,尤其在有关崇高的这一方面”(朗吉努斯1996:129)。
任何时代的艺术何不如此呢?文艺创作者,尤其是伟大作家必须具有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崇高的思想以及表达崇高思想的语言能力。一方面,创作题材必须源于生活,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时代潮流又不同流合污,既为大众所认可又具有一定前瞻性,既具有现世价值又具有传世价值。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创作要内容和形式并重。也就是说,作品既要具有庄严崇高的思想内容,又要强调优美的语言表达。一部作品无论其思想何等庄严崇高,读者都有权选择接受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读者是否接受一部作品的关键在其语言。如果一部作品语言表达毫无技巧、枯燥无味,甚至毫不掩饰地进行道德说教,读者就不会有兴趣去阅读它,更不用说接受其教化了。这一点,贺拉斯说得极好:“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其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转引自Richter 2007:91)。
2.4 文艺作品的整体布局观
整体布局观是《论崇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蕴涵。在第一章,朗吉努斯指出:“我们看到的技巧上的原创性、事件顺序和组构的得当,不是在一两段话中就能体现出来,而是整篇作品努力得来的结果”(ibid.:97)。朗吉努斯开门见山对凯齐留斯进行指责,就是因为他只抓住了“崇高”的一半即主题/内容,忽视了实现崇高风格应采取的方法/途径。朗吉努斯正是紧紧抓住凯齐留斯的疏漏,从整体布局观出发,写出了充满美学思想的论文《论崇高》。
内容和形式是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侧面。贺拉斯认为,艺术美的基础是不论作什么,至少要做到统一、一致,形象的合式在于具有整一性。朗吉努斯也充分认识到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重要性。在开篇,他就论述了主题以及如何实现主题途径的关系问题。凯齐留斯的致命缺点就在于,他大谈特谈了作品的“崇高主题”问题,却忽略了对如何实现这一主题的论述,这也是他成为批判对象的关键。在第八章,朗吉努斯所述的崇高风格五要素仍然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朗吉努斯同时指出,这五种要素的共同基础是语言的运用能力。在后续章节,他先后论及放大(amplification)、倒装法(hyperbaton)、叠叙法(polyptoton)、隐喻(metaphor)以及夸张(hyperbole)等修辞手法。这些都是运用语言的技巧。由此可见,朗吉努斯再次强调了“主题”(内容)与“形式”(语言)的关系问题,即“内容产生形式,形式是内容的一部分,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辩正关系”(赵丹丹2009:76)。
在结构上,朗吉努斯同样认为崇高的风格要有整体性。作家应该成为组织文本结构的大师,应该使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第一章,他就指出崇高的思想的效果源自“作品的整个结构”(Richter 2007:97),这是雄辩家的“全部威力”得以发挥的前提。在第十章,朗吉努斯进一步深入论述了选取与组织材料时的整体性原则⑤。他指出,任何一个话题都包含原始材料中固有的特定元素,因此选取与组织材料是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前者是指我们从最重要的特定元素中选取“崇高”元素,后者是指将这些“崇高”元素联结成一个整体。选取的过程通过“观点”或者“细节”⑥吸引读者,组织则是通过这些经过选择的材料综合(aggregation or density)去实现对读者的吸引。恰当的选取和组织材料有助于实现作品的崇高风格,反之则有损于这种风格。因此,选取和组织材料都必须在结构的整体性原则下进行。“独运匠心,善于章法,精于剪裁等等,不是在一两处可以觉察到的,而须在全篇的发展中逐渐表现出来”(ibid.)。这些言论强调的就是组织材料过程中的整体意识和整合为一的能力,体现了艺术的整体布局观。这一观点在他的崇高风格五要素的第五点——“庄严而高尚的布局”⑦中得到进一步强调。
朗吉努斯的整体布局观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影响力。蒲柏就认为,文艺鉴赏者要具有整体意识,“文情就像自然,能感动我等心灵的地方,不是那些独特部分的精致;我们称之为美的,不是一张嘴唇或一双眼,而是总体力量下形成的整张脸”(ibid.:203)。因此,有审美趣味的批评家应懂得看整体,而不是逐个部分挑错。思想家爱默生也认为,大自然使诗人的内心具有一种“诗性意识”(poetic sense),而且诗人具有将自然的不同部分联结统一起来的能力。在《自然》第一章,爱默生这样写道:
当我们这样谈论自然时,我们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清晰独特的诗性意识。我们在感觉多面的自然客体与和谐完整的映像。正是这映像区分了伐木工人手中的圆木和诗人心中的树木……他们(伐木工人)无法占有这片风景。只有诗人的双眼拥有这地平线,这是他们农场最可贵的,却没有人能通过产权对它据为己有。(Levine & Krupat 2007:1112)
爱默生此番论述的核心要旨,就是自然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影响。对伐木工人而言,自然是一种看得见的物质形态,他们也只能孤立地感知这些看得见的、物质的部分。然而,在诗人眼中,自然不仅是一种看得见的物质形态,而且具有一种视觉无法感知的内在的美。在爱默生看来,诗人必须具有整体意识,具有通过心灵的力量将自然不同的物质部分整合为一的能力。这就是诗人与伐木工人之间的本质区别。这些思想,无疑是对朗吉努斯的继承和发展。
朗吉努斯对“主题(内容)”与“形式(语言)关系的论述和文学批评的对象密切相关。20 世纪以来,形式主义批评所倡导的“为形式而形式”、结构主义批评所提倡的“作者之死”、读者反映批评以及认知语言学家所说的“表达没有意义”(Vyvyan 2006:366)等论断,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文学批评中整体意识的缺失。本质上,朗吉努斯对文艺作品“主题”(内容)与“形式”(语言)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一个至今都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即为什么应该用整体布局观去审视一件艺术品的美。
3.结语
著名批评家艾伦·泰特(Allen Tate)称朗吉努斯为“第一位文学批评家,尽管必然是不完善的”(1948:345)。朗吉努斯也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批评家。他一改古希腊将文学审美对象锁定在外部真实的现状,以极大的勇气将焦点转向审美主体的内心。对心灵的直接关照是《论崇高》立论的基石。通过对凯齐留斯崇高主张的批判,朗吉努斯以人的“心灵”为中心重新确立了“崇高”的审美标准。他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崇高的天赋,也有向往崇高的本能,具有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同时,即使有些人天生没有崇高感,也可以通过阅读古典加以培养。在《论崇高》中,无论是对“崇高”与“情感”的论述,还是关于崇高五要素的论述,朗吉努斯都是以“心灵”为中心的。他从美学角度肯定了人的心灵的力量,这是其优点所在。由于时代所限,朗吉努斯的美学思想也存在不足,他的崇高美学具有一些神秘主义倾向,他对崇高风格的论述也比较主观。总体而论,《论崇高》的美学思想内涵包含四个维度,超越了传统修辞学的范畴,达到一个新的美学高度,至今仍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由于年代久远,《论崇高》的原稿早已失传。笔者对比了分别由David H.Richter 和Vincent B.Leitch 两位主编收录的英文译本,差异较大。在前者的编著中,标题是On the Sublime,而后者的编著中,则是On Sublime。内容方面,后者收录的文本有一个简短的序言,章节的安排也有很大不同。
②在《论崇高》中,朗吉努斯援引《圣经·创世纪》的例子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说要有陆地,于是就有了陆地”。
③“心灵”也是亚里士多德思想中一个重要概念。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将“心灵”与“灵魂”两种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更为高尚。
④“神移”在里希特(David H.Richter)和里奇(Vincent B.Leitch)二人主编的著作中表述各不相同,前者为“transport”,后者译为“ecstasy”。
⑤在里希特主编的《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中,第十章有个标题为“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Material”。
⑥将其表述为观点或者细节,主要是参照了里希特与里奇两个版本,前者译为“idea”,后者则为“details”。
⑦虽然将“庄严而高尚的布局”放在《论崇高》最后,但这并不意味着朗吉努斯不重视它。将前面四种因素联系成一个整体是这个布局的重要前提。因此,这个布局是一个综合各种要素、集各方智慧的圆满结局。此外,朗吉努斯还强调指出,布局是一种语词的和谐,形成宏伟风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各种成分的适当组合,就像人体一样。单独的一个部分本身如果离开了其他部分,就没有任何可以值得引人注意的,但是当它们被全部结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这些论述表明,朗吉努斯对部分和整体的关系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