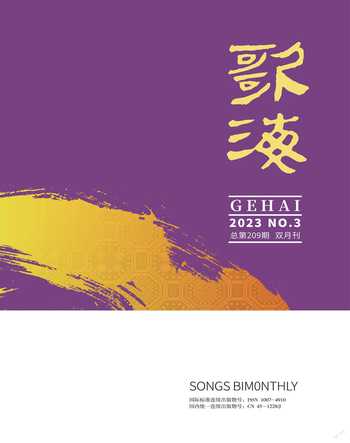追歌如梦

黄朝瑞 广西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第八届、第九届主席,中国音协理事),一级作曲。撰有《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苗剧分卷》《广西大百科全书·音乐卷》(编辑兼撰稿),发表《广西苗剧音乐的艺术特征》《谈广西音乐的本土意识和时代性》《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多篇论文;创作有戏剧、舞蹈音乐和歌曲百余首,在中央及区市级电台、电视台、大型晚会及核心期刊《音乐创作》《歌曲》等播放或演出、发表。曾担任国家艺术基金专家评审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五个一工程”奖等区内各类大型活动评委。创作的主要歌曲作品有《说中国》《跺跺脚》《嫁给山歌》《鲜花映彩虹》《蝶恋花》《喜鹊登枝》《蝴蝶飞》等,出版个人专辑《嫁给山歌:黄朝瑞作品选辑》。曾应邀为在美国堪萨斯举办的“斯诺《西行漫记》发表80周年纪念音乐会”创作主题歌《斯诺》。作品分别获“中国音乐金钟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和广西“五个一工程”奖等,个人获“广西文化先进工作者”“广西文联系统个人二等功”荣誉称号,策划组织了“唱广西”歌曲创作、“广西廉政歌曲创作”“全区少儿歌曲创作”“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歌曲创作”等活动以及“那坡壮族民歌”“平果嘹歌”的挖掘、整理、推广等,策划并组织生产了《壮族敬酒歌》《广西尼的呀》等有影响的歌曲作品,策划并组织创作《山歌好比春江水》《稻之韵》等大型音乐剧目。
一、关于我
我祖籍邕宁,父亲70多年前从那楼到南宁打工学手艺。他边打工边上会计夜校,18岁考入华南垦植局南宁分局文工团任会计,与现武汉音乐学院教授陈国权和自治区歌舞团作曲家詹景森成了同事。
1954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山区建设,去了大苗山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分配到毗邻贵州从江的大年区(乡)供销社任会计。从县城到供销社要翻过几座大山,走三天山路,没有公路没有电,条件相当艰苦。两年后我意外地在这里出生了。为什么说意外?因为当时山区条件艰苦,与父亲同来的八名援山干部都先后辞职返回原籍,父亲也动了离念。为了挽留人才,供销社主任和区委书记密谋施了个“美人计”,将同社18岁的母亲介绍给父亲结为连理。年轻人虽思乡心切,却经不起爱的诱惑,我便降生在那个偏远的山乡。那地方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晚上听狗叫,天亮听鸡鸣。我五岁那年回老家探视爷爷奶奶,才知道世上还有电灯、电话、留声机。山里有种风俗叫“坐妹”,一到晚上姑娘小伙子围坐在火塘边对山歌。父母的同事叔叔阿姨们都喜欢抱着还没懂事的我去听山歌。如今艺术家提倡下乡采风深入生活,我可能是深入基层“采风”最早、年纪最小的了。这也许是为我后来与音乐结缘埋下的一颗种子吧。
可要说音乐萌芽,应该是于懂事时看见父亲的一张拉小提琴照片开始。当时见到小提琴的第一眼,我心里便“咯噔”一下,大脑像照相机一样印下终身不忘的影像。后来再长大一点,见村头河边梁家老六常在家门口树下摆弄着一种叫“哦惹”的玩意。他虽有些残疾,却无师自通,用他父亲给他制作的后来才知道叫二胡的乐器,可以拉一些《東方红》那样的曲子,还可以模仿人说话,“要馍馍来拌辣椒吃哇——娘耶!”很有趣,吸引了一帮小玩伴。于是我父亲也给我买了一把二胡,从此学着“六哥”的模样拉,也许这就是我的音乐启蒙。
高中毕业下乡插队当农民,在乡里曾发起组建乡村文艺队。幸运的是两年后,我鬼使神差地上了广西艺术学院,开始了正规的音乐学习,更意外地得到广西艺术学院创始人、音乐教育家满谦子教授了一年课程。为什么说是意外?那是因为当年满老爷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我们班来“接受改造”,打倒“四人帮”后他才得以重登讲台。教育家的天职良心令他主动要求给我们恶补专业课,他教授的“腔词论”令我终生受用。假期,回乡实习住县招待所,练琴时突然听到敲门声,原来是住马路对面的文工团团长和乐队指挥循着琴声找到房间,寒暄后约我学成来团工作,并许诺再送我回母校专修大提琴。没想到这一意外“敲门”,竟领我踏进职业之门。毕业后我进了县文工团担任乐队演奏员兼创作员,参加过歌剧《江姐》及《刘三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大型剧目演出,创作的作品也被团里作为保留节目及在全区全国会演中获奖。那时,《歌海》杂志也发表了我不少作品。
1989年调入柳州地区群众艺术馆当音乐辅导员后,我又幸运地上了文化部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作曲进修班,学习了李西安教授讲授的音乐美学、李重光教授的乐理、罗忠容教授的现代音乐、施万春教授的和声、杜亚雄的民族音乐学、高为杰的音乐欣赏和曲式、王宁的配器、张韵弦的复调等专业课程,领略了大量的中外音乐经典。
1999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全区征集“共产党员正气歌”,我很幸运,有两首作品同时入选了,因此被调到自治区音协工作。
遇到贵人是人生之幸,而不断地遇到贵人是幸之又幸。把我从柳州招调来的傅磬,是广西音乐界的领军人物,我们在笔会中相识,他对我影响和帮助很大。后来我又有幸与著名词作家张名河为邻,忘年之交,友谊笃深,他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导师。是这些贵人的鞭策和引领提升了我的艺术境界和人生格局。在广西音乐家协会工作20余年,我在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也兼顾创作,曾策划各类音乐创作、表演、比赛、民歌挖掘等全区性大型活动,组织创作和催生了一批至今仍传唱的优秀作品,如《壮族敬酒歌》《山歌牵出月亮来》《广西尼的呀》《连心歌》《星星伴月亮》等歌曲以及音乐剧《山歌好比春江水》《稻之韵》等大型民族音乐剧目。“深耕民族音乐”“追求域风个性”是我秉承的理念和诉求,并以此带动和影响、培养青年一代的音乐人。在个人创作上,《嫁给山歌》《跺跺脚》《喜鹊登枝》《蝴蝶飞》《山里山外》《家在柳州》等是我追求域风个性的尝试。《嫁给山歌》幸运地获得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优秀作品奖”(本次评奖不分等次)。之后《鲜花映彩虹》《喜鹊登枝》《蝴蝶飞》《山里山外》等也传唱全国各地,成了全国各地高校、中小学和社会文化活动常演常唱的曲目。《跺跺脚》入选广西小学音乐教材。《蝴蝶飞》被我国著名指挥家吴灵芬选入由她指挥的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中外经典合唱音乐会”。2018年,我和麦展穗受美国斯诺基金会和华人协会的邀请,为在斯诺故乡堪萨斯举办的“纪念斯诺《西行漫记》发表80周年音乐会”创作主题歌《斯诺》,在考夫曼艺术中心由芝加哥等三个州的合唱团联袂演出。这是我的作品走出国门的精彩记录。
我与音乐结伴一生,音乐是我的至爱,数十年来虽然数易工作却始终没离开过音乐。大山的灵气涵养我,生活的风雨砥砺我,师友的关怀鞭策我,歌友的热情鼓舞我,助我把歌追进了国家大剧院,追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追到了大洋彼岸的考夫曼……追到了祖国大江南北。
二、我的创作观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他们都有一种表演艺术,深刻而生动地反映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比如希腊的悲剧、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芭蕾、意大利的歌剧、中国的京剧和昆曲等。如果要问,广西文化的精神代表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广西民歌。
广西的12个世居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都有以歌传情、以歌会友、以歌言事、无处不歌的传统习俗。所谓“故事唱着说,情书用歌写,山歌当茶饭,唱歌过大节”,就是这方水土,这片民风、民俗的生动写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方文化。在全国乃至国际有影响的以民歌为主要特色的剧目《刘三姐》,就是在这样一种人文氛围里面萌生的,在这片土壤里面成长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有一句口号,叫“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正是切广西之地,切民歌之实的色彩鲜明的艺术呼号。因此,自治区党委把“打山水牌,打民歌牌”作为广西文化战略写进党代会的报告,就不无深刻的道理了。
确实的,广西民歌是广西人的骄傲!
民歌,是这块土地上劳动人民祖祖辈辈传唱的歌谣,里面记录着先辈的喜怒哀乐,蕴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民族的根与魂。民歌属口头创作,是底层民众歌唱与文学结合的艺术形式。广西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区域都有不同的民歌曲调,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山歌好比春江水》,高亢嘹亮的《过山腔》,雄浑深沉的《红水河有三十三道弯》,清新明丽的多声部民歌《三顿欢》《蝴蝶歌》《嘹歌》《侗族大歌》等。就是这些民歌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多姿多彩的音乐海洋,无怪乎被艺术家们称为是民族音乐资源的富矿,是广大艺术家创作的丰富源泉。
但凡音乐大家,总是对民间音乐艺术深怀崇敬之情。远如俄国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近如我国何占豪、陈钢的《梁祝》,阿炳的《二泉映月》,赵季平的《大宅门》,这些传世之作,无不是从民间音乐或民间戏曲中汲取营养而产生的。长久以来,音乐工作者们怀着敬畏之心,将民歌曲调作为素材,创作了许多既富民族特色又呈新意新貌的广西优秀歌曲,深受民众欢迎,如《壮锦献给毛主席》《赶圩归来啊哩哩》《大地飞歌》流传久远……还有一直流传的《壮族敬酒歌》《挑着好日子山过山》《山歌牵出月亮来》《跺跺脚》《黑衣壮的酒》以及“三月三嘉年华”主题歌《广西尼的呀》等一批新民歌,哪一首没有民歌元素!
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常接触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同行及国外友人,当与他们谈及广西民风、民俗、山水,特别是谈到民歌时,他们无不流露出极其羡慕的眼光和兴奋的神情,每当此时我感到最为驕傲和自豪。广西民歌在我国专业学者眼中也有着相当地位,20世纪80年代广西曾因发掘出三声部民歌,打破了“中国无多声部民歌”的定论,引起学界轰动,而引来“全国民歌研讨会”众多顶级专家的与会。朱诵邠老师从壮族和瑶族民歌二度到同度特征总结出来的“k2终止式”理论,对丰富既定的和声学理论做出了贡献。富川瑶族《蝴蝶歌》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音乐,几乎贯穿、跨越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中国新民歌”理论探索和实践提供了平台,其影响力已被大家公认……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一方面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亲身经历了从物质匮乏到丰富的过程,另一方面,也看到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本土民族文化呈现出逐渐弱化乃至逐渐丧失的危险趋势。因此,爱护和保护作为本土民族文化精粹的民歌文化遗产,必是我们当今的一份责任和任务。民歌和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民族的DNA,也是民族的一个标识。艺术的本质要求艺术作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艺术家欲在多元文化中追求保持民歌之美、民族风之美,创造独特的品格和形貌,就要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艺术个性,在继承的基础上求新求变,不断积累经验,写出更多更好的为群众喜爱、易于传唱和流传的歌曲,写出真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我的民歌我骄傲。这是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民歌是历史,是民族史、是心灵史,是我们祖先发自心底的歌唱,我们祖先创造的精神财富,绝不能衰亡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那些在八桂大地上唱响千百年的民歌,继续回荡在祖国的晴空丽日下,让先辈血管里流淌的血脉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天职。
三、关于“山水乐歌”的理论构想
(一)何谓“山水乐歌”
习近平总书记说:《刘三姐》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根植于广西的山山水水,契合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总书记一语解开了《刘三姐》成功的密码,也给广西音乐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广西音乐人努力追求,创造了建立在广西山水文化基础之上,以广西山水文化为依托,以广西各族音乐元素为底色,以广西民族风格和表现广西民族真善美的作品为载体,根植于广西山水之间的音乐文化,形成了别致的音乐风格和特征。经一辈又一辈音乐人的坚守和努力,经过了几十年岁月风风雨雨的洗刷,逐步形成了一条域风浓郁、特色鲜明的“山水乐歌”长河,生生不息,一脉相承。这些长期积淀下来的根植于广西山山水水的优秀歌曲,在各个不同的年代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人认为,这些多年沉淀下来的歌曲,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风格浓郁、特色鲜明的曲风流派。她们是中国音乐艺术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建议且将其归纳一个统称,谓之“八桂山水乐歌”。
广西以山水著称于世,广西山水文化已被世人所公认。“山水乐歌”中的“山水”即取意于此;同时,也契合了“打山水牌,打民歌牌"的文化发展战略思路。“乐歌”取于“学堂乐歌”,“乐歌”意为“歌唱”,“山水乐歌”即为“山水间的歌唱”。
“山水乐歌”包含了“刘三姐歌谣”。“刘三姐歌谣”是“山水歌乐”的主要代表之一。《山歌好比春江水》取材于柳江民歌《石榴青》,是“刘三姐歌谣”的源头。从彩调剧到电影《刘三姐》的主题音乐均由她生发而来。树有根,水有源。凡取材于广西各族音乐元素生发而来的或表达广西人民民族情感的音乐均归属于“八桂山水乐歌”范畴。
(二)构建“山水乐歌”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根之所在,情之所系;梦之所绕,魂之所牵。祖祖辈辈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一种心之所向的情结。乡音乡情,这是一种“乡愁”,是一种精神寄托,是灵魂的归属。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的侵入,民族文化的传承处境十分尴尬。在文化的日益趋同大势下,音乐文化成了人们追求的重要精神领地。
广西音乐文化属岭南文化的一个分支,蕴含着强劲生命力和高度审美价值,只是由于一直以来没有作为整体在理论上勾画出来,未能受到广泛瞩目。理论上的滞后和缺失,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广西音乐的发展。而其他艺术门类如“漓江画派”“八桂书风”等先于音乐的文化构建,已突显和发挥出对其艺术应有的促进作用。因而,广西音乐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够包容各民族音乐文化内涵和强劲生命力以及高度审美价值的理论去统领,从而使之在音乐研究、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表演和音乐推广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以上是我从事音乐工作的主要经历和对广西音乐发展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