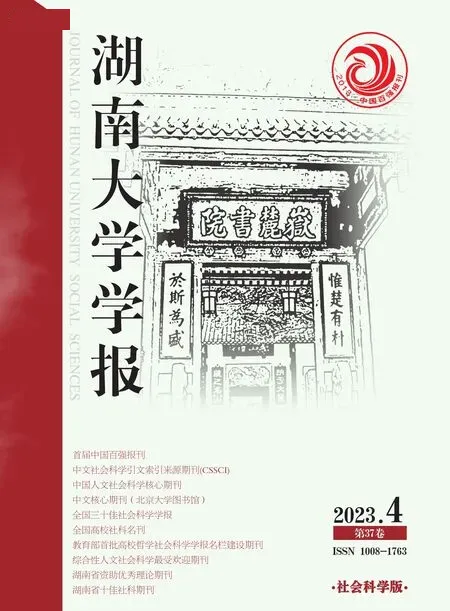文献流动性视域下清华简中之楚文化特征*
王 建,李静怡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文献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流传阶段,文献有着不同的记录和传播方式。就上古文献来说,其文本的产生多依赖特定的书写或刻写方式,历经甲骨、青铜、简帛等文献载体。此外,文献主要通过师生之间的“口耳相传”进行传播,许多文献并非单纯的“一次创作”。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以及学术界对文献与文本生成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先秦时期的文献群体并不存在“唯一作者”或“固定的作者群”[1],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层次性”与“流动性”。由于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会到达不同的地域,尤其在春秋战国这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文献选编及流传会带上本地的色彩,由此导致了文献系统的复杂性,使得某一特定的文献群体带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近年出土的清华简,由于其特殊的文献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早期的地域文献状态,在文献与文本问题上具有研究价值。
清华简虽不由考古发掘所得,但根据碳14测定,其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这也与专家的鉴定结果一致。此外,将文本与其他从楚地考古出土的文献比对,可以判定其属于战国中晚期的楚地文献[2]。清华简这一批战国文献的文本内容多样,有些后世亡佚,有些则被保存流传下来。与传世文献比对,清华简中许多篇目可在《逸周书》,以及成书于邹鲁地区儒生之手的《尚书》等传世典籍里找到对应文本,如《皇门》《程寤》《金縢》等;或者有不见于后世,但属于先秦战国时期的“书”类文献,如《尹至》《封许之命》《厚父》等。此外,这一批简文中有不少先秦时期的“诗”类文献,可与传世文献中的儒家“诗”篇相比较。由此可见,清华简的文本在当时应当属于经过一定积累沉淀后,已经流传一段时间的成熟文本。许多文本并非在楚地写就,而是由其他诸侯国流入。在这样的文献语境下,结合楚国的地域性特点,其文本层次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其由文本“层次性”所反映的地域“流动性”十分明显。因此,对这样一批在楚地流传和成书的先秦文献进行楚文化特征的“分层”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文化对先秦战国文献群体在文本生成过程上的影响。本文拟从文献“流动性”视角探究清华简中的楚文化特征,以期反映楚文化在清华简文献生成中的形塑表现。
一 从文本形态角度看清华简的楚文化属性
(一)楚文化在文字上的表现
作为流传在楚国的先秦简帛文献,清华简的抄手在转移抄写文本时,出于本地流传的需要,主要使用楚系文字。然而由于抄手所抄底本来源各不相同,很多底本并非在楚地生成,因此又有非楚因素在其中。一些抄手在文字的抄写上会忠于底本,而另一些则会进行楚地特色的改造。甚至同一篇目中会出现既有楚系特点,又有其他地域风格的文字。这使得清华简的文字呈现出复杂的形态。[3]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保训》《良臣》还是《系年》,文本中的文字结构基本上都属于楚文字。这说明非楚因素主要表现在文字书写上,而非文字结构中,因此它们仍然是楚地抄本。我们可以认为,清华简的文本通过文字上具有的楚地特征,以及部分文字所包含的异域书风特色,综合构成了这一批战国时期抄本的文字特点。这体现出楚文化对地域“流动性”文本在文字上的本地塑造,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文本“层次性”。
(二)楚文化在篇目上的表现
由上述分析可知,清华简的底本流传比较复杂,有些涵盖不同的国家地域。因此,清华简的文本在篇目版本上的表现也具有复杂性,反映出楚地特色。例如,清华简《封许之命》作为一篇“书”类文献,其主体文本编写应当早于清华简的整体成书年代,学者多认为在西周中期以后。[13,14]后来的整编者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改,使其脱离原本的册命实用性,变为典籍类的文献材料。[15]由此可看出,西周中期以后《封许之命》的改编,应当主要由受封地域的许国人整编,作为针对许国子弟教育学习的文献而保存。那么,从清华简的整体文献篇目上来看,除了像《尹至》《皇门》《程寤》等以三代圣王为主题的典型“书”类文献外,为何还会有像以许国为中心的《封许之命》这样的篇目存在呢?我们认为其中体现了楚文化的影响。楚国与许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关系密切。据《左传》记载,鲁成公十五年时楚君迁许于叶,此后许国逐渐沦为楚国的附庸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两国间的文献传递变得频繁,《封许之命》这样的文本便是在此情况下传抄流入楚国的。因此,在清华简这样的楚地文献整编中,《封许之命》也被作为楚国贵族阅读的典籍类教本编入,使得清华简中出现了与楚国关系密切的小国文献。
除《封许之命》外,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和《尹诰》《尹至》的紧密编联也体现了楚文化色彩。对于《赤鹄之集汤之屋》这样一篇具有楚地神巫文化特征的文献,学者多认为属于“小说类”文本,[16,17]而非与《尹至》《尹诰》一样属于“书”类文献。这样的认识大多基于《赤鹄之集汤之屋》中神秘虚构的描写而得出,认为不符合“书”类文献一贯的文体风格。我们认为,《赤鹄之集汤之屋》简长为45厘米,与《尹至》《尹诰》的简长一致,且背面的刻画线、抄写书体笔迹亦与《尹至》《尹诰》一致,说明三者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清华简的整编者是出于三者属于同一类文献的认识而做出此种编排,体现出整编者对于这些文献的接受和理解。《赤鹄之集汤之屋》通过伊尹叙述的事迹,说明伊尹虽然出身卑微,却能够辅佐商汤推翻夏桀暴政,以此说明“选贤举能”的内涵。因此,《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其他两篇简文在内在思想上仍然一致。由此可知,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定义与后世人不同。甚至战国时不同地域的人,对于“书”类文献的认识也不一样。这样的认识会随着地域文化差异带入文献的编排与分类中。[18]因而清华简的篇目中会出现《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尹至》《尹诰》紧密相连的情况,从而表现出具有楚文化色彩的篇目编联特点。
由《封许之命》及《赤鹄之集汤之屋》,可看出楚文化在清华简的篇目选编上的影响。此外,清华简的篇目中还有诸如《楚居》这样主要叙述楚地历史源流的文献,更加反映出清华简中的楚文化特色。这都是地域文化在文献群体塑造上的体现之一。
二 从文本内容角度看清华简的楚文化属性
文献的编选往往代表整编者对于文本内容的理解与认可,尤其在先秦文献中,文本形态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将清华简的文本与传世文献对比,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不一致的文句,说明清华简的文本在文献辗转传抄的流动过程中遭到了增删改动,这点当在情理之中。[19]清华简作为用楚地文字抄写完成的文本,其整编者必然是楚国人。因此,文本中许多思想内容的体现,也必然为楚地人所认可理解,通过对思想文化色彩的探讨,可以看出楚文化在其中的作用。
(一)神巫色彩浓厚
清华简中屡见带有神巫色彩的文本,像《赤鹄之集汤之屋》中就有描述神灵化的鸟类动物:
巫乌曰:“是小臣也,不可食也。夏后有疾,将抚楚,于食其祭。”众乌乃讯巫乌曰:“夏后之疾如何?”巫乌乃言曰……众乌乃往。巫乌乃歝小臣之喉胃,小臣乃起而行,至于夏后。[20]167
又有能听懂帝命的兔子与黄蛇:

以上这些动物在《赤鹄之集汤之屋》中均带有灵性的成分。众乌救下小臣,而受命于帝的黄蛇与兔子则加害夏后,使其“疾疾而不知人”“不可及于席”。不同的动物在其中具有不同态度,反映出神异化的特点。
《赤鹄之集汤之屋》在故事情节上亦显示出神巫特征。小臣去见夏后,夏后问他是谁时,小臣回答“我天巫”。一番对话后,小臣告诉夏后痊愈的办法是“后如撤屋,杀黄蛇与白兔,发地斩陵”。夏后照做,果然床下有黄蛇和白兔。由此可见,文中这一系列的故事发展鲜明地体现出了神巫色彩,而这些神巫色彩又正是楚地的特色。
除了《赤鹄之集汤之屋》以外,清华简《祝辞》一篇也含有强烈的巫楚色彩。巫祝向神明祭祀的场面和话语在《祝辞》中得到了体现:
恐溺,乃执币以祝曰: “有上茫茫,有下汤汤,司湍滂滂,侯兹某也发扬。”乃舍币……既祝,乃投以土。[20]164
司湍是水神。巫祝通过“执币”“舍币”“投土”等一系列动作进行祝祷,非常具有仪式感,正体现出巫楚文化的特点。《汉书·地理志》:“楚地……信巫鬼,重淫祀。”[21]259《淮南子·人间训》:“荆人鬼。”[22]1243先秦时期,中原一些部落族群有过两次朝楚地的大规模迁徙:一次是因中原部落之间的斗争,祝融部落被迫迁移到荆楚地区;一次是熊绎受周王室的分封,因此移至江汉流域,楚国由此建立。[23]因此,楚地作为处在江汉流域的地区,夏商时期的巫文化很大程度上在此得到传承,使得楚文化对自然、鬼神与灵巫十分重视。桓谭《新论》有言:
楚灵王……信巫祝之道……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与后、姬。[24]29
由此可见楚文化中神巫色彩的浓厚。此外,清华简中还有很多地方体现出这一点。例如,《楚居》一篇中记载的商楚联姻,以及丽季“溃自胁出”的离奇出生方式和巫师的助产等。将清华简《金縢》与传世文献比对,也明显发现其中删去了有关占卜的一段话。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占卜内容不符合楚人的信仰习惯。[19]以上都说明巫楚文化在清华简这一批文献群体中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也反映出清华简的文献内涵与独特之处。
(二)“楚墨”学派思想在清华简中的体现
韩非子谓“墨离为三”,指墨家后来分为“三墨”,其中之一的派别则是“楚墨”。[25]墨家与楚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且这样的关系从墨家自身发展开始就存在。第二代墨家巨子孟胜便死于为楚国阳城君守城。苦获、已齿、邓陵子都是楚国墨者,墨子本人也数次到访过楚国。早就有学者认为,1956年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地出土的一篇有关申徒狄问对周公的战国竹简,当为《太平御览》中收录的《墨子》佚文。[26]327-333;191-208此外,安徽大学近藏的一批战国楚地竹简中亦有《墨子》相关的篇目。[27]这都体现出楚国与墨家的联系,说明其学派观点的传布与影响在当时的楚地十分广泛。因此在清华简中,许多内容都反映出墨家学派思想的特点,而这些墨家思想又构成清华简这一批文献的楚文化特色。
“十论”为墨家的核心思想,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28]24关于“明鬼”,清华简《金縢》篇的后半部分有描写天人感应的文本。此外《殷高宗问于三寿》中亦体现出对于神鬼的敬畏:
彭祖答曰:“……冒神之福,同民之力,是名曰德……喜神而忧人,是名曰仁。恭神以敬,和民用正……神民莫责,是名曰智。”[29]150-151
文中反复出现“鬼”“神”等词,并将“神”与“民”结合起来讨论,反映出其中蕴含的神鬼思想。除《殷高宗问于三寿》外,清华简《傅说之命》中还有描写失仲生二牡豕的离奇传说。由此可见,在清华简的整编者的认知中,“怪力乱神”可以被接受,这体现出其中的墨家思想特点。除了“明鬼”以外,清华简中亦包含有“节葬”的思想,《治邦之道》中明言“不厚葬,祭以礼”。此外在《治邦之道》里,“非命”思想亦十分明显:
此治邦之道,智者知之,愚者曰:“在命。”[30]272
贤者与愚者的思想对比,反映出作者对于“命”的反对态度。此外《治邦之道》还含有“尚贤”的思想,强调“选贤举能”的重要性:
今夫逾人于其胜,不可不慎,非一人是为,万民是为。举而度以可士,兴;举而不度以可士,崩。故兴善人,必熟闻其行,焉观其貌,焉听其辞。既闻其辞,焉小谷其事,以程其功。如可,以佐身相家。[30]271
故求善人,必从身始,诘其行,变其政,则民改。彼善与不善,岂有恒种哉,唯上之流是从。[30]270
作者认为“举而度以可士,兴;举而不度以可士,崩”,由此得出对于“士”的任用需要“必从身始,诘其行,变其政”,强调能力在其中的重要性。作者不认为“善与不善”是恒定的,要“唯上之流是从”。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清华简中的墨家思想,及其在清华简的思想内容上起到的重要形塑作用。这使得清华简在思想文化上具有“楚墨”的文化特点。
(三)清华简中的楚地诗教
清华简中的“诗”类文献有许多类型,例如《周公之琴舞》记录周公和成王在典礼上所作的毖诗和组诗,又有《芮良夫毖》这样记录芮良夫所作毖诗的篇目,还有《耆夜》这样记载周公和周武王在饮至典礼上所作之诗的篇目。总的来说,清华简这些“诗”类文献都与儒家的“诗”教特点相似,具有“明德”“达情”的功能。然而清华简中有一篇特殊的含有先秦巫祝的咒语诗,即上文提到过的《祝辞》,这应当是楚地特有的巫祝诗歌。其首则“恐溺”是针对落水而作的祝辞,第二则为“救火”,后面的三则都是针对射箭时的情况而作。我们认为《祝辞》既含有楚地“重鬼神,尚淫祀”的风俗,又包含儒家“诗”教的影响。例如首则“有上茫茫,有下汤汤,司湍滂滂,侯兹某也发扬”这样四四六的句子结构,颇类传本《诗经·君子偕老》中“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的句式。此外“侯兹某也发扬”一句也与传本《诗经·君子阳阳》的“君子阳阳……右招我由敖”等句子所表达的意境相近。这些都反映出了复杂的文本结构与楚地“诗”教的特点。
随着国力的强盛,春秋时期楚国逐渐对中原有了觊觎之心,因此开始对中原地区文化产生主动意识上的接受。当时以周王室《诗》《书》为核心的“六经”教化对楚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此可见,清华简《祝辞》是一篇既具有楚文化特点,又含有中原“诗”教规范的典型文本,反映出楚文化在这一类诗歌文献上对本地文化的保留及对异域文化的再塑造。
三 结 语
由上所述可知,清华简具有多方面的楚文化特征,不论是从文本形态,还是从文本内容上,都可以看到鲜明的楚文化的痕迹。其中思想文化上最主要的特点是楚地“重鬼神,尚淫祀”的巫楚文化,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文本与文献生成的影响。通过对清华简中楚文化特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地域文化在文献流传中的烙印,这也是地域文化在文献“流动性”问题中的一个缩影。对此,我们应当重视思想文化在文献流传与文本建构上的形塑作用,并且对上古“层累”文献中不同的“文化记忆”给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