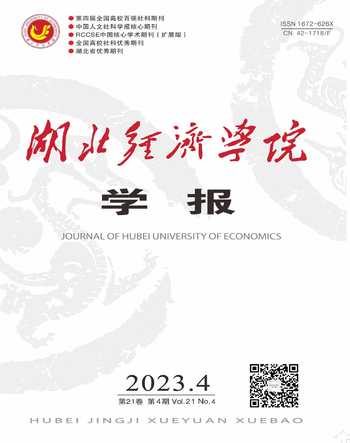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制约因素分析
李杨 张颖莉



摘要: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北、上、广、深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这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对于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示范价值。通过厘清绿色发展系统内在理论机制并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以北、上、广、深为典型代表的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探究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绿色发展水平依次排序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各城市的短板不一;各准则层的绿色发展水平主要呈上升趋势,但是绿色生活这一指标逐年下降;制约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障碍因素为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增长质量,并且绿色生活指标的障碍强度持续上升。最后,提出全面提升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建议。
关键词: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测度;转型障碍
中图分类号:F124.5;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3)04-0017-11
一、引言
绿色发展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从“五位一体”,到“新五化”,再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识和实践不断发展。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本质要求之一,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城市是人口、产业、交通运输等高度集聚的区域,超大城市是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有活力的核心地区,也是人口激增、能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更为严峻的地区。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新模式。北、上、广、深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这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引领我国绿色转型进程,是绿色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根据各城市统计年鉴,2021年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总计达到142381.27亿元,在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2%,人口总计达到8327.25万,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接近6%,人口、资源與环境相协调压力较大。北、上、广、深四个典型超大城市的绿色转型事关国家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计,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程的推进起着至关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以超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绿色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衡量与评价各城市绿色发展的现实情况,并且比照差距、寻找原因,既能丰富新发展阶段的绿色发展理论研究,又能为超大城市释放发展活力、发挥在中国绿色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提供决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对绿色发展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966年美国学者Boulding所提出的太空舱经济理论,该理论指出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环境,地球就会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1]。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在著作《绿色经济蓝图》中提出“绿色经济”一词[2],即不会由于资源耗尽而使社会经济无法持续发展,也不会由于盲目追求生产增加而造成社会分裂的“可承受经济”。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组织、国内外学者对绿色经济、绿色增长开展了丰富研究,绿色发展的概念从单纯环境保护[3~4]逐渐演化,是将生态保护内生为经济发展过程[5],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6],是以高效率、低污染、低损耗的绿色模式实现经济增长[7],是一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8],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9]。
自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对其概念与内涵[10~13]、测度与评价[14~16]、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17~19]、实现路径[20~21]等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上,已有文献从国家、省域、城市等不同视角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本文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以“绿色”“评价”为关键词的CSSCI来源期刊论文,选取并归纳有代表性的文献,将其研究对象和指标选取思路汇总见表1。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1)研究对象方面,现有研究多从国家和省域层面出发,或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研究为主,较少文献量化并比较研究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城市绿色转型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超大城市绿色转型走在前列,以北、上、广、深四个典型超大城市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研究指标方面,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影响测度结果。已有研究在评估绿色发展水平时缺少理论支撑,指标构建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指标选取较少,所得结果无法全面反映绿色发展实际情况;二是选取大量超过绿色发展概念边界的指标,存在泛化概念问题。
例如,含有过多创新、协调、共享等指标,新发展理念中的五个方面边界模糊,难以科学评估绿色发展真实水平。北、上、广、深四个典型超大城市统计数据相对较为完整,缺值较少,因此,本文基于理论推导构建了相对更为系统、更有针对性的绿色发展测度指标体系,集中体现绿色发展的各个重点领域,涵括能源总量与强度以及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环境质量控制的多重目标,同时考虑过程性指标和结果性指标。(3)研究内容方面,对绿色转型的障碍因素进行进一步探索。以“评价测度——演化特征——障碍因素”为研究思路,通过探究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把握超大城市绿色发展进程与现状,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阻碍绿色发展的影响因子,以期为城市绿色转型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研究前提。在实践中,国际组织所构建的国家间指标体系难以适用于城市层面,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制定的《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和《绿色发展指标体系》①。因此,本文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基于绿色发展的内在理论机制,并且重点参考和借鉴了该指标体系。但由于城市间资源禀赋不一、统计方式有别、部分数据难以获取,故在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代表性和可获取性原则基础上,结合现有文献进行指标替代和调整。
绿色发展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又是一种发展的结果,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基于绿色发展系统的驱动作用机制(见图1)。一方面,绿色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是在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一是企业层面,主要包括生产中的资源利用(从环境中获取资源)与污染排放(向环境排放废弃物质)行为。资源利用主要衡量对能源等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循环利用能力,选取能源消费总量、万元GDP能源资源消耗、废物综合利用率等6项指标。污染排放主要衡量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即通常所谓的“三废”排放强度。二是政府层面,主要包括在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的相关举措。环境治理是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衡量政府加强城市绿化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环保投资程度,包括节能环保支出、垃圾和污水治理等相关指标。生态保护是绿色转型的保障和基础,是积累绿色生态财富的过程,使用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6项指标。三是公众层面,绿色生活是绿色转型的关键一环,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选取生活能耗比重、绿色出行、人均用能用电用水等指标。
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发展状态,是绿色转型的结果。绿色发展兼具“绿色化”和“发展”两大特征,一是“绿色化”,体现绿色转型进程中环境质量的切实改善,从大气、水、土壤方面选取相关6项指标。二是“发展”,体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高质量转变,主要评价城市技术革新、产业绿色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情况,选取产业结构、高耗能产业比重、能源消费弹性、创新发展等6项指标。
依据上述理论机制,构建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共涵括7个大指标和41个子指标。
(二)研究方法
具体研究主要分为两步:一是用熵值法和综合指数法测度各指标层水平;二是用障碍度模型分析障碍因素。
1. 熵值法
指标权重确定是测度的基础,熵值法是根据各项指标的差异程度来客观确定权重的一种方法,熵值法的优点是客观、科学,避免主观因素干扰和主观意识带来的误差,适合于多层次多指标复杂系统的赋权决策。本文所构建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和指标较多,不容易直观判断结果,因此选用熵值法使得最终确定的权重可信度高、操作性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第一,采用极大极小值方法先进行标准化处理,变换成无量纲的标准化数值,消除指标计量单位的影响。
其中,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三)数据来源
为了使数据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十一五”末(2010年)、“十二五”末(2015年)以及“十三五”時期(2016-2020年)共7个年度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涵括了“十一五”末、“十二五”末以及“十三五”时期的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广东省、各城市公布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环境公报等权威公开数据。
四、结果分析
通过测算四个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总体水平,分析时空演变趋势,再从7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各城市在各指标维度的异同点和薄弱环节,并研究制约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
(一)目标层综合评价与分析
总体看,四个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均处于上升状态(见表3),绿色转型走势良好。从平均水平来看,其平均值由2010年的0.0290上升到2020年的0.0494,年均增长率为5.48%。尤其是“十三五”以来,各城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统筹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绿色发展水平在“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率高达9.06%,城市加快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变。具体来看,四个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都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变动趋势,绿色发展水平依次排序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北京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始终是唯一采用标准差分级法进行分级后绿色发展高水平区。2015年以来,北京与广州绿色发展指数之比基本都在2左右(除2019年比值为1.89),差距较大。
(二)准则层具体评价与分析
从整个研究期看,不同维度准则层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变化趋势不同,不同城市在各准则层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为深入分析四个超大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成因,进一步计算出各城市准则层的得分,结果见表4。
1. 各个准则层的分值呈现不同的时序动态演变轨迹
各个准则层的变化趋势存在较大差异。第一,各城市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四项指标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增长质量提升速度最快。增长质量提升是“治本”手段,研究期内,其他指标普遍呈个位数的年均速度增长,而北、上、广、深的增长质量分别呈20.62%、19.70%、14.07%、9.46%的年均速度增长,增长质量指标下的各项子指标都表现出显著改善趋势,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第二,各城市污染排放指标波动较大。虽然与2010年相比,各城市2020年的污染排放数据均有所改善,但若单看“十三五”时期,上海与深圳有所恶化,与工业固废排放强度(包括一般固废和危险固废)增加有关。第三,各城市在环境治理方面表现不一。其中,上海、深圳在波动中上升,但是北京、广州呈下降趋势,主要受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强度有所下降影响,如节能环保支出比重、环境卫生固定投资强度等。第四,各城市绿色生活指标均逐年下降。可以发现,居民生活方面的用能、用电、用水都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与超大城市步入高收入水平阶段所带来各种能源资源的消费潜力释放有关,也意味着未来常住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升将给各城市绿色化发展带来持续压力。
2. 各个城市绿色发展特征与短板存在较大差异
各个城市在7个维度的准则层也表现出不同的绿色发展水平。第一,北京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领先其他城市,但环境质量水平较低。具体来看,北京在污染排放、生态保护、增长质量方面均领先,环境治理开始领先,后来有小幅回落,在资源利用、绿色生活方面居中。但是环境质量表现较差,在四个超大城市中排最后,其子指标如衡量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率、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以及衡量土壤质量的化肥、农药使用强度都排在最后。第二,深圳绿色发展水平仅次于北京,该城市在7个准则层指标中没有表现特别落后的维度。其中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环境治理均位居第一,污染排放、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方面居中,绿色发展较为全面、均衡。第三,上海绿色发展水平在四大城市中位居第三,绿色生活水平较高。上海在绿色生活维度表现较好,位居第一,生态保护、增长质量方面居中。但是在资源利用、污染排放方面排在最后,环境治理跟广州不相上下,近两年稍落后于广州,也排在最后。从子指标看,上海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工业煤炭消耗强度、工业废水和固废排放强度、环境卫生固定投资、万人公交车拥有量、森林覆盖率、建成区绿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标都较为靠后。第四,广州绿色发展水平位居最后,缺乏表现特别突出的指标。广州在资源利用、污染排放、环境治理、环境质量方面居中,且在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方面位居最后。从子指标看,广州在节能环保支出、万人公厕量、公园个数、自然保护区面积、高耗能产业比重、能源消费弹性、研发强度、人均用能用电用水等方面绿色发展水平较低。
(三)障礙度分析
为厘清超大城市绿色发展短板,引入障碍度模型,分别从准则层和指标层深入挖掘阻碍超大城市绿色发展的制约因素,并识别关键障碍因素。
1. 准则层障碍度分析
随着时间推移,各准则层对四个超大城市绿色发展的障碍度作用大小和强度呈现不同态势(见表5)。
第一,从作用大小的变化来看,资源利用、污染排放、环境质量和增长质量呈波动下降态势,对绿色发展阻碍作用减弱;环境治理、生态保护②呈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两者在四个超大城市中的障碍度之和均超过50%;四个超大城市绿色生活的障碍度均处于逐年持续上升态势,对绿色发展水平的阻碍作用不断加强,2020年北京绿色生活的障碍度达到15.68%。这意味着,政府和公众对超大城市绿色发展的制约在不断提升,新形势下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对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众行为提出更高要求,在未来绿色转型中需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第二,从作用强度来看,研究期内阻碍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前三大因素始终为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增长质量,2020年三者对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度高达78.96%(北京)、91.46%(上海)、89.70%(广州)、92.12%(深圳),成为超大城市绿色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北京受环境治理(28.69%)、上海受生态保护(38.00%)、广州和深圳受增长质量(37.74%、40.84%)阻碍度最大。可见“十四五”时期,在加快绿色发展进程中,政府还需要更加注重生态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力度,更加从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角度协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2. 指标层障碍度分析
由于本文所选指标及涵盖年份较多,鉴于篇幅限制,且为了更好找出关键因素,只选取各个城市主要年份、障碍度排名前五位的指标进行分析(见表6)。总体上看,影响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前五的障碍度指标较为集中,共有9项,其中频次出现较高的依次为增长质量维度中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X3(3 出现11次,覆盖面92%)、技术合同成交额X35(出现11次,覆盖面92%),生态保护维度中的公园个数X27(出现9次,覆盖面75%)、自然保护区个数X2(8 出现9次,覆盖面75%),以及环境治理维度中的环境卫生固定投资X1(3 出现8次,覆盖面67%)。可见,超大城市在推动绿色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以创新带动绿色不足、绿色空间营造不够、政府投入力度不足等关键现实问题。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北、上、广、深四个典型超大一线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城市绿色发展系统内在驱动机理,选取“十一五”末、“十二五”末以及“十三五”时期的面板数据,从资源利用、污染排放、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7个层面构建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测度研究对象的绿色发展水平,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阻碍绿色发展的影响因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从目标层看,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逐年上升态势,尤其是“十三五”以来,各城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排序依次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北京与广州绿色发展指数之比基本稳定在2左右,差距较大。
第二,从准则层看,各个准则层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各城市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四项指标均呈上升趋势,污染排放指标波动较大、研究期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是各城市在污染治理方面表现不一,并且绿色生活指标均逐年下降。
第三,从具体城市的准则层看,各个城市的特征和短板不一。北京绿色发展水平明显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但环境质量水平较低;深圳绿色发展水平仅次于北京,7个准则层中没有表现特别落后的维度;上海绿色发展水平在四个超大城市中位居第三,在绿色生活维度表现较好;广州绿色发展水平位居第四,缺乏表现特别突出的指标。
第四,从障碍度分析来看,各准则层对四个超大城市绿色发展的障碍度作用大小和强度呈现不同态势。作用大小变化方面,资源利用、污染排放、环境质量和增长质量呈波动下降态势,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呈波动上升趋势,而绿色生活逐年持续上升。作用强度方面,对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阻碍强度居前三位的始终为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增长质量。指标层分析结果显示,制约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前五的障碍因素依次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技术合同成交额、公园个数、自然保护区个数和环境卫生固定投资。
(二)政策启示
第一,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持续提升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水平。“十四五”时期是生态环境质量由量变转向质变的关键期,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是影响绿色发展水平最为关键的要素,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两手发力,健全减污降碳协同机制,统筹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比例,加大投入完善如公共交通、公共厕所、固废处理等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深入开展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行动,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城市宜居性。
第二,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既要抓生态文明建设,更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促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增长质量是影响城市绿色发展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也是近几年绿色水平提升最快的准则层。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严控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盲目扩张、持续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上改变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三,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注重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在7个准则层中,绿色生活是唯一发展水平在四个超大城市中均逐年下降的指标,也是唯一障碍度在四个超大城市中逐年上升的指标。这要求警惕绿色生活障碍度增长态势,更加注重生活侧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大绿色低碳方面的宣传力度,提供更多可参与、可获得的绿色消费场景,还要加强引导全社会科学和节约使用能源资源,落实用水、用电、用气等各类能源资源消费的阶梯价格制度,健全能源资源需求侧响应市场化机制,最终实现全民生活方式的绿色变革。
注释:
①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制定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其包含7项一级指标、56项二级指标,涵盖了经济、资源、环境、人民生活、公众满意度等维度。
② 深圳生态保护近几年持续上升,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10年的水平。
③ 为便于阅读和比较分析,表格只列出“十一五”末、“十二五”末、“十三五”末三个关键年份的数据。
参考文献:
[1] BOULDING K E.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M]//Jarrett H.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Es?says from the Sixth RFF Foru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6.
[2] PEARCE D W,TURNER R K. Econom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M].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0.
[3] JACOBS M. The Green Economy: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Future[M].Massachusetts:Pluto Press,1991.
[4] 吴晓青.云南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建设绿色经济强省[J].生态经济,1999(6):1-6.
[5] 黄志斌,姚灿,王新.绿色发展理论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辨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8):108-113.
[6] 田时中,周晓星.长江经济带绿色化测度及其技术驱动效应检验[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12):39-49.
[7] 魏丽莉,侯宇琦.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8):60-79.
[8] 林卫斌,苏剑,周晔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还是减缓——基于能源环境视角的测度与分析[J].经济学家,2016(2):33-41.
[9] 甄霖,杜秉贞,刘纪远,等.国际经验对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启示:政策及实践[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0):8-16.
[10] 诸大建.绿色经济新理念及中国开展绿色经济研究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5):40-47.
[11] 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14-20.
[12] 林伯强,谭睿鹏.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J].经济研究,2019(2):119-132.
[13] 朱东波.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思想基础、内涵体系与时代价值[J].经济学家,2020(3):5-15.
[14] 高赢.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发展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9):3-23.
[15] 张旭,魏福丽,袁旭梅.中国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与演化[J].经济地理,2020(2):108-116.
[16] 徐晓光,樊华,苏应生,等.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7):65-82.
[17] FENG C,WANG M,LIU G C,Huang J B.Gree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A Glob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7,144:323-333.
[18] 岳立,薛丹.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资源科学,2020(12):2274-2284.
[19] 王婧,杜广杰.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12):11-27.
[20] 韩晶,蓝庆新.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5-16.
[21] 楊冕,谢泽宇,杨福霞.省界毗邻地区绿色发展路径探索:来自革命老区振兴的启示[J].世界经济,2022(8):157-179.
[22] 欧阳志云,赵娟娟,桂振华,等.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5):11-15.
[23] 李晓西,刘一萌,宋涛.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J].中国社会科学,2014(6):69-95+207-208.
[24] 吴传清,黄磊.演进轨迹、绩效评估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绿色发展[J].改革,2017(3):65-77.
[25] 黄跃,李琳.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测度与时空演化[J].地理研究,2017(7):1309-1322.
[26] 王勇,李海英,俞海.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10):96-104.
[27] 李波,张吉献.河南省绿色化发展评价及时空演变特征[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4):27-32.
[28] 熊曦,张陶,段宜嘉,等.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差异[J].经济地理,2019(12):96-102.
[29] 滕堂伟,孙蓉,胡森林.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空间关联[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11):2574-2585.
[30] 陈佳敏,霍增辉.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与比较[J].科技管理研究,2020(1):244-249.
[31] 郭艳花,佟连军,梅林.吉林省限制开发生态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与障碍因素[J].生态学报,2020(7):2463-2472.
[32] 舒成,朱沛阳,许波.江西省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空间分异分析[J].经济地理,2021(6):180-186.
[33] 徐晔,欧阳婉桦.江西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动态测度及影响机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2(5):1152-1168.
[34] 张仁杰,董会忠.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空间关联结构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2(8):118-123.
[35] 张虎,尹子擘,薛焱.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J].统计与决策,2022(11):93-98.
(责任编辑:彭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