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共识:一夜梦碎的区块链淘金赌局
Sean Guo

2023年6月1日起,香港《适用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营运者的指引》正式生效。在新制度下,所有在港经营虚拟资产交易所业务,或向投资者积极推广服务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均需向证监会申领牌照。香港证监会也表示,将在今年下半年落实交易平台向零售投资者提供服务的细则。
对中国专业投资者来说,在水面下汹涌多年的虚拟货币交易将被纳入管束,走上规范与创新并举的前进道路。但对广大散户来说,这个全新的掘金大陆,才刚刚拉开其神秘幕布的一角。
ELLEMEN邀请到一位在区块链行业沉浮几载的创业者写下了意外闯入者“阿强”的故事,记录他从建立职业理想,到最终被潜藏的规则侵蚀、击碎的魔幻过程。
故事或许部分取材自作者眼见的某些从业者的真实经历,又或许和这个圈子外围漂浮的彩色泡沫一样,只是被虚幻的财富折射出的数字光影。但无论如何,我们寄望其能给予后来者一瞬间的警示弧光。
特别提醒:本文涉及的人物、项目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亦不构成投资建议。
01阿珍与老K
三十三岁生日当天,阿强收到了来自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会议邀约。彼时,他刚享用完员工食堂里的免费早餐,还用工卡里的餐补刷上了一杯星巴克。
人力专员发来的信息简洁干净,没有会议主题。阿强把自己“陷”进办公椅里,电脑屏幕亮起,是被插件“美化”成工作文档的游戏论坛。想起在公司吹得正劲的“降本增效”的寒潮,他腱鞘炎复发的手腕突然发力不畅,才喝两口的咖啡径直倒扣在眼前的键盘上。
阿强被裁了,虽然绩效素来平平,但公司待他不算刻薄,给了不错的赔偿和一个月的缓冲期。下午6点,阿强没管被咖啡浸湿的键盘,准时离开公司,在园区外扫了辆共享单车往家骑。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太阳下山之前走出公司了,只觉得大街上明晃晃的,人来人往,不太真实。
这种虚幻感被一辆加速右转弯的火红色跑车击碎,阿强和共享单车趴在马路牙子上,手腕的疼痛加剧,他想蹦起来骂两句脏话,猛一下没站稳,又四仰八叉地躺下了。
跑车的副驾驶车窗摇下,一个留着海藻般长发的女人摘下墨镜盯着他,眉眼娇嫩飞扬:“阿强?阿强!诶,我阿珍啊!”阿强没想到,自己幻想过多次的浪漫重逢竟发生在这样不堪的当下,他想立刻逃走,但看着阿珍涂抹精致的笑脸,最终只是咬紧后槽牙,狠狠地把压在身上的单车蹬开。
阿珍要了阿强的微信,还和他约好周末赔礼道歉的饭局。夜里,阿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条一条翻看阿珍的朋友圈。这个曾经的校园女神穿着时髦,背着各种阿强叫不出名字,但也知其昂贵的名牌包包,在商务场合间穿梭。看坐标,女人两周前还在纽约,上周飞到了新加坡,接着又去了香港海港城。
阿强在南都这座高速发展的一线城市生活了多年,被各种创新浪潮兜头盖脸地拍来拍去,很快明白了阿珍在干些什么。他想起在一些酒局间耳边飘过的时髦的词汇。“玩区块链的啊。”阿强哂道,心里有些失落,又有些躁动。
“阿珍啊,你……你现在跟哪家公司啊?”吃饭时,阿强支支吾吾地试探。
“我没公司,就对接对接资源。”
“你们这行挺挣钱吧?”阿强想起自己听到的几段传奇故事,“我认识的好几个干开发的都转行做区块链了,听说这两年进账不少。”
“主要看行情。这行想拿钱也不轻松,但和你们干互联网的累法不太一样。自己老得惦记着学东西。”阿珍细长的眉头挑起,笑意深了几分:“你要想转行呢,可以先干干看,试试水。正好我认识个大哥,人不错,正起新项目呢,他下周从香港过来,你来聊聊。”
一周后,阿珍把阿强介绍给了老K。老K年纪和两人相仿,常年在南都和海港城间奔波,按照世俗标准,算混得很可以。市面上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真假参半。有人说老K是靠挖矿起家,也有人说他是替国内一些“有身份的人”操盘,为人真诚守信,幸得人家分点汤喝。
三人初见在一家年轻人聚集的特色酒吧。南方暑热潮湿,老K一身休闲装、踩着人字拖,姿态闲散,和阿强想象中的“大佬”全然不同。阿珍迎上去和老K热情拥抱,还不忘加上个“贴面礼”。“这是阿强,我念大学的时候很喜欢他。”阿珍拨拨头发,风情万种地向老K递去一个眼神:“人特别棒!”
阿強有些局促,在阿珍的示意下慌忙起身和老K握手。老K态度平和,简单问了问他的工作经历,又问他对区块链有多少了解。阿强说了自己作为程序员的履历,又讲起不久前读过的比特币白皮书,见老K兴致不高,他便诚恳道:“确实没写过圈里的项目,也没写过合约,但我对市面上流行的新语言都了解过,做起来应该不难。”
“阿珍看得上的人,肯定靠得住啦。半个月后,得闲过头来我这一趟。”老K递来一张名片,又举起手里的威士忌,轻轻碰在阿强攥紧的啤酒罐上,不待他答话,便转头贴近吧台边的明艳女人,低声招呼:“珍珍啊,下个月美国的峰会我们有个分会场,给个面子来当主持人呐?”
“我是想去,一看机票、酒店,都涨了好几倍哟。”女人的声音带上了钩子。
老K笑了:“点我呢这是?找你帮忙,哪能让你自费?”
“哎,得先说好,我可不想跟老鬼们喝酒,上次那谁,喝高了。一个劲儿往我这儿贴,你也看见了吧?”阿珍皱着眉,猫眼瞪圆,滟滟红唇嘟成一团。
“他就是个柒头(蠢货)啦。你看我几时有叫他过来玩过咩?没人理他的现在。”
“那敢情好,正好我有一个小闺蜜,最近刚开始做自媒体,我能不能带她过去见见世面?”
“好好,一起一起。”老K随意应道。


02共识
“这项目到了3月份也没有钱会进来的啦,说是一班硅谷来的印度人,实际上在后面做事的就是一帮华人。”老K端着杯手冲咖啡,拉着四五个年轻人讨论一个新项目。他们的声音不小,但其余位置上的员工都自顾自忙碌着,有的人盯着电脑屏幕上走势起伏的K线图,还有几个人戴着耳机看视频,里面都是一些外国人对着摄像头神叨叨说着什么。
这间位于海港城中环的数字资产管理公司,办公区很宽敞,但办完入职手续的阿强远远就看到人群中高谈阔论的老K,左顾右盼地向那磨蹭过去。老K随手抻了把椅子,招他一同坐下,和身侧几人介绍起阿强。阿强殷勤地问起自己加入的新项目,老K却道:“不急不急,和大家多聊聊先,听听他们的玩法。”他鼓励式地拍拍阿强的肩膀,“再去找财务领点项目代币,找找交易的感觉。”
阿强加入的是一个DeFi(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Finance)项目,这是市场时兴的热潮,他负责后端开发,与他搭档的有一个产品经理、一个前端开发工程师、一个市场运营经理,合约工程师和另一项目共用,设计与测试岗的同事手里也同时跑着另外三个项目。
头一个月的班还没上完,阿强就拿到了第一笔奖金。虽然他们的项目代码还没有白皮书行数多,但融资却很顺利:一家国内小有名气的基金做领投方,老K又拉来一些和他相熟的私募,野狗扑食似的把额度瓜分了个精光。
小组例会上,老K宣布给每人额外发两万块钱奖金,又说:“我自己再另外拿出来优先解锁的1000万个代币额度,你们可以在我这里买,给你们按这轮机构进入的价格打个8折。”会议室里瞬间爆发出比刚刚激烈得多的欢呼声。
散会后,阿强还有些莫名,他问已经熟悉的产品经理,为什么听到能拿代币的额度比发奖金还高兴?“额度就是钱,你一万块现金,拿在手里就是一万,但现在一万块的代币额度,明天可能变成十万、一百万……你之前是在互联网那边做事吧?就把这个想象成靠谱的期权。干这行谁是图賺死工资来的啊。”对方答道。
前端开发工程师凑过来,指了指他们工位对面的另一个项目组:“他们都不领工资,每月就是给币,发币之前就是给项目额度,其他福利都没有。”
“那不是画大饼吗?”阿强更疑惑了。
一群人哄笑起来:“阿强啊,你还要多理解理解。”
晚上,阿强在网上和阿珍聊起这件事。阿珍告诉他这是行业的常态,“一个项目不就是各尽其职的几个人,赶快把项目做出来、推出去,能挣几百万,几千万,大家再分一分,很单纯”。
“你觉着我这次应该买多少?”阿强的态度有些动摇。
“信不信他能涨,能涨多少?这是你的事情。但你要拿不满额度可得跟我说呀,你空多少我收多少。”阿珍想了想又叮嘱道:“但在老K那儿,你别说是我拿了。”
一个月后,阿强小组的项目在测试网站发布,社区里积累下的两千多个爱好者把参与测试的资格一抢而空。阿珍发来微信:“可以啊,我看有人在网上好几百美元转卖你们的测试资格呢!”
“奇了怪了,就一个测试白名单,什么也没有,不知道这些人图啥。”阿强是真纳闷。
“哎,你不懂,老K就是这么厉害。”
周末的晚上,项目组的几个人完成了一场面向海外粉丝的“在线问答”,结束后,老K带他们在公司楼下的日式烧鸟店吃宵夜。
几杯清酒下肚,酒意上涌,阿强瘫软在卡座里,趴在窗沿看月亮。海港城中环的夜色和南都科技园的夜色,这一刻似乎没有太大差别,夜风吹得人恍惚,他忍不住问老K:“我们这样的项目,只有个产品小样,有的项目甚至连小样都没有,为什么就有人愿意掏真金白银买测试资格,然后买那些代币呢?”
老K反问:“你还记得办公室墙上贴的那句话吗?”
“共识即价值。”阿强打了个酒嗝,疑惑道:“我看社区里很多人,对我们要干的事情的愿景、方法,其实并不是很理解,就更别说认同了,那怎么产生共识?”
“认同项目方的业务愿景,只是共识的一种。”老K说,“还有另一种共识,是认为你能吸引更多人相信你,把整个盘子做得更值钱。你说的共识,是你们这些专业开发人员做的事情;我说的后一种,是我和运营在做的事情。”
呷了口酒,老K不徐不疾地接着开口:“我们什么时候搞自己的社交媒体主页对外宣传,什么时候建社群,拉着关注我们的人天天一起聊,哪个阶段对外讲项目的哪些内容,在行业里是有比较成熟的规律的。老玩家看的项目多,一看我们的节奏,就知道后边的运营方是按规矩玩。那接下来按规矩我们要干什么?发币,拉盘?拉个三倍,拉个十倍?我们通过一种让他们熟悉的范式取得这种信任,大家当然愿意尽早拿住机会。”

第二天中午,阿强还没彻底清醒,宿醉让他神魂几度分离。日光刺眼,他翻过身去,恍惚想起老K昨夜说过的话,而后又是一阵猛烈的头疼,便干脆蒙起头脸,继续睡去。
03吴老板
项目代币在主流交易所发行后,研发工作变得更少,阿强除了每周在各种场合讲上两三次“莫须有”的开发计划,也没有太多业务。
老K喜欢轮着带项目成员“出台”,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上币以后就要多讲,你每年讲200场,每场有5个人愿意买你的币,每个人买10万美元,那就是一个亿。有几个项目能做到一个亿?你们都要出来讲,大家看见不同的人,才有新鲜感,就我一个人上,别人肯定觉得没意思。”
阿强很快习惯了和产品经理一起“出台”兜售梦想的日子。某次路演结束后,两人在路边等车聊起了兴致,产品经理直白问他,来老K这后挣了多少。
“就一个月五万多块钱,每月项目币发的也没你们早入场的多。”阿强很是坦诚。
“你自己没做点交易?接下来是利好还是利空,你我不比外边机构和散户心里有谱。”产品经理有些诧异。
阿强愣了会儿,反问:“我们这么玩,市值管理那边不是要出问题?”
“咳,”产品经理乐了,“你这是瞎操心,人家是什么资金量,就我们手里这一块八毛的,能有影响?而且你想,他们也要等我们放出消息后才能拉盘砸盘,制造控盘合理性。我们啊,这叫顺势而为,还给那边省了点资金成本。”
“你不怕老K知道?”阿强又问。
“他能不知道?他想得明白,大家无非都是卖币挣钱,他有他的节奏,你有你的节奏。挣钱嘛!这个圈子里没这么多不好意思。谁干活谁拿钱,别坑其他人就行,这也算是一个项目内部的最基础的共识吧。”产品经理推了推滑到鼻梁下的眼镜,补充道:“这个行业的逻辑其实挺原始,一起挣过钱的人才有信任,过手的钱越多,信任关系越牢固。”
很多时候,阿强觉得自己还没彻底融入这个圈子,他对交易和利益关系的看法和身边很多人不太一样。空闲的日子,他更喜欢琢磨新技术,没多久就把主流的智能合约掌握得差不多。
阿强的学习精神也收到了一些回报,阿珍认识的某个项目方正在找研发,待遇不错,她问阿强是不是能兼职,简要地铺垫了一下项目方背景:“吴老板,人嘛比较野,运作过几十个项目,你有个想法给他,他就能搞出个币,退出周期也快。”
“退出快,就是割得早的意思?”阿强撇了撇嘴。
“是也不是,总之有人愿意掏钱接盘。”
“算了,到时候一出事情他跑了,我把自己牌子砸了,也没办法和老K交代。”
“吴老板要是真割了就跑,也不可能一直这么玩呀。他有他的办法,有人会接这些项目。”阿珍拉过阿强的手,柔声劝道:“你放心,他的项目对外说都是一帮老外攒的局,不用你出台,明面上和你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阿强想先和吴老板聊聊,交个底,但阿珍却说,吴老板很少单独见生人,她也沒真见过。阿强犹豫了几天,想到不菲的报酬,还是应下了这个差事。
一个月后,他交去了项目代码,验收方很满意,如期支付了之前承诺的四万美金。阿珍后来告诉他,这个项目在一个圈内知名的开发者大赛上名列前茅,几个混迹硅谷的辍学拉美青年拿着他写的代码一炮而红。
两个半月后,阿强有了与吴老板见面的机会。阿珍与几个朋友拿到关系,凑伙替吴老板搭个线下见面会,她借机把阿强写进了现场嘉宾的名单末尾。在阿强的想象中,吴老板的形象一直不太磊落,直到收到入会邀请函,他还不忘指着手机页面上的商业标识向阿珍确认:“吴老板是这个全球最有名的早期孵化机构这块地区的话事人?”
“是啊,他就是做早期项目孵化的啊。孵化好了再卖出去。”
“我还以为是个骗子呢。”
“我可没这么说哟,是你自己这么想。”阿珍掐掉手里的烟,白了他一眼。
04聚光灯下
“各位,有没有谁,准备讲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故事?或者说,相信自己的故事能够承载十亿美元的共识?”聚光灯齐齐射向舞台中央的吴老板,四周的光好像全被吸过去了,谁也看不见谁。西装革履的男人面对台下黑暗里的人群,就像面对一堵墙,他沉默地从左到右扫视了一遍,张嘴,情绪饱满高昂:“讲个好故事,然后从这儿开始实现它!”
整个会场慢慢回过神来,掌声次第响起、汇聚,变得越来越大。阿强站在台下的角落里一声不吭,盯着灯光下的人若有所思。
阿珍今天打扮得很干练,只是一双猫眼依旧描得闪亮。她在场子里穿梭游走,走到哪,哪就聚起一圈人。她说累了,也走累了,看到杵在那儿愣神的阿强。“来,跟我过来。”她隔着人群朝阿强无声地喊,向他招手。
她带着阿强挤到吴老板身边,语气多了几分甜腻:“吴老板,介绍一下,上次帮您做开发的那个社区爱好者,阿强。”吴老板似乎并未想起阿珍说的具体是哪件事情,只礼貌性地同阿强握了握手,便利索地转身离开,留下阿强伸着没来得及抽回的手,愣在原地。
九个月后,阿强和吴老板在海外城市再次相遇,这个看不出年龄的成功人士坚称自己在之前的会场上,对阿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阿强身上看到了对成功的强烈渴望。对于这样的评价,阿强也深以为然。
“这种渴望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就是不服啊,必须把事情做成,没有这种气质的人,能力什么的都谈不上。”吴老板从保湿盒里抽出一支雪茄,施施然偎进真皮沙发里。
吴老板给了阿强20分钟时间做项目路演,10分后就打断了他。“OK,我理解了。项目叙事可以,但听起来还要费挺多苦功夫。我做事情,节奏都是短平快,你要不要再思考思考?”长长的雪茄才烧去一个头,深色的茄灰凝结在明暗闪烁的火星上,吴老板赏玩了一番,转头加重了语气:“我并不会长期把钱和精力放在里边,等你把故事讲完,那你俩要怎么办?”
阿珍瞥了眼阿强,她现在是阿强新规划的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通证)钱包项目的首席市场官,也列在阿强的商业计划书上。“您真舍得割完我就走呀。”她有点生硬地撒娇,吴老板却不接茬,只盯着阿强。
“我会继续和项目往下走,这就是我想干的事儿,您有您的角色,我有我的角色。”阿强张口几次,终于坚定说道。
“不,我没角色,当个角色是有额外成本的。反正你想明白了就行,技术、市场这些执行的琐事我不管,我只负责人和钱。有一天把你们打包卖了,也就卖了。”
阿强咬牙道:“在熊市想做点事情,能起步就不错。不管是卖给谁,我都继续干。”
“你就非要站在聚光灯下面?”吴老板的脸藏在烟雾后,有些高深莫测。
“嗯,我想试试。”
05投机者的借口
和吴老板谈完细节后,阿强犹豫了很长时间。他不知怎么和老K开口,最后鼓起勇气约老K去了公司附近大伙常去的大排档。几杯冷酒下肚,磨磨叽叽说起自己想做个项目,种子轮的融资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老K似是有点诧异:“想做项目怎么不找我先?”
“我想自己折腾折腾,碰碰壁,看看在你这儿学到了多少本事。拿你的钱,老觉得不像自己做买卖,亏了的话没办法跟你相处了。”
“你折腾什么呢?现在大熊市啊喂,品牌和社区推广的成本很难赚回来的喔。你在我这里,怎么样也不会让你饿死,自己有时间接接兼职,不是也挺好的吗?”
“我就想自己从头到尾好好做个项目,试一试。”阿强又给自己鼓了鼓劲儿。
“拿的谁的钱啦,吴老板的孵化器?”
“你怎么知道?”阿强愣住了。
“这个圈子讲来讲去都是这点事的啦。”老K给阿强添满了酒,“我当你是朋友,同你讲句真话。可能你来找我融资,我也会劝你放弃。你啊,还不太合适。”老K打开了话匣子,真心话一股脑地往外冒:“强仔,你不够狠,你的计划书我看过。你想做好东西,但你太讲人情。吴老板向外抛份额的时候,你呀,一想起这个世界上那些跟你理想一样的,最坚定、最早持有你份额的那几千个人,你可能就不舍得跟着一起出货砸盘,甚至还可能会自己拿钱接盘。”
这顿饭持续到了后半夜,临散场时,阿强问:“入圈两年,我一直在想,所有人都说共识是价值,但是所谓的共识,是不是只是投机者的一种说辞?”
“至少你自己觉得不是,对吧。”老K肯定道。
“我算什么?周围大多数人都在投机,都在搏傻。”
“那是你玩的圈子的问题。你看我们这班每天站在台前卖自己的人,搞来搞去的,资产体量统共有多少?其实没多少啦。”老K安抚地搭上阿强的肩膀,口气唏嘘:“在我看来,信仰更单纯的人拿着真正的大资产,你接触不到,我也一样。”
两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听老K讲起往事:“当年带我入行的朋友,早就移民了,现在应该在加拿大钓鱼吧。他就是拿着比特币,一直持有。他同我讲过一个逻辑,如果你相信这些新的故事,那你也应该持有比特币,这些新项目如果成功,只会增加大家对去中心化概念的信任,比特币的币价是这种信任的货币化表现,比特币的白皮书才是时至今日这个圈子里最大的共识。”
“我知道自己入圈晚了,但我不愿意接受有神。”月光把小路照得皎白,树叶儿沙沙地摩挲,阿强站起来,助跑几步,小孩似地跳起来去够头顶摇摆的尖桠。他蹦得欢实,但不仅没够到,还差点崴了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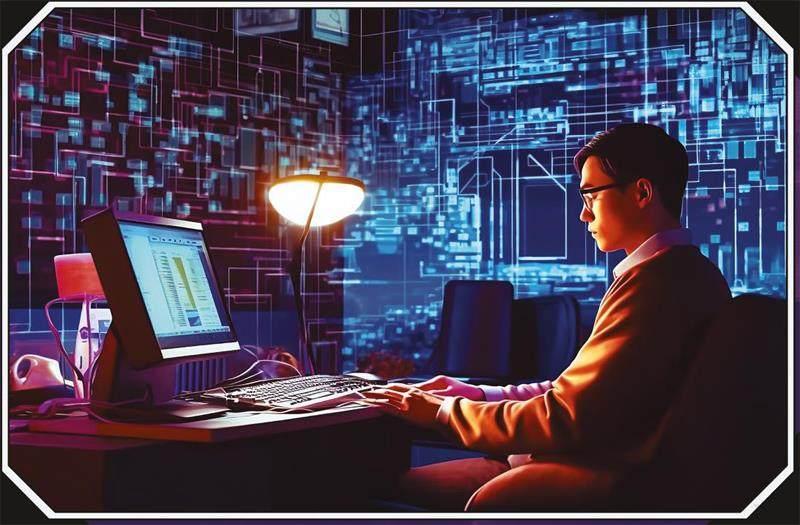
06鸡哥
阿强的项目白皮书发布前,吴老板在经济设计上提了些具体意见,比如要把“社区金库”的比重做大到百分之六七十,给项目方留出更多利润空间;再比如,一定要及时上币,代币釋放的衰减要再狠一点。至于其他项目细节,他都没有过问。
阿珍给自己定了具体的工作目标,每周上会宣讲三四次,抽空约四五家圈内媒体和投资人兜售项目,还总是加塞上一些热门的科技播客,忙起来饭也顾不上吃。她算是圈内的小名人,这样的努力加上还算新颖的项目方案,很快让这个新项目进入了大众视野,社区的活跃度也在持续增加。
“怎么回事啊珍总,自己当老板了就不出来和我们玩啦?”圈里的老混子常用这个当由头,在社交场合拿阿珍打趣。
“那可不是,我们最早想募点钱的时候,哪位大老板躲我躲到新加坡去了?”阿珍随口编排回去,又不忘给对方找回面子,端起酒杯先笑了:“哈哈,当然还得谢谢老板上次给我介绍的海外推广的合作方呢!”
有人问到项目的融资情况,阿珍按吴老板教她的话术,说是一群爱好者自发做的项目,没有融资。话还没说完,又有一双手勾在了她的腰上,“哪个穷小子把我们珍珍骗走了?下次领来让大家看看,他长得有多帅”。
阿强坐在车里等阿珍,微信上给她发消息问进度,却一直没有回复。夜里十一点多,他见人群散去便进去找阿珍,看见女人跪坐在会所角落的垃圾桶边呕吐,酒气熏天。
“这种局以后少来。”阿强皱眉。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您要能上来,我就不来了,老板!”阿珍没上阿强的车,拎着高跟鞋,摇晃着自己打车回家了。
第二天,阿强找阿珍道歉,问她需不需要休息一阵。阿珍还没消气,听了这话更是火上浇油。“我这又不是给你打工,和着搭档赚钱,还用您给我批假?”阿珍甩了脸,不再理他。
下午,阿强接到吴老板电话,叫他带上阿珍,晚上一起去见一个知名美元母基金的本地合伙人鸡哥。他又忙给阿珍打电话,讨饶过后,两人一起“复习”了一下午话术,但没想到最后一句也没用上。
饭桌上,吴老板和鸡哥一拍即合:把阿强的项目摆上台面,鸡哥找相熟的知名风投机构领投,等投资款入账后,领投的资金原路退返,鸡哥拿走十个点;作为种子轮投资者的吴老板,也会趁机退出部分早期份额,提前变现。
酒过三巡,鸡哥满意离场,饭局上没怎么吭声的阿强拦住吴老板,音调高了起来:“这次融资跟项目一毛钱关系没有?我还要拿份额去帮你们洗钱!”
吴老板倒是一身正气,反过来纠正他:“首先,出售的份额是白皮书上明确写着的,财务投资人占10%,这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第二,你要多少钱?研发、市场费用,我给你啊。我们是下一盘棋的,你和阿珍的那一份我一个子儿没动。今晚之前,归你俩那1亿枚代币,就值50万美元;现在值多少?值最少2000万美元!”吴老板伸指隔空点了点阿强和阿珍,转头走了。
阿珍没说话,嘴角依旧挂着软和的笑容,阿强却觉得有点累,靠在墙边深喘了口气,想歇一歇。
07价格
没过几个月,阿强的项目代币逆势在交易所发行,吴老板找了“信得过”的关系,自己承担了近百万美元的“上币费”。发行价是1美元/枚,阿强和阿珍手里的代币份额价值一个亿美金。按之前的约定,两人将均分这些代币。
第一个解锁期共解锁了1000万枚代币,吴老板警告两人:“币先不要动,你们的地址都是在社区里公开的,现在出手,散户难免觉得是创始人要跑路,价格一下就得砸下来。我让你们动你们再动,不然我做不了市值管理。”
两周后,吴老板把币价拉到5美元,告诉阿强“出货”的时机到了。但这次出的不是他们手中解锁的份额,而是吴老板“偷跑”出来的——项目方对外发布公告,要向最早期的参与者发放免费代币奖励,一共派发1000万枚。其中大约一半的接收账户地址是吴老板批量生成的虚拟账号。他左手倒右手,一天就洗出了500万枚。吴老板把其中的50万枚分给阿珍和阿强,叮嘱:“这些賣了吧,别挂在一个单子里啊。”
随着持有者大量出币,阿强这个项目的币价一度下跌到2美元,又很快被拉回3美元左右。稳定了近两个礼拜之后,又有投研机构发布负面消息,并迅速传播,两个小时内币价跌破了2美元。

阿强已经很久无心关注项目的后续开发进程,每天最能刺激他神经的就是起伏的币价。看到价格还在探底,他连忙给吴老板打去电话。
吴老板却很淡定。坏消息是他放的,目的是看近期交易量萎缩,刺激一下交易,也能给早期投资者制造一个币价下跌合理出货的机会。“别怕跌,跌了才有人出,有人出就有人进,没有波动、没有交易量,才是最可怕的。”电话那头,吴老板颇有些不耐烦:“以后这类事情,不用给我打电话,你们所见的现货价格基本都是做出来的,真有什么风险,我会比你更早发现。”
“吴老板的地址没向外公布过,你说他挣了多少钱?”阿强私下里问阿珍。
“管他呢,这种事永远也算不清楚。我们就云在青天水在瓶,把手里的筹码拿住了就好。”
“我想卖一点手里解锁的币。”想到自己那些始终未动的代币,阿强有些意动:“项目是咱俩共有的,我们又不欠他的,自己的币为什么不能卖。”
“哎呀,你就听他的吧,我们又不懂这些。而且不是也里外里挣了二百多万了么。”阿珍好声儿劝他。
“我不是为了钱,就觉得有点憋屈。”这件事在阿强心里梗成了个结。
08崩盘
因为吴老板的事,阿强和阿珍终于在一个雨夜大吵一架。摔门而去后,阿强来了兰桂坊,坐在灯红酒绿的街边,喝了不知多长时间的闷酒。
回到家,他酒意横生,却又难以成眠,便打开手机里的交易所APP把自己的代币挂了上去。先是挂了一百枚,一瞬间成交,之后又挂了一万枚,也迅速成交。他关上手机,心满意足地睡了。之后的八个小时里,阿强这个项目的币价跌去了90%,各种币值报警软件都没有叫醒醉酒的他。
阿强醒来后,下跌还在继续,但这一次,他没给吴老板打电话,也没打给阿珍,只是安静地在电脑上浏览社区里和媒体上的消息。在他熟睡的时间里,一伙儿黑客成功利用合约漏洞盗走了价值约八百万美元的项目币。社区里有人带节奏,说创始人阿强提前接到了黑客的通知,但并未支付对方赏金,也没有公开发布风险预警,只偷偷出售了自己的代币。
临近中午,吴老板要助理联系阿强,传话说想请他见个面,车就停在他家楼下。阿强走楼梯从后门溜了出去,他打给吴老板助理:“你转告吴老板,我不见他,我手里还有一千多万个币,要是砸下去,大家都别玩。”
夜晚,吴老板给阿强发来消息:“阿强,我真的谢谢你,我这一次出了四千多万个,四千多万啊!你这件事没完,哥哥我好心提醒你,出海躲一阵,南美、南欧都行,东南亚差点意思。几个做市商亏了钱,正找你呢。”他似是为了做事敞亮,还另给阿强转来一笔价值一百万美元的代币。
走之前,阿强忽然想见老K一面,在老K的公寓楼下堵到了人。事情的来龙去脉,老K早已了解了个大概。“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你被吴老板给做了,你动了帐,立马就有黑客盗了币,真的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咩?肯定是他一早就拿住这个漏洞了……他为了出货砸了盘,刚刚好可以反过来赖你,让你来做这个鬼咯。”
“那些做市商看不出来么?”阿强有些怀疑。
“他们损失了吗?可能也没有。之前倒来倒去的,这点利润早跑出来了。不就是要让这次的‘损失讲得过去的啦。”
阿强和老K拥抱道别,见他神情颓丧,老K又安慰道:“出去待一阵也好,到处走走,什么时候想家了,想回来了,提前两个礼拜和我说。”他在车里翻找了一会儿,给了阿强一个手机和一张电话卡。
去往港口的路上,阿强一直尝试联系阿珍,但始终得不到回复,早在事发后24小时内,阿珍就清空了自己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所有内容,顺道拉黑了阿强。上船前,他忍不住致电老K,拜托他帮忙打听阿珍是否平安。
老K回复得很快:“平安,放心。”
阿强选择的是一趟去往新加坡的游轮,在海上穿越几个晨昏,他蜷缩在舷窗下的小床上,分不清此时此刻到底是哪日哪时。陪伴他的是和老K分别时在街边书店随手买下的一本书,日光在粼粼的海水上摇晃,他用手指在一行又一行的油墨字下滑动、阅读,精神慢慢放松下来,很快便睡了过去。书从手边跌落,合起的扉页上,亚当·斯密的名言一闪而过——“当人们谋求自身利益时,无形的手会引导社会走向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