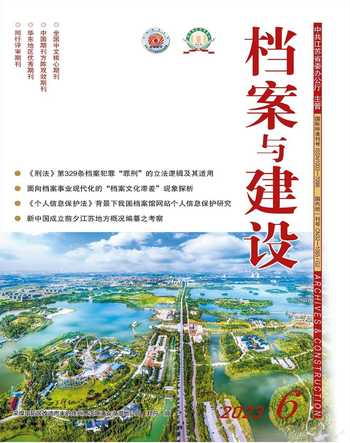清代苏州商业社会研究
宋萌


摘 要:文章以清末碑刻档案为视角,对清代苏州商业社会进行研究。在清代,苏州是中国工商业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这得益于清朝政府的支持及地理區位的优势。随着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阶级矛盾不断加深,制度弊端也不断被放大,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生产力与资本的大量流失、区位优势的丧失以及清朝政府的腐败无作为让苏州工商业逐步走向衰落。
关键词:清代苏州;苏州商业社会;苏州工商业
苏州作为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因其地理条件优越,“南达浙闽,北接齐豫,渡江而西,走皖鄂,逾彭蠡,引楚蜀岭南”(《武安会馆碑记》,碑立于苏州天库前武安会馆),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沃土,明清时期被誉为“东南第一大都会”。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涉及当地捐款慈善、劳资关系、货币制度等内容的清末碑刻档案进行梳理汇总,并以此为视角对当时苏州经济情况作系统考察,一窥清代苏州商业社会面貌。
一、 封建政权扶持下,资本高度集中
明清时期,苏州商业兴起,其政治经济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自雍正时起,唯有苏州辖有吴、长洲和元和3个附郭县。据学者统计考证,其设立的会馆至少有48处,相较于镇江的13处、常州的4处及上海的43处,足可见当时苏州的重要地位。[1]
随着清代专制统治发展到顶峰,地方官府联合富商巨贾以会馆、公所为中心,不断加强对行业的管控,以维系市场的稳定和发展,突出表现在资本的高度聚集。根据乾隆年间《钱江会馆各绸缎庄捐输厘费碑》(立于苏州桃花坞大街钱江会馆)公布的捐献明细,会馆成员26家绸缎庄共捐款11022.25两,其中源发字号等最大的三家绸缎庄共计捐款4346.74两,占捐款总数的39.44%,恒隆靖记等末三位绸缎庄共计捐款56.32两,占捐款总数的0.51%,最大捐款额是最小捐款额的397倍。巨大的捐款差异充分体现出资本的集聚性。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大商户、大商家所拥有的产业资本是中小商户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甚至已经掌握了整个行业的命脉,但对自由竞争依旧抵触,将其视为“争行类商,均非善类”。从时间上来看,直至清末仍然有诸多行会维持着封闭、排他的办事原则,在开店、收徒、定价、原料分配、产品规格方面实行严格控制,如小木作业“一议外行开张吾业,先交行规钱四两八钱;一议外来伙友开张,先交行规钱四两八钱;一议本城出师开张,先交行规钱二两四钱”(《小木公所会议条规并捐户姓名碑》,立于苏州憩桥巷小木公所),以维护本城从业人员利益。
二、 民众生存状态恶化,阶级矛盾加剧
自康熙九年(1670)至宣统三年(1911),苏州手工业有详细记录的罢工就达到了27次[2] ,参与罢工的行业涉及踹布业、纺织业、蜡烛业等,以及板箱作业、皮货业、粪段业等民生行业,究其根本原因是底层民众生存环境的逐步恶化,导致阶级之间矛盾爆发。
自明代以来苏州府是江南八府中赋税最高的城市,明代全国普遍田税为0.035石,苏州则高达0.285石,特别是在晚清时,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加重税率和税额,造成商人团体围绕着“厘金税捐”开展集体抗争。据《常熟县禁扰油麻钉铁铺户碑》记载,胥吏、商牙常利用职务之便“仅偿一、二,纹银化色银,时价减为低价。甚至克剥抽封,有名无实”[3] ,导致清代苏州底层民众薪资长期处在较低水平。
相较于米价的持续增长,各行业薪资增长极其缓慢。以踹布业为例,康熙九年(1670)、乾隆四十四年(1779)和同治十一年(1872)踹布业薪资分别为一分一厘/工、一分三厘/工和一分四厘/工,同期米价分别为0.5两/石、1.8两/石和1.9两/石。踹匠薪资自康熙九年至同治十一年间增长仅仅为3厘/工,而同期米价增幅高达380%。[4] 面对逐步恶化的生存环境,诸多工匠试图摆脱原有公所、行会的管制和约束,通过“自立行头”建立新兴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除了受到清朝官府与作坊主、商户打压以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已逐渐解体,传统行会组织功能被极大削弱,近代新式工商团体“商会”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吸引着各业公所、客帮加入。同时,自发形成的组织较为零散,参与人数占比不足,未能形成合力,工匠之间也有派系划分,在受到清朝官府打压的同时,也受到了同业者的抵制。
三、 货币制度引发的市场紊乱
清代对于市场、商业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大清律例》中《户律·市廛》一节,有学者认为立法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持政府经济和皇室经济,焦点是赋税,而不在发展民间经济。[5] 清代中国采用白银为本位货币、铜钱为辅币的货币制度,“各省各府县间所用之平,每不相同,各以其习惯上所用者为标准;甚至同一地方,其货币种量所用之权衡有至数十种者,通国殆不下数千”[6] 。
以苏州为例,市场上流通着曹平、陈平、足兑纹银、九五色银、九七色银、九八色银、银洋、半开洋等银质货币以及制钱、七折钱、七三折钱、九折钱等铜质货币,货币种类不下数十种,各行业也相继制定了行业内部的货币使用规约(见表1)[7] 。
从上表可知,纸业、粪段业等与民生相关行业均使用制钱作为交易货币,而私钱泛滥加剧了当权者贪污腐败。同治十三年(1874)商牙在买卖草席时“即敢搀搭禁钱,克扣短串,以及抬高洋价”(《长洲县严禁席行买卖草席克扣病民碑》,现立于苏州浒墅关)。地方政府并没有强制各行业建立规范统一的地方货币制度,而是放任其自行确定商事活动中使用的货币类型。紊乱的货币制度带来的汇率波动,催生了扰乱市场秩序、蠹吏奸牙剥削压榨底层民众的温床,进而成为阶级矛盾加剧的引线。
另一方面,外币流入也催化了金融市场的紊乱。外国银元进入中国后因其“既不必比较银色之高低,又无需称分量之轻重,远行服贾,便于携带”[8] 的优势,迅速占领市场,乾隆五十年(1785)后苏州工商业市场逐渐出现“一切货物渐以洋钱定价”[9] 的现象。洋钱的便利也使其汇率时常波动,汇率常高于同等价值的纹银,苏州钱业各铺便囤货居奇,“私立洋拆,买空卖空情事。输赢之数,动即盈千累万,亏负者……潜逃,累及无干”(《元长吴三县永禁钱业各铺私立洋拆买空卖空碑》,现收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收藏编号:苏碑-238),严重扰乱了市场。
四、 兵燹摧残后工商业逐步衰落
随着太平军攻打苏州,苏州工商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直至清朝灭亡时还未能恢复到原先水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生产力与资本的缺失造成贸易瘫痪
太平天国运动前苏州城区人口可达150万[10] ,经历兵燹之后,苏州人口总数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据文献记载,直至清末苏州及下辖郭县人口共计17万余人[11] 。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在社会生产力严重不足的情形下,生产陷于停滞状态。以丝织业为例,1863年清军攻占苏州后就着手恢复苏州织染、总织两局,直至同治十年(1871)“用钱四万二千余串。其司库、库使、笔帖式等署,一律修缮”(《重建苏州织造署记》,拓片现收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收藏编号:C-1386),试图让苏州丝织业恢复旧貌,可规复以后,工匠星散,无处招募,直到光绪年间“尚未足额”。此外,诸多富商巨贾也离开苏州举家逃亡,“以上海一隅为避秦之桃源,庚辛之岁,上海烟户顿增百万”[12],他们撤资离开致使战后苏州地区的重建严重缺乏资金,诸多行业贸易的重启举步维艰。
2. 区位优势的丧失引发商贸停滞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大运河苏州段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如位于苏州东北处的水路要道娄门“当攻战之冲,被兵尤酷。自城外至昆山界牌,其桥已毁者五”(《重建苏城娄门外各桥记》,碑立于苏州宝林寺前)。同时河道淤塞愈加严重,致使沿途“节节阻滞,艰险备尝”,“船户不愿北行”[13]。整个江南的商业交通网络也逐渐从河运转向海运,苏州逐渐丧失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
3. 朝廷腐败无作为遏制了行业复苏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庚申之变后,地方政府依旧维持着以往“开放式”的市场管理模式,各行业商户只能在资本、人才严重流失的环境下艰苦经营。以圆金业为例,“克复后,客帮寥寥,生意日清,各店多有亏闭,各伙因此失业流落”(《圆金业兴复公所办理善举碑》,现收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收藏编号:苏碑-659),各商户只能采取停收学徒的方式,设法安插伙友工作。战后地方官府勾结胥吏商牙,贪腐日盛,“各牙故智复萌,较前尤甚”,“各镇各牙搀搭禁钱,高抬洋价,明则抽用,暗则射利”(《长洲县严禁席行买卖草席克扣病民碑》,立于苏州浒墅关),让各行業难以恢复到战前水平。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苏州得益于清朝政府的扶持及优越的地理条件成为当时全国核心城市之一,随着专制发展至顶峰,地方官员协同巨贾富商不断强化行业管控,形成了资本高度集中、贫富差距巨大、市场监管混乱的营商环境,导致苏州工商业逐步走向萧条。太平天国运动后,苏州工商业弊端凸显,生产力、资本大量流失,同时丧失了地理区位优势,整个行业复苏举步维艰,城市整体逐渐走向衰落。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范金民、罗晓翔:《明清苏州经济中心地位略论》,《史学集刊》2021年第3辑,第48-59页。
[2]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333页。
[3]《常熟县禁扰油麻钉铁铺户碑》,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4]文中薪资数据参考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文中米价数据引自卢锋、彭凯翔:《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第438页。
[5]经君健:《清代关于民间经济的立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辑,第55页。
[6]君实:《记山西票号》,《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6号。
[7]表中统计数据引自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陆雪梅主编:《工商经济碑刻》,古吴轩出版社,2012年版。
[8]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3页。
[9]郑光祖:《一斑录·杂述》,《续修四库全书》第11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页。
[10]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8页。
[11]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12]冯桂芬:《(光绪)苏州府志 卷十九 田赋八》,第32页。
[13](清)刘坤一:《刘坤一遗集》(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