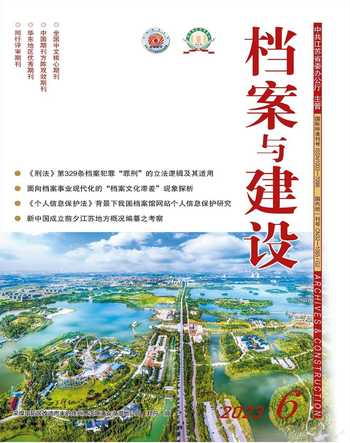中共早期留苏学员的“布尔什维克化”训练
徐霞翔

摘 要: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学员在中共东大旅莫支部的领导下,于课程学习外,尤为注重“布尔什维克化”训练。其中第十一组成员通过召开小组会议,开展批评训练,以强化集体、组织、纪律等观念;进行“反对学院派式的研究”训练,特别“注意基本观点的认识”。这些训练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职业革命家,但受多重因素制约,其成效也存在一定的限制。
关键词:莫斯科东方大学;东大旅莫支部;留苏学员;布尔什维克化
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需要,1921年10月至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四批学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学习。[1]本文根据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初步探讨1924年10月至12月底东大中国班第十一组成员的训练情况,以期展现部分中共早期留苏学员成长为职业革命家的阶段性历程,揭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尝试“走俄国人的路”的一些细微面相。
一、 第十一组成员之构成
1921年2月10日,根据国内外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一所“专为东方殖民地国家、地区和劳动者共产党以及苏俄境内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培训政工干部”的高等院校,并命名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2]
本文论及的第十一组成员,主要属于东大招收的第二批中国学员。他们是1923—1924年间由国内中共组织选派和中共旅欧总支部转入的,来自欧洲的人选包括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来自国内的有黄平、叶挺、徐成章、张浩、聂荣臻、李富春等人。[3]据统计,截至1925年4月14日,东大中国班学员共计112人(其中“社会地位”为“学生”的有88人,占比近79%)。[4]东大中國班学员是由中共东大旅莫支部统一领导的。东大旅莫支部成立于1922年底,1926年被撤销,在其存在的4年时间里,一直是东大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留学生的管理组织。[5]为方便管理,旅莫支部将东大中国班学员分为多个小组。东大第二批中国班学员一度被分为20个小组,每组一般为5人左右,设有小组长1名。[6]东大中国班第十一组成员的构成并非一成不变的。最初成员有武胡景、陈九鼎、刘子刚、张继渠、杨名栋5人,武胡景为组长。[7]此后组内人员有所变化,除了上述5人外,又增加高风、粟泽、华鄂阳、王西屏、郭玉昌5人。[8]
1924年11月,来俄约两个月的刘子刚与张继渠对来东大“我们为什么要受训练”这一问题进行谈话,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因“我们的本身,本非无产阶级,而我们所担负的使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首先要紧的就是我们本身‘无产阶级化”;若“我们想在最短期间回国作工,更有受训练之必要”。[9]这里提及的“训练”,即东大旅莫支部所主导的“布尔什维克化”训练,其中除了开展谈话训练外,更为重要的是批评及研究训练。
二、 “严格的批评制度”
据陈碧兰(1924年10月来俄)回忆,东大旅莫支部“实行严格的批评制度,而这种批评,不但在各小组会里进行,于必要时还在全体大会上进行”[10]。
1924年10月17日至12月12日,第十一组成员召开小组会议有8次。小组会议大致每周召开一次,会议议程主要包括理论学习、批评及其他事项等内容。从11月初开始,议事日程与之前有所变化,批评的内容明显增多且形式趋于固定。
在第三次小组会上,第十一组全体成员都参与了相互批评,问题主要集中在:“做事不灵敏,活动少技术,气量亦太偏狭”;“固执成见……不肯普遍活动,不肯发表意见”;“对于事实认识不清并有点感情作用”;“性浮燥(躁)并少系统研究,有活动能力而不大努力”;“欠果断,性情亦近于温和”;“有学者态度,言语少条理,观察力亦不十分精确”;“个性太强……对团体训练的意义亦不明瞭(了)”等。[11]其中一位成员在历次小组会上都遭到批评,但经过几次批评后,他的“研究有相当的进步”,且“研究努力,活动亦有进步”,这些都显示其行为已初有改善。[12]
除了组内成员相互批评之外,第十一组成员还在小组会上对“本组总现象”进行批评。如在第四次小组会上,成员的批评意见是:“好的方面”包括“研究上肯努力,在基本观点上讨论——合于团体的计划”,还有“同志能相互了解”;“坏的方面”包括“多不能纪律化”“多个人的行动”“多不能相互训练”以及“讨论多没结果”。[13]成员的批评颇见成效,在第五次小组会上已经提出,“好的方面”是“对于上次提出的四点均有相当的进步”。[14]
在第七次小组会上,成员对“本组总现象”的批评更为具体而集中。如在“行动方面”提出多条:“1.对于集体生活的习惯有相当进步。2.参加工作亦较自然。3.谈话能注意实际问题和训练问题。4.多肯发表意见。5.对于规约有相当实行。6.能守会场秩序。7.说话噪乱且有时任意唾啖。”[15]与之前相比,无疑成员对小组的批评更加全面,这或提示成员对团体事务愈加热心,以及集体认同感逐渐增强。
三、 “反对学院派的研究”
郑超麟(1923年4月来俄)曾说在他来东大之前,旅莫支部就流行一种口号: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学做“学院派”。[16]正因为此,第十一组成员采取“反对学院派式的研究并注意从初步根本的认识起始”[17]或“反对学院派的研究,注意基本观点的认识”[18]的路径,以期选择性地汲取认知。
为确定研究方法,第十一组成员召开临时小组会“讨论本组研究方法”,会上陈九鼎提出他所拟订的方法,即“每星期每组员须读共产主义入门若干节”,“并须做一提纲,以备在小组会中报告”;“关于其他校课,诸同志可互相传观”,若“有疑难处,可问九鼎,如解答不了时,可提出小组会议讨论,如仍不决,可请其他组外较有研究的同志解答”,对此“大家都十分同意”。[19]粟泽还提出“除正课外可请秀峰同志酌教浅近俄文”,会上“众亦无异议”。[20]第十一组成员每周的研究内容多由小组临时会议确定,研究内容虽较为庞杂,但甚为集中,主要侧重于革命理论(历史)、中国时事、党团课等,明显体现出一些特征,如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问题”导向及注重党团员的锤炼等。在小组临时会上成员有时也直接讨论问题。如在第四次临时小组会上,第十一组成员讨论“中国时事问题”,首先由组长武胡景“先说明问题的意义,然后由组员逐条尽量发挥意见”,末由武胡景“做结论——每条均有结论”。[21]

此外,第十一组成员在小组会上研究《共产主义ABC》似已为固定程式。在8次小组会上,“讨论”《共产主义ABC》一书有7次,共有19节内容。[22]如在第二次小组会上,当粟泽做完《共产主义入门》的报告后,华鄂阳和刘子刚“均有补充”,陈九鼎“更特别提出”有关“政党的普遍的原则”,并阐述“多数党的特点”为“工人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坚固的组织”和“统一的意志”,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惟(唯)一工具”,并“时常淘汰不良分子”。[23]陈九鼎提及的“多数党”即布尔什维克,而上述讨论即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化”训练的一部分。对于第十一组成员来说,研究一般并非学理性探讨,更多的是一种对特定问题的基本认识的探讨及“言语的技术”的操练。但此种训练有一定难度,因此第十一组仍然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如有成员在报告时没有提纲,或少有发言表述,以及未注意到“有系统、有结论的讨论”。[24]
总的来说,东大旅莫支部对研究训练的“反对学院派的研究”取向,恰体现了其务实的一面。特别是通过小组会开展的“学科阅读研究和讨论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且“对党员和团员的教育从各方加紧进行,确实加速提高了同志们的理论水准”。[25]
四、 结语
在东大旅莫支部的领导下,第十一组成员经由召开小组会开展相互批评,追求训练的“绝对化,纪律化,系统化”[26],以促进自身的“无产阶级化”;同时进行有计划的研究,尤为“注意基本观点的认识”。批评训练逐步增强成员的组织纪律性,而研究训练则凸显出希望成员“在短期间内将基本观点认识清楚,准备回国做工”[27]的实用取向。这些训练为提升学员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思想认识、能力素养创造了条件。1923年4月,郑超麟刚到莫斯科时即感慨道:“前面等待我们的”,“是革命生涯”,“是斗争,是暴动,是革命,是监狱,是流血,是牺牲”。[28]这是第十一组成员中多数人的人生映照,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如武胡景一度担任上海“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且有多位成为革命烈士。
当然,这一时期中共早期留苏学员的“布尔什维克化”训练成效也受到多重因素制约,如苏联的既定中国战略与东大旅莫支部渐趋激进的训练方针之抵牾等[29]。这些“紧张”与“冲突”一方面凸显出中国革命的“国际化”景象,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本文系2022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留苏雨花英烈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SYA-017)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孙建军、朱志敏等主编:《1921—2011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合作北伐》,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
[2][3][5][29]张泽宇:《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述论》,《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24、25、24、29 页。
[4]《中国班的名单》(1925年4月14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1-393。
[6]《各小组的分配》(1924年),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1-393。
[7]《各小组的分配》(1924年),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1-393;《第十一组纪录本(1)》(1924年10月12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8]《第十一组纪录本(2)》(1924年11月3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9]刘子刚:《报告表》(1924年11月23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10][25]陈碧兰:《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52、152页。
[11]《第三次小组会会议纪实》(1924年10月31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12]《小组会会议纪录》(1924年10月17日至1924年12月12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13]《第四次小组会》(1924年11月8、9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14]《第五次小组会会议纪实》(1924年11月14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15]《第七次小组会会议纪录》(1924年11月28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16][28]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194、182页。
[17]《第三次临时小组会纪实》(1924年10月27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18]《第五次临时小组会会议纪实》(1924年11月3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19][20]《第二次临时小组会会议纪录》(1924年10月17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21]《第四次临时小组会会议纪实》(1924年10月31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22]《小组会会议纪录》(1924年10月24日至1924年12月12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23]《第二次小组会会议纪实》(1924年10月24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24]《第十一組报告》(1924年10月31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第十一组第二次报告》(1924年11月14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26]华鄂阳:《每周报告表》(1924年10月12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
[27]《第十一组报告》(1924年10月31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532-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