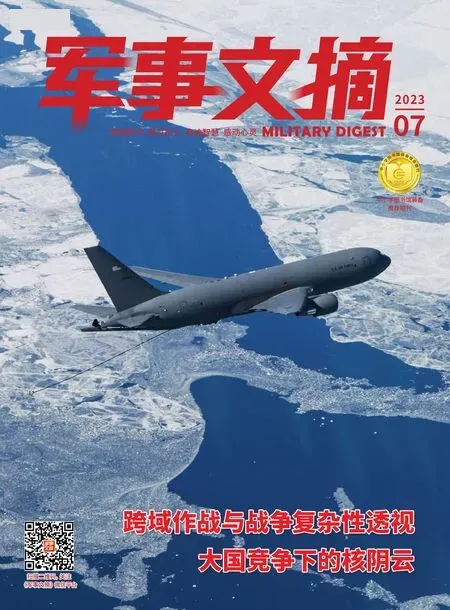人工智能塑造作战指挥要素新特点
陈志华 张 勇 刘远航
作战指挥要素是实现军队指挥活动正常运行必须具备的要素构成,包括指挥主体、指挥客体和指挥手段。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必然带来作战指挥领域的深刻变革,作战指挥要素首当其冲。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影响下的作战指挥要素新特点新变化,对于把握智能化作战指挥规律、提升作战指挥效能、制胜未来战争意义深远。
作战指挥主体向新架构转变
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的优势远超人类,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由人独自担任作战指挥主体的传统局面。这一转变从形式上看是人机结构的变化,实则是指挥权的重新分配。随着人类赋予人工智能更多指挥权,作战指挥主体将呈现人机结合的全新架构。
多数战术指挥由人工智能负责。在面对问题边界清晰、策略空间有限、数据信息完整的有限决策领域,人工智能反应速度显著快于指挥人员。发挥人工智能在战术行动指挥中的敏捷优势,有助于畅通传感器-射手链路,不断加快“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循环速度,“秒杀”制敌,制胜未来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一些政治敏感度高、环境复杂、目标特殊的作战任务时,仍需由人直接指挥。因此,指挥员在合理赋予人工智能指挥职权的同时,还应科学界定交战规则,实时监控行动进程,确保行动有序可控。
战役指挥由指挥员主导人工智能辅助。人工智能融入作战指挥机构,形成了以指挥员为核心、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全新编组模式。首先,指挥员是核心。虽然人工智能在决策活动中能够给予指挥员一定支持,包括情报分析处理、战场态势融合和方案计划拟制等,但决策的核心工作仍需指挥员亲力亲为,例如,关键情报需求的确定、决策方案的选定、作战命令的下达、作战重心的权衡和关键作战行动的把控等。其次,人工智能辅助决策。云计算、大数据、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在精准性、快速性上远超人类,在情报处理、态势感知、方案检索和任务规划等方面能够给予指挥员实时可靠的决策支持。在此过程中,指挥员应积极引导人工智能有重点、有选择地进行计算分析,减少无效运算,提高计算效率,使之更加适应指挥员的思维决策方式,达到人机深度融合。
战略指挥由战略指挥员牢牢把控。战略指挥是对战争中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具有宏观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特征,受到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决策难度大、风险高,通常由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直接掌握,而绝不能交由人工智能负责。特别是对于军事强国而言,一旦形成战略误判,将可能招致核战争危机,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人工智能发展到高级阶段,赢得更多的指挥职权,但是人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是永恒不变的。人的主要任务是关照全局、把握核心、确保可控,机器的主要任务是辅助决策、落实行动,人在宏观层面、思想认知层面更好地指导机器,机器在微观层面、技术层面更好地辅助人。准确把握人与机器的关系,对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机器辅助作用,实现人机协作合理分工,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显得至关重要。

无人狼群概念图
作战指挥客体朝着新方向不断演变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无人机在军事上的运用更加广泛,为作战指挥客体带来了根本性变革,即作战力量无人化、作战行动智能化和作战样式集群化。
作战力量无人化。随着无人装备的大量运用,作战指挥客体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从以人为主到有人/无人混合编组,再到完全无人化。美国《21世纪战略技术》报告指出:“20世纪的核心武器是坦克,21世纪的核心武器是无人系统。”无人装备以其特有的全天候、全方位作战能力、生存能力、低费效比和绝对服从命令的优势,业已成为装备发展主流趋势,世界各军事强国甚至是小国都加紧研制无人武器装备,加快战场运用。2020年9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为争夺纳卡地区控制权爆发冲突,双方倚重大量无人飞机遂行空中交战和对地攻击行动,揭开了大规模无人机战争序幕。
作战行动智能化。尽管无人装备具有先天优势,但难以具备人的思维与意识,依赖人的操控,自主性差。传统的机器人,通常受制于程序设定,执行预先编程的重复性任务,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但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的自主化程度不断提高,可以感知并适应周围环境,理解人的行为和命令,能够快速可靠地完成各种非确定性的复杂任务,朝着“类人”“智人”方向不断迈进。
作战样式集群化。随着集群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无人蜂群作战样式越发受到青睐,不只是“无人蜂群”,还有“无人狼群”“无人鱼群”,他们通过大量单功能或多功能小型无人机组成无人作战集群,在网络的支撑下,通过单个平台自主决策或平台间行为协同,达到倾巢出动、群起攻击的效果,实现自主式集群作战,发挥“小而多”的规模作战优势。DARPA多年来一直在实验从C-130型平台上发射并回收小型无人机集群,这些无人机被设计成诱饵和小型电子战干扰平台,用以迷惑和蒙蔽敌方的防空系统,也可配置成分布式“网状”传感网络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携带小型弹头进行“自杀式”攻击。这种依托母舰实现远距投放回收的方式,克服了无人机集群作战持续时间短、航程有限的先天不足,提高了实战化运用效益。
作战指挥手段瞄准新目标飞速发展
作为作战指挥主体与客体间联系的桥梁纽带,作战指挥手段将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向着“信息获取广域精确、信息传递安全高效、信息处理并行实时”方向飞速发展。
信息获取广域精确。随着感知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光学、红外、电磁、声学和生物为基础的传感器的探测精度越来越高,感知能力越来越强,为战场精确感知奠定了基础。此外,无人装备的大量运用,极大拓展了战场侦察空间。高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增大了情报获取的广度与时限,微型仿生机器人采取缝隙管道渗透进入敌方核心涉密场所的方式实现了关键敏感情报收集。这些广域灵活部署的集成了传感器模块的海量无人装备,形成了一个全时域、全维度的立体侦察监视系统,能够精确全面探测战场信息,为指挥员提供可靠的情报决策支持。

无人机摧毁萨姆-8防空系统
信息传递安全高效。以战略通信网、战役通信网、野战通信网、卫星通信网、计算机通信网等通信网络为基础建立的网络信息系统,可将任意作战单元、作战平台或单兵按需接入动态自适应、韧性抗毁的战场神经网络,并利用大容量、高速度、多方式、高质量的数字通信技术,实现各信息节点间的高效通联。此外,以智能算法为支撑的数据加密技术,极大提高了信息的安全保密性。
信息处理并行实时。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是将源头信息统一回传至后台处理器,再集中进行分析处理,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且时效性差,特别是面对日益增长的海量战场信息时,指挥员容易陷入“数据海洋”,难以自拔。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使得大型计算和数据存储中心和靠近数据源头的具备存储和计算能力的信息节点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在注重发挥云计算中心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的同时,又能够发挥边缘计算平台分散部署、随时处理的优势。此外,大数据技术依靠其强大的数据存储、数据并行处理以及数据分析能力,通过寻找数据规律,从海量情报信息中进行数据挖掘,汇聚有效信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处理模式,形成了基于广泛数据积累、关联数据深度挖掘的情报信息生产模式,提高了信息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总的来说,人工智能在作战指挥领域的深度融入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顺势而为,应不断深化人工智能在作战指挥领域运用研究,探索作战指挥智能化转型的方法路径,谋求智能化战争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