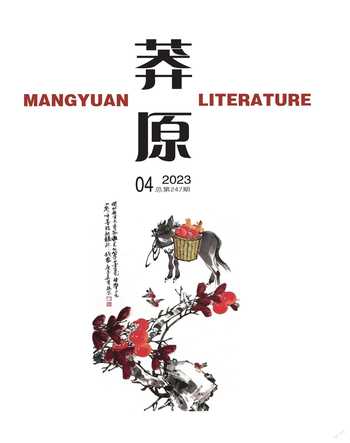灰莉
吴隐
Time drops in decay,
Like a candle burnt out,
And the mountains and woods,
Have their day, have their day.
1
她走进剧场的时候,舞台灯光已完成了最后的调试。电子屏闪烁,长臂摄像机也悉数就位,黑黢黢矗立着,几棵旧世孑遗的老树,孤高傲立于其他草木。一切都蒙昧不清,像闯进了萤火幽微的雨后森林,气息燠热,尽管开着空调,正夜雷低沉般轰隆作响。
她目不斜视,打定主意只考量眼前可选的座位——区域合适,还空着一大片。但还是看到了他,余光一瞥,第一排有个熟悉的背影,衬衫浅蓝,映出颈间工作证挂绳的深蓝。没有熟人上前寒暄,她深吸一口气,原地踌躇了半秒,镇定地选了一个中区靠门廊的位置,坐在了最外侧,心想,如果看得厌烦,随时可以抬脚离开。
刚一坐定,就立刻低下头,解围似的点开手机。新闻推送,一篇;装修文章推送,一篇;未读消息,无。时间才六点三十二分,离开演还有将近半小时,早来只是为了占座位,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在溺于睡衣拖鞋的休息日里出门总是很麻烦,提前设定好热水器、匆忙洗澡,笨拙地化妆,然后穿裙子、试袜、换鞋,临走又匆匆戴上耳坠,只为了某些说不清的东西。她舒缓下来,心脏回到原本的位置。
三十五岁的中年女性,坐在满场艺术生中旁观毕业晚会,万人如海一身藏,恰到好处的自艾自怜,而又略带悲剧意味。乐音渐起,舞台背景浮现青春的面孔,当下偏狭审美选出的孩子,千篇一律地显出乏味之美,尖下巴,杏仁眼,小而窄的鼻梁,笑起来没有酒窝;连毕业视频中的临别寄语也是千篇一律的——“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真可怕,永是少年不老不死的,恐怕只有吸血鬼;“今朝各奔天涯,明日有缘再聚”,这话听起来老气横秋,实际却幼稚得不得了,见面靠约定靠情分甚至靠勉强,从不靠缘分,坐在树桩前等待天注定,兔子也等不来半只。
邻座忽然一阵香风,一袭轻粉鹅黄的巴洛克风紧身连衣裙勾勒着水蛇腰。“大家都在呀,宝宝,快说姐姐们好。”陌生的年轻女人拉着小女儿在熟人瞩目中落座,一一致过意,又拿出手机自拍,容色秀丽,红唇欲滴。“妈妈要去后台准备了,你在这儿乖乖坐着。”
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变得如此刻薄?她回神自問,大家不过都是普通人,何必呢?但这些普通人仍令她心绪不安。五分钟前,同一年留校的林涓在座位区间里停留了一阵,她是某个节目的编导,正在为演出做最后的细节准备。符合大众审美的林涓并不乏味,相反她很迷人,迷人到仅仅一个背影就足够了:短发蓬松,黑色的短裙,黑蝴蝶一样憩在膝盖上方五厘米处,没穿高跟鞋,双腿的线条流畅而细致,比例均匀。林涓未曾回头,即便回头也不可能认出她,她们只不过曾经一起出现在一张入职合影里罢了——合影中,所有人都显得严肃而古板,通身白加黑,“像卖保险的制服”,她过后主动向好友自嘲,“最多也就大堂经理了。”但那时,还有句话噎在喉咙里,不曾吐露:“你看,第一排最右边的女孩,没按规定穿制服,是不是很漂亮?”没有出口的问句,答案过期的考题。如果好友说“是”,当初她又会怎样回复呢。
她终于看向他。
2
她过去不信命。直到第一个深深喜欢的人拿出一张照片:“这是我女朋友。”直到初恋在电话里说:“对不起,我还是忘不掉她。”直到……
也许有人在摇篮里就注定了拥有什么,失去什么,就像一种写在基因里的天分。她给自己的独身找到了一个看似科学的模糊解释,“你看,我就是没有恋爱的天分,没有这个运数。”当然更别提结婚了。
自然的,她把工作也解释为运数。一个暗示性的开头,一旦追认,就更具宿命色彩。“灰莉”是一切的开头。那天,她走了很久才找到笔试考场。将雨未雨的天气,空气灼人,荷叶给热得打了卷,只有紫色睡莲强撑着精神。她半是烦闷半是懊悔,甚至觉得了无意趣。走到考点入口的时候,她看到了那朵花,开在半人高的陌生植物上,满树肥厚的叶片,碧绿莹润,但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全无花苞,单有一朵绽放的白花,显得十分突兀。她喜爱极了,凑近才觉出它有淡淡的清香。不防有人笑问:
“是来考试的吗?状态还挺轻松哦。”她那时已经心情大好,顺口回答:“无知者无畏啊。”她抬起头,看到一个从未见过的人。
许久,等到终于忐忑不安地闯进面试考场时,她才大致闹明白他的身份。他坐在正对面,脸上带着一丝戏谑而真诚的笑容。她不知道他是出于礼貌的宽慰,还是真心觉得她幼稚到好笑。但她因此沉静下来,像一句老话——“吃了定心丸”。之后的每一道关卡,她都没再紧张过。
她去查了植物的名字,“灰莉”,Fagraea ceilanica Thunb,名字奇特到令人不解,仿佛沦落尘世的“灰色丽人”;马钱科的常绿灌木,花期4-8月,生于海拔500-1800米山地密林中或石灰岩地区阔叶林中。真幸运啊,在不适合它生长的地方,撞见了当年花期的第一朵,她想。
万物有时。灰莉如约告别了花期,他也像辞别枝头的花朵,很快接到了调离通知,那天恰好是他四十岁生日。
盛满了观众还显得空荡荡的剧场,他又像十年前那样,坐在最显眼的位置。她从不能准确地描述出他的长相,他们工作交集不多。她只是跟好友提起过她的感觉:“像山一样,从未远离,从未老去。”而她是矢志不移的山民,庙碑、传说、故事、劳作、观察、体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也听到过零零碎碎的八卦,他的婚姻,他的前妻,他的现任,“一个赛一个漂亮。”这是她悄悄探听到的最准确评价,不含任何具体信息,又似乎切中了关键。她们当然是漂亮得不能再漂亮的女人,当然是一见倾心,除此之外,还能以什么更合理的方式同他坠入爱河。
其间她又照规矩续了一次合同,只是她没有放好原本,更没费心扫描留存副本。新版的签名和盖章都很潦草,毫无美感,同经手的人一样庸俗敷衍,她翻看确认无误后,只是把它叠到旧合同上,没再打开过。
3
回忆中断。她今晚第一次把目光转向自己身上。模糊了曲线的衣襟设计,遮挡住双腿的黑白裙摆,羊绒面高跟鞋,老套的酒杯跟款式,像不像當年保险公司制服的变体?还有一部分是她想要隐去而无法隐去的,脸庞。她变了多少?她不确定,她只记得一个旧人,在最近一次碰面后迅速失去音讯,继而相亲结婚,“再见”“预告”,一字皆无,她再次明白了岁月难堪。家里的镜子逐渐裁减到一面,小小的一面。连不得不记起的生日,也成了额外的提醒。
追光灯亮起,一路护送盛装熠熠的主持人走至台心。南来熏风,北疆草野,粉臂如藕,杨柳腰身,但音乐全部乱糟糟的,舞步尚酣,音符业已用完,只好草草接续下一曲;服装的颜色也说不出的刺眼,《忆江南》哪像《忆江南》,倒像《忆秦淮》。她有点恍惚。她在他离开后才注意到石青,这人不笑,脸上常年带着怅怅的讥讽味的神色,能把松松垮垮的运动服穿出博衣广带的味道。今天“石青”两字印在总编导的位置,白纸黑字,却叫她一点也不敢信。指尖颤动,顺着纸张轻轻地往上滑,光线幽昧,她更不敢信“石青”上方那三个小黑方块——是他的名字。
她坚信他累了。所有人,所有事,都倚定他拿最后的主意。“前天调试灯光,忙到夜里两点。”不是没人抱怨。怎么会不累,场面上的关节,幕布后的调度,甚至是每一个动作都得审查。然而远远没到说“老”的时候,别人都以为他才三十出头。
她凝望他的脊背,像野草渴慕平坦宽阔的大地。假如,如果此刻她有权利设想一个假如,她要舞台坍塌、屋顶掀起、狂风大作、兵荒马乱,要洪水,要湮灭,要飘摇,要他们一起流落到孤岛相偎相依,幕天席地,星辰为证,她将终于贴近他,如丝萝向它的大树伸出最柔软最坚定的触须。
古典的节目单元结束,舞台变换出爵士与拉丁的热烈,直白的爱的肢体,微微灼痛了她的眼睛。她别过头去,目光随着转动的顶灯漫无目的地扫视剧场的边角。置物台边零散倚立几个观众,还有一个小女孩,无人照管,很放松地趴在台面上看着表演。她好像被吸引住了,神情很专注,隐约可见弯弯眉毛,一点三白眼,薄薄的倔强嘴唇,真像……
念头甫起,她就意识到自己的荒谬。当年的小女孩早该是亭亭少女了。那时也有光,从夏雨擦洗过的天空直射,穿透层层枝叶,在地面洒下些梦一样的小圆点。她加班结束,习惯性地跑去图书馆抱出几本书才往回走。一步,两步,她雀跃着追赶因微风而闪烁变幻的光斑,远远看见一个好看的背影——一位父亲,正不厌其烦地为怀里的女儿举高高,稳稳抛出,再牢牢接住,每一道漂亮的弧线划过,小女孩都会立刻发出幼小动物才会有的愉快叫声。日影依旧明亮,他耐心站着,肩头像落满了金急雨的细碎花瓣。她被那人健美的四肢所吸引,呆看了好一会儿才发觉是他,讷讷挪步过去,和恰巧落在地面的小女孩问了声好。如出一辙的父女俩,尤其是眉毛,既称得上刚健英气,又显得清秀如画。他的样貌,经由其他的女人模铸出翻版,这一点也不让她苦楚,反而令她倍感欣慰。
4
节目过半,最陡峭的崖壁已小心经过,没有人在空翻时摔倒,也没有人在托举中跌落,没有人错踏裙摆,也没有人甩飞帽子,一切顺利,一切顺利,他的脊背渐渐从直线松弛成弧线。
她忘了低头。一个深埋许久的符号,重新展露出它的真实含义,这种突变带来的惊诧程度,不亚于小孩第一次品尝压缩蔬菜汤,几片干槁失色的可疑物体,与热水相逢,眨眼间就膨胀饱满,鲜亮如初。他以别人注意不到的轻微幅度活动了一下脖颈,用眼睛逡巡着自己的“领土”,座位,观众,光束,甚至连他自己,都是图画中的一个个色点,它们互相连接,彼此呼应,直至完全融入同一片背景,完美,协调。当他的目光触及她的面孔,零点一秒,零点二秒,嘀—嗒—嘀—嗒……这个色点让他觉得有点冷清,有点孤立,有点古怪,也有点熟悉,但只是有点,嘀—嗒—嘀—嗒,他没能深究,因为它很快就被更夸张绝艳的色彩之潮淹没、裹挟,渐渐沉到水波深处去了。
她忽然感到置身空屋,四下雪光明澈,照亮里里外外的角落,纤尘不遗。其实她今天晚上坐在哪里都一样,无人问津,无人知晓,犹如那株叫“灰莉”的植物,仿佛沦落尘世的“灰色丽人”。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