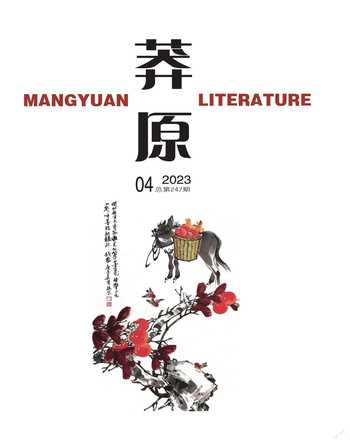一盘录音带
董新铎
这是一桩陈年旧案,对于屈辱的麻木,使我一向习惯于遗忘。然而,那盘录音带里的内容我却记忆犹新。
在那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像我这样家境贫寒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很难抑制对物的渴望,以至于我每次经过垃圾堆,总是习惯于多瞟几眼。那次途经火车站,看到垃圾堆旁有一个灰色女包,尽管那个女包有些陈旧,拉链也已被扯开,老远就能看见包内空空如也,可我还是不由得驻足良久,四下张望,而后走近它,把脖子伸得老长,以图一探究竟。
没人知道我当时接近女包仅仅是出于习惯,更没人知道我走近女包时看见了一盘磁带。磁带在女包里装着,只露出硬币大小的一角。也正是这小小的一角,诱使我轰走垃圾堆上的苍蝇,扒拉开女包,把那盘脏兮兮的磁带捡了起来,在腋下蹭去污迹,翻来覆去仔细端详了一番,见磁带表面没有任何字迹,心想,可能是谁复制的歌曲或戏曲。
正要离开时,无意间又看见一个脂粉盒被一群苍蝇盖着。我再次轰走苍蝇,捡起脂粉盒嗅了嗅,一股馨香瞬间弥漫周身,随之一种莫名的欲望在体内升起。于是,我把那个脂粉盒擦拭干净,连同磁带一并装进胸前的衣兜。有几只苍蝇追了上来,恋恋不舍地在我脸前飞来飞去,苍蝇对香味也情有独钟,这一点与人类相同。
离开垃圾堆,我不时低下头去闻那个脂粉盒。脂粉的馨香让我心绪躁动,想入非非。当时,我正值青春年少,一种病态的窥探欲让我急切地赶回家里。闻着脂粉的馨香,我把磁带装入录音机里,按下了播放键——磁带里竟是一男一女的录音:女孩儿的声音如脂粉的甜腻香艳,沁人心脾,却是听不懂的外语。女孩儿说完,接下来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的也是外语,声音浑厚低沉,透着无以言状的伤感。虽然我不懂外语,可两人的声音里明明蕴含着悲壮与苍凉,间或有女孩儿微弱的叹息声。
越是听不懂这对儿男女的谈话,那谈话越显神秘,这让我抓耳挠腮,无所适从。忽想起我二叔在学院外语系任教,就骑上自行车,单手扶把,另一只手提着录音机,匆匆赶往学院。
别问我的职业,实在是羞于启齿。学院的基础设施年代久远,排污功能极差,随着学生逐年增加,即便不是雨天,个别低洼处也时常污水横流、臭不可闻,不得不用吸污车不定期地从沉淀池里吸走粪便。而我,就是开吸污车的司机,当然是临时工。我念完初中就学会了开车,可开轿车的好差事也轮不到我呀。考虑到开货车终日奔波,极其劳累,考虑到自己一向懒散,害怕吃苦,而开吸污车的差事不会很忙很累,整天跟臭烘烘的厕所打交道,应聘者也指定不多,于是,在二叔的举荐下,我开上了吸污车。因为不是每天都要吸粪,我的工资自然很低。
“二叔,我捡到一盘录音带,里面说的都是外语,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语言,你帮我听听两人说的什么。”见二叔正在校园里溜达,我急不可待地请他帮忙。
自行车没有放稳,那破车摇晃两下,扑通一声倒向一侧,旁边的一个花盆被砸得稀烂。
“你也老大不小了,天天毛毛糙糙的,什么时候能安稳点?”二叔怪道。
我望了一眼花盆,没有理会自行车,把录音机递到二叔跟前,按下了播放键。
“俄语,这是俄语,你连俄语都听不出来?”二叔不耐烦地说,好像忘了我只念完了初中,也忘了那时中小学早就不学俄语了。
“二叔啊,你别不耐烦好不好?我一听吸污车的声音就知道吸出来的是稠的还是稀的,可磁带里嘟嘟噜噜,我哪听得懂呀?”我对二叔嬉笑着说。
磁带在录音机内缓缓转动,我看见二叔的神色渐渐肃穆起来。他把录音机抱到怀里,侧耳细听。其实,那声音已经够大了,我哼着小曲就能听见那鸟语一般的聲音,女孩儿甜润的嗓音像极了燕子的私语,百听不厌。
初春时节,校园里不知名的花儿竞相开放,已经有彩蝶成群结队,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我悠然叼着烟卷,等待二叔将磁带里的内容讲给我听。
二叔忽然关掉录音机,环顾左右,然后示意我跟着他走。
我们来到二叔的办公室,他惊惶地关上房门,靠在门上,低声问我:“大江,你老实告诉我,这盘磁带是从哪里来的?我被二叔弄蒙了。”
见我没有及时回话,二叔厉声问我:“我们李家世世代代都是本分人,你爹娘更是菩萨心肠,走路都怕踩住蚂蚁,你千万不能干出什么缺德事啊!”
我回过神来,笑着对二叔说:“二叔啊,你侄子虽然胸无大志,平时吊儿郎当的,可侄子的心肠那是爹娘给的,怎么可能跟爹娘的不一样啊。”
二叔的神色依旧肃穆,他单薄的身子套着宽大的上衣,很像是木撑子撑了件衣服,他的声音更加低沉下去: “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这盘磁带非同一般,怎么会落到你手里?”
我收敛笑容,认真地说:“这盘录音带是我在火车站的垃圾堆旁捡来的,真的,骗人我不是你侄子。”
二叔像没有听见似的,好像在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这么重要的东西,绝不会被主人遗失在车站,更不会被主人随意扔掉,不是你偷的,就是别人偷的。这会儿,磁带的主人一定急得要发疯了。”
我好奇地问:“二叔,磁带里到底是什么内容啊?被你说得神乎其神的。”
二叔轻声说:“一个宇航员竟然被遗忘在太空了!三百一十一天啊,他历尽磨难,好不容易回到地球,可他的祖国却没有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闻所未闻!”
我的嘴巴张得溜圆。好奇心促使我死缠烂磨地让二叔把录音带里的内容全部讲给我听。二叔点点头,算是应下了。他回到桌前缓缓坐下,又让我把录音机打开,说他要仔细地再听一遍。
我耐着性子,等二叔把录音听完,而后怀着极大的热忱,急巴巴等二叔揭开谜底。
然而,二叔听完录音,定定望着我说:“大江,你听二叔的,赶快把这盘录音带交出去,要么交给报社,要么交给派出所。”
我说:“这盘录音带很重要吗?”
二叔说: “这可能是报社记者的采访录音,嗯,就是采访录音,那女的肯定是个记者。丢失了这盘录音带,人家不定急成什么样子呢,说不定女记者还会被报社开除的,不为别的,咱得为这个女记者的前程想想啊。”
“二叔,录音到底说的什么啊?”我问。
“等哪天没事了,我再把磁带里的内容讲给你听。眼下,先处理这录音带的事。交出去,赶快交出去。”二叔说着,从录音机里取出了磁带,“居然有这样的事,真是天下奇闻啊!”
看二叔那焦急的样子,我点了点头。回味着女记者那柔美的声音,想象着女记者着急的模样,我不再追问,接过磁带揣进兜里,起身出屋,竟忘了带上我的录音机,骑着单车就匆匆出了学院大门。
随着自行车的颠簸,我怀中不时溢出沁人心脾的脂粉馨香。隔着衬衫,我感觉那脂粉盒紧贴着胸脯,光滑细腻,如同女人温柔的肌肤。有那么一刻,我竟然猥琐地想象把那个女记者抱在了怀里。
省城的报社远不止一家,究竟该去哪家报社呢?我心里盘算着。省报是不能去的,虽然那是最大的报社,但发的文章都是一本正经的面孔,可能不会在意这马路新闻;那么还是去晚报社吧,晚报发行量大,而且内容丰富多彩,跟女记者那甜美的声音更搭调。想到这里,我心中充满了激情,穿过闹市,直奔晚报社而去。
“你找谁?”在晚报社门口,一个看门的老头儿将干瘦的手臂拦到了我的面前。
我拨开了那满是黑毛的手背,说我想找一位女记者,一个会说俄语的女记者。
老头儿不屑地盯着我说:“你?你找女记者?她叫什么名字?”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其实,一路上我已经给女记者取了好几个名字,娜娜,莎莎,琳琳……之所以给她取这样的名字,是我觉得这样的名字跟俄语更搭。但毕竟只是我一厢情愿,人家的真名咱哪知道?
老头儿讪笑一声说:“小伙子,你可看清了,这里是报社。”
我说我知道这里是报社,是澡堂子我还不来呢。大约是这句话招惹了老头儿,他把手按在我的自行车把上,使蛮劲往外推。我后退了几步,被脚蹬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正要发火,还是忍住了。我说我要还给记者一样东西,这东西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老头儿的话差一点把我逗乐,他像说相声一样对我说:“对她来说非常重要?那对你来说肯定不重要,不然你也不会主动还给人家,更不会硬着脖子往院子里闯。”
我说我硬脖子了吗?老头儿已转身离去,他坐在大门口的阴影里,懒洋洋望着马路。
我本来是要学雷锋,却似乎是被人家当成了无赖。见老头儿不再搭理我,只好推着自行车离开。路边停着一辆小汽车,车玻璃上的我,肤色稍重,消瘦的脸庞,衬托得下巴更长,我一点都不像无赖啊。再看时,我的面容瞬间被树枝的阴影搅得凌乱不清。
我很想把怀中的磁带扔进一旁的垃圾桶,而后回家睡觉,可一想到那个叫娜娜或莎莎抑或琳琳的女记者,我还是不忍心。犹豫了一会儿,决定骑车去电视台。
到了电视台大门口,看见一个面色红润的人被众人簇拥着走了出来。他的胡须看上去非常漂亮,我一直盯着他的胡须看,直至他接近我的单车。大约是我的专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下了脚步,看我的目光也充满了和善。我顺势问他:“领导,请问你们这里有个精通俄语的女记者吗?”
领导模样的人扭转头向众人询问:“精通俄语的女记者,有吗?”
见众人摇头,那人像是遇到了什么稀罕物件一样,上下打量我一番,而后扑哧一笑,说:“你会说俄语?来两句?”
我说我不会说俄语,可我捡到一盘录音带,是一名女记者的采访录音,她说的全是俄语,我怕耽误人家的大事,就把磁带送来了。
那人看我的目光里带着问号,说:“你不懂俄语,那你怎么知道人家讲的全是俄語呀?哈哈,哈哈哈哈。”
众人一起笑着,簇拥着领导模样的人,走了。
我一点都听不出那人话中之意,也就没去在意那人的话。思前想后,与其这么鲁莽地四处乱撞,倒不如把磁带交到派出所去,警察同志一定能找到那位女记者。可惜如此一来,我就无缘面见那个女记者了。不过,不见就不见了吧,见了面又能如何呢?
我骑上自行车离去,赶往离学院最近的派出所。其实电视台附近就有一个派出所,我之所以舍近求远,是想借此赢得学院领导对我的关注。平日里常有派出所民警来学院巡查安保工作,他们与学院领导常有接触,如果跟学院领导说起这事,说不定就能把我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
想到这里,我心情大好,不由哼起小时候学过的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刚唱两句,就忍不住笑了。一分钱,那是过去,过去你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警察会夸你是拾金不昧的好少年,现在,别说是一分钱,就是一毛钱、一块钱,怕也没人愿意弯腰拾起了,你要是把一分钱交给警察,警察不但不会夸你,说不定还会说你故意捣乱呢。
赶到派出所,我说明来意后,一名年轻警察随即将我领进一个房间。但他没有进来,反手就把房门锁上了,将我一人滞留在幽暗的屋子内。我环视四周,见墙壁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黑森森的大字,心里感觉很不舒服。我正揣摩着这年轻警察的用意,忽听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门锁打开,屋里突然闪进一道亮光,我看见年轻警察的身后跟着一个胖乎乎的中年警察。
门被重新关上,屋里暗了一下,又明亮起来——他们开了灯,所有的灯光都聚在我的身上,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两个警察走到一张桌子后面,将腋下的本子放在桌上,而后指着桌子对面一个带扶手的凳子对我说:“坐下!”
我说你们不用客气,把东西交给你们就行了,不会过多打扰你们的。一边说着,我走近桌子,同时从怀里掏出磁带。大约是有些紧张,我把那个脂粉盒也一并掏了出来。
“坐下!别动!”一声断喝让我顿感毛骨悚然。
中年警察接过我手中的东西,然后示意我去凳子上坐下。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年轻警察看了看录音带,又看了看脂粉盒,然后严肃对我说:“姓名?”
我说我叫李大江。
“性别?”
我没有吭声。可笑,一个大小伙子坐在你们面前,还问我性别,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我终于意识到我正在被审查了。平白无故的,他们凭什么这样对我!一股火气渐渐在体内膨胀,我看着他们,仰着头一言不发。
年轻警察重复一遍刚才的问话,我依旧没有搭理他。
中年警察倒是和蔼许多,他慢吞吞地问我:“还有别的东西吗?包呢?钱呢?哦,还有个微型录音机,录音机呢?”
看来不开口终究是不行了。我说磁带和脂粉盒是我在火车站附近捡来的,有个女包,但我没有捡,包里也没见什么钱,更没有什么微型录音机。
年轻警察盯着我大声说:“报案人说她的包里不但有磁带和脂粉盒,还有现金。她的包就是在火车站被人偷走的。火车站是你经常作案的地方吧?”
我彻底崩溃了。我相信警察说的是真的,也相信女记者真的丢了包和钱,但除了这磁带和脂粉盒,别的都与我无关啊。这可真是丢牛逮住了拔橛的,冤枉死了。无奈,我结结巴巴地把捡到磁带和脂粉盒的过程仔细说了一遍。我说得很详细,包括那堆垃圾和垃圾堆上的苍蝇,包括苍蝇也喜欢脂粉的香气。我只觉得头脑发胀,双眼发昏,急得脑门子上渗出了汗水。
年轻警察说:“钱和录音机就在包里,难道你只喜欢脂粉盒不喜欢钱?难道你只喜欢磁带不喜欢录音机?”
我提高了嗓门,几乎是咆哮着说,你们把我当成小偷了?世界上有我这样的小偷吗?把偷来的东西送到你们这里来,缺心眼呀!你们平白无故地把我带进审讯室来,这是执法违法,我要告你们!
中年警察用粗短的手指敲敲桌子,说:“嗬,看你瘦得虫脸猴腮的,嗓门倒不小啊。”
中年警察竟然说我虫脸猴腮,我平生第一次听人这么评价我的长相。我不就是下巴稍微有点长,腮帮子上肉是少了点,说我猴腮我没意见,可怎么能说我是虫脸呢?虫子有脸吗?虫子细长身子连脖子都没有,直接就是脑袋了,脑袋上是眼睛和嘴巴,哪有脸啊?我这么想时,不由得望向窗子。窗子上有我的瘦长脸,可一点儿都不像虫子。
两位警察还算讲理,最终结果也不算太坏。他们耳语一阵后,其中一位打个电话,通知学院的保卫科长把我领走了。
保卫科长看我的目光有点异样;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人们看我的目光都有点异样。
我来到二叔的办公室。二叔也在为我鸣不平,他踱着步子像是自言自语,他说不知道在你捡磁带的地方是否安有监控探头,如果有的话,那探头就能说明一切;又说警察应该是看了监控的,不然不会就这么轻易放你出来;最后,摇摇头叹息一声,说现在的人啊……
在二叔为我鸣不平的时候,我却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那个女记者,钱就不说了,多多少少,丢了可以再挣,丢了录音机她以后怎么采访?再说,那录音机里是否还有另一盘磁带?那盘磁带里是否还有重要的采访内容?她是否会因为丢了录音机和磁带,进而丢掉工作?也太不小心了,在火车站那种治安极差的地方,你将自行车锁在电杆上,说不准就会丢了车座。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一辆面包车被人偷走了一个轮胎,那车子歪斜着身子,让我想起呼扇着一侧翅膀的公鸡。我见过用那种姿势跟母鸡调情的公鸡。
这么一想,越发为女记者担心起来,就问二叔那磁带上录了什么。
二叔把一张纸放到我面前,那盘磁带里的内容已经被他翻译成了文字。我粗粗地看了,心里大吃一惊——比起那个丢了包的女记者,那男人要倒霉千百倍、上万倍——他的祖国竟然丢了!
男人是一位苏联宇航员,他在太空度过了三百一十一天,可等他返回地球时,苏联已经解体了,一个庞大的超级大国分解为十五个国家;更可悲的是,他不知道他应该属于哪个国家,他的家乡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一个小镇,同在一个苏维埃大家庭时,边界十分模糊,也没人在意,可眼下分家了,竟说不清小镇的归属。按说,国家培养一个宇航员那可是下了血本的,像他这种人,说是国宝都不为过。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男人搭乘美国的飞船返回地球,便被美国中情局扣留了。后来,他在美国见到曾经的领袖,没想到领袖竟劝他留下来,不要再回自己的祖国了。他知道他也回不去了,只好答应。接下来,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都悄悄派人跟他私下接触,都说他是自己人,要他回去给祖国效力。他这才明白,原来那个三不管的小镇,现在三个国家都想要,都想管。他更明白,都想要,都想管,就谁也要不成,谁也管不了;都说能帮他回家,但谁也没有办法带他离开。他彻底感到无所适从了。可他想家,想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他想回到那个阔别了许久的小镇。后来,他开始酗酒,开始泡夜总会,跟各种肤色的女人鬼混……直到有一次,他酒后驾车出了车祸,弄残了两条腿,才再也没人搭理他了。他只能靠给人打零工度日,但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长,因为一个残疾人总是会出这样那样的差错,也因此常常被老板解雇。直到后来,他被一个开中餐馆的华人收留,直到遇到一个中国记者。
我感到像做梦一样,像看一本科幻小说。看了看二叔,二叔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二叔,这个男人怎么会来到中国?”我问。
“不一定。他只是遇到了一个中国记者,也许是在中国,也许是在美国,当然,也可能在别的哪个国家。一盘磁带说明不了什么。”二叔说。
但这个离奇的故事吸引了我,我接着往下看,这一次看得很仔细。下面是女记者与男人的对话:
女:尊敬的先生,我尊重您的意见,为保密起见,此次访谈不出现您的名字,但您确实值得我尊重。我很想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独自在太空坚守了311天?
男:祖国,母亲,还有我的妻子和女儿。是对祖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对母亲、妻子和女儿刻骨铭心的爱。但你无法体会一个人在茫茫太空的孤独,更无法体会那份责任的沉重,那份挚爱的折磨。
女:是的,我无从体会,但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但如今您总算回来了。
男:回来了?回到哪儿了?我的祖国没有了,我成了没有国籍的人;家也不知怎样了,我成了有家难回的人。
女:对不起,我让您伤感了。
男:我伤感了吗?我以为我早就不会伤感了。是的,我應该伤感。最后那段日子,我怎么也跟地面控制中心联系不上,起初我认为是飞船出了故障,或者是地面的通信系统出了问题,现在想来,那时他们都在争权夺利,谁会想起一个远在太空里流浪的人呢?
女:是的,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那时他们都很忙,哦,也不是忙,您的国家正处在混乱状态,每个人都自顾不暇,自然也就顾不上您了。
男:我伤感的还不只这个,还有我曾经的领袖。他曾经接见过我,也给我授过勋章,可他竟抛弃他的国家和人民,在美国过着上等人的生活,还劝我留下来不要回国。
女:也许……您的领袖认为科学没有国界吧。
男: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国籍的。我留下来做什么?给美国人服务吗?要知道,美国可是苏维埃的敌对国啊。
女:所以,后来他们才又去找您了。
男:他们?他们代表谁?俄罗斯?乌克兰?还是白俄罗斯?而这三个国家,哪个是我的祖国?何况现在呢?他们怎么不再找我了?我双腿残了,他们把我当成一块臭肉抛弃了!
二叔写到这里,下面没有内容了。
我抬头看着二叔,试图了解故事的结局。二叔说:“你别看我,我又不在采访现场。下面是砰砰啪啪的摔打声,还有男人歇斯底里的哭喊声,然后就没有了。”
虽然警察没有给我定罪,虽然我平安回到了学院,可我阻止不了保卫科长怀疑的目光。保卫科长的目光有很强的传染性,他把怀疑和提防传染给了学院的人们,甚至传染给了厕所的苍蝇。每当我开着吸污车在校园经过时,总能听到人们的窃窃私语;每当我在厕所开始作业时,那些苍蝇们都一哄而散。好像我的行为不是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好像我做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不过,想到那盘磁带,想到那个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倒霉蛋,我心里就释然了。跟人家遭遇的苦难和委屈相比,我摊上的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呀!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