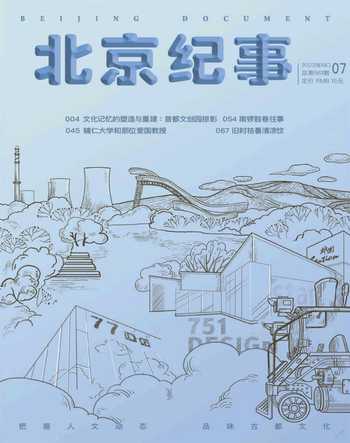北京国槐
王莺

从我家北窗,能看见军博顶上那个五角星。五角星下是燦灿的花朵,绿荫如盖。鸟儿飞过车水马龙,带领所有的喧嚣、浮烟、杂尘,消失在槐树丛中。
那时,军博广场上停着真的飞机、真的大炮坦克和一些真的机关枪。广场被槐树包围着。没开花的蕾,叫槐米,槐花在花序上,一串串儿的,次第绽放,花期绵长。
北京,三千年的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槐树是生物界里最强盛的世袭贵族,最忠实的见证者。
槐树,作为北京常见的行道树、庭荫树,遍布大街小巷,广植于宫廷宅第、寺庙公园、学校机关、乡舍人家。盛夏,青白浅黄的花雨;寒冬,水墨丹青,映画天空。但凡被国槐树覆盖的地方,总是天地灿烂。
十里长安街的十里国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的,长安街附近的老城区、胡同,远处的郊野、山河都有国槐树立。
树立的树,是槐树。独树一帜、树碑立传、蚍蜉撼树、玉树临风、枯树生华、春树暮云、因树为屋、尺树寸泓等等的“树”,也是指这个槐树。“大树底下好乘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是指这个槐树。
国槐,家槐,中华树。唯一冠之“国”字的中国树。原产于中国,北京的乡土树种,这也是我知道的最能活树的树。
国槐,北京市树,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在北京顶天立地。又圆又大的树冠,温柔、豪迈。羽状的复生叶从早春绿到立冬。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似乎只有这叶的秀慧,才般配得上这木的挺拔。疏朗与繁密,完全取决于它四季分明的光芒。
与其他树种比,国槐的花期在流火七月;与其他树种相遇,国槐生长的速度显得略为缓慢;与其他树种相同,它也是在青壮期内发育迅速。分枝点一般大约在三四米。行人行走,刚好有一把伞的撑起。
它们自觉地以所处环境、所属气候、所受待遇,来规划自己长度与高度;以自主和谐正义的名义,天生一副少要张狂老要稳持的秉性。侧枝分杈极少旁逸,顶部冠幅常常大于树干,彰显它荫庇的职能与权力。
故宫槐林
1990年我带着五·三班小学生春游,我拉着队伍从天安门域楼下进去,一路都是金碧辉煌,红墙宫里万重门。
世界五大宫殿之首。国内外的游客一直很多。我数人数,突然发现少了一个,我想,这是出了大事了!
故宫那么大,我上哪儿找去呢?往回走,南午门、神武门,太和殿、中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都没有。最终,我在槐林,找到了他,这小子,靠在一棵大槐树干睡觉呢!“我梦见我当了皇帝。”他沮丧地说。
人们逛故宫,往往直走中轴线,汉白玉石阶,名木建筑,宫、楼、亭、门、阁、台都是权力的布局,谨严的形制,礼制的营造。
知道槐林的人并不多。所以,这里人很少,很安静。
《旧都文物略》这样记载:断虹桥北地广数亩,有古槐十八,排列成荫,颇饱幽致。一个断虹,让我们无比惆怅。饱不足以描绘那一棵树半亩荫的景致。不仅仅十八棵。过去的,尚活着的,原只剩下十七棵,或者说是十六棵半。因为其中一棵早已枯死,却在根部萌生了一棵小苗。后又补种了两个十八棵,形成了故宫槐林。
“树冠羞避”,这是森林才有的奇观,指的是林冠之间的孔隙度。大树树冠的空间仿佛被均匀分配,树冠与树冠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相互避开,从而形成一条条弯弯曲曲的空隙带。鸟瞰,仰视,这些空隙带同等宽窄,彼此之间给对方留有余地,更仿佛河流水渠交错流通。这种现象的成因至今还是自然界的一个未解之谜。而故宫的槐木们,自觉不自觉地矗立得错落有致,也形成了这奇观,并比宫殿布局还要合理曼妙。
十八槐最帅的是它的“野”。
故作端庄的皇帝大臣进出西华门及各种宫殿时,都要经过此处。一片难得的野趣开阔地,能让他们片刻休闲。我怀疑这是清人想着唐朝王维写《宫槐陌》“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而造的景境。仄经上的每一棵,像老子一样,有道法自然的力量,长了美轮美奂的树样儿。这是紫禁城里唯一留下的活的文物,撒尽狂野几百年,哪管什么风云变幻呢?
凤凰国槐
北京有许多以槐树命名的地方,槐房、槐树岭、槐柏树街、龙爪槐胡同、槐树街、槐树院、槐花社区等。北京新建小区,新建街道,一定会种下很多槐树,这是国槐的新生力量。
说槐树,归根结底最想说明白的是:槐的品格,槐的本事,槐的生命力。无数的槐,这神慧的生灵,几百年、上千年拓展了北京城,繁华强壮了北京城。
很多国槐因为品行,因为故事,因为神情、气质、风貌、外形,或者因它生长的地点或年代,被熟悉它的人们赋予一个名字。例如,凤凰国槐。
宋庆龄故居。整整十八个春天,这棵600年的凤凰槐,每时每刻都在她身边起舞。不知是因为凤凰槐的风景,让她在这里,还是因为她的姿态,让凤凰成槐。
西面的树干崛起向阳,枝条屏散,羽状的叶子十分丰满。东面的树枝则匍匐于地。大地的引力没能阻挡它崛起、昂首。颈长,硬朗,秀美。向上的是肩胛,是枝。层羽、尾羽是叶。跖骨、胫骨,是干、是铁臂铜戈、是振翅欲飞的凤凰。树干是褐红色的撑开的剖面:一半是纵横捭阖的老树皮,一半是光滑布满云纹水层样的木骨。
头上的叶积是“德”字的形状,翅膀上“羲”字的枝条,背部是 “礼”字的茎脉,胸部的用新芽滋生出一个“仁”字。腹部的主干与韧皮刻满了一个“信”字。
宋庆龄生前十分喜欢这棵古槐。后院还有很多她养的鸽子。庭前一棵树,后院一群鸽,我想那些鸽子会来这里栖息吧。
国子监槐树
小染问我,来你们北京有啥好玩的?北京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哪儿最有意思?我说,去国子监吧。
她是中学语文老师,我是小学语文老师。我特别爱上生字课。我教“监”字,这个生字可好玩了,皿堆儿底,是个盆。我学着甲骨文的监形,画了个有人低着头,以盆水为镜,照自己的小漫画儿。后来有了铜境,便为钅监,后又简化为“鉴。”意思也演化了、丰富了。总之,“监”字其中几个意思:监察,机构,鉴别等。国子监,就是天之子、国之栋梁们上学的地方。教育部,最高学府,大学。北京的国子监建于元朝,曾是最高管理教育机构,当然也曾经掌控过政治权力。那时,很多民族和其他国家的学生也来这里交流学习。国子监的国槐,一个“国”的概念与内涵,不禁使人畅想连篇。那时,还没有清华和北大,也没有哈佛和耶鲁。

今年放暑假,小染惊呼,哎呦呦,国子监,没有一个学生,怎么这么多槐树,这么多花呀!
北京今年雨水充沛,开了比往年都多的槐花。国子监有一棵七百多年的吉祥槐。高约十五米,由两棵主干组成,似一对孪生兄弟,并肩而立,沐着花雨。据说这是元代国子监第一任大学校长许衡所植。经明清两朝,经一个春天,枯而复荣。
北京国子监为何有很多槐树呢?
这还源于周代的面三槐,三公位焉之说。三槐分别象征太师、太傅、太保这样的官位、官职。槐树被称为公卿大夫之树,国子监里种有这么多的槐树,就是暗示着监生们能榜上有名,踏上高官仕途之路,并且当个清明的好官。踏槐,举子脚踏槐花去高考。我国古人视槐树为科第吉兆的象征。
我对小染说:“国子监就是有那么多槐树。那时,不种槐树,又能种什么树呢?”
小染说,是呢!我想让我儿子考上北京的大学,我们一定来国子监,拜谒北京的国槐。
冯家峪村古槐
要说在北京,最美的、最有资历的国槐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我暂时这样说吧,在密云县冯家峪村,长城脚下。
冯家峪村,并没冯姓村民。穆桂英挂帅中盔甲被撕破了,但她仍然催马抡枪,奋力杀敌,最终杀退了辽兵。穆桂英趁空隙,在一棵大槐树下,缝补起撕裂的盔甲来。当地百姓敬佩穆桂英的战绩,就把她缝盔甲的地方称缝甲峪,后叫冯家峪。
当时槐树很多,密云白马古道上有驻军的城堡也很多,城堡虽多,但大多年久失修,隐居于山谷丛林,唯有古槐树站岗的这一段,坚固无比。
2022年10月17日上午,我再次来看老槐树在哪儿。刚一问,立刻围上几个晒太阳的老人,齐刷刷地指着同一方向。
“就在我们这儿,一拐弯,村口,城口儿。”
我依旧不改习惯,拜了拜,丈量它的荫浓冠幅,丈量它的主干高度。胸径:高23米,干周长达7.60米。好大一棵树。高大之余,还有奇妙。树身有大洞。
树干有多长,洞穴就有多深。人,可以钻进去。膝盖下是松软的落叶层。
我小心翼翼钻进这个树洞,打开手电筒,照亮树中空的木层木壁,周围表面如山如海如土地,凹凸不平,跌宕起伏,朽而不腐。我的光线向上移,树,好高,照不到顶,一缕阳光透过来,树洞是光亮亮的。
树腰围缠着多条红绸布,红绸很新,村民已经把古槐视为自己的长者,寄托着美好愿望,保佑家人平安。
据当地村民讲,当年秦始皇修边时所建,先有古槐树后有烽火台。 树旁,是山,是长城,是碉堡,是农田,是菜地,是农舍,是庙宇,是小路,是水溪,还有很多。总之,该有的东西一定有,偏僻得四通八达。槐树,这是你们最爱待的地方吧。
我生在北京,每天行走在北京,五个脚趾紧紧地叩在这里。我右脚的最小趾甲是两瓣儿的。你的,可能也是。我们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儿歌唱遍了大半个中国,也回荡在年轻而古老的北京。明朝的大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迁徙,出发的地点就是人丁兴旺的洪洞大槐树村。传说从老槐树下迁出来的人,最小的那个脚趾甲都是两瓣儿的。
结语
国槐,浑身都是宝,建筑的栋梁,食用的药材,衣服的染料,酿酒,造纸,采蜜。在北京,它最重要的任务:环保,绿化。
万里江山,只此青绿。北京国槐,形祎祎以畅条,色彩彩而鲜明。丰茂叶之幽蔼,履中夏而敷荣。 这唯一以“国”字冠名的树种,该有怎样的担当?我不好定义,它太唯美神明。是北京的记忆、见证、象征、符号?也可能就是图腾。
槐的好,很多很多人想说出来,也想让别人知道。北京步入城市化改革道路后,很多郊外、村镇,要乡村振兴。盖楼,修路,建公园。2008年有人提议在朝阳平房乡用1000亩地建京城槐园。且不说这I000亩农田消失,试想用槐文化,展开老北京城的记忆,槐树要树立起来,是一年两年的事吗?
我在京城槐园,转了一大圈儿,人不多,树,弱弱的。苗圃一样临时种着。整齐排列,很不情愿的样子。也许它们正在开着花。槐花,淡香,淡淡的香。淡香,倒也没什么,我算计着它们秋天能不能結荚。不是所有开花的都能结果的。
小东庄,原顺义镇辖村。2004年,小东庄村整体改造拆迁,原址上建起了金汉绿港小区。在三区7号楼南北的两处约四米高的土台上,遗存420年古槐各一株。树体扭结,螺旋而生,上升,仿佛永远带着暴风,带着横扫一切的气象。
北京城区现有国槐294.29万株,行道树国槐44.33万株,分布在2969条道路,占总行道树数量42.3%,百岁、千岁的古槐并不罕见。
北京,很大。我还要找槐树,我还要再登长城,环绕北京绿色隔离带,穿越北京时空。淌水永定河,爬石景山,去平谷,探险门头沟,迎面朝阳,观揽密云,感受昌平,体验大兴,我想寻遍北京天下所有的国槐。绘制一幅画卷,建立一个档案,记下北京国槐,她的姓氏名谁,年龄,外貌,性格,健康成长程度。
我就是一个小学老师,不是国槐专家。我认定自己就是一棵槐树。树木生长并非只能用年轮来计算,切身感受它无与伦比的构造,了解树木机能运转的方式,才能体悟树与我们之间的血脉联系。
我感受了时光赋予它们的气概与尊严。感受了为数众多的古槐,它的智慧与情感。它们高级地从不被动地活着。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它永远向天际生长,入地厚积蕴。我们看不到,它的细胞因分解和扩大而变成粗壮、强悍。 初生长、顶端生长、直径生长、次生长,总在生长。这不仅仅是光合作用,还有细胞断裂组合扩大。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抗“城市化”的攻击。
三千年建城史的北京也许就是从槐的肇始,八百年的建都史也许就是槐的赓续。
我讲了很多有关槐树的故事,不是因为有了故事才有了槐树,是因为有了槐树才有了这么多故事。
先有国槐后有城乡,因有城乡后有国槐。北京国槐能识别北京城的多维条码。五沃之土,其木易槐,千年轮回百年转世,积淀、组合,生成这枝枝蔓蔓。北窗望去,鸟取栖?投翼,?望庇?披衿。
后来,我搬走了,到了西南郊一个叫花乡的地方。后来,花乡也没有了,但我能听到它们的声音。后来,我一直没离开北京国槐。国槐给予我的恩泽与护佑,给我树德。它始终作为一个背景,阔展,矗立在我的身后。
编辑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