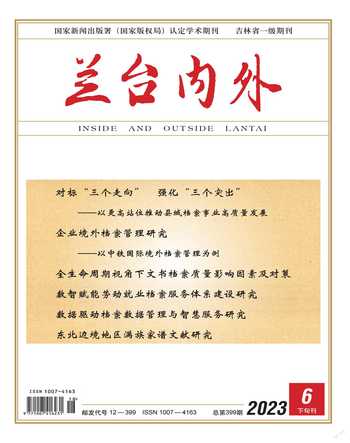“华亭周氏图书”述略
摘 要:周大烈所藏“华亭周氏图书”被其后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分三批捐赠给上海市图书馆、静安区图书馆和金山区图书馆。捐给静安区图书馆的藏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部署要求,近年来静安区图书馆对周大烈“华亭周氏图书”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研究,包括古籍版本鉴定,破损情况调查,编写善本书目、善本书志和善本书录等,揭示善本的存世价值。本文旨在呈现“华亭周氏图书”的整理研究成果,展示静安区图书馆在古籍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关键词:华亭周氏图书;古籍;藏书
引言
“华亭周氏图书”是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所藏古籍的重要部分,为周大烈先生旧藏[1]。
周大烈(1901—1976),字迪前,号述庐,松江县亭林镇(今属上海市金山区)人,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中华图书馆协会首批会员,藏书家、国学家,有藏书楼名“后来雨楼”。周大烈是清代江南著名藏书家周厚堉之后。周厚堉“来雨楼”藏有历代古籍善本。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向民间征书,周厚堉进呈的藏书逾百册被录用。周大烈的藏书室命名“后来雨楼”,有承继祖辈藏书之志之用意。周大烈喜欢藏书,也勤于著述,著有《松江文钞》《松江诗钞》《南齐书校注》《南史艺文志》《四库附存简明目录》《后来雨楼书目》《知见辑佚书目补》《清代校勘学书目》《述庐文录》等。1937年冬,日寇从金山卫悍然登陆,周大烈与家人到上海躲避。一年后将劫余的藏书运到上海静安区一处公寓,从此再没有回家乡。1976年,年事已高的周大烈逝世。20世纪90年代,周大烈七位子女将劫后幸存的近万册图书捐赠上海市图书馆。1994年6月,周大烈七位子女再将1288册藏书捐赠静安区图书馆。2016年11月,周大烈之子周东壁先生作为子女代表又将1197册藏书捐赠给金山区图书馆。关于捐赠静安区图书馆的藏书,笔者协同文献专家进行整理和研究,以便学界对周大烈及其“华亭周氏图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1 静安区图书馆与“华亭周氏图书”的渊源
周大烈先生从避居上海到去世,一直住在静安区。其子周东壁就住在静安区图书馆附近,爱阅读的他经常到图书馆看书、参加活动和做志愿者。基于对静安区图书馆的深厚感情和信任,周东壁先生提出将父亲周大烈先生的1288册藏书捐赠给静安区图书馆,得到了兄妹们的一致支持。1994年6月,周氏兄妹将其父亲藏书的一部分捐赠给静安区图书馆。静安区文化局和静安区图书馆举办捐赠仪式,并向周氏兄妹颁发捐赠荣誉证书。证书写道:“周迪前先生收藏之古籍,经子女周东序、周东垣、周东塾、周东壁、周孟繁、周梅诧、周季苹七位,将1288册藏书捐赠静安区图书馆。使这些古籍为更多读者所用,是为造福后人,功德无量。”同年11月,静安区图书馆聘请周东壁先生为荣誉馆员。2020年4月,图书馆领导登门拜访耄耋之年的周东壁先生,向他介绍捐赠古籍的整理情况,提出将把整理成果陆续予以出版的设想,以此种方式致敬周大烈先生及后人捐书之大义[2]。同时,为了使这些古籍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利用,图书馆将通过举办周大烈藏书展览、论坛、研讨会、影印出版等形式,使更多的读者了解藏书的内容和价值。周东壁先生对此表示支持,并深感欣慰。
2 馆藏“华亭周氏图书”整理情况
2.1 整理背景
自1994年至2018年,“华亭周氏图书”作为镇馆之宝一直保存在静安区图书馆专门定制的书橱里,考虑到古籍的珍贵性及破损情况,没有向公众开放。为了完成周大烈先生子女捐书的心愿,继承和发扬周大烈先生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爱护精神,静安区图书馆于2018年开始与复旦大学古籍保护专家一起,对这批藏书进行整理和研究,一方面响应国家号召,另一方面对这些古籍进行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使之走出书橱,走向社会,真正服务读者。
2.2 整理过程与成果
2.2.1对“华亭周氏图书”进行梳理和书目编纂。静安区图书馆将获赠的“华亭周氏图书”收藏于原中华民国海关图书馆,即如今的海关楼版本主题馆。图书馆收录时制成馆藏古籍资产登录簿,但未对这些古籍从文献专业的角度进行编目整理、系统分析与研究。图书馆邀请文献专家对全部藏书进行清点,共梳理出属于线装书藏书245部1167册,并按照国家《古籍著录规则》(GB/T3792.7-2008)标准,从题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存卷、内封、卷端、藏印等款目内容方面对古籍进行著录,最后编纂完成《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藏古籍书目》。书目按照经、史、子、集、丛五部进行分类,其中经部29部148册;史部52部323册;子部74部202册;集部87部464册;丛书部3部30册。
2.2.2对“华亭周氏圖书”古籍破损情况进行调查。“华亭周氏图书”历经战火和多次转运,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加之年代久远等原因,纸张存在酸化、老化等现象。此次整理,不但对每册古籍的尺寸和厚度进行测量,还对其破损情况开展调查登记。包括各册的装具、书衣、题签、订线、霉蚀、虫蚀、鼠啮、断裂、书口开裂、水渍等内容,共完成破损调查记录6000余项,形成《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古籍尺寸测量与破损调查清单》,为今后制订古籍修复保护方案提供了基础数据。
2.2.3版本鉴定和编纂善本书录。区图书馆邀请复旦大学图书馆文献专家对“华亭周氏图书”进行版本鉴定。在245部古籍中,清代乾隆六十年及以前的刻本、稿本、抄本、批校题跋本,以及乾隆六十年以后的稿本、抄本、校本及稀见刻本等可以列入善本的,有69部361册,其中明刻本就有27部。专家调查了69部善本在国内外各收藏机构存藏情况,发现有的仅见于国内外几家图书馆。例如《论语义疏》十卷本,是三国时魏国大臣何晏所做的集解,唐朝时传到日本,并有手抄本流传。到清代时,日本的足利学校还收藏有手抄本,第三任驻日公使徐承祖等人经过多方努力,才获得足利学校同意,对该手抄本进行抄录。带回国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付诸刻录。陈捷《关于清驻日公使馆借抄日本足利学校藏<论语义疏>古钞本的交涉》详细介绍此事经过,并感慨一直找不到此抄本的下落。
2.2.4撰写善本书志。在编纂《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藏古籍善本书录》之后,通过各书的序跋、识语、牌记、批校题跋、藏书印、版式、刻工等信息,参考《中国古籍总目》、《中国丛书综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工具书和网上数据库[3],选择《南华真经》《论语义疏》《嵇中散集》《林屋全集》等重要善本撰写书志,向读者揭示这些善本的存世价值。
在此试举一例,《南华真经十卷》书志:战国庄子撰,晋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明刻《六子全书》本。六册。半叶八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单白鱼尾,四周双边,版心镌题名、卷次及页次。框高十九点七厘米,宽十三点五厘米。前有郭象序。《南华真经》即《庄子》。唐玄宗天宝元年,庄子被封为南华真人,其著作亦被尊为《南华真经》。此书《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最早版本为宋刻本,另有明嘉靖十二年顾春世德堂刻《六子全书》本、桐阴书屋刻本、万历十一年金陵胡东塘重刻顾氏《六子全书》本,清嘉庆九年姑苏王氏聚文堂刻《十子全书》本、宝庆经纶堂刻本、爱日堂刻本、清刘履芬抄本等。其中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徐州市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明桐阴书屋刻《六子全书》本(袁廷梼跋并录顾之逵校,叶景葵跋)分别入选第二批和第五批。此本乃据明嘉靖十二年顾春世德堂《六子全书》本翻刻。顾春字符卿,号东沧居士,江苏吴郡人。有“世德堂”以刻书闻名。《六子全书》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包括《老子道德经》《南华真经》《冲虚至德真经》《荀子》《扬子法言》和《中说》六种。其始刻于明嘉靖九年,竣于明嘉靖十二年,因校刻精良,后来多有仿刻、翻刻。前述明桐阴书屋刻本,《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有著录,并认为乃“翻刻嘉靖十二年顾春世德堂《六子全书》本零种”。此本不避“玄”讳,版式、行款、字体均与顾春世德堂本同,惟版心上未镌“世德堂刊”。哈佛燕京图书馆有收藏,并著录为“明刻《六子书》本”。《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称其“乃据明嘉靖十二年顾春世德堂刻《六子书》本重刻。顾春世德堂本书口上有‘世德堂刊四字,此重刻本则无”。此本通篇有沈大成录惠栋红豆斋校并跋。《南华真经序》题名下有沈大成绿笔跋语:“乾隆丙子中冬,借红豆斋本录,其《音义》则以陆氏《释文》校正。小寒日大雪,云间沈大成记。”卷端题名下有朱笔识语:“乾隆丙子岁莫,大雪累日,借红豆斋本校读于广陵客舍。沈大成记。”卷二眉端有朱笔批点:“庄生知道,实开予心。壬申九月二十一日识。”钤有“学子”朱文连珠方、“有华书塾珍藏”朱方、“徐暎玉印”白方、“鹿樵”白方、“桐城萧穆经籍图记”朱方、“曾植私印”白方、“灊庸”朱方、“蘧传”白方、“嘉禾姚埭沈氏金石图史”朱方、“宋戉”朱文连珠方、“娄邨宋肎堂珍藏”朱方、“肎堂”朱方、“宋钺私印”白方、“臣钺之印”白方、“宋钺之印”白方、“长宜子孙”朱方、“羲皇侣”朱方、“?锋”朱方、“华亭周氏图书”朱方印。
3 “华亭周氏图书”的藏印情况
“华亭周氏图书”的最大特征是钤有“华亭周氏图书”的朱文方印。静安区图书馆的周大烈藏书几乎都盖有此印章。除“华亭周氏图书”藏印外,许多书还盖有历任主人的藏印,如明崇祯刻本《翰海》十二卷钤有“光风霁月”“侠胆傲骨”藏印,清康熙钱唐龚氏玉玲珑阁刻本《浙西六家词》钤有“澹渊真赏”“王澹渊审定”“华亭王庆麟字畤祥一字澹渊印章”藏印[4]。更难得的是,“华亭周氏图书”有很多是名家旧藏,如明刻六子全书本《南华真经》十卷钤有沈大成、张大镛、沈曾植等人的藏印,他们都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学者;明万历徐氏刻清康熙二十年徐佺重修本《世经堂集》二十六卷钤有邓汝功、吴引孙等人藏印,邓汝功是清乾隆四十年进士,吴引孙是晚清官员和著名藏书家;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富顺官廨刻本《六书音均表》五卷钤有温葆淳藏印,温保淳后改名温保深,做过咸丰、同治两任皇帝的老师,官至福建学政、太子少保等职。
4 施蛰存与“华亭周氏图书”
现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学者施蛰存先生多次借阅周大烈先生藏书。这些藏书对施蛰存先生在校勘学、词学、金石学、地方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很大帮助。据《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收录的施蛰存日记、信件中的记载,仅在1963年至1965年三年间,施蛰存先后21次到周大烈家中借阅研究所需要的珍贵书籍。这些书籍有《杜诗阐》《释柯集》《葩庐诗经书目》《松江诗钞》《湘瑟词》《谷水旧闻》《金石莂》《封荫甫传》。施蛰存每次从周大烈处借到所需藏书都欣喜万分,常在日记中记录下兴奋难已的心情,如:借到《云间文献》八册,回家后从早读到晚;借到《萍因蕉梦阁题辞》《熙朝咏物雅词》《金石莂》《犹得住楼诗选》等书,说这都是自己好长时间就想得到的。其中就有捐赠给静安区图書馆的《金石莂》。此书为清代冯承辉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云间冯氏刻本,内封题有“金石莂,云间冯少眉影摹金石拓本上版,刊者金陵镏贡九,时嘉庆戊寅春日印行”,并盖有“华亭周氏图书”朱方印。
“华亭周氏图书” 使施蛰存先生与周大烈先生成为学问上的知己。周大烈去世后,施蛰存亲自为其撰写《处士周迪前先生诔》,称其“艺征七略,文律两京”,“知其学朴茂渊渟,真儒士也[5]”,“失我益友,滋可痛也”。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厚。
结语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6]该意见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为此,静安区图书馆将继续做好“华亭周氏图书”整理研究工作,通过推动古籍数字化、开展古籍专题展览展示[7]、编辑出版、开发文创产品等方式[8],加强“华亭周氏图书”古籍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参考文献
[1]周大烈选辑,张青云整理.清百家词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3.
[2]周大烈,姚竹修著,张青云点校.述庐文录·惠风簃剩稿[M].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7.
[3]沈建中编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陈捷.关于清驻日公使馆借抄日本足利学校藏《论语义疏》古钞本的交涉[J].版本目录学研究,2010(10):375-408.
[5]周东壁,戴群.亭林周迪前先生纪念册[J].都会遗踪,2021(1):71-86.
[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12):30-33.
[7]黄瑾.古籍的保护与利用分析——以南京图书馆为例[J].收藏与投资,2023(3):100-103.
[8]林立涛,王东波.古籍文本挖掘技术综述[J].科技情报研究,2023(1):78-91.
作者简介:韩怡星(1971— ),研究生,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文献保护与传承,文献整理研究。
档案史话
“清档”——清代档案的汇抄制度
在清代,军机处建有一种档案汇抄制度,称为“清档”。据《枢垣纪略》一书载:“凡本日所奉谕旨及所递片单,抄订成册,按日递添,按月一换,谓之清档。”由于“清档”系军机处日常之事,故汇抄的范围非常广泛,数量繁多。诸如凡军机处拟定的谕旨,经送交皇帝审定以后,均发还军机处,由军机处值日章京逐日逐条地誊录在特别的簿册之上,每月一册,名曰“现月档”。每年的“现月档”均需另修一副本,按季分别命名为“春季档”“夏季档”“秋季档”“冬季档”总称为“四季档”。此外,军机处还根据具体需要,按专题或事件汇抄档案。例如在清乾隆朝以后将镇压农民起义的有关上谕和奏折汇抄而成的“剿捕档”;抄录有关西藏的各种档案而成的“西藏挡”;记载皇帝出巡各地的“巡幸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