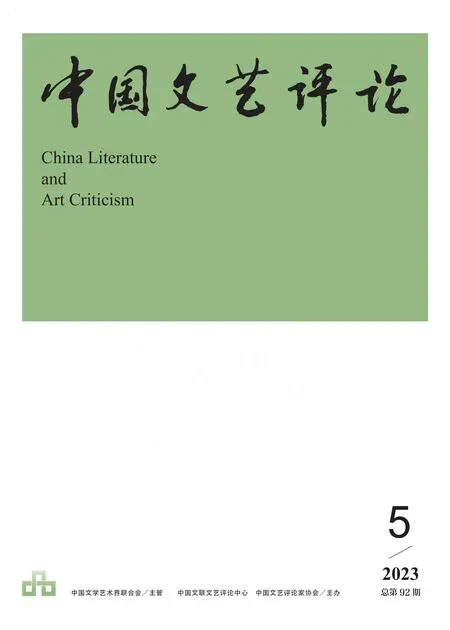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与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
——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举隅
■ 饶曙光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页。在此背景下,2018年8月14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受总局电视剧司委托,在北京举办“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研评会”,对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在总结我国“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电视剧”[2]在电视剧研究领域,有关“现实题材电视剧”和“现实主义电视剧”两个概念的使用,2019年9月11日,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期间,在由《广电时评》杂志社主办的“影视剧创作论坛——现实主义的新能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论坛主持人冷凇,从厘清概念的角度指出:“要么说现实主义创作,要么说现实题材剧。”本文采用“现实主义电视剧”这一概念,指的是以现实主义为根本态度和方法,源于现实、反映现实并影响现实,具有现实主义审美精神和品格的电视剧作品。参见四方:《划重点!“现实主义”和“现实题材”如何厘清?这场论坛说清楚了!》,2019年9月11日,https://www.sohu.com/a/340635853_100253016。在艺术和审美层面上的主要创作经验时,与会专家指出的“要在美学表达和审美价值上不断创新,主旋律电视剧要避免落入简单化、概念化的窠臼”[3]刘汉文、孙晖:《电视剧司委托召开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研评会,透露了哪些重要信息?》,微信公众号“国家广电智库”,2018年8月15日。,对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尤其是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入新时代以来,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回潮并引发收视热潮。以2023年开年大戏《狂飙》为例,人民网给出“是一部兼具广度、深度与力度的现实主义作品”[4]李宁:《人民艺起评:国产影视剧需要更多的〈狂飙〉涌现》,2023年1月28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3/0128/c1003-32613145.html。的高度评价。根据“人民数据”网络平台的报道,《狂飙》上线的30天内,与其有关的新闻报道数量高达285万篇,在豆瓣平台上有46万多人参与评价,并给出了平均8.6的评分,在微博平台上,关于《狂飙》及其剧集相关内容话题的热搜也接连不断。[5]参见叶德恒:《开年“狂飙”,政务新媒体如何借势传播?》,2023年2月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266190804265980&wfr=spider&for=pc。在这其中,围绕高启强这一剧中反面人物的塑造,是引发广大网民热烈讨论的核心议题。事实上,除了《狂飙》中的高启强,近年来国产剧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形象,如《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隐秘的角落》中的张东升、《开端》中的陶映红,等等。他们虽是反面人物,却受到了不少观众的追捧,其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年轻观剧群体中引发追剧潮和热议。而在这一热议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正是文艺创作中关于人物塑造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关于如何塑造典型人物“复杂性性格”的问题,“我们无法做到不考虑他们复杂的人性而单纯地去憎恶他们”[6][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李浚帆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3页。。但在创作中,如何把握好反面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塑造尺度,如何保持一种正向的创作立意,如何在创作中做到坚守人民立场、以人民利益作为最高创作标准,从而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是新时代电视艺术工作者应该重视的问题。文章从这一现象入手并以这些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塑造为例,从性格结构的角度分析反面人物的性格塑造及其在审美表达上的新变,以此管窥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作为一种方法的现实主义的内部实践中的升华与深化。
一、性格善面的建构与儒家“性善论”观念的内置
众所周知,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则中,人物是作品表现的中心,人物塑造是作品创作的核心。而在人物塑造这一问题上,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又尤为重要,这在电视剧创作领域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有关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一议题的探讨,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有学者曾较为系统地从性格结构的角度来探索这一古老的课题,并提出了“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这一美学原理,此所言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是一元化的二重组合,不是二重人格的分裂结构,亦不是性格两极的机械相加或模式套用,而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人物性格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回望这一论断,对今日现实主义文艺如何塑造典型人物的复杂性性格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借由这一方法论视角,从性格结构的角度来看,在《人民的名义》《隐秘的角落》《开端》《狂飙》等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中,如祁同伟、张东升、陶映红、高启强等反面人物性格塑造上,其共有的性格结构无一例外地体现为“善恶同体”或者说“美恶并举”的二重组合。而所谓“善恶同体”或者说“美恶并举”就是性格的二重组合。诚如人民网所刊发的评论,高启强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了作品在人物塑造上的深度,写出了其人性的复杂性与命运的偶然性。[1]参见李宁:《人民艺起评:国产影视剧需要更多的〈狂飙〉涌现》,2023年1月28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23/0128/c1003-32613145.html。而确切地说,这种人物塑造上的深度、人性的复杂性正是构筑在其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之上的。下沉到剧作实践层面而言,这种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又是借助其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来完成的。
在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的方法论视角下,人的伦理取向有美/善的一面,也有丑/恶的一面。塑造典型人物的复杂性性格必然涉及到人物性格的两极,正面人物的塑造如此,反面人物的塑造亦如此。对反面人物性格善面的建构,是塑造反面人物复杂性性格不可或缺的性格面向,抹去了这一性格面向,一味地呈现其人性之恶,就等于抹去了反面人物作为一个普通人普遍具有的性格结构的二重性。以《人民的名义》《隐秘的角落》《开端》《狂飙》等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中反面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一个基本的共性就是在其性格反向转化之前,其人物性格的伊始都是“性本善”的,且在其身份转换之前无一例外地都是出身底层或基层。这种出身底层或基层的身份起点与“性本善”的性格基底,不仅从细微之处建构出传统现实主义在塑造反面人物上常忽视甚至抹除的反面人物本该具有的性格善面,同时也建构出其身份结构中无法抹除的底层底色及其精神世界中无法抹除的底层图景,进而建构出作品在整体叙事结构中隐含的底层逻辑。举例来说,一方面,《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出身农村贫困家庭,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后一路做到省公安厅厅长的位子,但他始终无法忘怀自己出身寒门及其受过的屈辱和遭遇的不平;《开端》中的陶映红在成为化工厂质检员之前是一名中学化学老师,但其女儿因车祸被撞死后而遭受的网络暴力和无法获知真相的无奈,使其性情大变而丢掉工作后成为底层化工厂质检员,“哀莫大于心死”地租住在社区车库研制炸弹;《狂飙》中的高启强在转变为黑道大佬之前是一名鱼贩,出身寒微,受尽欺压,即便在其从卑微渺小的底层鱼贩转变成涉黑组织的头目后,其口头言语上仍不忘“我是卖鱼的”“告诉老默,我想吃鱼了”……另一方面,祁同伟成为公安厅厅长后对老家亲戚没有底线的照顾、对待下属和朋友的仗义、富贵之后的不忘本,也在剧作层面悄无声息地建构着其与生俱来的“性本善”,也建构出反面人物难得的人情味;同样的建构逻辑也反映在陶映红和高启强身上,陶映红对女儿可以舍弃生命的与生俱来的母爱、高启强对其家人尤其是对其弟弟高启盛的兄友之爱亦是如此。剧中这些对反面人物性格善面的细微建构,显示出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反面人物塑造上所呈现出的审美新变,不仅使反面人物更加饱满化、立体化、生活化,更具复杂性,也更具人情味和毛边感,反映出作为一种方法的现实主义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审美观念层面上的变更、松动与延展,或者说在思维方式上对传统现实主义中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的人物塑造观念的打破、开阔与转化。
在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底层和美善往往被捆绑在一起。上述作品对反面人物性格结构中与生俱来的“性本善”的细微建构,从审美表达所依托的文化土壤上说,植根于儒家“性善论”的文化观念。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孟子首倡“性善论”,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1页。;宋明理学以后,“性善论”这一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朱熹认为“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2]同上,第325页。,王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3][明]王阳明:《传习录》,叶圣陶点校,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255页。……“性善论”的理论主张不仅对国人文化观念的形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文艺理论研究中关于“人性论”的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指出:所谓“人性”就是人类自然本性,反映人性,就是反映具体的人性。[4]参见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第39-40页。反映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人性就是写英国小说家福斯特意义上的圆形人物,就是写马克思所言的具有丰富性格特征的“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就是肯定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的美学意义和承认美感的二重性。从人性的伦理取向上看,人性之中必然包含着善与恶的二重性,正面人物如此,反面人物亦是如此。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巧妙地将反面人物出身底层的身份起点与“性善论”这一儒家文化观念缝合在一起,在作品整体叙事结构中建构出隐含的底层逻辑,进而建构出反面人物难能可贵的性格善面即人性之美好的一面,这正是反面人物与观众建立情感共通点和审美共通点的重要连接点。正是借由这一逻辑起点,观众才对其身份转换及其性格反向转化后导致的悲剧命运产生同情感,观众对反面人物所产生的情动、与反面人物之间发生的共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反面人物的热议,正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而内置在文本之内的儒家“性善论”的文化观念,对观众的主体认知建构产生的重要影响则在于,观众借由作品建构的意义场域和伦理取向,通过叙事这一行为及其叙事技巧,在叙述与情动的辩证关系中引导观众产生“意会”,并最终诱发观众对反面人物的悲剧命运产生共情。
二、性格的反向转化及其悲剧命运的流溯式再现
某种意义上说,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构成文艺作品创造具有高级审美意义典型不可或缺的美学基础。在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的方法论框架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一般都要呈现出性格的发展史,即要呈现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史,以显示其性格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过程,这就是性格的辩证法,亦是心灵的辩证法。这种性格运动的辩证过程包含着空间上的差异性和时间上的变迁性。而从时间维度上看,人物的性格大都可在流动变化的过程中被划分为两大性格阶段,进而构成性格组合的辩证法。从对性格结构中丑/恶面的呈现来看,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对反面人物性格恶面的呈现是通过性格的反向转化来完成的。换句话说,从性格与命运的勾连关系来看,反面人物最终的悲剧命运是由其性格的反向转化导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性格的反向转化不仅是其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作品叙事的转折点。所谓性格的反向转化指的是:“一个人往往在人生的某一时刻放弃先前执着的价值、信念,转而追求相反的价值和信念,或放弃先前的生活方式。”[1]苏宁:《现实主义与人格二重性》,《江汉论坛》1998年第4期,第61页。它可以理解为人的心理变化的一种趋势,即在人的心理系统中,这种相反的势力一旦突破心理意识的防线并在人的心理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就会导致情感与价值信念的反向转化。对于反面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说,即在性格发展史的时间维度上呈现出由美善转化为丑恶的渐进式过程,进而将人物命运转向一个不可知的偶然性中,实则即转向一个宿命式的悲剧命运及其悲剧结局中。
举例来说,在《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性格反向转化的转折点是他对梁璐的那“一跪”,当他跪下的那一刻,编剧似在表达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他不仅抛弃了之前的信念,而且抛弃了其性格中的善端。编剧周梅森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意将其出身、学业、爱情、婚姻、事业等人生具体事项,细微地再现给观众,使观众不仅看到了一个性格饱满的反面人物形象,而且在其悲剧命运的悲剧结局中感受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凭借激发怜悯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缪朗山译、章安祺编订:《缪朗山文集1 西方美学经典选译(古代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那就是悲剧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悲剧美的美学力量所在。在《开端》中,陶映红性格反向转化的转折点是其女儿死后遭遇网暴,她却无法借助法律渠道获得真相和公平,于是当她最相信的东西动摇了之后,她的人生信念也随之跟着动摇,复仇的心理欲望使她的性格走向一个完全反向的极端并最终导致她的悲剧结局。而《狂飙》中高启强性格反向转化的转折点则是多个事件叠加后的累积转化,先是从徐江的儿子徐雷被电死后他决定收白江波的钱的那一刻开始,他的性格开始黑化,而后当他成了泰叔的儿子后又杀死了徐江,其人物性格彻底黑化并一发不可收拾地坠入深渊……这些作品紧紧抓住性格的反向转化这一性格转折点亦是叙事转折点,并以“一种在向前流动的形象系统中不时地通过向后回溯而获取力量的流动性与回溯性之间相互交融”[2]王一川:《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成熟道路——兼以〈人世间〉为个案》,《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4期,第71页。的流溯式的艺术手法,再现由其性格的反向转化而导致的悲剧命运及其悲剧结局。在这种流溯式的再现中,对观众而言,有时反面人物的心理世界的矛盾及其真相的展开过程远比结局更重要。正是在这种流溯式的展开过程中,观众不仅一点点了解到他们的心路历程,也一点点与他们建立起情感的连接,这种由性格的反向转化构筑起来的反面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由作品外溢给观众,引发观众热议并使观众随之产生与之相对应的复杂的情感心理反应,而这正是由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带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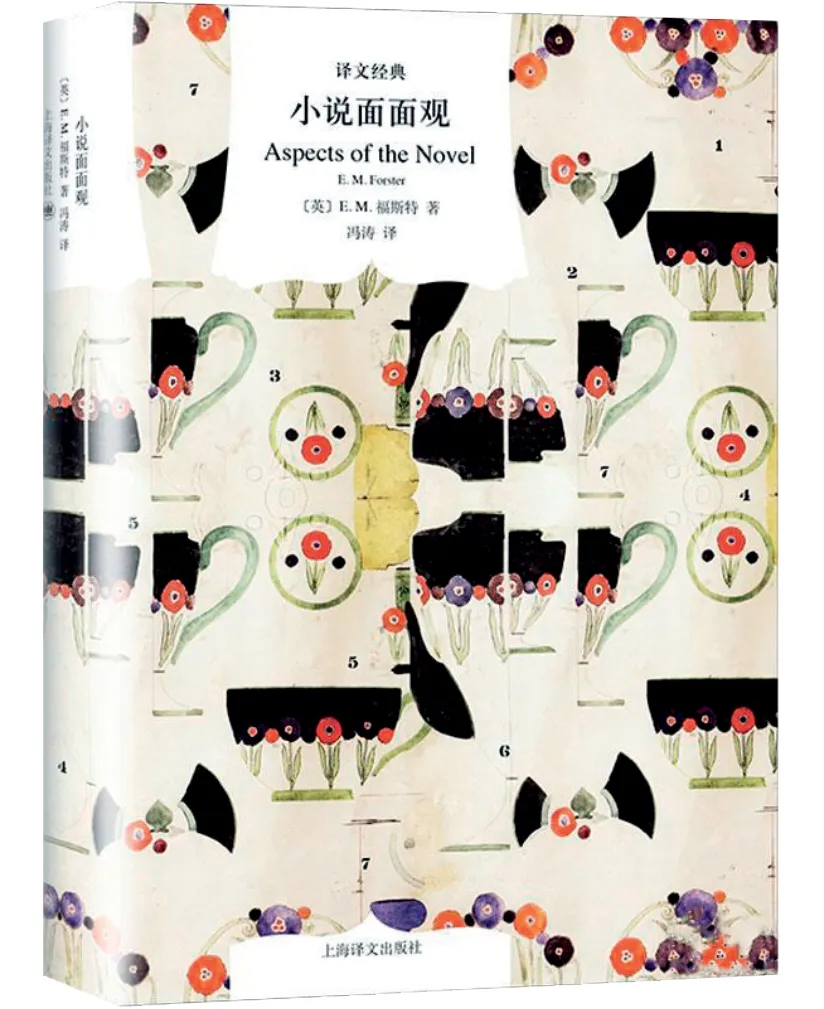
图1 [英] E.M.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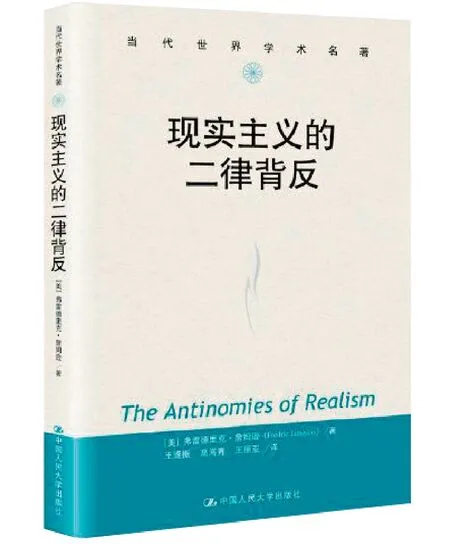
图2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

图3 [法]罗杰·加洛蒂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性格的反向转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外在环境、突发事件及其与他人、社会复杂的交涉关系中持续转化的。反面人物每一次性格的反向转化一方面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其自身命运的逆转。从性格的反向转化与个人命运的关系上看,上述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塑造成由性格的反向转化导致的悲剧命运。在悲剧美学的研究范畴中,悲剧与命运这两个概念往往被搅拌在一起,因为人的悲剧遭遇常常被当作人与命运的冲突或者命运干涉的后果。性格反向转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人物命运注定走向悲剧的宿命性结局。因此,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中反面人物在审美意象的表达上无一例外地都体现为一种悲剧美,这种悲剧美正是通过对性格的反向转化导致的悲剧命运的流溯式再现来获得的。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把人物分成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他认为“扁形人物诉诸的是我们的幽默感和适度心,圆形人物激发的则是我们拥有的所有其他情感”[1][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79页。。在这个意义上,叙事作品正是借助叙述与情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反面人物的悲剧美成为观众与其建立情感共通点和审美共通点的关键桥梁,这正是这些反面人物引发观众产生复杂的情感心理反应并引发观众热议的内在情感机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善恶同体”或者说“美恶并举”的性格结构及其悲剧命运的流溯式再现,给这些反面角色带来了更具感染力的悲剧美,其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中掺杂着现实可感的粗粝感、生活感、毛边感,这正是福斯特意义上的圆形人物所该具有的性格特征,也是现实主义在人物塑造上所追求的恩格斯所言的“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德]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的复杂性性格所在。
三、人格二重性与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
在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中,反面人物所具有的“善恶同体”或者说“美恶并举”的二重组合的性格结构,体现的即是人物性格的二重性,概言之即人格二重性。从哲学上说,二重性这一概念源于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的概念。根据我国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的解释,“所谓二律背反就是矛盾对立的意思,或译先验矛盾亦可”[3]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修订第六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22页。。通俗地说,就是当理性运用于超验对象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即两种命题虽然各自成立但两者之间却相互矛盾的现象。后来这一概念被马克思移植应用到经济学领域,用以分析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由此,二重性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事物所可能包含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属性。人格二重性是人普遍存在的性格结构,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内在冲突,亦是现实主义文艺创造具有高级审美价值的典型人物形象的美学方法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不仅在审美表达上成为塑造复杂性性格的美学策略、方法、手段,而且在期待视野上拓宽了观众的审美空间,给观众带来一种更丰盈也更复杂的情感心理反应,更为确切地说,就是观众对这样一个“善恶同体”的人物形象产生了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心理反应,既生出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情感的净化与怜悯,又借由情动生出一种另类的同情或者说共情,而这正是这些反面人物在年轻观剧群体中引发热议的核心问题所在,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由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即人物性格的二重性带来的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而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这种由人物性格的二重性带来的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就其本质而言,反映出现实主义本身在认知与审美即在认识论与美学之间的二律背反。关于这一点,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中早就指出:“现实主义作品的内部本就蕴含着一对矛盾,具体表现为它既要求一种美学地位,又要求一种认知地位。由于认知与审美的因素并非完全和谐地共存,现实主义作品的内部就存在着天然的二律背反。”[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王逢振、高海青、王丽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反面人物塑造上所呈现的人格二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不过是现实主义自身二律背反的一个侧面。
辩证地看待现实主义,聚焦于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实际上都围绕着二律背反形成。[2]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王逢振、高海青、王丽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5页。举例来说,《开端》导演孙墨龙曾在参加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开端》研讨会时表示,现实主义表达是本次主创团队应对创作挑战的抓手,也是贯穿创作始终的关键词,与其说《开端》是一部悬疑剧、科幻剧,不如说是一部生活剧,因为该剧在非常规的故事设定下,所蕴含的是对善良正义、良好社会秩序的追求,在超现实的时间循环里,展现的是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相信小人物也是生活的主角,剧中的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但他们拥有普通人的真实与可爱,这样的现实主义表达,是这部作品在超现实的设定下的精神内核。[1]参见《导演孙墨龙谈〈开端〉:超现实设定中的现实主义表达》,2022年2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5827326315662377&wfr=spider&for=pc。这事实上体现出现实主义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二律背反,“现实主义的形式通常表现在内容层面,这同样是一种建构物,由现实主义和叙事共同参与完成”[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王逢振、高海青、王丽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页。。诸如此类问题和现象恰恰表明,在现实主义的内部实践中,正是由于存在着种种二律背反,现实主义作品才具有一种极强的张力性。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正是在认知与审美的两极之间走钢丝,既要考虑现实生活,又要考虑虚构性质、形式选择与内容表达面临这样的问题,人物塑造亦面临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由人物性格的二重性带来的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就其本质而言,反映的其实是作为一种方法的现实主义在其具体的内部实践中在认知与审美即在认识论与美学之间的二律背反。
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中,詹姆逊将叙事和情动视为现实主义的双生源头。在詹姆逊那里,叙事和情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辩证关系,即一方面情动似乎抵制叙事,而另一方面叙事又不得不承担对情动的再现。由此,詹姆逊认定在现实主义内部存在着叙事与情动之间的内在矛盾,并从本质上将这种矛盾视为现实主义在认知与审美即在认识论与美学之间的二律背反:“现实主义是一个混杂的概念,从认识论层面提出的关于言说的知识或真理的界定将它形容为一个美学概念,而现实主义又是个无法用统一标准进行衡量的概念,这就使两个方面的讨论变得愈加困难。”[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王逢振、高海青、王丽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页。聚焦到人物塑造这一问题上,当叙事与情动共生互利时,由影视视听语言强化的感官细节及其感受连同叙事一同打开或者说创造了观众情动的空间,而情动作为一种身体的感觉,由此成为连接观众与剧中人物共情的纽带。从叙事与情动的辩证关系上看,由人物性格的二重性带来的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的审美心理机制正在于此。从美学原理上看,这正是李泽厚所指出的“美感二重性”的问题:“美感的矛盾的二重性,即主观直觉性和客观功利性,美感的这两种特性是互相对立矛盾着的,但它们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形成为美感的统一体”;“美感从心理学看,是感知、想象、情感、理解四种基本功能所组成的综合统一,而不只是其中的某一种因素”。[4]李泽厚:《从美感两重性到情本体——李泽厚美学文录》,马群林编,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30、39页。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反面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所呈现出的人物性格二重性,有时会因创作尺度的失衡而模糊了善与恶的边界,在带来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同时,也带来人物性格上的“含混性”或“不确定性”,“含混意味着一种悖论”[1]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166页。,这种悖论对于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中的反面人物塑造来说就是由人物性格二重性带来的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现实主义能在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内容、人物与现实、观众与作品、创作者与叙事行为等诸多二项对立式之间显现出现实主义本身的二律背反,然后又能在其内部矛盾的张力关系中达成对立统一。这正是詹姆逊所揭示的,现实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叙事、一种社会形式诗学的价值及其张力所在。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即人格二重性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极对立统一的关系与联系,也是人物性格自我分化、自我克服、自我统一的过程。有鉴于此,创作者应把握好“美感二重性”的潜在审美规律,避免从以往善恶分明的单一和刻板走向另一种极端“善恶同体”的单一和刻板,在这个意义上,创作者应把握好这个“度”,在塑造人物复杂性性格的审美表达过程中着重处理好主观直觉与客观功利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处理好创作者、作品与观众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也是新时代电视艺术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人民利益作为创作标准,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充盈人民精神世界、鼓舞人民精神追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使命。
二律背反不是单方面的强调矛盾的一方,而是强调在同一性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在矛盾在观念或意义层面存在着的矛盾性,进而思考其融合或者说对立统一的可能性。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来说,由人物性格的二重性带来的作品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实际上牵涉的是创作者与观众的视野融合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部作品的完成、一个人物的塑造都是由两个创造者共同创造的,一个是创作者,另一个是观众,而这就必然牵涉到视野融合的问题。观众对作品的观看、欣赏、接受、评价、反馈本身就是观看者的视野与创作者的视野相互融合的过程。由于读者先在经验结构的不同,这一过程必然导致创作者与观看者在审美视野的心理机制及其产生的审美价值判断上的迥异,当这种迥异发生时,就必然导致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化与顺应的交替过程中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着自身的心理图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也是这样,当他体味了作品意蕴,把作品纳入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时便同化了作品,相反则在顺应作品的过程中逐渐调整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2]冯冀:《制约与提升:创作与接受的二律背反》,《丽水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第23页。观众对反面人物的同情、共情实际上就是作品的叙事结构与观众的经验结构相互融合后在审美心理层面产生的情动反应。这种情动反应由叙事发出,但跟人物性格的二重性不无关联。观众的观看与接受本身即作品被具体化、被经验化、被阐释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意义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接受主体不断产生审美价值判断的过程。且最重要的是:观众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的信息,而是不断地参与到作品信息的生产过程中,正是由于观众不断地介入与观看,并在此过程中将感觉和知觉的经验代入到作品中,而后再通过物质形态作品所产生的知觉系列的总和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观念形态作品即真正的审美对象,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才由此产生。
四、结语:重提一种“毛边现实主义”
演员张颂文在电影《不止不休》路演时表示,在表演里本无“毛边”这个词,但“毛边”带来的不准确性有时恰恰构成了我们生活中最琐碎的点点滴滴的真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准确有时候是不准确,不准确有时候是准确。[1]参见电影《不止不休》路演时张颂文的采访视频,2023 年3 月20 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v4y1V7mv/。表演艺术家唐国强在电视综艺节目《声临其境》中也曾表示,对于表演来说,最可贵的就是“毛边”,而不是撕得整整齐齐,撕得整整齐齐就没了语言的味道。[2]参见综艺节目《声临其境》2018年1月13日视频片段,2018年1月13日,https://www.iqiyi.com/w_19rwc9r7m1.html。事实上,不仅是表演,对于人物塑造以及更广阔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来说,“今天的现实主义,已经走过了对现实被动模仿的古典阶段、追求理性和主动模仿的现代阶段。现实主义,正成为一种状态,一种表现过程的真实状态、一种追求、一种倾向。……由于生活多元化、思维的多层次和人性的复杂化,造就了现实主义典型论的多元化”[3]苏宁:《现实主义与人格二重性》,《江汉论坛》1998年第4期,第55页。。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观念,更是一种审美精神和品格。现实生活有很多毛边,有很多无法抽离出来的本质,因为那种本质一旦抽象出来就不真实了,就不能反映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矛盾性。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不是机械地反映社会的真实,而是要把生活的复杂性表现出来,这其中包括很多毛边,这些毛边往往最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品格,这就要求创作者要下沉到现实生活中去才能对生活本身有新发现。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艺界曾对现实主义展开过热烈讨论,秦兆阳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对教条主义提出质疑,进而倡导现实主义的广阔性与开放性;邵荃麟提出“现实主义的深化、写中间人物”等观点,等等,无不是在倡导“现实主义的毛边”。如今回看,重提一种“毛边现实主义”,对于今日中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而言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意义。诚如秦兆阳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是广阔的、开放的,也是常提常新的,当历史、现实生活已经起了空前的变化的时候,现实主义本身也应该有所发展。[1]参见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署名“何直”。这与法国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在其《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中提出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概念旨归殊途同归,罗氏认为“没有非现实主义的,即不参照在它之外并独立于它的现实的艺术”[2][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现实主义源于现实、反映现实又反作用于现实,但现实主义从来不是对现实机械地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3]参见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署名“何直”。,其对于人物的塑造也从来不是抽象概念的呈现,而是在对生活的新发现中不断注入新的审美感知和具体可感的人性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经英雄人物、中间人物、高大全人物、典型人物等不同时期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论主张,进入新时代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主张在塑造典型尤其是塑造典型人物的复杂性性格上因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暴露出模式化、公式化、概念化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现实主义在中国具体的文艺创作中不断调试其内在意涵、拓宽其自身边界,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反面人物性格塑造上所呈现出的审美新变——更加饱满、立体,更加生活化,更具人情味和毛边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为一种方法的现实主义在其内部实践中不断地升华和深化。其在人物塑造上基于对生活的新发现和对时代的新感悟所呈现出的一种难得的“毛边感”,为当前现实主义文艺创作重提“毛边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示范。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毛边指“经裁剪而没有锁边的布边”[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21页。,百度百科将其解释为“在针刻(DRYPOINT)和雕版(ENGRAVING)中,由针或刻刀在金属板表面刻线形成的粗糙的边”[5]参见百度百科“毛边”一词的释义,搜索日期2023年4月26日,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B%E8%BE%B9/9765105?fr=aladdin。。挪用到中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中,“毛边现实主义”指向一种特定的创制方法与创制倾向,一种特定的审美观念、审美价值取向,一种具有现实生活粗粝质感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和美学风格。在这种美学风格中,现实主义被毛边化、被粗粝化、被生活化,其人物塑造更加饱满、立体,也更具人情味和毛边感,而这种毛边感正来源于创作者通过不断下沉到现实生活并在对生活的新感知与新发现中获得的。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人物塑造上,逐渐从英雄人物向普通人物、边缘人物、底层人物拓展,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逐渐从单一化、扁平化向二重性乃至多重性延展,并由外部行为逐渐向内在精神靠拢、向人性本身难以言说的复杂性靠拢,努力从更具新时代特征的社会环境入手,再现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通过揭示与呈现人物的复杂性性格,表现出生活的本质特征,进而推进现实主义向人性的复杂深处跋涉。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人物塑造上所呈现出的审美新变,不仅反映出其在新时代语境下对现实主义的不断升华和深化,与此同时也将一种更具新时代审美品格的“毛边现实主义”清晰地写在了当代荧屏上,进而使其创作观念不断走向现实生活、走向人民群众、走向社会基层,使人物性格从单一化、刻板化走向立体化、饱满化,从而创作出更具现实生活可感性的典型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