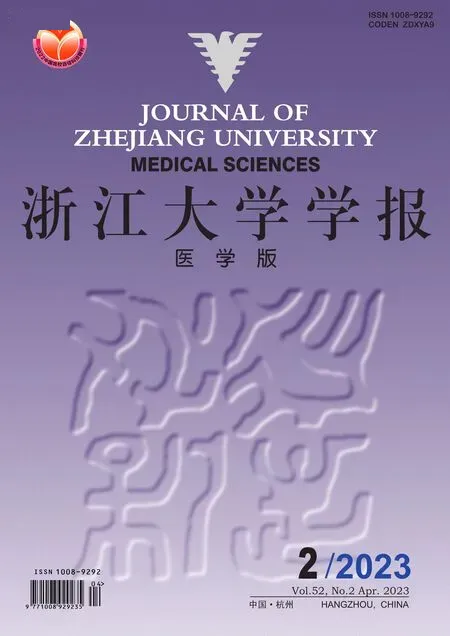855例前列腺癌患者错配修复基因胚系突变临床研究
方邦伟,韦煜,潘剑,张挺维,叶定伟,朱耀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上海 200032
前列腺癌是全球第二大男性肿瘤,且是西方国家发病率最高的男性恶性肿瘤[1]。尽管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较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影响,前列腺癌的发病率正在迅速上升。据估计,2022年我国新发前列腺癌患者将达125 646例,死亡患者将达56 239例[2]。
肿瘤具有遗传易感性,在前列腺癌中尤为突出,前列腺癌的遗传性高达57%[3]。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已经确认近180种导致前列腺癌风险增加的遗传突变,这些突变与约30%的家族性前列腺癌相关[4]。前期研究表明,中国前列腺癌患者有9.8%(31/316)携带DDR基因胚系突变,并且携带突变的患者具有初诊年龄小,对内分泌治疗反应差等特征[5-6]。MMR是DDR的重要机制之一,在维持正常细胞分裂期间的基因组保真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功能的行使主要依赖于MLH1、MSH2、MSH6和PMS2这四个MMR系统核心基因所对应的蛋白产物。MMR基因致病性胚系突变会导致MMR功能缺陷,进而引起林奇综合征的发生。尽管林奇综合征患者以发生结直肠癌和子宫内膜癌为主[7],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类患者发生前列腺癌的风险同样显著上升。如一项大型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携带MSH2、MSH6基因致病性胚系突变的人群前列腺癌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携带人群[8]。
然而,在前列腺癌患者人群中,MMR基因胚系突变的占比相对较低,仅存在于1%左右的前列腺癌患者中[9-10]。有研究表明,MMR基因胚系突变患者是免疫治疗的潜在受益者[10-11]。受限于MMR基因胚系突变在前列腺癌中的罕见性,其在中国前列腺癌患者中该类人群的临床病理特点以及是否与携带其他DDR基因胚系突变的患者存在差异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855例前列腺癌患者胚系突变数据,以期了解中国前列腺癌患者携带MMR基因致病性胚系突变的占比及其临床特征。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回顾性分析855例2018至2022年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诊且病理检查确诊为前列腺泡腺癌的患者(排除病理组织呈神经内分泌分化或具有其他非腺癌特征者)的胚系测序数据。855例患者中,MMR基因突变者纳入MMR+组,携带除外MMR基因的DDR基因致病性胚系突变者纳入DDR+MMR-组,未携带DDR基因致病性胚系突变者纳入DDR-组。临床资料来自随访以及医院电子病历记录系统。本研究方案通过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伦理道德委员会审查(050432-4-1911D)。
1.2 高通量测序检测基因突变
通过基于目标基因区域捕获方法的二代测序技术平台Illumina Novaseq 6000 [莲和(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检测患者基因突变情况。提取患者外周血中的白细胞DNA后进行基因测序,测序深度约为200X,纳入分析的突变形式为点突变和插入/缺失突变。将突变丰度大于1%的突变纳入后续分析。纳入分析的目标基因包括MLH1、MSH2、MSH6和PMS2等MMR基因,以及ATM、ATR、BRCA1、BRCA2、BRIP1、CDK12、CHEK2、FAM175A、FANCA、GEN1、MRE11、NBN、PALB2、RAD51C和RAD51D等除MMR基因外的DDR基因。
1.3 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突变基因的致病性
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遗传分类标准[12]判断胚系突变的致病性。对于意义不明的突变,进一步通过Clinvar数据库[13]和Intervar数据库[14]对突变进行注释。
1.4 去势抵抗的定义及诊断标准
将使用去势治疗后血清睾酮达到去势水平(50 pg/mL或1.7 nmol/L以上),PSA超过2 ng/mL且PSA 相隔1周连续3次上升,2次较最低值升高大于50%或发生影像学进展的患者定义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R语言(4.2.1版)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法检验。使用Kaplan-Meier法评估各组对去势治疗的反应,使用survminer包的pairwise_survdiff函数比较各组对去势治疗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因检测结果
855 例前列腺癌患者中,13例(1.52%)患者纳入MMR+组,其中MLH1基因突变1例,MSH2基因突变6例,MSH6基因突变4例,PMS2基因突变2例,其中1例患者在MSH2基因上存在2个不同的致病性突变位点(表1和图1),MMR+组中未发现同时携带其他DDR基因致病性胚系突变;105例(11.9%)患者纳入DDR+MMR-组;737例(86.2%)患者纳入DDR-组。结果提示,MMR基因胚系突变在中国前列腺癌患者中的整体发生率较低。

图1 错配修复基因的致病性以及可能致病性的胚系突变Figure 1 Germline pathogenic and likely pathogenic mutations in mismatch repair genes

表1 13例前列腺癌患者错配修复基因的致病性/可能致病性突变位点Table 1 Pathogenic/likely pathogenic mutations in mismatch repair genes in 13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2.2 不同突变状态的前列腺癌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与DDR-组比较,MMR+组患者初诊年龄小(P<0.05)、PSA水平低(P<0.01),而在格里森评分和TMN分期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DDR+MMR-组与MMR+组、DDR-组间临床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结果提示在早发、初诊PSA水平低的前列腺癌患者中,MMR基因胚系突变的发生率可能较高。
表2 不同突变状态的前列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比较Table 2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mutation carriers and non-carriers(±s或n)

表2 不同突变状态的前列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比较Table 2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mutation carriers and non-carriers(±s或n)
与MMR+组比较,*P<0.05,**P<0.01.#9例DDR+MMR-患者和53例DDR-患者由于在病理活检前已经接受了去势治疗,导致无法评估.MMR:错配修复;DDR:DNA损伤修复;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组 别MMR+组DDR+MMR-组DDR-组n 13 105 737诊断年龄(岁)61.5±6.41 64.6±7.68 66.6±8.01*格里森评分(≥8分/<8分/未知)#9/4/0 81/15/9 549/135/53 TMN分期M0/M1 4/9 30/75 299/438 N0/N1 3/10 25/80 261/476诊断时的PSA(<20 ng·mL-1/≥20 ng·mL-1/未知)7/6/0 25/65/15 137/531/69**
2.3 不同突变状态的前列腺癌患者达到去势抵抗状态的时间比较
MMR+组、DDR+MMR-组和DDR-组进展至去势抵抗阶段用时的中位数分别为8个月(95%CI:6个月~无法估计)、16个月(95%CI:12~32个月)、24个月(95%CI:21~27个月),其中达到去势抵抗状态的时间MMR+组较DDR+MMR-组和DDR-组明显缩短(均P<0.01),而DDR+MMR-组与DDR-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结果提示传统内分泌治疗药物可能对携带MMR基因胚系突变的前列腺癌患者疗效欠佳。

图2 不同突变状态前列腺癌患者达到去势抵抗状态的Kaplan-Meier曲线Figure 2 Kaplan-Meier curves of time from castration therapy initiation to castration-resistant
3 讨 论
尽管MMR基因胚系突变在前列腺癌中较为罕见,但该突变的检测对于患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携带DDR基因胚系突变的前列腺癌患者具有高度恶性的临床表型[6],而MMR基因突变作为DDR基因突变中的一个特殊亚群,这类患者是否具有独特的临床特征仍然缺乏相关数据的支持。本研究探索了855例前列腺癌患者中致病性MMR基因胚系突变的发生率,并对携带不同基因突变类型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前列腺癌患者中MMR基因胚系突变率为1.52%,以MSH2基因突变为主,致病性突变形式主要为截断突变(包括移码突变和无义突变)。MMR基因突变患者平均确诊年龄显著低于未携带DDR基因胚系致病性突变患者,且该类患者初诊时PSA往往不高却多数已发生肿瘤转移。更重要的是,与携带MMR基因外的DDR基因胚系致病性突变患者和未携带DDR基因胚系致病性突变患者比较,MMR基因突变患者对去势治疗的反应更差。这些结果提示,对于发病年龄早、初诊PSA水平不高却已经发生转移以及对去势治疗迅速耐药的患者应考虑进行MMR基因的胚系突变检测。
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癌症治疗方式,已经在许多实体肿瘤中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5]。然而,在未经选择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中,免疫治疗收效甚微[16]。携带MMR基因胚系突变不仅仅与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且接近1/2的MMR缺陷型前列腺患者能够从免疫治疗中获益,部分患者在接受免疫治疗后还可获得长期缓解[10-11]。因此,识别该类患者对于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精准筛选免疫治疗获益人群具有重大意义。此外,一些研究表明,一些关键基因的突变位点、突变形式同样能对免疫治疗的疗效产生影响,在MMR基因突变前列腺癌患者中是否也存在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17-18]。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①病例来源于单中心,样本量有限,且因MMR基因胚系突变在前列腺癌中占比较低而致本研究中MMR基因突变患者数较少,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②以往研究表明,在转移性前列腺患者中DDR基因胚系突变率显著高于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分别为18.18%和5.97%)[19]。本组病例中格里森评分8及以上的患者占80.5%,初诊转移患者占60.9%,初诊PSA水平为20 ng/mL及以上的患者占80.0%,可能导致DDR基因包括MMR基因胚系突变患者占比升高,因而影响MMR基因胚系突变与前列腺癌高危临床特征关联的分析。
综上所述,中国前列腺癌患者人群中MMR基因的胚系突变发生率约为1.52%,发病年龄低,对去势治疗反应差提示其可能携带有MMR基因胚系突变。鉴于MMR基因突变患者是免疫治疗的潜在获益人群,对发病年龄在60岁及以下或对去势治疗早期耐药的前列腺癌患者人群可以进行MMR基因检测或MMR蛋白肿瘤组织免疫组化染色检查以帮助临床决策。
志谢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172621)支持
Acknowledgments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2172621)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Conflict of InterestsThe authors declare that there i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e author(s) 2023.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ND 4.0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