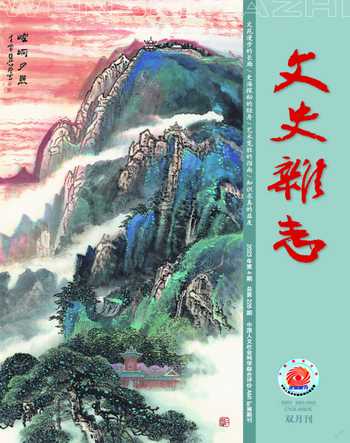裴斐先生印象
摘 要:裴斐先生是当代颇有建树的文学理论家。笔者与他交往十余年,其学者兼长者风范至今历历在目。他对故乡成都饱含深情,对成都美食萦怀在心。其代表作《文学原理》浸润着先生的坎坷人生经历和真知灼见。
关键词:李白研究;成都美食;《文学原理》;福所倚之
裴斐先生(1933—1997)是我所认识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中过从较多、文字交往较为密切的长者。他为人端直耿介,和霭可亲,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亲切、真诚,令人难忘。
我与裴斐先生相识于1985年的春深时节,那是一次在安徽马鞍山市举办的中日李白诗词研讨会上。时令既是春夏之交,与会地点又是江南风景胜地。与会者乃中日双方研究李白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的人数不多(五十人左右),规格却高。其时我以学术刊物《天府新论》的责任编辑身份忝列会议。
会议期间,我分别拜会了诸专家,与他们建立了较为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北大教授王瑶,是我年轻时就从学术刊物中获知的著名学者。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陶渊明集》就是由王瑶先生编注的,是我案头经常研读的书籍之一。王瑶先生学识卓越,见解精当,注释简明扼要,行文精审,可谓要言不烦之典范。此次研讨会期间,我与王先生朝夕相处,时或交谈,且向王先生请教问学。王教授用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平易而霭然地为之解答。我就南北朝文学向王瑶先生请教颇多,并表示读了他编注的陶集之后,对陶渊明兴趣渐浓。王先生则说,他近年来主要精力放在现代文学方面;并对我讲,如有兴趣,多读陶诗文是很好的,王瑶先生的教诲,我始终铭记在心,也是我后来完成《陶渊明悬案之谜》的内在动因;展衍开来,也是我撰写二谢(谢朓、谢灵运)等文章的缘由。
复旦大学的王运熙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朱金城编审、西北大学的安旗教授、中国社科院的乔象钟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的郁贤皓先生,都是我联络请教的学者、专家。有些琐事趣事,似可一述。安旗原为四川省作协的著名作家,丈夫戈壁舟也是名噪当时的作家,“文革”后调往西北工作。安旗教授执教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是一个干练、精明、口若悬河的学者、作家。她在四川工作期间,我在四川作协听过她的讲演。我向她请教、问好并约稿,她友好地表示接受。我对安先生说,你很像我的堂姐。安先生微笑回道,你就认我作姐吧!乔象钟先生见过我几次面,她说老是记不住我的名字。幽默风趣的安先生对乔说,他的名字很好记:“王定璋,天下的文章由他来定。”说罢,大笑起来。
日本学者松蒲友久、松原朗、山田胜久、中岛敏夫、坂井健一、佐藤一郎等人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从各个方面探索李白的行实及诗文创作,引起了与会者兴趣。
我在与裴斐先生的交谈中,得知他是四川成都人,彼此感兴趣的话题自然也就丰富、生动得多了。虽然他早在1951年就负笈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然而故乡人情习俗、人文故典、美食风景、坊间掌故依然令先生记忆犹新,印象美好。
裴先生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李白与魏晋六朝诗人》(载《会议论文集》),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李白与魏晋诗人的关系。这是我很感兴趣的课题。(1984年,我撰写过一篇题为《李白与六朝文学的渊源》的文章。)
会议后,我与裴斐先生就唐代诗歌、唐代文学、唐诗繁荣文化条件,盛唐文化、盛唐气象诸问题有过较为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对于盛唐气象的探讨,交流较多。裴先生的见解很独到。他不认同林庚先生在《诗人李白》一文把李白视为“盛唐气象”的最典型的代表的观点。裴先生指出,李白对自己所处时代具有清醒的认知,并非一味歌颂盛世,而是看透盛世背后隐藏的危机。裴先生之论颇具识见,新人耳目,令我受益良多。
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曾出现较为强劲的古代文学研究热潮,学术研讨会议也很活跃。专家学者各自拿出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互相交流、討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与学术界的名流晤面聚首也相应频繁。1985年初冬,四川省李白研究会隆重成立,研究会邀请了全国知名的李白研究专家近百人参加了会议,裴斐先生也出席了。我与裴先生重逢叙旧,相见甚欢;随即向裴先生请教一些问题,并把我对唐诗繁荣的原因的几点构想(简而言之,是唐代开放性的社会形态背景下的思想解放)与他交流,得到他的肯定,并鼓励将之结撰成文。尔后,我循此完成了《唐诗繁荣原因新探》一文,发表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上,旋即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庞朴等人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创刊号摘登了此文。
不久,安徽省马鞍市酝酿成立中国李白研究会,我又与裴斐先生再度聚首于马鞍山。德高望重的河北大学詹锳教授任会长。他那两本研究李白的力作《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论丛》奠定其在李白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裴斐先生在李白方面的学术著作《李白十论》《李杜卮言》及《李白选集》以及系列研究李白的文章,在学术界反应良好,因之被选为副会长。自此之后,每届李白研讨会的学术活动,都是我与裴先生晤面请教的良机。
值得一叙的是1987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讨会。参加此次会议的专家学者阵容可观,主办单位乃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学评论》编辑部、杭州大学《语文杂志》以及《天府新论》杂志社。我因此得以参加会议的筹备诸事项。会议间隙,我与裴斐先生漫步西湖,泛舟绿水,互道契阔,交流信息。裴先生在大会发言中,论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士的人文品格和理想人生目标的构建,给人印象较深。他对作家的品格和个性展现等问题,见解独到。他不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很讲究“中庸之道”的观点,指出“中庸”的思想反映在文艺观上,是提倡“中和之美”;认为文艺作品是作家个性展示,不是情理中和,而是不平之鸣,如此等等。会议上的思想碰撞激烈、学术争鸣之情况可见一斑。
杭州会议之后,我与裴先生联系渐多。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春日,裴先生回成都处理一些家事,我俩得此再次相聚,地点在距他居住地东二巷不远的白果林茶园。这里环境不错,实为成都闹市中的一方幽静小地,距《天府新论》编辑部较近,彼此都很方便。裴先生选定于西玉龙街之陈麻婆豆腐餐厅进午餐,彼此边聊边小饮。裴先生钟情于成都美食,对“陈麻婆”的菜品赞不绝口,足见其乡愁深植,情怀难忘。
此后,裴先生参加西南地区的学术交流或讲学、研究生论文答辩等活动,时或于成都停留,于是我与裴先生见面茶叙、小饮是必不可少的;而我参加东北、华北地区的学术会议,或取道北京,都会麻烦裴先生。他热情好客,真诚爽朗,令人有居家般的适意与自然。这也是我每次旅京常去先生家的缘故。只是后来,先生投身学术研究工作繁忙,焚膏继晷般地投入写作,并向我表明他正在忙于杜甫诗文的分期研究。即或如此,当我辞别先生返蓉之际,他也要与我餐饮小叙。由此足见先生对故乡人是一往情深。
先生每有著作问世,均赐寄于我。《李白十论》《诗缘情辨》都先后由裴先生题记。其《文学原理》不仅赐寄给我,还嘱我最好能写个书评。我认真拜读之后,撰就一篇论文,即《一部闪耀着睿智和真知灼见的专著——简评裴斐的〈文学原理〉》。
此文提及裴先生曾告诉我,他是从文学创作开始与文学事业结缘的。至于他以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姿态为学术界所熟知,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近十余年来的事情。
他的《文学原理》顾名思义,当然是研究文学的本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以及创作规律等方面的理论。当我细加披阅之后,以为此书与过去汗牛充栋的从形而上把握文学的基本理论的专著有很大不同:它浸润着裴先生的坎坷人生经历和真知灼见,诚如他的老师吴组湘先生所谓:“满纸都有你的血肉的真知灼见,所持的论点往往入木三分,一語破的,说得那么斩截、明确、稳靠而有分寸。”
我认为此书见解深警,阐释透辟,逻辑严谨,行文简洁而流畅。具体而言,当有以下特出之处,值得关注。首先,作者指出,研究文学必须重视文学自身规律,强调文学理论应当联系实际,关切人生。尤为要紧的是,须把握文学的本质,认识文学规律;与此同时,必须懂得人生,联系现实,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概念推演与逻辑判断。这样始可形成自己的见解,有益于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其次,对文学规律的重视,是此书极为鲜明的特征。作者对现代反映论的剖视,对文学创作个性化的强调,对作家品格与才能的确认和对作家保持心灵的自由与积极人生态度的赞扬,以及对作家在艺术构思中把握特殊性的重要意义的揭示等等,无不说明了作者对文学理论的深刻领悟。在此基础上,裴斐认为:“任何作家的创作,从本质上说,都是写历史,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历史。”这实际上告诉人们,文学与人生的关联密切。
复次,作者异常重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个性特征。这是十分必要的。作者讲,文学的对象是人生,文学作品是写人的;质言之,文学人来写,写给人看,每个人又是自具面目,各不相同。因此,无论文学本体论也好,创作论也罢,批评(鉴赏论)也好,均须以承认差异即尊重人的个性为前提。为此,作者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此处特指文学创作)进行了比较。裴先生指出,物质生产需要合作,体现的是共性;而精神生产强调个体,尊重个性。试想,一部文学作品失去了个性,那将是没有存在价值的废品。“个性是艺术的灵魂”,实为至理名言。
在与裴先生的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他耿介刚毅的个性和深湛精审的学术眼光,是他对文学理论的准确把握和个性化的发挥。这在其所撰《文学原理》中即有生动的展现。文学原理中有些问题深奥难明,但是很多道理又是文学常识。裴先生深入浅出的论述,不仅免除了枯燥乏味般的推演,而且令深奥的理论平添诱人的魅力。他从具体事例、文学现象切入理论,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层层深入,渐次展开,行文浅近,阐释透辟,剖析精到,结论明了。例如他讲文学作品的产生,“就像养活孩子,绝非单方面能办到,除了生活的客观,还有作家的主观,二者结合所产生的结果亦绝不是只反映一面,而必须反映两方面。作者坚信真理永远是朴素的,简赅明确的,如果不能对真理作出浅显的表述,多半是自己还没有认识清楚的缘故。”裴先生在阐述较难把握的审美情趣时,就举出繁星满天的宁静夜空和达·芬奇《蒙娜丽萨》两个具体事例来展开论述,深入浅出,便于理解。
此外,裴先生把中国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并以之与西方文学理论与创作相沟通,再予以比较,进而阐明了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譬如他讲,西方文论的模仿说属于再现论,强调客观;现代主义属于表现论,强调主观。中国言志(缘情)说属于表现论,亦强调主观。西方的再现论与中国的表现论都是建立在对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上,但中国文论重直观,较之重思辨的西方文论和美学而言,显得缺乏系统性,但更准确可靠。
裴先生的这些见解,除了与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学养有关外,更与他曲折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联。裴先生少年即崭露头角,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年甫21岁便留校任教,在著名教授王瑶指导下,从事现代文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并开始其古典文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时有“北大才子”之誉。
1958年,裴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在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被迫停止。此后,他从事体力劳动二十载,做过泥瓦匠。1979年其“右派”得以改正,旋即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重新开始教学科研工作。这段人生经历,加深了裴先生的人生体悟,使其于文学研究中,避免了从理论到理论的肤浅说教,学术认知水准得以升华,视野已然宏阔。裴先生后来成为一代大家,成就斐然,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可谓“福所倚之”。
谨以此文,聊表对先生旧情的怀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