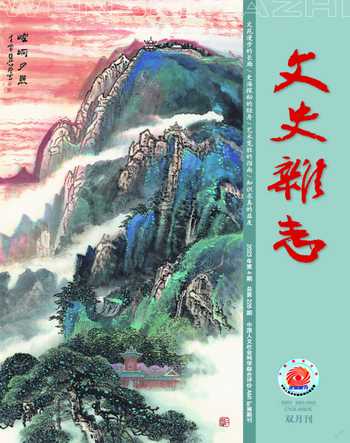“丑书”别议
摘 要:
“丑书”的出现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并非当代书法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然而,却已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其中,旨在致力于书法发展探索的“丑书”实践,若能谙熟并践行书法发展基本规律,则可能建构传统;同时,成为中华民族“美丑兼审”思维方式与认识特征的一个实证。
关键词:
书法;审美;审丑;建构
“丑书”已成为当代书法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当代“丑书”之争,关涉书法传统与现代的对接、现代书学体系的建构等问题,这些都是当前书法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故此,考量“丑书”,需要立足书法本身。而这亦可有助于人们对书法传统及其美学观念的全面体认。
“丑书”并非某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书法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几乎都有“审丑”实践。在书法书体演变过程中,甲骨、金文、帛书、简牍、碑碣等,给人质朴印象,亦都有未尽“中和”之处。东晋王羲之兼精诸体,融通文人书法与民间书法之特征,提纯总结,“俱变古形”,并去“平划宽结”之体,而取“斜划紧结”之势,于万千姿态中既得平和秀逸,亦得欹侧跌宕。其子王献之所书势态则趋奇峭、瘦挺而外拓,相较其父蕴藉更为飞动峭拔。唐代颜真卿得篆籀笔意。其成熟时期楷书复有“平划宽结”之态,质朴敦厚,变革成法,别出一格;行草书初师“二王”,却绝去姿媚气息,尤是点画狼藉、参差多变者,率真烂漫之中颇显沉雄之气,意味杂陈,颇为特殊。宋人米芾之书“胜在姿”,“徘徊晋唐之间”而成面貌。其行书尤得“二王”欹侧跌宕一路之精髓,用笔“八面出锋”,体势欹侧灵动,布局疏密错落。后人学其书,怪异其形,而开“尚奇”之门。可见,“审丑”之风亦有其“帖学”根源,并非清人发掘“碑学”之独力所致。
从书法本身来看,无论是“求平正”,或是“追险绝”等,都是书法美的体现,审美意义上的“丑感”也不例外。不过,我们面对的“丑书”,是丑在形式,或是丑在形象,需要作以辨别。在书法艺术中,形式与形象是不同概念,形式语言通过有机组合与塑造产生形象。而且,书写形式无论美丑,如果塑造出的形象本质上是真、善、美的,便具有了艺术的基本特质;否则,即失去了谈论书法艺术的意义。也就是说,形象性是构成书法艺术性的基本特性,对汉字的书写形式要被称为书法艺术,其必须具有形象性——一种鲜明的、生动的、情感化的、包孕内美的典型性。当然,对书法形象性的塑造是需要熟练的技巧能力与个性化的笔墨形式来实现的,而熟练的技巧与个性化的笔墨形式则需要精神修养来滋养。值得注意的是,书法笔墨形式本身也可以具有形象性,同样可以呈现典型性,成为书法审美的内容。从而,从书法本体来看,书法的美,或者说书法成为艺术,既有精熟的技法形式,更有富于生命意味的形象。[1]二者共同呈现着创作主体的精神风貌与人格气质。而这也是当代“丑书”实践在积极探索中所不懈追求的。
可以说,书法之美,正是人们在汉字书写中,不断塑造各种可能形象时形成的。并且,人们以一种美界定另一种美时,丑便产生了。而美与丑本来就同属观念范畴。“审丑”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与“审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亦即,中国人的美学观念是“美丑兼审”的。而且,其所谓的“丑”实际是具有内美的“丑”,“审丑”实际是审视内在精神之美、生命力量之美。笔者于拙文《书法“丑书”现象再认识》[2]中曾对此作过初步阐释,并对书法发展过程中的“审丑”现象进行了一定探讨。据其所论,当人们非要对书法史上或是当代某些书法现象以“丑怪”论之,或许透过它们,人们可以获取的正是蕴涵着内美的消息。譬如文中所及书法演进中被认为与“审丑”相关的书家里,颜真卿之宽博雄放与傅山之人格抒发的浪漫风格;杨凝式与宋人以主体精神求书法“意趣”的刻意探索;元代隐士书家与清代“扬州八怪”抒发生活感受的文人精神境界;当代书家以天真朴拙之形式感显示其独立个性的书写态度;等等,都是他们对书法传统、时代内涵、生命状态的体悟,以此彰显出他们的精神追求与气格内质。
书法作为一种可以达情性、形哀乐的艺术形态,是有自我规定性的。书法艺术不是也不可能是任意式的自由存在。而且,正是书法艺术的自我规定性即它自身的规制性和规律性,才使其产生美,并在符合规律中不断吸收、借鉴,以探索自身的更多可能性来丰富美、发展美。汉字是先辈仰观俯察天地万物、感悟自然生命运动规律而得。汉字在产生时已被赋予生命形构之理,已是有主体潜在审美意味的形式。汉字的符号形式一经确定,其自身结构的规定性也就随之确定。而书法必然需要遵循汉字的基本结构,否则,基于汉字所书写的形象将可能呈现出边界化特征。书法艺术的自我规定性就是汉字形体构成的规制性及其书写规律,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可识读、可审美。而“丑书”是真意于书法本身时,也往往于书写规制中通过怪逸其形,试图突围既定思维与已有程式;或是力求践行“无意”“天趣”“大巧若拙”“大朴不雕”等观念,以追求意趣,呈现出汉字构造在书法意象化后的多种可能性。其可以扩大审美视野,丰富审美经验,从而为当代的人们提供更宽的书法艺术探索路径。这里,文字学基础是其基本保障。同时,书法艺术的探索亦更需要生活感受的支撑;如果停留于形式层面,徒有形式,则易于迷失方向,陷入真丑泥潭。书法最终还是必须塑造出个性化的生动形象。而“外师造化”,师法古人,感悟于生活又深味传统,“中得心源”,基于此塑造出的书法艺术形象方更为可靠。
如同其他艺术,书法的发展需要面向生活在多元中进行。而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它的必然性、合理性,包括“丑书”概念的提出,以及作为艺术现象而形成为当代书坛的一种艺术潮流。但是合理性的存在,是否能够造就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结果,则是另一回事情。这依赖于实践者的把握和洞察,也依附于时代的需求与宽容。二者无论谁走偏,都将使其失去应有的价值与意义。可见,“丑书”的发生有书法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亦是有其接受论根源的。书法新思想、新潮流的出现,因其对时下而言具有“陌生感”往往会招致排异现象。如果这种“陌生感”与当时人们的审美经验存有合理范围的共识区,将会被那个时代认同;如果相去甚远,将被排斥。书法发展史中,有些书法现象被认同为美,有些则被排斥为丑。但是,被排斥并非意味着其毫无价值。因为一切事物与观念都是发展变化的,随着人们在实践中认识美的经验不断丰富,那些被排斥者,或可能是最具价值者。
其实,对于书法,人们总是从自身形成的既定立场去审视。人们在积极获取书法史信息的过程中,已经受到以往历史上一代代书法史学家与理論家的艺术观念与审美经验的影响,使自己形成独特的审美意识与态度,以用于对书法美与丑的体验与判断。即使人们可以在对书法的摹写中倾听到来自那个时代的生命脉动与心灵颤音,从而可能更为真切地体认书法传统,也仍然无法完全以书法作品产生的当时的时代的眼光去评判。或许因此,人们错过了更为客观的视角。历史地看,亦正是在这种错位中人们逐渐建构并明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与意识取向。而且,基于此的艺术演进最终建构起中国书法“碑学”“帖学”两大传统。面对这两大传统,如何继承与出新,于右任、沈尹默等前辈在他们的时代已经做出了榜样。然而,在书法更为注重艺术性的今天,复杂的文化思想氛围使书法的当代与传统对接存有许多问题;对书法现代美学体系去如何建构,亦有着众多争议。或许,无论回眸传统,还是面对当代的各种书法现象,对于旨在致力于书法探索者,所谓“审美”或“审丑”,本就无须在意。而如今,为了更有意义地出新,要建构适应当代的时代特征的书学观念,就必须广泛而积极地继承传统,使艺术探索途径的多元化可以成为常态。何况书法发展的历史也已证明:当某种书法现象能够符合书法发展规律、契合时代特征、感悟人类性情时,它就最终会建构传统。
注释:
[1]陈方既:《从“丑书”的观赏说起》,《中国书法》2014年第6期。
[2]李朝晖:《书法“丑书”现象再认识》,《书法》2021年第8期。
作者:硕士,从事书法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