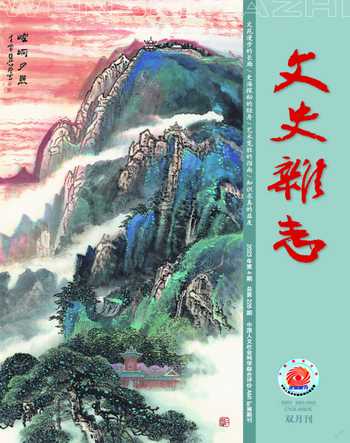为“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点赞
李绍先
摘 要:李殿元先生提出的“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是至今所见关于“成都”的来历和涵义最清晰的表述。史有明载,对“成都”而言,公元前311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之前没有成都城,也没有“成都”这个名称。张仪、张若新建的命名为“成都”的这座城,不仅只能由占据蜀地的秦统治者来命名,而且他们所命名的名称还应该体现其渴望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成都”两字必定是中原文字,其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当然是中原文化。对“成都”两字的理解,必须按照中原文化去认识。“蜀学”的兴起和渊源,与秦对蜀地的统一,与“成都”的涵义是“走向成功之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它为“蜀学”在宋代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千年古都;统一全国战略;走向成功之都;蜀学兴起
最近一段时间,李殿元先生经过长期研究而提出的“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为成都这座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之名称的来历和涵义理清迷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1]李先生采用三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文物考古、口传资料,辅以语言学、文字学、比较学,对成都上下数千年的相关历史记载、文化事件、社会问题予以整饬剖判,条分缕析,并将它们置于人类文明长河以及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大格局中进行观察、审视,从而使其论证依据充分,张弛有度,要言不烦,直击肯綮。其结论虽独辟蹊径,却基本在理。在为李先生所论点赞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思考与认识,写在这里,算是对“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种观点的支持吧!
一、公元前311年对成都的重要性
对“成都”之名的来历和涵义而言,公元前311年无疑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性。
《华阳国志·蜀志》说:
(周)赧王四年,(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2]
这里的周“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是公元前311年,说得上是确切的证据。即是说,秦军于公元前316年征服古蜀国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建立管理机构,驻扎军队,需要城垣了,所以秦统治者在公元前311年新建了成都城,与成都城同时兴建的还有郫城和临邛城。
这说明,在公元前311年以前,没有成都城,否则就不是新建而是重建。
从张仪、张若修成都城的艰难性也可证明在公元前311年以前没有成都城。
东晋史学家干宝编撰的《搜神记》卷十三载: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3]
除《搜神记》外,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都有关于成都号“龟城”的记载,其中《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载:
《九州记》曰:益州城初累筑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因其行筑之,遂得坚固,故曰龟城。[4]
成都之所以产生“龟城”的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成都在当时建城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按史书所说,古蜀国时期曾经“移治郫邑,或治瞿上”,甚至还“徙治成都”,但可以肯定,那时并没有成都城,因为在李冰“开二江之前”的川西平原完全不适合修建城垣。众所周知,由岷江、沱江冲击而成的川西平原就是水洼地,李冰之所以要“开二江”,就是为了排涝,彻底解决川西平原的土质松软问题。所以,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后详),故郫本在九陇。”[5]又说:“蜀王世,成都平原之冲积土部分犹洳湿,故营邑皆在赤土浅丘上,郫、新都、广都、成都皆然。”[6]
因为川西平原低洼潮湿,土质松软,所以张仪兴建成都城必须取土填埋,《华阳国志·蜀志》对此记载说:
(成都)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龍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4]
尽管取土填埋,仍然因为当时的土质太松软,故而修建中的成都城屡筑屡颓。虽然秦国国力强大,仅“一月余”就可征服古蜀国,可是新建成都城却花了太多时间,足证其过程存在太多困难。后来不得已而为之,只能立基础于高亢之处。结果不仅历时九年,还因为随地形而修建的原因,故造成城墙非方非圆,南北不正,其形状就像是一个乌龟,所以古代的成都就被称为“龟城”。因为是“龟城”,有人便杜撰了“神龟示迹”的传说。这样的传说,其实客观反映了成都建城所经历的艰难过程。
所以,对成都来说,公元前311年非常重要,在此之前没有成都城,也没有“成都”这个名称。
说公元前311年才有成都城和“成都”之名,影不影响成都作为“中国十大古都”中早就有了的“千年古都”的形象?不影响!因为,从新津宝墩、温江万春鱼凫、广汉三星堆以及大邑、都江堰等地均发现有古蜀人在4500年—3000年前的古城遗址,证明成都平原在当时是严重的水洼地,不宜修建城池,故古蜀人已建都城都不可能长期存在,而不得不经常迁徙,屡次新建都城。最后由秦人修建的成都城是因为有了“二江”排水,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蜀地都城不断迁徙的问题。新津宝墩、温江万春鱼凫、广汉三星堆等古城,与成都城是一脉相承的成都平原上的“千年古都”。
二、谁能为张仪新建大城命名
秦军是在公元前316年由张仪、司马错统领征服古蜀国的,其后在此地设立蜀郡。张仪、张若是秦国先后派往蜀郡的郡守,并由他们新建了“周回十二里,高七丈”,[7]与秦国国都咸阳同样大小,在当时确为大城的蜀郡首府。
张仪、张若新建的这座城,该谁来命名?当然只能由占据了蜀地的新统治者。
秦军之所以要征服古蜀国并将其纳入秦国版图,是因为强盛起来的秦国制定了统一天下的大战略。
关于秦统一战略第一步的决策,《战国策》记载得最为清楚: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司马错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8]
司马错认为,张仪提出的“攻韩劫天子”之策,会遭到社会“恶名”,东进远不如先南下,南下伐巴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远比“攻韩劫天子”更具有战略意义。从战略地位说,获得巴蜀后,蜀地可以水路直接通于楚,加之巴人勇猛善战,可以从水路攻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从物资方面说,蜀地非常富饶,得其地即可解决攻楚需要的各种军用物资;更何况,此时“师出有名”,因为蜀国正与苴、巴二国失和,战端蜂起,南下蜀地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可避免诸侯警觉。司马错的战略构想非常完善,故得到了秦惠王的批准。
司马错、张仪率秦军攻蜀,很快就获得成功。秦统一巴蜀后,不仅移大量秦人于蜀地,强行改变蜀地的居民主体,奠定牢固的统治基础,而且还强力将秦国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推行到蜀地,仅几年时间就将巴蜀之地打造成了秦国后方根据地,由此不断向南向东出击,逐步推进秦帝国的统一大业。
秦国在蜀地推行的政策中有郡县制,设立了蜀郡,并在蜀郡之下首先设立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分别新建了这三个县的三座城池。蜀郡首府在成都,成都城的修建居然是按秦国国都的标准进行建设,足见秦统治者对实施秦统一战略后首先纳入秦疆土的蜀地的重视,并渴望以此为开端,迅速结束战国纷争的混乱局面,完成统一天下的战略规划,实现大一统。
所以,張仪、张若新建的这座城,不仅只能由占据蜀地的秦统治者来命名,而且他们所命名的名称一定不会体现古蜀文化因素,只会体现他们渴望统一天下的战略意图。
众所周知,张仪、张若新建的这座城,最终的命名是“成都”。
三、“成都”两字的涵义
关于“成都”这个名称的涵义,在成都博物馆的古蜀史部分有专门的介绍,共有十种说法。其中只有李殿元先生是主张“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以后,其他均认为“成都”得名与古蜀有关,甚至是在古蜀时期就已经存在。
这就很奇怪了。秦统一古蜀后,强力推行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各项中原制度,大量考古发掘也证明是在此时以后蜀地才开始有了中原文字。虽然古蜀曾有过辉煌的文化,但是,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古蜀文化包括可能存在过的古蜀文字已经灰飞烟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新产生的“成都”这个名称,不去使用中原文字来体现中原文化涵义,却偏要使用被秦征服了的,已经放弃了的,与中原文化、文字完全不同的古蜀文化,为他们千辛万苦才建成的新城池命名,当属匪夷所思。我们看“成都”这个名称,其所体现出的中原文化的涵义是那么坚强有力、清晰明白——那里面并无古蜀文化的影子!
“成都”的“都”字,按中原汉语涵义,结合语境,自是“大城市”无疑。
“成都”的“成”字,是认识这个名称的关键。汉字是多义字,一个字往往有多重涵义。研究远古历史,当然不能仅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之类对汉语“现代”用法的释义,而必须使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汉语言文字工具书。李殿元先生说:
“成都”的“成”字在古代不是这样的写法,翻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就知道,它比现在多一划,是由“丁”与“戈”所组成,所以,《辞源》释“成”字就有“……四、和解,讲和。……五、平服、平定。……六、必、定。七、并。”这些释义,显示出由“丁”与“戈”所组成的“成”字的强势意蕴。兵丁、刀枪等在军事方面的意味非常明显,而平服、平定、并合等字眼说的就是秦征服古蜀的事实。
秦攻占巴蜀,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最早实施。设立蜀郡、成都县,修建成都城,也是秦统治者所确定并实施的。那么,他们为这个新设立的县、新修建的城取名为“成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成都”这个名称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意味,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吻合,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应该就是“成都”之名的来源及其涵义。[9]
这是至今所见关于“成都”来历和涵义的最清晰最正确的表述。
为什么说成都自此“走向成功之都”?
因为秦对古蜀的统一,使古蜀文化湮灭了,只留下少许经过中原文化改造的传说和丰富的、考证有难度的地下文物,这可以说是古蜀文化的不幸。但是,秦对古蜀的统一,让蜀地首先加入“大一统”,接受更为先进的各项制度,并因作为秦之统一全国战略的后方基地而加大加快建设,先后打造出成都城、都江堰、文翁石室等标志性工程,让蜀地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进入到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并“走向成功之都”,乃至呈现出“扬一益二”的趋势,这又是古蜀之地的大幸,也是“统一全国战略”的大幸。
四、“成都”为蜀学兴起奠定坚实基础
在宋代,由苏洵开始,由苏轼、苏辙、张栻、魏了翁等一大批有共同思想基础、共同学术倾向的著名理学家,在巴蜀之地及巴蜀以外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彰显了蜀地厚重的学术成就,形成时人所称的“蜀学”。蜀学的影响,不仅在蜀地,更是走出巴蜀,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学派,堪与齐鲁之学、关学、洛学等著名学派相颉颃。
不过,就蜀学的渊源而言,必须承认,它与秦对蜀地的统一,与“成都”的涵义是“走向成功之都”,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可以说,它们为蜀学在宋代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换言之,秦统一古蜀与设立蜀郡、成都县的举措,推动了蜀地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酝酿、产生了蜀学。
不可否认,在秦统一前的古蜀之地,早就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优秀传统,对知识与文化人都非常尊重。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10]传说嫘祖是西平(今四川盐亭县)人,因为她教民养蚕缫丝,所以被祀为神。
《华阳国志·蜀志》说:“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11]古蜀王杜宇传授农耕技术、督促农耕生产;古蜀王开明治理水患,使人民方便生产生活。杜宇、开明因此被蜀人尊为望帝、丛帝。蜀人为感谢他们的教民功勋而建庙立祠,郫县望丛祠就是实证。
《汉书·艺文志》说:“《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12]作为商鞅变法的重要助手,尸佼在变法失败后逃往蜀地,在这里撰写出他的重要著作《尸子》。
……
秦统一古蜀后,采取了若干措施,使蜀地原有的教育内容发生了变化,以利于传播中原文化;但以私学为主要方式的教育活动仍然存在。
后世有“蜀文冠天下”之说。这其实与蜀地的私学教育十分发达有关。在蜀地产生的许多领先全国的文化成果,例如“易学在蜀”“天数在蜀”“道教之源”等等,就是对蜀地私学教育的肯定。
西汉时期蜀守文翁兴学。其时在私学传统之外,文翁在蜀地兴官学,让中原的儒家、道家文化在蜀地得到广泛传播,从此蜀地人才济济,蜀学“比于齐鲁”,文章不亚中原。汉赋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在公认的“汉赋四大家”中,除了班固一家外,其他三家即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均出自蜀地,所以班固赞曰“文章冠天下”。[13]
在班固所撰的《汉书》中,《司马相如传》《扬雄传》是篇幅最大,所载事迹最多的个人传记。司马相如被称之为“赋圣”“辞宗”,他是汉代最伟大的文人、学者、汉赋的代表作家。扬雄堪称两汉之际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无论是学识、学力和研究兴趣,在当时都无人可与扬雄比肩。
《华阳国志》说,西汉的严君平“雅性淡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14]他所著的《老子指归》是汉代道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著作,时人称之为“道书之宗”。
《尔雅》是中国第一本汇总、解释先秦古籍中的古词古义的词典。《尔雅》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时备受推崇的工具书,而为《尔雅》作注的就是姓“郭”的“犍为舍人”,他是犍为郡管教育的“文学”吏。[15]
巴蜀文化在汉代的强势崛起,使汉代的四川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些既是中华文化主流同时又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思想,为宋代“蜀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证明“在统一全国战略”后的成都确实“走向成功”。
注释:
[1]《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讲座袁庭栋“巴蜀文化研究三题”成功举行》说:“袁先生回答了校内外师生有关‘成都得名等热点提问”。据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23—03—11。
[2][5][6][7][11]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第120页,第131页,第128页,第141页。
[3](晋)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2页。
[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益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册,第575页。
[8]《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战国策》之《秦策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9]李殿元:《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文史杂志》2021年第2期。
[10](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页。
[12](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75页。
[13](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第1313页。
[1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先贤士女总赞论》,第532页。
[15]蒙默、劉琳等:《四川古代史稿》第二章《秦汉时期的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作者: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