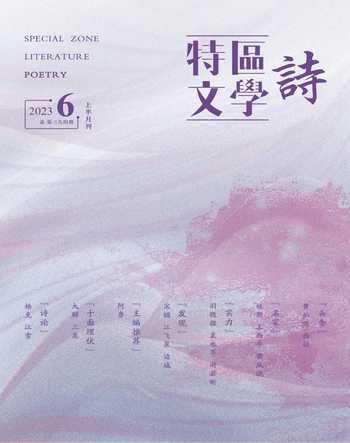最初与最终
袁永苹,诗人、编辑,2009年获复旦大学“在南方”诗歌提名奖;2011年获北大未名诗歌奖;2012年获DJS(诗东西)第一本诗集奖,并在其资助之下出版了首部诗集小册子《私人生活》;出版有诗集《心灵之火的日常》《小哀歌》《人鱼表演》等,翻译有史蒂芬妮·伯特诗论集《别去读诗》以及安德里安·里奇、劳拉·卡西切克的部分诗歌。现居哈尔滨。
恭迎
现在可以来说说
我们那些过去的日子了。
整日燃烧的干树叶,
烧着我们的黎明和旧床单。
我们爱着,在爱的间歇
我们也在爱。
清空了那间房所有的陈设。
计划着读书、看电影、聊天,
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做。
一周兩天去box酒吧排练。
电吉他揪着我的耳膜,
而心弦在震颤。
吃饭是多余的,尽量少,尽量。
几个月里,我拜会了你所有的女孩,
你也与我的男孩们逐个决斗。
我得罪了赫拉,但司命运的女神
宽宏大量,放过了我们,
阿波罗怜爱我们。
我们的爱洗净了洁白
但不干净的床单。
如今在初冬的日子里,
在乡村生活的图景中,
我们在一起。
需要抵抗的神,越来越多,
而共同恭迎的那一位,
那唯一亲切的。你知道的。
伟大的
“伟大的抒情诗可能
死亡,再生,再死亡。”
—蒙塔莱
伟大的抒情诗的确
可能死亡,
以一种不相容的遗忘开端,
时代!而它会再生,
因着它一直没真的死,
可它还会再死,
因有生命力的新物,
诞生,在交替诞生的过程中,
人,不再喑哑失声,他们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嗓子。
我要分得这嗓子中的一个,
唱我该唱的。
这嗓子曾吞占过卡图鲁斯,
如今它吞占我。
发现蝴蝶
有次在昆虫馆里看见了成千上万只蝴蝶。
它们是如此“蝴蝶”而不是如此美。
它们如同蝴蝶那样蝴蝶,而不是那样美。
但是色彩的确五彩斑斓,别具一格。
你无法想象,或者创造一只全新的蝴蝶,
因为你无法穷尽这些蝴蝶的样子。
“它们太蝴蝶了!”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我加诸它之上的任何观念,
都是对它的一种误解,就像我们将它们
全都命名为蝴蝶,而从属于的那一类。
瓮瓶
—唱和史蒂文斯
在最高的胸膛中
一个浑圆的瓮瓶孤独。
久久回望于荒野。
田纳西睡了而我游泳。
巨海藏其日与月,
水波清沁分一幽暗世界
唯一幸存难民。
唯一孤独亲眷。
永不倒戈之友。
既是空灵地也是孤绝城,
这里重建一砖一瓦,
这里需要掏出身心,
必须不断分离两臂,
才能游走寸距。
这是深深坛—
回声在此处
几近于无。
必须勤勉热情
而又耐心恳切,
唤身生彩翼
如心有灵犀。
有时你游得越快,
瓮的两壁就距你越远。
你与水中的影子竞赛,
但瓮瓶不会生出自己。
这是不能安慰的安慰,
这是一方边缘的轻薄。
混沌下着时间雪……
如此漫长,等待熬人,
催逼着你一次次重返
深潭水中默哭悬停。
我是否已将全部家当
搬于这瓮瓶中,
受最高虚构的永恒惩处?
将来若有人摔碎
这用于别离的瓦罐
那巨响,会否重聚
你我一世闪电的回声。
最初与最终
我是流动的,
我鲜活
起初在
婴儿篮里。
慢慢地,
我的属性
凝固。
我的一半
被关闭掉了
为的是
我的另一半
取代我,
成为我。
我成为
我了吗?
没有。我
是流动的。
小夜曲
你们可以拥抱我怀里欢乐的轮叶百合
我可以佩戴我心爱的眼球珍珠
你哭泣为一个门缝轻声掰开我们梦中的父母
我们相爱的耳边歌声悠扬它梦的空街道
冰的门铃冻在飓风的冰箱中
我们的过去闪耀透明酒杯与双膝对饮为无
杜鹃和蝉鸣紧绷在深夜的枝头脱线。
你用镜子围猎墙上的光摸我们的时间猫
随影子跳空舞步跳入沙漏的沙中
当我们有了新的人物与图谱
我们掷骰子并有了三个睡眠,
我们睡了三个单独的醒来
我们缠绕梦中的拉结和利亚
橙色郁金香悬停在永远孤独的餐桌上
我们爆破一枚深夜寂静沉闷的果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