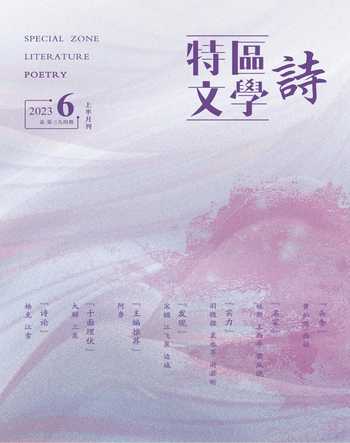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
我一直在过剩下的时光
剩下的黄昏,剩下的照耀,剩下的晚餐
人也是剩下的
父亲走后,母亲是剩下的。
霍金说:如果没有外力,事物总是向更无
序发展。
我常想:这个外力是上帝吗?
这样的追问,耗尽了剩下的悲伤。
当我走后,剩下整个世界,剩下大海和星空
也剩下孟姜女河,剩下两个女儿
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
诗人简介:
三泉,出生于河南卫辉,现居贵州。“以商入世,以诗出世”。出版有诗集《寻找站牌》《云彩草书的丰沛》(合集)。作品散见于《诗刊》《诗歌月刊》《飞天》《深圳诗歌》《诗潮》《诗林》《延河》《大河》《中国诗歌》《中国诗人》等。被评为2021年中诗网年度诗人、2021年诗歌周刊年度诗人,获2021年世界诗歌网年度创作奖、贵州第四届尹珍诗歌奖。
世 宾:剩下来的人
《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是一首智力相当高超的诗歌。虽然有点悲伤,但写得十分冷静,也说出了人生的真相和无限之中的秩序。这种悲伤是“大忧郁”,是关于终极追问的结果,它不同于日常的小忧郁的诗歌,也不同于喧嚣和激昂的诗歌,它在透彻地目睹生命的过程和宇宙的必然。是的,当我们站在“此时”的基点上,过去的时光已经“死”了,接下来要过的时光就是“剩下来”的。从生命规律来讲,消逝的已经消逝了,只有“剩下来”的才是属于我的。在这个逻辑思维下,诗人罗列了“剩下来”的一切,诗人把剩下来的时间转换成空间、人和物,使剩下来的一切变得可以触摸。“剩下的黄昏,剩下的照耀,剩下的晚餐”“父亲走后,母亲是剩下的”,“剩下来”的意味着残缺,但正是意识到残缺,才使剩下来的更加可贵,更加值得珍惜。如果没有意识到这存在的是剩下来的,也就无法意识到这真实的存在,因为被剩下来了,才全部存在于生命当中。这是站在“我”作为“剩下来”的存在的一部分对存在的认知。但“当我走后”,世界依然是剩下来的,“剩下整个世界,剩下大海和星空/也剩下孟姜女河,剩下两个女儿”,这一切的剩下物,会因为我的缺席而成为孤独的存在物,它们的存在也会因为我的离去而成为孤独本身。诗歌的最后一句“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使“我走后”的世界依然与“我”保持着部分的联系。两个女儿作为剩下物的存在,她们承担也见证了在我离开后作为剩下物的全部孤独的命运,但也因为她们的存在,使我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使这剩下的世界不会被绝对的孤独统治。
“霍金说”“我常想”三行看似有点溢出诗歌主干,实则非常重要。它加深了诗歌的主题,使我作为剩下物的主体性得到了确立,“我思故我在”。而且此“思”是关于宇宙秩序的思考,它使有限性和无限性建立了关联。在这首诗中,这看似散文化的三行使“剩下来”的人和物以及那消逝的得到庇护,因为他们都在宇宙的秩序中。诗歌最后一行的“她们”,诗人可能指的是两个女儿,当然也可以指所有“剩下来”的,它们也是离去的“我”的一部分。这个怎么解读都可以,如果强调血缘、亲情和人,那就是特指两个“剩下来”的女儿。
吴投文:“我”与“一部分的我”
“我一直在过剩下的时光”,这是关于生命的一个悖论性的表达。诞生即意味着不断趋向结束,死亡被限定在那里,不可移易。一个人的生命实际上就是“剩下的时光”,生命以减法的方式确定某种秩序,把人限定在对剩下之物的挽留中,而这也是悲伤的来源。“剩下的黄昏,剩下的照耀,剩下的晚餐/人也是剩下的”,“剩下”的这一切变得依稀珍贵。“父亲走后,母亲是剩下的”,他是带着对母亲的不舍与眷恋离开人世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剩下的时光”都弥足珍贵,“剩下”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恰恰是珍重与眷念,也是反思与追问,是省察生命存在的意义。
在世界的神秘秩序中,一切都朝向一个终极之问:上帝是秩序的确定者吗?而这样的追问,徒使诗人耗尽“剩下的悲伤”。诗人想到,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后,“剩下整个世界,剩下大海和星空”,这是每一个人的结局。对诗人自己来说,他有自己特定的处境,“也剩下孟姜女河,剩下两个女儿”。诗人把孟姜女河和两个女儿联系在一起,可能意在强调悲伤的浓度。诗的最后一行,“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呼应标题,点明诗人心里最深切的眷恋之所在。“我”和“剩下”的两个女儿并未断绝人世的所有联结,“我”仍有“一部分的我”活在这个世上。
此诗的主题具有多义性,深究起来,关涉人生的很多方面,值得品读。诗中有一种孤独与零落的气氛,而孤独也好,零落也好,似乎又都指涉着人世的复杂情状,让人读后无言,陷入深深的沉思。
向卫国:关于世界与情感的“剩下”现象学
从过去的角度看,今天是昨天剩下来的一天,现在的世界也是过去的世界剩下来的那部分;当某人死去,整个世界都是他剩下来的。很难说,这是一个逻辑命题还是一种诡辩?
诗歌中插入了霍金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外力,事物总是向更无序发展。”诗人问,霍金说的这个“外力”是不是上帝?当然不是,“剩下”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让世界摆脱“无序”状态的“外力”显然就是时间本身,所謂有序,其实也就是有了时间之“序”;但也可以说是,无始无终、无影无形,却又创造并容纳万物的上帝,跟人类虚构出来的时间简直一模一样。
去除掉这个逻辑或者时间虚构的抽象性框架,诗歌“剩下”的实际内容有两处:“父亲走后,母亲是剩下的。”“当我走后……/……剩下两个女儿/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
这也可以说是这首诗具有实在意义的两个支撑点(前者也许是实,后者必然暂时为虚,只是一种推测或想象),它们都事关“亲人”之间的情感寄托,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孤独”的主题也自在其中。我们不知道,这首诗的缘起是这种实际的情感事件使诗人产生了对世界的“剩下”性的哲学沉思,还是反过来,由于对世界“剩下”性的现象学思考,从而引发了对生活中的亲人的生离死别问题的重新认识和感受?不管怎样,这首诗的整体建构必定来自对“剩下”这个词的意义的展开。
最后还是应该指出,这首诗隐约有诗人雷平阳的名作《亲人》的影子。从空间的角度讲,“剩下”即同构于“不断缩小”的过程,而“这样的追问,耗尽了剩下的悲伤”这个句子,更是直接模仿了《亲人》的最后一句。
周瑟瑟:一首诗就是一口深井
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趴到井边,往里面呼喊,井水在井底晃荡,什么也没有。有一天,我独自一人走向了那口深井,我探出头,一股凉气从井里冒出来,我看到了井中的另一个自己。
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三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诗人,他(她)这首《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犹如一口深井,在人到中年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一直在过剩下的时光/剩下的黄昏,剩下的照耀,剩下的晚餐”,就像小时候我从深井里看到我胆怯的样子。读这首诗如临一口深井,是一股从井底冒出来的凉气将我倒吸了进去。
读三泉的诗恍若隔世,“人也是剩下的/父亲走后,母亲是剩下的。//霍金说:如果没有外力,事物总是向更无序发展”。平静的叙述,生者对死者的诉说,听来如星空旋转,看不见的“外力”牵引着生命走向浩瀚的宇宙。
我们生活在未知的世界,“我常想:这个外力是上帝吗?/这样的追问,耗尽了剩下的悲伤”。诗人的追問如滴落井中的一滴水,生命的“悲伤”必将“耗尽”最后一丝力气,连悲伤都没有了。诗的最后一段,“当我走后,剩下整个世界,剩下大海和星空/也剩下孟姜女河,剩下两个女儿/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读诗如临深井,我心甘情愿被另一个自己吸进去,只有被吸进去才能发现诗里“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那是诗人留下来的另一个我。悲伤已经带走,“一部分的我”是另一个生命,留下了“全部的孤独”。
我怀疑三泉是小时候和我们一起趴在井边的一个孩子,只是我不知道他(她)是哪一个。应该不是那个吓得尖叫的孩子,而是默默转身离开的那一个。多年以后,三泉才重新回来,引领我来到《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这口幽深的井边。“你看你看……你看到了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你了吗?”三泉这样问我。
宫白云:对现实的一种提醒
司马迁因“心有郁结”而发愤述作,诗人也常常会因“心有郁结”而成诗。三泉这首《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正是因生命的消逝而“心有郁结”所成的一首诗。它是对生命与亲情的别样呈现,它打破了这类诗的日常惯性的思维,从“剩下”这一新颖别致的角度为读者展现了诸多“剩下”的画面。这些画面我们耳熟能详,但经诗人这一集中展示,生命的孤寂感与对亲情的留恋直指人心,把“剩下”的光景与“剩下者”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人更是火候极好地引用了霍金的话“如果没有外力,事物总是向更无序发展。”并由此发出“这个外力是上帝吗?”的追问,成功地道出了现实的残酷与心灵的悲伤。这个“悲伤”让诗人无法自拔,他想象着自己“走后”“剩下”的种种和“剩下”的自己的两个女儿的心境,对生命消逝的由衷的喟叹和挥之不去的孤寂感占据了他全部的身心。所谓的“走后”其实就是对生与死强烈的确立,如果诗人没有这种“走后”的想象,身后那些“剩下”的事情就无法连接、延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走后”,“剩下”就不可能这么刺痛人心,中间如果没有霍金语与“追问”的过度,这首诗也不可能这么深邃、深厚。一切都是那么天衣无缝、张弛有度、水到渠成。诗人深知,生命与亲情都同时拥有天堂和地狱,这才是他情之所系。因此,他让自己最后“剩下两个女儿”,让“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充分表达了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
赵目珍:思考与想象和语言浑然一体
美国作家海伦·文德勒在其《诗人的思考》一书中以蒲柏、惠特曼、狄金森和叶芝为例重新启动了诗人与思考之间的关系的美妙话题。尽管它所言“思考”是诗学意义上的另一种考虑,但话题的打开仍然对诗歌的阐释有着重要启示。与大解的《肉身乃是绝境》作对比,三泉此诗在“思考”的强度上略逊一些,即它的议论、说理的色彩柔和很多。但是,三泉此诗在语言的质地和想象的灵动性上要高出一筹。海伦·文德勒在其著作的导言中说:“在诗歌中,思考不仅是显而易见的循循善诱,而且还是为了怡情悦性;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诗中,与想象和语言浑然一体。”三泉的这首诗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三泉这首诗“思考”的问题,是关于诗歌的又一个核心命题:孤独。此前写孤独的诗篇有很多,但像三泉这样的写法着实少见。从写作理路上来分析,此诗大致分为三个层面:首先,诗人立足于个人生活,陈述当下的孤独状态(第一节);其次,跳出主题,引入一个“外力”(霍金的言语)来推动“孤独”继续往前走(第二、三节);最后,以一个假设促使孤独在叙述中达到巅峰,收束诗歌。从具体的写法上看,全诗以“剩下”为中心,以“剩下”的对象为“武器”来对“孤独”实施形象的“围捕”。最终,诗人的“围猎”成功了。这种成功的因素无他,唯得益于诗人所拥有的那种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在诗歌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诗人在表达孤独时,并非一味地对读者进行说教,而是以形象化的语言意象来提示和感化他们。海伦·文德勒引叶芝的观点说,在审美的瞬间,“所有的思想都变成了形象”。三泉这首诗把这一理论实践得可谓既自然又有力。具体地看,在诗歌中,“剩下的时光”“剩下的黄昏,剩下的照耀,剩下的晚餐”“剩下的悲伤”“剩下(的)世界,剩下(的)大海和星空”“剩下(的)孟姜女河,剩下(的)两个女儿”,这些意象构成了一个象征的系列,透过它们,我们看到了被诗人抽象化的现实。当然,更多的是,我们看到诗人把现实进行了理想主义的“抽象化”。这些意象是作者惨淡经营的产物,它们承载着诗人的“思考”,同时构成了审美的独创性。
海伦·文德勒在著作中说,他“希望把诗人塑造成善于思考的人”,希望他们“能创造出体现细致入微(以及本质上无穷无尽的)静心深思的文本”,这种对文本近乎完美的要求,不是哪一个诗人都能够达到的。三泉的这首诗,尽管也没有达到这样完美的建构,但是轻盈是思考、美好的想象、自然的语言这三者的合一,已经非常接近这种要求了。
张无为:调动关键词强化诗意
三泉的诗大多是写寻机,即围绕生老病死、爱怜与悲伤等人之常情展开的,并以自我冥思,甚至直接阐发理趣方式去进行个性化诗意的呈现。
该诗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剩下的”,二是“外力”。前者贯穿全诗,包括“我”在场与“我”走后的两个阶段。“我”在场时可见证我和一切都是“剩下的”;“我走后”可确认那剩下的一切,尤其与我相关密切的,如女儿与孟姜女河。
“外力”作为第二个关键词似乎是半路杀出的,其实不然,它在人活到一定时段才可能出现。作者书写此诗,独特之处在于为生命阶段加持;援引外力能避免“更无序”的大家名言,既认同了宗教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也揭示出因追问而耗尽“剩下的悲伤”的更大的怪圈。可见这两个关键词在诗中的确很关键。
到此,有人会感觉到诗中似乎沉郁悲伤的比重较大,词语“剩下(的)”排比式反复出现,犹如人进入暮年的感受。其实这只是诗人对时光的敏感使然,多愁还能善悟。如戴望舒写《寻梦者》揭示梦花开人已衰的主题时,年仅27岁,而从现代性角度考察却觉其恰如其分。三泉这首诗,同样包含了巨大的人生悲悯,而且针对的不止于个体,更是群体。读后你能够感受到,作者擅于用诗意感悟逼近生命本质。在诗的表层或外围似乎有令人无法抚慰甚至令人绝望的包装,而内里却是最温暖可人的大关爱。如诗中透出亘古的怆然与贯通的落寞,但那“一部分的我”成為白茫茫中一点红,且并非点缀,而是根本。
在诗写中,人生有限、无缘永恒的主题由来已久,但这首诗从新视角切入,着重以两个关键词调动诗意,因而表现出鲜明的风格及个性感悟,值得思考与借鉴。
高亚斌:意义感的获得
自从出现了伊甸园的神话之后,“失乐园”的主题成为人类命运的永恒象征。三泉的这首《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是对人的生存的短暂微不足道和荒谬处境的生动和沉痛的哀吟和诉说。诗人以“剩下的”为诗意生发的引子和贯穿诗意的根脉,寓言了生命最富有宿命意味的悲剧和最激荡人心的感慨,开启了人们对于存在的意义感的反思和考量。
无论人们如何满怀期望和饱含希冀、多么雄心勃勃和豪情万丈,“人生几何”“人生不满百”的宿命感始终催逼着人们,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恐惧始终伴随着人们。“我一直在过剩下的时光”,人从降临到这个人世,注定所有的日子都成了“剩下的时光”,每一个日子的来临,既意味着新的一天的开始,又意味着“昨日之日不可留”的过去。同时,这里的“剩下的”又意味着不断地失去:父亲、母亲、童年、梦想……失去才是生活的本质,才是一切拥有都值得珍惜的唯一理由。甚至,连悲伤、孤独、寂寞都会失去,剩下的只有空荡荡的虚无。
当然,“剩下的”也意味着不断地剥离:从感伤的记忆中剥离、从冗余的时间中剥离、从无意义的场景中剥离、从虚假的言辞中剥离……每个人都在有限的生命中进行着筛选、舍弃和剥离,这样,一个无比孤独而真实的自我就出现了,一个可贵而又饱满自足的自我也就形成了。哪怕生命如惠特曼所言:“生活是死亡留下的一点点残羹剩饭。” 是如何的短促和荒诞,只要我们守住了最为珍贵和最为真实的时光,也就守住了生命中最明亮、温暖和动人的部分——“剩下的黄昏,剩下的照耀,剩下的晚餐”。
并且,“剩下的”也会是一种境界、一种舍弃和逊让的境界,“当我走后,剩下整个世界,剩下大海和星空”,可以把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留给他人和后世。以此作为递进和绵延,诗歌最终落到了“剩下两个女儿/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这一叙事重心上,凸显出诗歌“爱”的主题。人的存在是脆弱的,而爱使生命和存在得以延长和永恒,由此,失去也变得具有了意义感,“剩下的”得到了价值和意义的优厚回馈和丰足报答。
徐敬亚:诗人的本事就是偷换概念
三泉是琢磨时间的能手。我读过他另一些诗。这个人对“时间”的感觉惊人。他写过,“我刚写下时间,时间就被我用掉”。他还写过,“我用掉自己,证明我是时间的边缘”等。
在这首诗里,三泉突然抽出一把刀,轻轻一划,整个世界骤然一分为二:身后的过往已被消费,而前面不可知的未来则全部成了剩余物。
关于“剩”的哲学意义我就不说了。当今中国诗歌评论界太乐于阐释诗的文化意义、抽象意义——所以我最近评诗,特别想发现诗人写作时的秘密。
这首诗的秘密是:三泉的“剩下”怎样悄悄进行了三次转化。
开头的五个“剩下”,意思完全一致——即他以生存为界,从“纯时间”的意义上划分吃过的饭和剩下的饭——在三泉这首诗之前,我,以及差不多所有读者们大概都不会想到:“剩”,这样一个包含着“剩饭、剩菜”一样的半馊半酸的破烂词语,呜呼,突然焕发出了哲学的光彩!
注意:这个“剩”,在转换。显示了诗艺的暗中高明!
转化一定要不知不觉:在“时光、黄昏、照耀、晚餐”……4个“剩下”后,在父亲身后亲人出现,“母亲是剩下的”——这时,母亲的含意,已不再是“未发生”的、中性的“纯时间”概念,而是转化成一个悲伤的人文意象——成为某种多余的、残留的、孤独的、悲伤的……从“剩下”到“遗弃”,诗人已经偷偷换了概念。
正是带着这些悄悄转化后的人文含义,三泉在诗的中间段,把“剩下的”快速地转化成了“剩下的悲伤”。这时的“剩”第二次转化为悲伤,它已经成为了形容词。
最后,诗在“非时间性”的、苦难的社会含义下,继续前进。结尾处,他用刀剖开了自己,交给读者“两个等式”:
等式一:大海+星空+孟姜女河+两个女儿=剩下的世界
等式二:剩下的世界=我全部的孤独+部分的我
是不是很清楚?“剩下的”在这首诗里经过了三次转化:①时间转化为人文。②人文转化为悲伤。③悲伤转化为拆解。
诗意的转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概念的移动、演化与变形,闪转腾挪而不动声色即是高手。
霍俊明:面向自我的焦虑之诗
三泉的这首《她们代表全部的孤独和一部分的我》显然属于“自我之诗”。在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无疑是“我”,诗人直接面向自身的局限及其渊薮——这也是每一个人的。与“我”相对应的是“剩下”,在单向道式的一次性消耗中,在面向“大海和星空”这样的永恒之物时,悲伤和孤独就不可避免地被反复激活和强化了。这时,面向自我的诗也就转化成了“孤独之诗”和“焦虑之诗”。这首诗也可以视为“寄托”之作,一个人百年之后尚有一条河和两个女儿作为精神的投身之物,这使得整首诗多少携带了一丝难得的慰藉。需要补充一点,这首诗中间那句“霍金说:如果没有外力,事物总是向更无序发展”在我看来多少有些突兀甚至生硬,尽管诗人在此是为了强化自我的疑问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