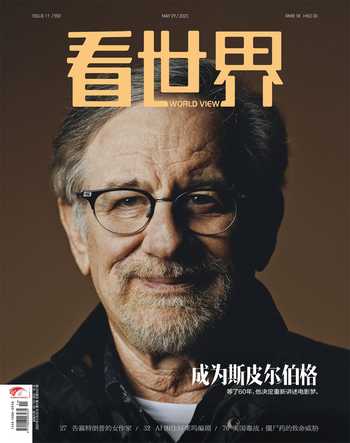于坚的漫游:一边写诗,一边看世界
白莉莉

诗人于坚
诗人于坚又出书了,这一次是一本名为《漫游》的诗集。“面粉可以塑造各种意义,我的诗集可以说是一种我生产的面粉。”
当一个诗人以漫游为名,开始在生活里探索的时候,他前往的漫游目的地也就“随心所欲不逾矩”了—它可以是承载一碗“加盐加料不加价”米线的故乡昆明,可以是埋藏最多日常细节的大都市巴黎,也可以是被高楼、牛奶、汉堡和果汁裹挟的纽约,以及诗人在不经意间造访的密西西比河。
对于坚来说,从早年间行走在昆明的《尚义街六号》,到近年来因为工作和旅游的原因,前往国外那些他所称的“迷人的异域”,一如这本诗集的名字,“漫游”,这个满口“昆普(昆明普通话)”的作家、诗人、文化细节观察家、不同生活体验者,近些年最习惯的一种生活节奏就是:背上背包就上路。在路上,他看見了不同的民族风情和文化差异,也看见了长在石头缝里那些微不足道的隐性文明。
盘点耙梳一下于坚的“漫游笔记”,既是对既有日常和生活习性的缅怀和传承,也是对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接纳和肯定。

云南昆明,官渡古镇
在昆明,看见世界的细节
“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沦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
这是于坚在《昆明记》里写的一段话。在他看来,自己的故乡,昆明这座城市,“置气喘吁吁的叫作‘时代的列车于不顾”,同时也有着一种“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的劲儿”,更是一座可以“用脚丈量”空间肌体的城市。
记得之前采访于坚时,他穿着一件汗衫前来受访,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吃了没有”,好像一旦听到我“还没吃呢”的回答,就要推荐昆明最地道的过桥米线馆子给我一样。
对于每一个初到昆明的朋友,于坚都有讲不完的话要和他分享,比如他就非常注重向对方推荐,以“暴走”和“漫游”的方式看昆明。“来到我们这里以后,你不要打的,不要坐车,不要走马观花,要暴走,要慢慢用脚去探索这里(昆明)的花花草草。”于坚说。
在巴黎遇见故乡
这种“用暴走向城市致敬”的漫游方式,也在多年后被他“复制”到了在巴黎的漫游过程中。“人们来到巴黎,仿佛都成了艺术僧侣。即便睡去,祭典也不会结束,黑暗之光在那些古老的街道、尖塔、玻璃、门面、石头墙壁、各式各样的雕塑、花园、宫殿、水池、公寓和睡在某个角落里的流浪者之间跟着夜巡人,警车的尾灯在塞纳河边上亮着,一只狗正在坦然穿过卢浮宫和巴黎警察局之间的大片空地。就地理态势来说,巴黎也是一种祭典般的分布,蒙马特高地上的圣心教堂高踞,从高地向下走,踩着那些凸凸凹凹的石头,有时候会遇到秋天留下的水洼和落叶。途中有个小广场,许多拙劣的画家在那里兜售行画或者为游客画肖像,他们永远画不出杰作,永远是那个水平,就像塞纳河,永远是那个水平。”
不要走马观花,要暴走,要慢慢用脚去探索这里(昆明)的花花草草。

法国巴黎,塞纳河风光
于坚说,行走在塞纳河畔,脑海里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小时候在滇池边玩耍的场景,想起范仲淹那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昆明不是世界的驿站,而是终点。人们来到昆明,就想筑窝,不想再挪窝了。这就是他们梦想的大地天堂。在别处,或许必须愚公移山,改天换地,才有筑窝的可能,而昆明,老天已经将一切准备好,水好、地好、花好、月圆,伊甸园,只需亚当夏娃们筑窝而已。”
在昆明,于坚看见了巴黎的影子。在他多年后漫步在塞纳河左岸和造访那个被称为“小资天堂”的花神咖啡馆时,这种感受尤为明显,以至于到最后,他把昆明看成了巴黎,“反认他乡作故乡”—
“巴黎有一种废墟气质。弥漫着某种悲情,最后的,最后的,某种波西米亚式的感伤。美好的事物都抵达了‘最后。故乡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人类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故乡,不是现实中的遗址、方言。而是某种传统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乃是对古老、包浆、人性,爱,慈悲、时间,浪漫主义、永恒、灵魂、‘金色池塘、本雅明所谓‘灵光—这些东西的迷恋,惋惜、刻骨铭心的记忆……呵,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快乐,这样的疯狂,这样的好日子。在这种记忆中,希腊就是巴黎,巴黎就是长安,长安就是洛阳,昆明就是巴黎,十九世纪就是二十世纪。”
谁说不是呢,我们总能在每个新造访的目的地,找到自己昔日最熟悉的那些符号和影子。
暴走,打开城市的最佳方式
采访于坚时,他一直在向我灌输暴走的乐趣。“如果观察城市存在一种绝佳的角度,那一定是用脚去逛遍这座城市。从这点来看,踩单车都没意思。”于坚说。
“林间探头探脑的麂子告诉过我/只有那棵灰色的杨草果树告诉过我/只有正午飞过武成路的虎纹蝴蝶告诉过我(我家在铁局巷92号) /只有那个翻倒在水井边的木桶告诉过我”
在昆明,于坚看见了巴黎的影子。

云南昆明,滇池南岸“鯨鱼岛”
于坚把生活的细节写进诗句,他觉得这是对日常琐碎生活的一首赞美诗。“那些破碎的,分割的,缓慢的,过时的,被时代抛弃的,被高楼大厦遗忘的,才是我们生活里最丰富的细节,而这些东西,是你无法用一辆小汽车就阅尽的。”
其实了解一个地方,或者说漫游某座城市的绝佳方式,一定是一身轻松地暴走在街头巷陌,一定是毫无负担地穿上最松弛的那双运动鞋,一定是和一个向你推荐暴走的当地人坐上一个下午,听他讲述这座城市的过去和掌故,“昆明自古就是移民城市,这个移民城市与一般移民城市不同,在别处,移民之间一般必然生出争强斗狠的文化,因为要抢滩夺地嘛。昆明不消抢,到处好在。因此呢,产生了一种慢吞吞慢腾腾的守窝文化,家乡宝文化……”
虽说“云南人都是家乡宝”,但云南的阳光、雨水、空气、枝蔓、石桥、河流……于坚似乎都在巴黎见到过。即使没有自己心心念念的过桥米线,但一根又长又粗的法棍似乎也能带给诗人独特的“地域化观感刺激”。
在巴黎,于坚发现,日常生活其实也是慢悠悠的,和美国人不一样,和英国人不一样,巴黎人的生活显得缓慢自在,以至于他不得不用一种另类的,此生从未用过的笔触来描写从没见过的巴黎:“在巴黎漫游是在时间中旅行。我通过絮语、陈述、引文、图片写下了我的经历、见闻、思路,灵感。写作就是重构记忆,这本书我实验着一种写法,回到传统的文,文就是没有文体形式的分类,只有文。在这本书里面,随笔、散文,记叙文、小说式的片段、分行的诗、引文,图片混为一谈,时空,过去与现在交错往复。”
要暴走,要漫游,要爱生活
巴黎“好在”,昆明也“好在”。这或许是巴黎的“异乡客”,昆明的“老熟人”于坚通过漫游得出的一个最深的感悟。
“我有时候给外省刊物写文章,不知不觉要用昆明话—好在,多次被编辑问,这是方言吗?原来他们那些地方没有这种方言。好在,因此昆明有一种朴实的存在主义哲学,重要的是身体的在场,而不是用观念来为身体的不在场辩护。海德格尔的思想很适合于昆明,诗意地栖居,是因为大地本身就暗合文明梦想的诗意,只需要守护,天地神人,其乐融融。这令昆明人的品性一般不是积极、斗狠,而是守护、保守,庄子般的逍遥自在,比庄子还逍遥,昆明人不是观念上觉悟的逍遥,逍遥是一种大地启示的世界观。”于坚在散文《昆明这个窝》里这样写道。
上次采访结束时,他请我吃了碗米线,顺带捎上了一盒鲜花饼,并赠予我三句“临别赠言”—
“多出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写文章和过生活都要注意细节。”
“要暴走,要漫游,要爱生活。”
许是被他彻底说动,又或者是吃了人家一碗米线后不听人劝显得不好意思,告别于坚后,我独自迈开腿,绕着滇池暴走了一个半小时。
责任编辑何任远 hr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