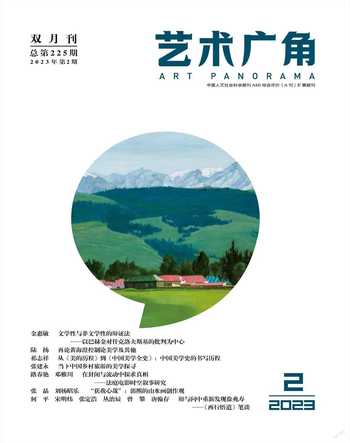东北工业长征路上的散文诗
张翠 张硕
摘 要 李铁的长篇小说《锦绣》充满大工业的深邃气质,同时洋溢着浪漫的诗意味道。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以张大河、张怀勇、张怀双为代表的企业人在七十余年的国有企业工业化进程中勇于变革、传承开创、接续奋斗的故事。在小说的结构和形式上,以叙述、白描、日记、厂志、安全简报等方式来讲述一座工业城市和一个企业的历史,讲述一群工业人的生活和命运,以众多片段的叠拼形成一幅工业城市的图景;以昂首创业、悲壮改革、振兴突破这样内在的节奏,抒写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激情与浪漫,这是几代国企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自觉担当,饱经沧桑磨砺铸就的东北工业长征路上的散文诗。关键词东北工业;散文诗;《锦绣》
一、工人精神共同体的传承延续
作家李铁几十年来从未放弃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始终站在东北工业文化的第一线,对工人群体投注深邃而温热的目光。《锦绣》一书真诚地传递出李铁的国有企业情结和工业文化情怀。第一卷“家园”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厂故事,李铁选取了具有化工、钢铁等综合属性的锦绣金属厂作为典型对象,这也是东北大型国有企业的缩影。小说中的张大河是位技术大拿,他有着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使老旧破败的厂子焕发生机、步入生产快车道。当听到厂里书记牛洪波说“以后有了国产设备,我们再进自己的生产设备,职工人数也要成五倍、十倍地增加,将锦绣厂打造为千人大厂、万人大厂”,“张大河心里热热的,豪气也一下子上来了,说,我自豪呢!”[1]牛洪波将“传、帮、带”的责任落到张大河肩膀头,张大河只是觉得这样沉甸甸的责任令他浑身燥热,如同喝了烈酒,满脸通红。“朝阳洒满厂院,朝前走的人们脸上都是朝阳一样的颜色”[2],新中国的工人犹如红日初升,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创造了早期东北工业的辉煌。东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它记载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发展的沧桑巨变和风云历程,作为曾经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为国家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小说中提到当车间出现泥浆槽堵塞事故时,锦绣厂组织部干部刘英花身先士卒不顾危险跳入设备手动清淤,其他党员见状也纷纷跳入设备清理。如此紧急的时刻,工人们全然不顾个人安危,“犹如蛟龙戏水,人欢马叫,像舞台,像群舞”[3],李铁对这些场景描写得生动逼真、驾轻就熟、颇具抒情性,将东北人骨子里笑对生活、从容不迫的乐观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除了主要描写工人沸腾热情的工作场景,也以不少篇幅描绘工人生产生活中的趣事,像书中多次写到“比武”和“赌酒”,例如张大河与苏联专家彼得洛夫比试炼锰铁手艺时,张大河在不太熟悉苏式设备的条件下以分毫之差赢得胜利。张大河的徒弟们比自己得奖都高兴,让张大河请客吃饭,不料在饭店遇到了彼得洛夫,两人又比起了喝酒。“谁怕谁啊,后悔的是娘们儿,酸白菜就算了,鲜黄瓜整两根也行……”[1]推杯换盏后又直接对瓶吹,喝醉酒的张大河哧溜一下跌到桌子底下,气氛轻松愉快。这样极为生活化的口语交流与鲜活的场景,无不展现出东北工人豪爽敞亮、自信好客的精神面貌,大家痛快畅饮、尽兴而归,两人也因酒结缘,成为朋友。古河两岸的工业区组织的多项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技术比武。书中用“叭叭叭,机枪似的回答、爆炸般的欢呼、握拳挥舞、叫阵似的大吼”凸显出工人群众气宇轩昂、排山倒海的气势,这股气势好似开天辟地的利剑,锐不可当。工人群体既有新生劳动者的尊严、又有对国家和工厂的认同,强烈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情感丰富、品格勇敢、心态从容 。无论“锦绣人”处于何种境地都分享着“锦绣人”共同的情感体验,工人精神共同体的意识像毛细血管一样将意义、信仰与价值输送到并无血缘关系的工人体内,大家始终保持“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联结,普遍有着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的“铁人精神”,有着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奋斗的精神和建设美好家园的坚定信念。
李铁所塑造的张大河之所以能在中国工业小说人物形象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大河身上有着最具代表性的时代精神——潜心钻研、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张大河是炼猛高手,不怕得罪上级领导也要维护自己对专业技术的尊重,身为核心技术组成员勇于奉献,对工业技术一丝不苟,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让技术更上一层楼,并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出去:“我要让大家都跟我学,成不了大拿也要成个内行。”[2]这就是曾在建设社会主义高潮中被工人们广泛认同的“技术第一”论。[3]小说再现了上世纪看重技术、提倡技术的整体氛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张大河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得到了良好的发挥。张大河的小儿子张怀双继承父亲志向,勇于攻坚克难,在新时代有新作为。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一代,都有不怕牺牲、敢为人先的精神与为国家填补空白的勇气和干劲。
二、工业改革浪潮下的开创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党的领导下以炽热情怀和冲天干劲建设社会主义,为新中国工业奠基,并从此开启了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作为新的时代的主体,必然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塑造对象。工业题材小说以表现工人生活、工厂图景,反映工业战线为主题,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塑造了钢铁工人李少祥(草明《乘风破浪》)、铁人周挺杉(张天民《创业》)、改革者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与时代共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成绩。但工业小说受限于题材影响,存在着一定局限,写出来容易枯燥、不生动、文学性弱。蒋子龙曾在《大地和天空》一文中,总结了文学反映工业建设的六种方式:写成生产作坊,小打小闹;写以厂为家,好人好事;用写农村的方法写工厂,将工厂里的矛盾写成家族矛盾;以工厂为幌子,把人物拉到公园或农村进行描写;写二元对立的方案之争;写小改小革,围绕一个机器修个没完没了。[1]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工业大步向前发展,作家们的视野愈发开阔舒展,不断打破上述六种方式的桎梏。
工厂是社会生活一条强劲、敏锐的脉搏,它串联着个人、集体和国家命运,而置身其中的工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辽远。李铁以文化学的视角,把筆触深入到工人的精神细胞,引领读者领悟工人世界的丰富和独特,领略工业文明的律动和工业改革浪潮的冲击。第二卷“山河”围绕着张家第二代张怀智、张怀勇和张怀双展开。老二张怀勇是本卷的核心人物,他早年上山下乡后回到锦绣厂没有蒙受到父亲余荫庇佑,多次竞选干部落败,面对全员并轨的裁员要求能提出更具人情味的方案,积极处理厂子内部的矛盾斗争。面对上级组织前来调查,张怀勇也能向组织摆明利害关系,言辞恳切,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也彰显出他公正严明,不偏不私的品格。如果说张大河关注的是自身技术的掌握,带徒弟传技术;张怀勇则一直致力于公司的创新发展探索外部合作机制,完成了国企强强联手的合资,真正实现钛白粉国产化,这既是父亲张大河一生的夙愿也是几代“锦绣人”毕生的追求。从这点来说张怀勇真正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老二张怀勇是父亲变革思想的继承者,那么老三张怀双无疑是父亲工业技术上最坚定的继承人,他十几年来勤勤恳恳、心无旁骛,始终奋斗在生产的第一线,像父亲一样钻技术、带徒弟,有升迁机会也不为所动。李铁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像写张大河一样刻画张怀双,我们能看到张怀双有更多的时代思考,主动思考技术革新的意义价值,与一线炉前工共同研究出“无外加熔剂法”,寻找突破钛白粉工艺的出路。新时代下不再刻意强调工人阶级对身份的自我认同,而是在面对压力与挑战时找准自己的兴趣和兴奋点,乐于创新创造,立足岗位创出新绩。老大张怀智表面看起来是个“反面人物”,但也在父亲和兄弟的感召下步入正轨。这既为小说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人物弧光的复杂性增添可读性,也通过这三个人物的发展路径和向度让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时代赋予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成长。李铁敏锐地捕捉到社会转型与跃进之时,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投下的巨大的影子,社会与个人命运如此密切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几代人丰富的精神谱系,同时让我们瞥见中国工业文明在沧桑巨变中走向成熟的成程。
李铁在工业领域沉浸已久,在工厂生活过、工作过,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工人师傅、工程师、班组长、企业高管……经历过生产的波动、工厂命运的转换,他的热爱度和熟悉度足够深,之前的创作积累足够厚,情感在胸怀中堆积、酝酿,由此迸发出新的审美力量。李铁以写中篇擅长,但此次他超越了自己,以长篇小说来感应工人的感受,来回应时代的洪流。他构建了时间跨度长达70余年的工业时空和东北这片土地上烟火气息浓郁的生活全景图,站在见证者的角度将自己心仪的人物、心念的情感、心系的信念投射到中国工业史发展进程中来。李铁无疑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家,他有着悲悯的人文情怀,本着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未回避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逆境与阵痛、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日薄西山的工业环境。作家在生活的基石上为我们铺展出一幅壮阔豪迈的历史图景,其中并非平铺直叙的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从辉煌——挫折与牺牲——新辉煌的过程,前进与曲折相统一,欢乐昂扬与苦痛艰辛同在。里面有诸多情节、矛盾的埋伏设置凸显出时间变化的复杂性,构成了含蕴丰盈的时间链条。小说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审美形塑下的时代人物及人物关系张力十足。人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李铁搭建出一种复杂的工厂大院生态,将人物置于工业文明社会生态和改革的波峰浪谷之中。工厂子弟从开始经历的喜乐荣辱同频共振,到后来的巨大牺牲、意识溃散与身份分化,作者并未躲避,并选取了三个典型代表:去私企工作的侯卫国、生意场上当老板的大包、修理工的王建设,他们失去了锦绣厂的庇护不得已自谋出路,这就是当时东北经历改革震荡后最真实的社会情景。经历风雨洗礼的阳光背后必有彩虹,国有企业焕发新姿,顶天立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而正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改革浪潮下奋楫扬帆,过险滩、闯激流,才有了“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工业奋斗园景。
三、创造工业题材审美性的新高度
李铁引起文坛关注是从“女工人系列”开始的,《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花》《乔师傅的手艺》《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等作品,塑造了于小雨、乔师傅、杨彤等文学形象,以微观个体人物的精神苦痛和工人命运的转折反映国企转型的阵痛。《我们的负荷》质疑了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弊端,塑造了维护国家利益的企业高管孙兆伟的形象。《杜一民的复辟阴谋》在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文道德关怀的矛盾张力中展开主题,塑造了有头脑、有智慧、有情有义的工人班长杜一民的鲜明形象。《合同制老总》《梦想工厂》塑造了一心向着已变成弱势群体的工人兄弟的老总、工会主席。《点灯》塑造了下岗工人形象赵永春,尽管生活里有诸多艰辛和不如意,但他坚韧乐观、尊重日常生活、坚守道德底线,散发出朴素的人性温暖与光亮。李铁在工业题材中一路走来,已经通过多年的创作实践构筑了属于他的工业题材的美学高原。而《锦绣》则开创了李铁本人工业题材小说审美性的一座高峰。
《锦绣》通过对各个时期的工厂氛围的渲染和劳动场景细致入微的描写,营造出劳动审美和生态审美的工业小说新形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到“劳动创造美”的著名论断,系统科学地论证了艺术审美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所定义的审美脱离了传统意义上与纯粹主观上的美,不是脱离于人作为主体的实体化存在的美,而是一种建立在自由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劳动之上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审美。[2]劳动创造了审美主体的人和审美客体的自然。人类对于审美过程、审美欲望和审美创造离不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同样,艺术与审美创造中的“自然美”,也是人与自然能动与受动关系的结果。正如曾繁仁先生所说: “自然之美绝非实体之美,也非‘人化自然之美,而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之美,一种共同体之美。”[3]这便是生态审美的内蕴所在。
锦绣厂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李铁以生产劳动为抓手和推手,勾勒出劳动者们生生不息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面。这种劳动活力始终存在,它超越了关于勞动价值创造的视角、人物关系谱系的视角,直达劳动情感和审美维度。文中的开炉、点火、沸腾、屏息噤声观察金属波浪以及机器的轰鸣……为我们铺展出一幅极具活力与吸引力的劳动画卷。那叮叮当当的捶打铁器声,那轰隆轰隆机器蜂鸣声,那咕嘟咕嘟液体沸腾声是劳动的声音、劳动的节奏、劳动的美感。工人们在劳动中结成社会关系,劳动也成了维系他们情感依赖的纽带,工人们满是集体自豪感与荣光感,充满着国企情怀和家国情怀。
对于工业小说生态景物的描写,《锦绣》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小说的生态审美包括风景、人景和心景,是工人们共同构成锦绣工业风景多维度的展现。小说的开篇便是对古河大坝自然景色的描写,“黏度极高的黑土,种类繁多的杂草,杨树、刺槐、柳树、针叶松在内的各种树木”,白山黑水的东北景色描写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的心,“另一条胡同,厂独身宿舍院子里开满了鸡冠花、矮牵牛和紫藤花,都是适合庭院的花草”。这是工人子弟的闲情雅致,他们的生活已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而当张大河面对上级领导派给自己繁重任务时,环境变成了“黄昏,古河岸边的空气里有一种燃烧的气味,西边的太阳快落山了,此时的天空说黑就黑”。这展现出张大河巨大的压力和“以锦绣厂为己任”强烈的责任感。可以说作者李铁展现出复杂生活的美,生态环境的描写始终服务于小说人物、事件与情节,为枯燥乏味流水线的工业化生活带来了“一抹绿色”。小说的结尾“阳光洒了满地,道路、树木和田野上泛起绸缎般的光泽”,这种诗意化、意境化的语言唤起每位“锦绣人”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彰显出审美的魅力,展现出现实主义工业题材框架下浪漫主义的生态审美情致。
文本之美也是《锦绣》的一个审美特征。面对粗笨的机器、标准化的冶炼流程、规格固定的金属零件和流水线前工人们日复一日的重复操作,小说创新性地采用多角度叙述模式,作品中大量使用日记摘抄、安全简报、厂志等文体,这种文本审美的模式有助于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外延小说叙事,补充故事情节,增加现实质感和真实性。李铁在了解和吃透工厂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深挖所塑造意象的内涵和意蕴,这也是工业题材审美化的必由之路。李铁对于工业题材审美化的处理趋于成熟,从劳动、生态、意象等多维度阐释更趋完美,从始至终保持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和实践上的无痕。
生于东北、长于东北、立业于东北的李铁,用他对东北工业文化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和娴熟的小说技术锻造出《锦绣》这一东北工业小说的高峰,使工业题材小说获得了新的审美生命,向着新的境界和新的风光伸展。
【作者简介】
张 翠: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教授。
张 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宏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