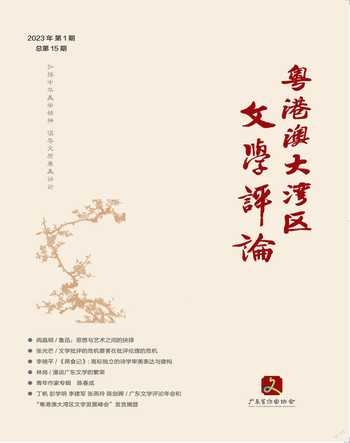论国家人格与个体人格的分裂
袁敦卫
摘要:西方亲历者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叙述使我们得以在主流文学和历史记载之外,更立体、更生动地来审视这场战争中有可能被忽略的一些历史片段和政治—文化现象。霍布斯关于国家人格与个体人格的理论工具,有助于我们切入旅华文学构造的历史情境,从而凸显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中英政治—文化结构的显在差异及其深远影响。
关键词:国家人格;个体人格;西方视角;第二次鸦片战争;爱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和深化,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进程。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说是西方列强针对近代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在任何情境下都不能否认的基本前提。但从人文角度看,战败者的历史固然沉重令人警醒,而战胜者的叙述未必就没有价值。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许多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通过日记、书信、杂记、回忆录、个人传记(有些是由后人撰写)甚至摄影和绘画等,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成为各国学者研究19世纪中国社会和文化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它们多以亲历者的线性记事为主,诸如使团访华、沿海贸易、鸦片战争、帝国内乱、传教历程、风俗民情等,事无巨细均挫于笔端,间以描写、议论和抒情,文笔可观,部分作品还具有浓厚的文学性。本文把这些对中国既有历史亲历性(非虚构性)又有一定文学性(想象性)的私人作品界定为19世纪西方人笔下的“旅华文学”(the travel writing in China)1。这一类型的文学应被视为19世纪西方文学家族的成员2。
一、旅华文学中流露的英国国家人格
以往的人文历史研究偏重于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本性来分析英国发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动机和动力问题,实际上有其局限性,因为这种分析既可能忽略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格局,也可能忽略了——同样作为资本主义强国和主要参战国,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角色意识就明显不如英国那样统一且具有人格性。“人格”正是本文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取景范围,分析某种政治—文化现象的基本切入点。
关于国家的人格性,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早在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一书中这样描述:“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这一人格是大家人人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目的在于“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1。鉴于霍布斯在书中也直接将这一抽象人格称为“国家人格”,我们不妨借以指称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具有人格意味的国家意志。与此相应,霍布斯在论述国家与个人关系时,也曾以“每一个人的人格”“自己的人格”等来表述“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欲望”。因此我们暂且把“国家人格”与“个体人格”当作一组具有相对性的理论工具引入对具体历史情境的分析,以获得某种直观效果。
在英国人看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英国国家人格的彰显。正是为了维护这一具有整体性的人格形象,英国远征军成员认为在中国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不应是偶然和草率的,都应该尽力“保持英国在东方的威望”2。譬如英国对华全权大使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1811-1863,即第八代额尔金勋爵)在许多场合都流露出其作为英国国家人格代言人的角色意识3,并自觉为凝聚和强化这一人格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抒发特定的情感。大致来看,旅华文学中的英军对国家人格的彰显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第一方面:为国家利益征战的自豪感。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已经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在某种意义上,额尔金的自豪感是以英国的国家实力以及遍布全世界的殖民地为基础的。当他于1857年11月抵达香港为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成果做准备时,在1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俩(另一人指印度总督坎宁)接下来将携起手来,“一同玩东方这盘大棋”4。在额尔金眼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等)都只是英国按照自己的国家意志来攫利取乐的“游戏场”5,而他则是由英国女王亲自挑选的高明的棋手,要将女王所“承当”的国家人格和战略意图发挥到极致。这种态度不仅在额尔金等高级官员身上存在,而且也体现在中下层军官的言行上。法军的一名翻译官在回忆录中说:“为女王干杯!……每一次当我听到不管是哪个军官、哪个政府官员为这种忠诚举杯祝酒时,我似乎立刻会在他和他的祖国之间发现一根神秘的连接线……它会让他对这个养育了他的祖国永远怀着一种甜蜜而崇高的情感”1。这让当时年仅20岁的法军翻译官埃利松(Maurice Irisson)深深被英国人的爱国情怀“振奋”和感动。可见同为参战国,英国的国家人格就明显比法国鲜明,以至伯纳·布立赛教授也不得不承认在对华远征行动中,“法国人的形象”遭到了英国人的“极力贬低”2,而这种“贬低”正是以国家人格为视角的。
第二方面:对东方民族的强烈优越感。虽然英法两国在远征行动中所彰显的国家人格并不一致,但在面对东方民族时流露出的优越感却显得高度相似,在他们眼中,东方民族几乎都是“劣等民族”和“野蛮人”。英法联军从广州经上海进抵天津、北京,不但嘲讽当时中国的几乎一切社会文化现象,如官方礼仪、吸食鸦片、妇女的小脚、男人的辫子、百姓的装束、落后的医疗条件、不守信用、缺乏爱国意识等,而且肆意贬低中国的传统医学和文化艺术。尤其令人痛惜的是,圆明园遭英法联军劫掠然后焚毁,与额尔金等人以无知和狂妄为底色的优越感是紧密相关的。他在1861年伦敦皇家艺术院的年度宴会上曾这样表明自己的心态:
反复有人问我,中国的开放,对于英国艺术的发展,是否是件好事。我的回答是,在艺术上,中国没有什么能教给我们的3。
“额尔金之火”(指焚毁圆明园)是无知和狂妄之火。这把火一方面使他遭受国内外知识和文艺界(包括法国文豪雨果等人)的严厉谴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人格一旦交由个体人格来“承当”,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个人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这种状况使霍布斯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家论中格外强调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换个角度看,额尔金贬低中国艺术的言辞,或许也是他试图减轻自己摧毁东方艺术珍宝之罪责的无力辩解。至于法国人,则一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坟墓”4,中国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5,亟需欧洲文明来改造和重建,其优越感自不待言。
第三方面:以欧洲文明同化东方的使命感。英法联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完善的军事协作机制,以二万五千人的兵力攻陷北京,对于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大国来说,难免会让人夸耀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英勇之举”6。英法联军在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之后,带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为改变中国的贫弱状况提出了一些设想。实际上有些设想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陆续在中国各大通商口岸付诸实践——按照欧洲文明的范本来改造他们中国:办学校、建医院、立教堂……以及管理上海这样完全开放的城市。战后,额尔金曾这样表述自己作为国家人格代言人在远征行动中的“使命感”:
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有勤劳的人民,将这个国家带到国际大家庭之中……依然有待我们的努力7。
中国固然需要加入“国际大家庭”,接受先进文明的洗礼,但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割地赔款接受经济剥削的不平等条约,在本质上暴露了英国国家人格的侵犯性和非正义性。这种带有侵犯性和非正义性的国家人格通常是个体人格无法左右和抗拒的,正如国家主权往往强悍于个人权利的简单相加,但个体人格在具体历史情境的分析中仍然保留着人文学上的特殊价值。
第四方面:英国国家人格在旁观者眼中的整一性。英军在东方展示国家人格的行动既有主观方面“刻意”而自发的流露,也有旁观者对这一国家人格形象的确认和强化。也就是说,英国的国家人格形象是多维建构的结果,它不但表现在精神状态和思想观念上,也表现在一切可能的物质形式上。这一建构过程在旅华文学及某些历史夹缝中同样留下了浓重的痕迹:1857年7月2日下午,额尔金勋爵乘船抵达香港,当时英国汉学家、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与洪仁玕(1822-1864,后来任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正在码头旁边的凯恩路上散步。“额尔金爵士就在船上。船进港时,‘香农与‘海军上将号相互致意,炮声如雷鸣,在山间回荡,四周景物尽陷雾中。”于是理雅各对洪仁玕说:“这就是清朝的丧钟。它对这些巨兽(Leviathan)是莫之奈何的”1。这一历史场景清楚地表明,离政治稍远的传教士已经毫无困难地从英国在东方的行动中认出了具有整一性的国家人格(Leviathan,即利维坦)。这对洪仁玕主政太平天国后加强向列强学习显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旅华文学塑造的国家人格
大幕下的个体人格
如果说国家人格从形成的那一天起,指向的就是国家的整体意志和共同利益,那么个体人格指向的则是个人在自由状态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旅华文学中,额尔金或许是功臣,但对中国人而言,额尔金却是英法联军成员中最该谴责的罪魁祸首。综合来看,额尔金大概是通过存世文字最能体现国家人格与个体人格冲突性、丰富性的矛盾体。英法联军对华远征期间,额尔金通过大量日记和书信(大部分日记还以电报形式及时传送给远在英伦岛国的额尔金夫人),反复表达了自己内心对侵略行为的反省和自责:
(一)有些人为了实现自己最为自私的目的,竟要将古老的文明踩在自己的脚下,想到此,我的心里就隐隐作痛。(1857年12月22日日记)
(二)如果有人问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机会,而我们只能答以从我们所发现或是制造的废墟中牟取利益塞满口袋,那么我们自身的良心和人类的评断都不会放过我们。(对1859年1月18日上海商会来函的回复)2
(三)英国人又要在另一个孱弱的东方民族身上施以暴行,必遭天谴……难道我为之奋斗的,只是让英国人在更为广阔的地域上去展现我们空洞的文明和信仰?(1860年5月22日日记)
(四)洗劫这样一个胜地(指圆明园)已是罪过,但更糟的是其中的浪费和破坏……战争实在可恶。你见证得越多,就会越憎恨它。(1860年10月7日日记)1
额尔金对侵华行动的愧疚和自责显然不是普遍的道德反应,而是个体人格的自然流露,因为与他相比,旅华文学的大多数作者如士官、翻译官、外交官面对中国所遭受的灾难,并未像他那样表现出过多的道德自省,有的参战者甚至还流露出中国人罪有应得、劫掠理所当然的心理。法军翻译官埃利松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
在面包店抢走一块面包的人是一个小偷,从另一个国家抢走五十亿的国家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洗劫圆明园是合法的,因为它发生在战争时期。这种原则是不容置疑的2。
虽然埃利松在回忆录中也写到为圆明园的劫难“心在流血”,但并不是要否定上述“原则”,而是目睹联军的浪费和破坏比肆意掠夺更让他痛心。埃利松的看法极有可能来自他的前辈同胞霍布斯,因为卡尔·施米特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霍布斯的思想和概念“浸透”了19世纪的欧洲法制国家3。这些思想可以这样表述:“在一个没有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4但我们还是看到,即便在國与国之间的公共权力缺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额尔金所代表的个体远比埃利松所代表的个体更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比现代意味更强的公共权力的约束更容易抵达个人内心。按照霍布斯的理论构想,在人的统治不能奏效的地方,应该服从上帝的统治;而在一切不违反神律的事情上,臣民应当绝对服从承当国家人格的主权者5。在这一点上,英国外交官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体现的个体人格近乎是一个极端的类型。
巴夏礼在中国先后担任翻译、外交官长达25年,曾目睹《南京条约》在英舰皋华丽号的签约仪式,当时年仅14岁。从他成为驻华外交官以来,忠实严酷地执行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以至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毫不妥协地以铁血手段来保障条约权利的代名词”6。他不但鄙视晚清政府的治理能力,仇视新生的太平天国政权,甚至轻视中国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他也是极力主张焚毁圆明园的西方人之一,对中国既无好感,从他的日记和信函中也几乎看不出在国家人格大幕下个体人格面对战争罪恶时的柔软和丰富——虽然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的性质和方向,恰与额尔金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旅华文学中国家人格与
个体人格的分裂
国家人格与个体人格既有融合的一面,也有冲撞的一面。旅华文学中国家人格与个体人格在历史情境中的冲撞与分裂,显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英政治—文化结构的内在差异,而且这一差异仍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头来考察“国家人格”这一概念所取用的思想资源——霍布斯所描述的“利维坦(Leviathan)”。在霍布斯看来,利维坦这个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的庞然大物是一个“人造的人”:主权是它的“灵魂”,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公平和法律是它的“理智”和“意志”,司法、行政人员等是它的“关节”,而内战则是它的“死亡”1。霍布斯提出利维坦这一神话般的“巨灵”形象(神—人—兽的合体),本意在于避免自然状态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以一个理性集权国家的理性统一体来对抗中世纪的多元主义”2。
霍布斯所指的中世纪的多元主义主要包括教会、国内的叛乱、各种利益组织等“间接”权力。虽然各国状况迥异,但至少我们在旅华文学中看到,英法联军代表各自国家来实现其主权意志时,个体人格的差异和分化导致了一种似乎更为现代的“多元主义”。从额尔金的自述来看,他下令焚毁圆明园更多体现的是其个人好恶和价值判断:惩戒不能针对无辜的“中国人民”,而应该“针对清朝皇帝”3。更何况他认为中国艺术“没有什么能教给我们的”。而巴夏礼持此主张则是因为圆明园“是我们的国人最初受到拷问和虐待的地方”4。鉴于巴夏礼也是在《北京条约》签订前被清政府羁押、虐待于圆明园的联军成员之一,他内心对圆明园的痛恨是不难揣测的。至于参与劫掠圆明园的多数英军普通士兵来说,在个体人格上对他们提出过高的期望,“无异于要求他们具有超人的自控能力”,于是在圆明园的高墙内,已经完全失控的英法联军成员迎来了“一个士兵职业生涯中或许可称之为‘精神失控的时刻”5。也就是说,驱使士兵劫掠的是个人欲望而非任何政治理念。虽然额尔金和巴夏礼焚烧圆明园的举动促成了签约,符合英国扩大在华利益的国家意志,但毕竟也使额尔金等人的个体人格受到多方面的谴责,也间接打击了英国的国家人格——正如雨果称英法联军为“强盗”。以霍布斯的理论眼光来看,英国远征军在北京的作为既不代表教会,也不属于叛乱,而似乎应该归结为临时利益组织(即军队)的自行其是。而这种行为是不会杀死“利维坦”这只国家巨兽的。
换个角度看,在联军攻陷北京前后,英、法、美等国驻华政界人士对盘踞在南京的太平天国政权逐步形成了比较恶劣的印象。他们视太平军为“渣滓”“海盗”“暴徒”和“害虫”,在政治上倾向于联合清政府来扑灭叛乱,这既有维护各自国家既得利益的考量,也不排除带有个人情感和主观印象。假如把当时的中国也看作一个具有人格意味的利维坦,那么在严重的叛乱冲击下,它已经死了。与英国不同的是,它面临的挑战除了太平天国叛乱,还包括长期存在的满汉对立、列强入侵以及众多缺乏国家观念、个体人格比较模糊的普通民众:他们与国家之间似乎从未建立起霍布斯所称的“契约”观念,以至额尔金觉得“整个民心对这场冲突(指太平天国战争)的双方都不是很关注”6。巴夏礼在1861年3月28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他在安徽芜湖听到一个农民向他表达一个在战争期间被无数次重述的观点:这个农民“认为官军(指清军)和叛军(指太平军)没什么两样,他在这两者底下都没过上好日子”1。国家人格的分裂、弱化与个体人格的模糊、冷漠交织在一起,这大体上就是西方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所看到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状况,并且成为旅华文学对中国的主流印象。
特别有意味的是,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他们从“钢铁时代”带入“电气时代”。新的技术改变了国家人格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个人的工作方式。在晚清政坛极其活跃的英国外交官巴夏礼也深刻感受到了新技术在逐渐改变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现代外交中电报线的存在破坏了外交使节工作的主导权”,因为伦敦唐宁街的思考代替了他们的思考,以至“公使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行”2。向来在外交活动中善于发挥“个人影响力”的巴夏礼们遇到了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味的问题:中立化的制度和技术正在逐步侵蚀传统意义上的人格化的“利維坦”。而这正是卡尔·施米特在深入探究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时思考过的一个问题:曾经作为巨灵、充满生机的利维坦“对一种总体技术的思想方式施加不了任何可怕的影响”,而“法规本身也转而变作驯服利维坦、‘用钩子钩住利维坦鼻子的技术手段”3。个体人格在日益以机械装置和机器形象出现的国家人格面前,变得苍白无力和微不足道。因为这些带有个人情感色彩和偶然因素的东西也都被卷入机械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巴夏礼似乎比额尔金更好地见证了英国这个“巨灵型”利维坦向“技术型”利维坦演变的轨迹。而且他自己就是这台庞大的国家人格之机械装置上的一只零件,一台冷酷的工作机器,以至被当时的西方外交界视为“工作狂”4。在某种意义上,“工作狂”乃是个体人格被国家人格全面吸收后的躯壳。
四、国人的“爱国”与“不爱国”:
旅华文学的反向探讨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及其他旅华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记录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成员在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两岸观察到的一个特殊又常见的现象:许多中国人的国家意识非常淡薄,简单说,他们不爱国,或者说不知道怎样爱国。以下是西方人记录下来的四个场景或案例:
(一)1857年12月11日,有艘炮舰在离广州城一箭之遥的地方搁了浅,炮舰上的指挥官立即召唤一帮正在驳岸上的中国人,叫他们把搁浅的炮舰推下水。“这帮人竟然二话没说,立刻干了起来!”5
(二)1860年4月21日,英法联军不费一枪一弹攻占了舟山群岛。当法国人要离开时,当地百姓在乡绅的带领下,“一直送到码头,以表示他们依依不舍的伤感之情”。而宁波的民众听说联军占领舟山之后,马上派代表来见欧洲的将军们,“抱怨我们为什么不先占领宁波”1。
(三)1860年夏季英法联军集结到天津白河口,准备攻击大沽炮台,攻入北京。一名被派来会见法国公使葛罗男爵的清朝官员随口说,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在意联军舰队会不会炮轰大沽要塞,因为防守要塞的军人“全是汉人”2。
(四)1860年8月3日,由英法联军从广州雇佣的中国苦力闯入天津北塘一个居民的家里,抢劫了他们的财物,还用暴力威逼他们,最后六个女人(其中四个服毒)死了,只有一个男人活了下来。巴夏礼认为英国人的行为并不好,法国人更糟,军队的苦力“比法国人还要过分”3。
仅仅从“西方视角”来判定当时的中国人“不爱国”显然是不够审慎的,因为上述的四个例子所反映的政治—文化状况并不相同。
第(一)个例子既可能说明中国老百姓“单纯”,也可能说明他们“狡猾”。当他们对某个政权严重不满的时候,他们并不太在意应由哪支力量(甚至包括洋人)来推翻这个政权,必要时他们甚至愿意帮上一把。譬如英法联军在进攻天津北塘的战斗中,中国苦力本没有为英法联军作战的义务,但他们还是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攻打炮台的行动,因为他们不喜欢满人的政权。
第(二)个例子,我们可以部分借用霍布斯的解释:当臣民失去了原有主权者的保护(当时东部沿海居民常受海盗侵害而清政府无力清剿)而落在征服者手中时,他们宁愿牺牲部分财产以示服从而获得征服者的友好对待,也不愿在不可能获胜的情况下选择抵抗而失去全部财产。这是普通人的正常想法。在霍布斯看来,他们这样做不能视为“非法”4,除非他们具有极其强烈的国家观念,愿意为了维护国家人格的统一而牺牲个人利益。只是在满汉对立的处境下,“有民族,无国家”的状况显然无法培养统一的国家观念。
第(三)个例子说明满族统治者并没有从国家人格的高度来理解主权问题。显得悖谬的是,满清政权这个国家人格的承当者一开始就面临着“利维坦”被民族矛盾从内部绞杀的危险。
第(四)个例子,因为中国苦力知道自己受雇于英法联军,即使他们伤害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同胞),也不会受到公共权力的惩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苦力在天津北塘碰到的问题与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碰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没有强大的公共权力,没有作为“必要之恶”存在的利维坦,一切人将成为一切人的灾难,没有种族和国界之分。可为佐证的是,圆明园遭劫后,英法联军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带着战利品返回自己的国家,有人沿途(比如在香港)出售,不少人因此一夜暴富,而趁着联军劫掠之机浑水摸鱼的海淀周边的百姓都遭到了清政府的严厉清算。可见清政府的公共权力无法施及英法联军,对力量弱小的帝国臣民仍然是有效的。
總而言之,在西方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观察中,中国人的“不爱国”本质上并不是单纯的思想观念问题,而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结构的反映,是国家人格与个体人格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非常态滋生和组合。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细致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土壤,比简单划分“爱国”或“不爱国”的阵营要切实得多。如果说“不爱国”确实是一种“无知”,那么这种无知“有大部分要归罪于主权者”,其过失在于没有使人民受到更好的教导1。
旅华文学中的多部作品都提到:英法联军的随军医生在通州附近的张家湾营地,曾经利用他们掌握的现代外科技术为部分受伤的清军士兵截肢(这大概是中国人第一次集体接受外科手术),然而这些好不容易活过来的士兵大部分“仍死于国人的遗弃和虐待”2。可以想见,他们的遭遇必然与当时许多人所持的“爱国”或“不爱国”的国家人格有关——接受外国人尤其是侵略者的帮助就是“不爱国”,“遗弃”“虐待”接受过敌人治疗的士兵反倒可能是“爱国”的表现。所幸的是,这一细节至少还表明:在公共权力缺席的时空里,人类似乎并不必然堕入霍布斯所称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毕竟个体人格凭依的精神世界有时比国家人格还要大。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不少西方旅华文学的作者都表现出个体人格与国家人格的分裂,体现了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但并不能改变侵略战争的本质,更与所谓的“反战文学”相距甚远。在抗日战争(1931—1945)期间及战后,日本出现了大量“战记”类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可以窥测到作家的‘欲望与国家的‘欲望相互协调或碰撞摩擦的不同侧面”3,与西方旅华文化的情感倾向有相似处。
从深层文化心理来看,这种闪耀着人道主义色彩的个体人格恰恰是对国家人格缺陷的弥补,正如周宁所说:“只有通过这种文化忏悔机制,才能达成并维持一种道德平衡,使(西方侵略性的)扩张造成的文化紧张不至于崩溃。”而这种“包容对立面的结构”,从自我监督的民主政治到自我否定的文化批评,始终是“西方现代文明最有活力的结构”4。正因只是一种补偿—平衡机制,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西方旅华文学不可能从根本上反思进而反对战争:第一,为何会产生战争?第二,有无比战争更好的解决国际与族群冲突的方法?第三,假如战争不可避免,如何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滥杀、掳掠、奸淫等灾难?5第四,或许更重要的是,如何不通过战争也能学会尊重另一种异质的文明?这或许才是我们研究西方旅华文学的落脚点。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行政学院文化与社会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