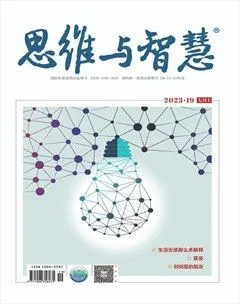柴与火的往事
卢海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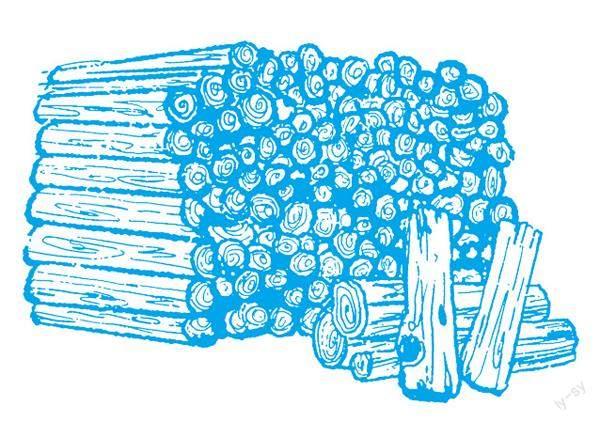
一条泥泞的村路忽高忽低由北向南蜿蜒蛇行。北面地势高,村里人称之为“北头大坎”。住在“坎上”的住户稀稀落落,民房一律建在村路东侧,就势盖在山脚下。西侧为沼泽地,靠近道边的地方,是每家的巨大粪堆,还有一两个柴垛。居住在山区,最不缺的就是柴,柴垛高高屹立,是家人的脸面。
幼年学做活,从给母亲架火开始。母亲的要求,柴一定要撅折,撅折的柴草可以板板正正投进灶里,同时,折过来的细枝聚集在一起,更容易引燃,且不占地方,干净利索。
撅柴是个难题,母亲不允许我们把柴放到膝盖上撅,怕磨坏裤子,要用脚踩着撅,根据杠杆原理,用膝盖省力,用脚踩费力。离开母亲监督的眼神,我立刻把干柴放到膝盖上,两只手向后用力,膝盖努力往前顶,干柴在两种力的作用下应声折断。陈年的灰尘像黄土飞舞,裤子一下变了颜色。最难撅的是柞树棵子,又粗壮又质地坚韧,有时用力过猛,一屁股坐到地上,膝盖被硌得疼痛难忍,柴却并没有被撅折。
倘若煮粥,一把毛柴就好。煮大子、高粱米饭,就要架劈柴柈子。柈子火硬,架上一灶,可以端个簸箕去菜园里摘生菜,拔水萝卜,拔小葱,去门口的小河洗去泥沙,再用井水冲洗干净。
大子和高粱米饭都要焐。初秋,菜园子里多的是黄瓜、辣椒、洋葱和新蒜,黄瓜擦丝,拌大酱,辣椒、洋葱和新蒜洗了,装到小盆子里,直接拿上桌,连同生菜水萝卜小葱……这些都是蘸酱菜,都是大子和高粱米饭的绝配。倘若天热,还可以用凉水把饭投凉,来一碗爽口爽心的水捞饭。
小孩子惦记的是烤苞米。劈柴柈子燃烧之后,满灶膛都是火炭,掰几棒苞米扔进灶坑里,放在炭火上烤,兄弟姊妹蹲在灶坑门前争争抢抢,谁抢了谁的苞米,谁占了谁的火炭,谁把谁的苞米挤进了灰堆里……苞米吸收炭火最后的光芒,眼看火炭黑下去,大姐便拿了盖帘或是簸箕对着灶坑扇动,火炭瞬间红艳,苞米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香甜的味道直钻进人的鼻孔,孩子们馋涎欲滴。
出去采山菜的孩子掏了一窝鸟蛋,直接放到炭火里一烧,蛋就炸裂了,也不知谁想出的办法,把鸟蛋放到葱叶里烧。母亲养的半大鸡崽被老鹰啄死了,孩子们掰下两只大腿,放到灶坑里烧……等到火炭化尽,灰土里藏着最后的火星子,还可以埋几个土豆地瓜,继续烧。
那时候,我们的小零食不在超市,在灶膛里。
母亲每天睡觉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去柴垛抱柴回家。有时,一家人已经睡下,母亲忽然起身问:“抱柴火了吗?”阴天打雷,母亲立刻紧张起来,要抱好几捆柴放到厨房。
每一年冬天,父亲都要出去打柴,新打的柴垒在原来的柴垛上。一年一年,柴垛矮了,又高了,垛底的柴年头太久,已经朽烂,成了蛇和黄鼬的家园。
柴垛摞得紧实,父亲常常将几捆柴放到柴垛边上。夏天,我们去抱柴,常常遇见蛇在柴捆上晒太阳,有时,蛇钻进柴捆里,被我们抱回家,蛇失了广阔天地,吓得藏进我们的碗柜。
等我们打开碗柜,看见一盘蛇吐著芯子,又是一种肝胆俱裂的恐惧。
没有电炊具,没有煤和燃气,柴与火给了我们所有的原始美味,给我们的生活制造了数不清的惊喜。
(编辑 兔咪/图 槿喑)
- 思维与智慧·上半月的其它文章
- 轮椅之上,乘风破浪
- 害怕输与侥幸赢
- 什么时候需要过河拆桥
- 夏日山中
- 生日
- 读书的“入”与“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