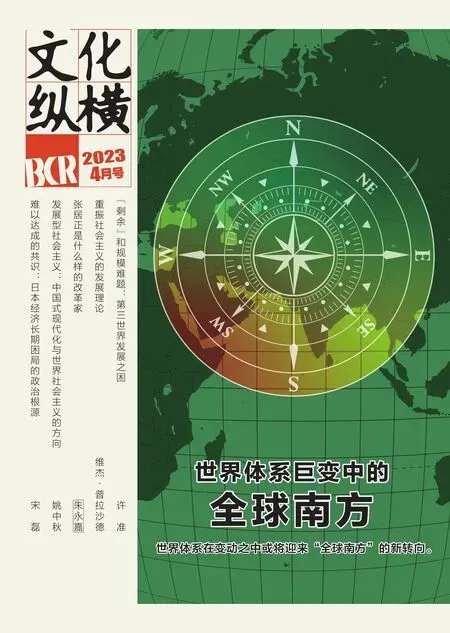全球变局召唤新理论
——从朱云汉的理论贡献说起
瞿宛文
朱云汉教授近日辞世,引发了广泛的悼念与感怀,部分应是因为他是如今极少数能够为我们在面对今日巨大变局时,及时提供犀利的分析及合理的见解的学者。而这稀少性或也呈现了我们面对变局的困难状态。就是非西方地区,尤其包括先发展起来的中国与东亚地区的知识界,对于如何理解进而因应这全球变局,缺乏足够的准备。毕竟,对后进者而言,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与积累,远比经济领域的追赶要困难缓慢得多。
简言之,如今的变局,不单涉及短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混乱,也涉及战后持续数十多年美国霸权的衰落甚而变动,更涉及数百年来西方文明对世界主导权的逐步下降,变动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战后建立起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自由民主与自由经济等,以及西方霸权体系惯性思维下认为新兴的中国必然是要争夺霸权的预设,可说仍然强力地引领着世界对变局的理解。因此,我们要去认识变局并进而设法建立新局,所惯用的既定理解框架却是难以因应的,所拥有的知识准备是远远不足够的,挑战是艰巨的。
中国复兴是国际秩序改变的基础
近年来,国际秩序大幅的动荡,一方面是源于西方本身的日渐衰弱,尤其是美国霸权的实力与领导力的下降,日益难以维持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中国的复兴,中国在实质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上有了十足的成长,并且是相对地独立于美国霸权控制的。中国迅速兴起后,虽一再宣示不寻求霸权,但仍引发了衰弱中的西方的危机感,而至今,霸主美国则日益显现出压制中国兴起的企图,而不是包容适应,这更加深了既有秩序的动荡与不确定性。
全球现实力量版图的变动,也可预见地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二战”后,美国霸权提出了一套“普世性的”现代化论述,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只要依循这个理想模式,就能追随西方进而成功发展。
然而至今,在政治现代化方面,第三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已几近全面失败,而并不依循这一模式的中国则展现了强大的国家能力,成功地维持统治并推动发展。在经济发展方面,西方标榜的自由放任模式,并没有促成后发地区发展经济,反而是得以成功追赶的东亚,都采取了国家干预的政策模式。不过,中国的复兴虽是最重要的变化,但是理论上的说法并不完备,而未来如何发展,国际秩序的愿景为何,仍待进一步摸索。意识形态上的改变与创新是艰巨的工作,本文仅在此先探讨既定的认识框架,检视其是如何继续影响着我们。
缺乏分析秩序大变动的理论工具
就理解近来国际秩序的变化而言,通常“趋势论”甚为普遍,通用名词如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区域化、脱钩化、碎片化等。这些趋势论背后主要假设是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因素是主要的决定因素。此外,在科技与经济决定的趋势之外,政治与战争导致的秩序变化,包括中美对峙等,虽会影响趋势走向,但被视为必须接受的外在因素,即使要分析也是常被纳入国际博弈的赛局讨论框架,似乎隐含着对丛林法则的接纳。在现今主流社会科学中,技术决定论据有主导性地位,高度影响着世界。例如,一般会认为西方率先发展了现代科技,进而推动了工业革命,因此得以主导全世界。趋势论与技术决定论关注在既定秩序之下的变化,把技术变化当作外在变数。这背后隐含的世界观其实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相类似,也还是西方线性文明进步论,把“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当作是一种人类的正常,因此不需要探讨既定秩序的历史来源,不需要历史化的视野。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人类进步的必然或正常,而是由霸主美国运用其主导世界的霸权力量所主导制定的。
然而,现在全球的秩序开始有了大变动,不可能再宣称历史已终结,而何谓国际文明秩序的“正常”再次成为加上问号的议题。但是,要如何去分析,却缺乏合适的理论与工具,因为通行的理论多半假设了原先看似稳定的既有秩序为正常。因此,例如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出乎国际经济学界意料的,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掀起的贸易战与技术战,也是违背既有经济学理论的,而政治学理论也拙于解释。如前述,朱云汉教授犀利分析时局的能力之所以稀有,也正显示既有理论的不足。换言之,我们必须全面检讨通行的理论,理解它们的时代局限性,才能开始理解现今的变局。
我们必须采取历史化的视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人类进步的必然或正常,而是由霸主美国运用其主导世界的霸权力量所主导制定的。现今世界秩序的动荡,其中关键因素是霸主美国如何应对自身力量的衰弱,如何试图挽回。美国设计国际秩序时运用到一套意识形态作为支持,也涉及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历史性所累积的立国精神、制度与组织。我们需要一套霸权理论来理解这一切。
中国崛起挑战既有霸权理论
我们需要借助霸权理论来理解现今这一历史时刻,这个霸权的衰弱并更动国际秩序的时刻。而阿瑞基奠基于布罗代尔三卷本《15 至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所推导出的霸权理论正适合我们的需要。[1]
首先,此处的“霸权”不是一般性的霸权,而是有特定历史属性的,是指近数百年来西欧形成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其秩序是由一个霸权国主导。简言之,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多国系统下国际竞争激烈,战争不断,善于利用经济与军事资源者较能胜出,因此推动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结合,进而催生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体系有其周期,每一个周期都有一个主导的霸权,霸权除了基于自身优势的实力之外,也必须建立有效的国际新秩序。
体系与霸权的转移互相联系,至今共曾有过北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四轮霸权周期。在每个周期的晚期阶段,资本主义体系会进入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的“秋天”阶段,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与政治秩序混乱加剧,国际秩序也开始动荡。这动荡会持续到新的霸权出现,其能领导世界建立新的体系秩序,新的组织。在这数百年来,这四个周期显现出体系涵盖范围越趋扩大,权力越趋集中,组织越趋复杂的趋势。然而资本与国家各有目的,这虽是一个有强势推动力的制度,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合,同时现今资本日益增强的流动性,对国家的控制力与国际秩序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
美国在“二战”后从英国接手霸权,建立起新的体系秩序。20 世纪70 年代起,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金融扩张和权力衰落的阶段。与以往霸权转移过程不同,此次新的经济力量虽于东方兴起,但旧霸权仍然握有军事与金融力量。同时,挑战者第一次来自非西方世界,增加了霸权转型的不确定性。
我们需要对霸权有更多的理解,探索其蓝图、动力与目标,而不是假设一切都是丛林法则。
我们需要对霸权有更多的理解,探索其蓝图、动力与目标,而不是假设一切都是丛林法则。每个霸权的设计蓝图并不完全相同,就霸权转移而言,过去转移的经验并不代表是必然的结果。霸权转移是否必然会发生战争?在过去,霸权转移确实都涉及战争,但不一定是在新旧霸权之间。如英国在两次大战中对付的挑战者是德国。但最终接手的是另一挑战者——美国,英美之间没有打仗,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

朱云汉教授2015 年出版的著作《高思在云》
更重要的是,阿瑞基指认的霸权,是西欧数百年发展出来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每次霸权的转移都源自资本循环的周期,以及资本主义先进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霸权的争夺战都是激烈而残酷的,即如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显示。然而,参与竞争者都是西欧这个体系生成过程的共同参与者,它们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共享相同的文明、价值与游戏规则,共享整个体系的不断扩张的倾向,包括领土国家对领土以及资本对利润的不断扩张的倾向。同时,在惨烈的争夺战之后,它们接受新霸主,重启体系。因此,它们自然地会预设中国兴起就是为了要争夺这个霸权。
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欧的文明,经由百多年的转型,终于成功地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在各方面累积了力量,但是绝不意谓中国完全接受西欧的文明价值与取向。中国的转型主要是出于自卫,而非源于自身扩张的需求。如阿瑞基所正确指出的,中国文明本身没有向外扩张寻求称霸的传统。这正是此次霸权变动与之前的三次霸权转移的基本不同之处。既然中国不寻求霸权,此次就不会是霸权“转移”,而是西方霸权体系的变动。
阿瑞基认为未来有三种可能:一、旧霸主成功压制新力量,重建秩序;二、旧霸主包容变化,新旧并存,建立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三、旧霸主不接受变化但未能压制新力量,世界陷入系统性混乱。他认为结果没有必然性,他期待的是第二种结果,并且期许中国能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国际秩序。[2]在他逝世后这十多年来,霸权政治的发展让人难以乐观,美国自身的弱化却加强了其以剩余力量维护霸权的企图。而中国要如何因应这场霸权变动的竞争,要如何建立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愿景,并非自明,却已经是迫在眉睫的挑战。
中国的转型主要是出于自卫,而非源于自身扩张的需求。如阿瑞基所正确指出的,中国文明本身没有向外扩张寻求称霸的传统。
文明兴衰的视角
数百年来西方文明主导世界,霸权一直在西方国家之间转移,无论它们互相之间的争夺如何激烈残酷,但每一次新霸权仍得以建立新秩序,并被其他西方国家接受。此次挑战来自东方,对于双方都是挑战。西方要从占据了数百年的世界优势主导者的位置上下来,在心理上无疑需要极大的调整。这变化对于中国也是极大的挑战。除如上所述,至今大家仍把“二战”后美国霸权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因而必须对此反思之外,还需要重新回到文明兴衰的问题。重点是要将数百年来的西方文明放在人类历史长流、文明兴衰的角度来思考。
百多年前,在西方入侵中国之际,中国正衰弱中、力不如人、难以抵挡。为了自立自强,五四带来全盘西化的方向。至今中国正在复兴,而西方正在衰弱。重新肯定中国传统文明,虽有助于恢复自信,然而却远不足够。中国在学习西方后已有大幅度的改变,文明永远在变动中,静态比较并不足够,还须将原先学习的西方模式相对化,认识到文明有兴衰,包括西方与中国文明。比较不同的文明必然是一件复杂且不易做得好的工作,不过将文明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比较视野,应该是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下。
迈克尔·曼曾比较过西欧与中国文明,[3]他认为西欧是“多权力行动者的文明”,多国体制激烈竞争下,发展出诸多制衡机制与规范性团结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催生了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文明制度。但这也是一个造成无止境的战争、并持续扩张将战争转嫁他人的文明。而中国“这个过于保守的国家对秩序的迷恋似乎为其帝国发展途径强加了许多限制”,但相较于欧洲,确实“较少发动战争、较少屠戮土著居民,这也是先进文明的一种标志”。他也表示对这两种社会发展选项,他尚未做足够的研究来做评判及选择。他或因谨慎而未对两种文明孰优孰劣做出评判。这评判虽甚为困难,却已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学习西方后已有大幅度的改变,文明永远在变动中,静态比较并不足够,还须将原先学习的西方模式相对化,认识到文明有兴衰。
如前述,西方资本与国家结合的资本主义体系,给予资本发展的空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业文明。但发展至今,这一模式的问题日渐凸显,国家日益难以约束跨国资本,民怨多以右翼民粹形式出现,尚难预见西方内部能集结反制资本的力量来改良体制。此外,资本利益驱动的生产力进步,虽带来日新月异的创新,但也呈现出人类社会对科技越发难以驾驭的风险。
相对照的,如布罗代尔与阿瑞基等学者所言,以往千百年来,中国发展出大一统的强势政治力量主导的统治模式,着重稳定不主动向外扩张,由官员管理资本,限制了商业的发展。[4]至今,中国高度利用了国家主导模式的优势,同时也给予各种形式的资本发展空间,集中力量快速追赶,已成功发展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高度嵌入了国际经济体系。然而,相较于西方早已发展出的国家与资本共享不断扩张的倾向,中国如今要如何界定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以及中国对外的关系?如何在维系市场机制运作的前提下,避免被资本不断扩张的倾向所驱动?如何在自身不向外扩张的文明基因上,建立起有活力的全球市场经济,内部外部共荣共存的世界体系?
换言之,数百年后,西方模式的优缺点已同时显现。中国学习西方,调整了自身的模式,然而进一步的发展牵涉更艰难的选择。
结语
如朱云汉教授曾清楚地指出,中国正开始复兴,然则在话语权上,美国主导的相关说法却仍甚为通行,亦即认为中国的所作所为,皆违反了美国所界定的普世标准,并且认定中国正企图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而我们要理解当今全球变局,正是要接续朱云汉教授未完成的工作,全面检讨这些通行的说法,寻求一个不同的未来的可能性。
反思的重点是认识到既有意识形态是美国霸权的相伴产品,更需要理解其历史阶段的性质,并努力脱离其框架。通行论述是去历史化的,仍是源自历史终结论式的思维:一则是将西方文明与战后国际秩序当作是自然秩序,再则也是将这数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逻辑,视为人类的正常。我们必须将其历史化,认识到西欧资本主义体系及其霸权,只是人类历史的一环,目前也正开始走向衰弱。如此才能脱离西方霸权思维的惯性,从而理解现今是一个历史转变时刻,涉及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型,也涉及中国这个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如何在自身传统中寻求资源,寻求一个不同于以往西方霸权体系主导的国际秩序,改变霸权争夺的逻辑,探索中国在世界中的合宜的位置。这挑战无疑是艰巨的,但也无可逃避。
寻求一个不同于以往西方霸权体系主导的国际秩序,改变霸权争夺的逻辑,探索中国在世界中的合宜的位置。这挑战无疑是艰巨的,但也无可逃避。
注释:
[1] 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 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笔者曾撰文介绍此书及相关说法,参见瞿宛文:《霸权还会转移吗?——重读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载《文化纵横》2022 年第5 期。
[2]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
[3]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来源与赵鼎新对中国历史的解读》,载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巨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附录,第499~509 页。
[4] 参见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巨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