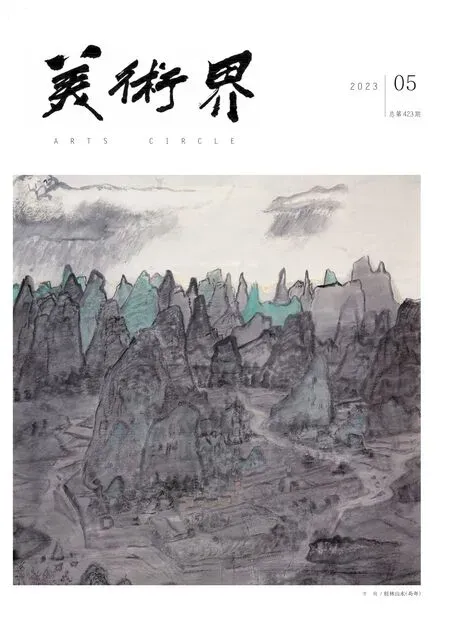从『笔墨时期』到『水墨时代』(3)
刘进安
从中国画的演变轨迹来看,真正改变和撬动中国画传统的是现代文明对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为此付出努力并把艺术的另一种方式带到中国画内的是以林风眠为代表的先辈们。在这个时期,无论是油画家、版画家还是留洋归来的中国画人,其观点的意义远大于我们对作品现实的理解,从他们的身上不仅看到了中国画走向“现当代”的可能性,也让中国画人看到了现代文明对艺术的作用远远大于艺术自身的演绎能力。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文明才是提升和改变一个事物的主要动力。

刘进安/米脂 纸本水墨68cm×56cm 2021年
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百年间,“中西问题”成了社会各行各业的主要问题,甚至是反复纠正和探讨的问题,最起码我们是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中西问题”的关注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话题或文化问题。所以,在文化艺术里曾经出现的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思潮和运动,都是围绕着这个“中西”问题此起彼伏争吵不断,直至今日“中西”关系与文化问题依然是“学术”的主要问题。是西方文化侵害了我们,和我们过不去,还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与自作多情?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双方在认知上的差异与不同。
其实,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艺术文明”对于文化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关系中没有(特别的原因)或因为“技术”成了社会问题,文化的改变与进步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这是“艺术文明”必备的前提。所以,在中国画领域之内,能够领悟此道者是由先辈林风眠们和之后的李可染、吴冠中、卢沉、周思聪、朱振庚等一批中坚力量,他们致力于中国画的变化和改变,他们创造了新语言、新笔墨和新的水墨形式。秉持着这份执着和努力,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画从创作到教学的专业化系统,具体地改变了中国画造型方式和审美方向,在笔墨方法和西方技术关系中创造性地让“笔墨”走向“水墨”并形成标准化格式,把两种元素进行了积极有效地分解和归类。如果说中国画有“转型”一说的话,这代人的努力给予了很好的证明。
应该承认,他们既是传统绘画的沿革者又是中国现代水墨艺术的创造者。从“笔墨时期”到“水墨时代”的实践与衔接由他们完成了艺术的基本形态,“水墨”从“笔墨”中脱身出来由水墨走向艺术,走向现实。笔墨与水墨相融相通,画家与生活相关相对应,这个时期中国画条理清晰,取向明确,也相得益彰。
在这之后,50、60后画家继承了上几代人的研究方法和创作习惯,在画面结构、表现方式、视觉艺术等方面创造了比较个性化的图式,同时也使“笔墨”重新回到技术位置,并强调了水墨语言可以“特别突出”的特点,整体来说“水墨”格局似乎往前又走了一步。当然,技术性游戏与执着的技术在这一代人身上已经根深蒂固,留恋技法的美感也很难更改,这也就意味着画家在表达时受限于技术影响而不能做到有的放矢。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实验水墨”“新水墨”“现代水墨”等为主体的学术或主张其技术性作用依旧是这些作品的主要成分。
其实,50、60后画家的独立创作与独立追求是这一代人的基本点。他们用水墨的方式阐释笔墨的可能性,用另外一种方法说明“水墨”具有的意义,以“水墨”为立足点展开的研究和吸收借鉴的“水墨”是有本质区别的。
几年前,我曾用“社会型、文人型、文化型”说明中国画当下的现实样态。社会型是指以服务功能为主体的创作方式;文人型是以重复、回归传统图式为目标的类型;文化型则是上述以水墨研究和创造中国画为主体的类型,这条线索虽然在现实中只是其中之一,或是有褒有贬的类型,但它的存在为中国画还有“正常”的一面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文化类型”遵守的是艺术规律,坚持的是独立价值,以艺术本体作为创造旨要,排除非艺术问题的指导与影响,并以个性的方式、艺术和文化的方式阐释生活与社会,这在中国画传统和历史中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