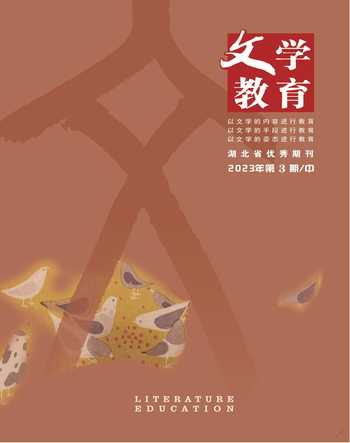忆父亲

1
2022年1月23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天,距他八十七岁生日相差十七天。
从医学角度讲,父亲是无疾而终。但对父亲而言,却是他始料未及的。父亲一向身体很好,他曾说过要活到一百岁。向着这一目标,他打太极拳,快步走路,外出旅游,热心老年人活动,与母亲一起经营小菜园,坚持不请保姆,凡能力所能及的事都自己去做。我们全家以及父亲的朋友都认为,父亲身体好、心态好、为人好,有这“三好”做底色,父亲怎么也能活到一百岁呀。
可是,父亲这架机器的零部件,终不像其他长寿老人一样能够持续正常运转。父亲的学生——中医王荣涛几次上门诊疗,结论均是脾胃皆虚,阴阳不接。母亲问其有无扳过来的希望?王医生如实相告,老師脉象不佳,肝、心、脾、肺、肾功能整体衰退,只能用些调理脾胃的药予以维系。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以父母身体健康为骄傲。自2015年始,父亲每年都携母亲去海南过冬。2021年,两位老人在海南过罢春节,被外甥天添接至中山小居,直到4月中旬才回保康。经停襄阳时,父亲只是说腿脚没过去那么有力了。“十一”长假,我与大妹分别从襄阳和武汉回家看望二老,其间,腿脚无力的父亲尚能同我们一起到酒店用餐。
而回襄阳仅仅一周,母亲即打来电话说父亲的耳朵忽然听不见了,腿脚也随之难能自主行动。我安慰母亲说总有办法治疗的。我心里清楚,8月末,父亲来市里做全面检查,医生说,老人家没有任何基础病,常见的“三高”全无,主要就是脏器自然老化衰退,注意加强营养、平和心态、适当运动。父亲并无致命顽疾,这是我们最放心的。可是,王医生的诊断也是准确的。因为脾胃双虚,饮食不易吸收,营养难以跟上,短时间内,父亲本就消瘦的身体益发瘦得脱了形,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辛苦了母亲、弟弟与小妹。
腊月二十,我与母亲通话,母亲说,你年底事多,这个双休就不要往回跑了,但要做好思想准备,争取挨过年关吧。当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总担心着什么。凌晨七时,手机响起,一种不祥之感掠过心头。果然,母亲悲伤地说:“你爸走了。”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但听到从母亲口中说出来的这四个字,我的眼泪一下子溢满了眼眶,为父为子六十载,怎会如此之快地就阴阳两隔了呢?
赶回保康,弟弟、小妹夫已为父亲做好了入殓善后,我跪倒在父亲的灵柩前放声大哭,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与痛苦如同刀搅剑刮,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众亲扶起我说,先节哀,还要你拿主意商定下葬时间呢。弟弟说,白事先生讲最近四五天皆不宜出殡。我说,老爸一生不信迷信,不怕鬼神,魂兮归去,入土为安,尊重必要的下葬讲究,让老爸安息吧。
1月25日凌晨,送父亲上山后,我们兄妹四家齐齐回到母亲身边,簇拥着母亲一起为父亲祈祷,祝他在天堂一路好走。
母亲哽咽道:“你们老爸走了,我的天空就塌了。但你们老爸走了我一点也不害怕,就像他还在这个家里一样。这一生,你们老爸从没与我红过脸,他性格直爽,生活节俭,待人真诚,对人从无二心。一路走到现在,我们彼此吸引、相互支撑的莫过于此。也许,这就叫作‘做人吧”。
在充满哀痛与思念的氛围里,母亲声轻音弱的话语,却如洪钟大吕,震撼了我们所有依偎在她身旁的晚辈的心灵——是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唯有“做人”,唯有把“人”做好,才不枉为人父、人母、人子、人女。母亲对父亲温馨的追思,更勾起了储存在我记忆深处的无尽回忆。
2
1935年2月,父亲出生于马桥古镇。因排行老大,深得教私塾的祖父喜爱。祖父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他自幼聪颖好学。及至新中国成立,十四岁的父亲成为全县首届师范生,十六岁毕业分至店垭完小任教。其后,在三十五年的乡村教学生涯中,父亲的足迹踏遍了保南五个乡镇的数十所学校。
在困难年代,父亲的经历是我们不可想象的。
按讲,父亲赶上了新社会,又恰值年少风华,子承父业,受人尊敬。大批乡村孩子渴求知识,父亲语数兼教,工作如鱼得水。可是,这种为学生解疑释惑的乐趣仅只持续了五个年头,一个巨大的噩耗从天而降——祖父被划“右派”,屡遭批斗,折磨致死。父亲家庭成分本是“富农”,头上又无端多了顶“右派儿子”的帽子,使其常常抬不起头来。更不幸的是,祖父含怨去世后,祖母与三个叔叔从马桥街被撵至乡下,强制劳动,接受监管;也是师范毕业的姑姑,经受不住打击,辞教陪祖母一同去到乡下。原本一门三个教师,现在却三个叔叔辍学在家,生活陷入困顿。这种惊天变故,对于任何一个家庭都是灭顶之灾。父亲以超乎年龄、超出心智的坚毅,把一切都咽进肚子,除了定期把攒下来的一点钱带给奶奶补贴家用外,嘱告叔叔姑姑守护好奶奶,用本分、勤劳去面对逆境,承受苦难,自己则以拼命工作来抵御心头的痛楚。
父亲的勇毅与艰忍,赢取了母亲的芳心。母亲曾是父亲的学生。因为贫穷,母亲十二岁才走进学堂,而十七岁的父亲恰好就做了她的老师——那是1952年。母亲发蒙晚,却成绩好,小学五年级便被推荐考入县简师,速成后任教于欧店小学。暑期教师集训与父亲邂逅,看到父亲大难在身而意志不衰,原本敬佩父亲教学能力的母亲,认为父亲是个值得信赖、值得依靠的人。于是,不惧其政治面貌不好的压力,坚持同父亲成了家。
在我四岁的时候,文革风暴来袭,成分论、挖历史问题骤然升级,无数次株连式的深揭深批,父亲未能躲过被打为“黑帮”的厄运。1969年秋,教师被遣回原籍。为避讳父亲出身,我们从歇马茅坪迁到了店垭天宝寨跟外婆生活,母亲到村小任教,父亲被勒令参加生产队劳动。直到第二年开春,父亲才被安排到偏远的断缰复教,后又在万寿、重阳等几所学校调来调去。无论任教地点怎样变动,父亲周末必定赶回天宝寨,挑水,打柴,种菜园,上街买商品粮,备足我们一周的生活所需。
断缰距天宝寨三十余里,高山连绵,路途崎岖,父亲周末回家,常常会采撷一些山菇、板栗、柿子等;到了冬天,连续几个周末都会背回一背篓木炭。父亲任教万寿时,回天宝寨有条穿越千担沟的捷径,五六里荒无人烟,沟二面壁立千仞,狭窄处一线通天,沟底乱石嶙峋,阴森可怖,早年还发生过杀人越货事件,白天行走尚有几分胆怯。可父亲有时周六忙得晚了,为避免绕道店垭十多里路程,一个人打着手电筒穿沟越谷,经过好几处坟地回到家里。母亲问他不怕鬼呀,父亲说,世上本没鬼,不信则更无。
1974年秋,我随父亲到重阳读初一,父亲做初二(一)班班主任。班上有一部分家住高山的寄宿生,他们以粮食换饭票,吃菜大都是带一罐酸菜或炒酱豆、铡胡椒(传统腌制,不易坏掉),生活极其艰苦。父亲对这些学生特别关照,从住宿(一人带一床被子,垫、盖合二为一)搭配、菜罐安放到粮食过称、饭票发放,父亲无一不做得周全细致。而在夏天的周末,遇上沮河涨水,父亲必会邀上家住河边会游泳的大个头男生,一起把女生及家住高山的学生,或背、或搀扶着一个个送过河去。
那个年代,因贫辍学的事经常发生,家访便成为父亲的家常便饭。记得父亲班上有个叫王家富的尖子生,兄弟三人上学,家庭负担很重。父亲几次去家访,都讲王家富学习天赋高,鼓励家人克服困难,支持其更好学习。高考恢复第二年,王家富以优异成績考取大学。父亲在马良中学做高一(二)班班主任时,其学生刘兴全品学兼优,却多次要求辍学。父亲步行二十余里去了解情况,得知刘兴全父亲早逝,母亲一人撑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活异常困难。父亲做好其家人工作后,为其支付课本费,把我的旧衣服、旧鞋袜接济给他,使其坚持读完高中考上了师范,成为全村历史上第一位老师。
大约整个七十年代,父母月工资总额只有七十余元,供我们一家六口吃穿用度外,外婆、秦外公(外婆后夫)以及父亲的家人都需要关照。于是,省吃俭用,箪食瓢饮,成为渗入父母骨子里的信条。但是,自打我与大妹上了初中,父亲就开始为我们订阅《上海少年》《中国少年报》《故事会》,后来随其到马良读高中,父亲又追订了《大众电影》《人民文学》(当然他自己也阅读这些期刊)。尽管这些刊物每期订价只有两三角钱,但全年下来,也要花去父亲大半个月工资。现在想来,我们从小生活于闭塞的山乡,初、高中阶段的这些课外读物,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特别是培养了我爱好文学的兴趣。
1978年,我高中毕业,高考前夜却突发高烧,腹泻不止。高考泡汤,上不了学,就意味着要下乡。十月份,我与十七名城镇户口同学到水田茶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为我腾出一口木箱,置办了被褥、保温瓶、洗漱等生活用品。赴知青点那天,父亲并无什么不舍,也无多少叮嘱,反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愉悦。我知道,父亲认为十六岁的我终于能够自食其力了——按照规定,下放第一年,国家每月给予十元生活费,吃饭绰绰有余。所以,父亲不愁我生活问题。加之我是男孩,的确没有什么值得父亲担心的。
次年初夏,全国出现知青返城潮,县里出台了由知青父母所在单位为返城者安排临时性工作的政策。因为教育行业的特殊性,我成为难以安置人员。情急之下,父亲想起一位旧识——山东籍南下干部、县外贸局副局长张惠东。数年前,张局长到天宝寨了解桑蚕发展情况,路遇父亲,两人一路攀谈,很是投缘,父亲把他接到家里热情招待,自此结下友谊。父亲试着给他写信求助,不想很快就接到让我去外贸局待业的通知。
报到那天,父亲拿出一双他未舍得穿的皮鞋(系一位在部队工作的亲戚赠送)对我说:“这次去外贸局待业,是你第一次到县城,也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虽是临时性工作,但必须珍惜机会,好好做事。这双鞋算是爸爸送给你走上工作岗位的礼物。”我接过来穿上(这是我第一次穿皮鞋,父亲也未曾穿过)试着走了几步,觉得自己一下子帅气了许多。接着,父亲用一个网袋装上我下放用的原套生活行头,扛上装有被子、衣服的木箱,送我到马良车站。来到班车处,父亲敏捷地攀上车顶(老式客车大件行李架设在车顶,车尾装有固定铁梯方便上下),帮我安放好木箱,又在同乘者中寻到一位熟人,嘱他到了县城帮我从车顶拿下木箱。上车前,父亲掏出十五元钱递给我,嘱咐我用十元买第一个月的饭菜票,其余五元留作临用。我点点头,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父亲第一次对我如此大方。一直以来,父亲都是狠不能一分钱掰作两半儿花。我读初二时,脚上的解放鞋破了洞,父亲看鞋底尚好,说鞋帮上有洞夏天穿着凉爽,并不舍得给我换双新的。而这一回,父亲不仅把自己舍不得穿的皮鞋送给我穿,还一次性掏出十五元钱,把我参加工作首月的生活费及临用钱全都付了。
父爱如山,父亲深重而博大的爱,如同一座永恒的灯塔,直至今天,仍在指引着我生活的航向。
3
1981年春节前,我写信告诉父亲要留站(时我已正式招工至马桥电站)值班,父亲决定全家到马桥过年。这是不正常岁月的阴霾消逝之后,我们首次在奶奶家团聚,奶奶、姑姑、叔叔们高兴至极,体己的话儿怎么都说不够。父亲更是无比惬意,从正月初一到初三,带着我们四处走亲拜年,还特意去镇街中心的魁星楼旁察看尚未归还的老屋,领着我们进入张家祠堂祭拜先祖、追念先人,用传统仪式让我们认祖归宗、续接族缘……
因为不甘于电站的枯燥工作,我利用业余时间读读写写,在地、县新闻媒体刊播了一些稿件。父亲知道后,一面鼓励我的行为,一面叮嘱我电站运行值班非同小可,决不可影响工作。我记着父亲的话,力求工作学习两不误,在1984年5月调县委办公室工作前,我已当了一年多值班长。
到县里工作不久,父亲也在暑假里被抽调做落实政策外调工作。那个暑期,父亲下荆州,上河南,查证汇据,呈交材料,使几名曾遭错误处理的外地教师洗去了不白之冤,恢复了教师身份。外调差旅费本可报销,可父亲途经县城却来与我挤一张小床。他告诉我,爷爷右派帽子被摘后,镇上的房产得以归还(也属落实政策范畴),轻松的语气里,传递着压抑他经年的精神负担彻底卸下来的喜悦。而谈起被错误处理老师回原籍农村生活的艰辛,父亲却显得分外沉重。他说,抓紧从快落实政策太有必要了。言下之意,我听出了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父亲还算个幸运者。而幸运之人现在帮助不够幸运者——也就不难理解父亲牺牲暑假,冒着大热天搭乘长途班车,风尘仆仆到异地为其同行证察清白的意义所在了。
1986年,父亲调至新成立的县财校工作,这与其长期从事的基础教育完全是两个体系。财校是为从事财税、财务工作者补充大专文凭而设立的,除了语文父亲可以承担外,其他专业课大都需请中南财大的老师面授或函授。年过半百的父亲仍被安排做班主任,在恶补大专语文知识以适应教学的同时,父亲多次外出观摩学习教学经验,尽心尽力做好函授教学服务工作。那时没有高速、高铁,保康距武汉五百多公里,父亲常常日夜兼程赴汉接请授课老师,授完课后,再按授课老师的要求,督促学员完成作业,检查学员学习笔记,定期组织学员测验、考试。财校连续办了九年,父亲做了九年班主任,为全县三百八十多名财税工作者获得大专文凭付出了辛勤劳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其间,父亲结合函授教学实践,在函授教育内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和信息稿件,其《质疑比较》一文获《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举办的全国语文教师论文大赛一等奖,年年被省市县财政部门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以说,在县财校最后工作的九年,是父亲最拚的九年,也是父亲最辉煌的九年。
4
1995年,财校教学工作终止,父亲也到了退休年龄,这年母亲也刚好退休。几十年来,一直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的二老,双双离开工作岗位后,却出乎意料地没有一丝失落感,更无患得患失的焦虑与攀高比低的牢骚。在陪伴、服侍年过八十的外婆的同时,二老盯上单元楼前的一处死角——那是建财校砌筑驳岸空出来的缓冲边角地,面积近五十平米,东窄西宽,凸凹不平,堆满了砂砾碎砖,弃之可惜,用则需要大动干戈。父母一起一筐筐搬走砂砾砖头后,再雇请城郊拖拉机运来熟土,一铲铲填垫,一锹锹平整,终于拾掇成菜园。自此,二老像绣花一样地经营菜地,分畦种植多品种时令蔬菜,且从不施放化肥,有了菜虫则花工夫一条条捉走,种的是真正绿色无公害时蔬。我们兄妹回家,除了最喜欢吃小菜园的菜外,还必到小菜园打卡,观赏蔬菜长势,体验父母种菜乐趣。
父亲还在菜园周边栽植了两棵樱桃、一棵核桃、一棵石榴、一棵枇杷、一棵柿树。这些果树虽然有点遮阳袭田,对蔬菜生长有一定影响,但把菜园装点得更加生机盎然、春华秋实,让我们回家去菜园有了更多惊喜。多年来,初夏回家,我们都吃得上父亲栽植的樱桃、枇杷;而秋季回家,则可到菜园打核桃、采石榴、摘柿子。
父亲孝老帮亲堪称家族楷模。1990年秦外公去世后,父亲即与母亲将外婆接来县城,共同生活了十五个春秋。母亲说,父亲对外婆的好让她感动。十五年里,父亲始终依着外婆的生活习惯,特别是退休后有更多时间照顾外婆,早晨为外婆烧水冲鸡蛋,晚上为外婆准备洗脚水;外婆出门下楼,父亲总是搀扶着送到楼下;外婆生病,第一个送医买药的必是父亲;外婆过生日,必与母亲做一桌好吃的让我们兄妹回家陪同;尽管外婆不会用钱,过年父亲也会给外婆一个红包。2005年腊月,外婆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父亲与母亲为其守灵五天,并承担全部安葬费用。在父亲心里,我奶奶承受了较多苦难,好日子没享多久就离开了人世,而外婆是他与母亲的最后一位老人,善待、赡养、送终责无旁贷。因为父亲对外婆孝敬有加,母亲也理解和支持父亲帮助亲人。二叔、三叔成家晚,孩子小,家庭比较困难,父亲为他们购种地化肥、买老少衣物,扶持侄男侄女上学;三婶患病来县医院治疗,出院相差五千余元费用,父亲掏腰包予以接济;小叔盖新房,父亲解囊相助……母亲明白,父亲之父早逝,他作为老大,力所能及帮衬兄弟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好家风。母亲更清楚,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节俭成习,惜物成癖,经年的旧物装满了库屋都不舍得扔掉。因而,与父亲相守六十一载,母亲从不担心父亲会有什么不合理开支,坚持父亲的工资完全由其自主支配。这种公平、和谐与信任,润泽了他们持久的感情,也滋养了我们儿女的心灵。
老有所乐在父亲身上有着完美的体现。忙毕菜园,照顾好外婆之余,他带母亲积极参加老体协活动,鼓励母亲参加老年腰鼓队,他自己则进入太极拳队,愉悦身心的同时,也有效增强了体质。父亲善学,进队不久,即精准掌握了太极拳术,以致大家推举他为队长。既然做了队长,就得为全队搞好服务。有次我从市里回家看望二老,父亲拿出他起草的关于解决老年体协经费的申请报告让我看,说队上的音响质量不佳,服装、鞋子、太极剑不统一,如果方便,让我帮助做些工作。冲着父亲的认真劲儿,我找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为老人们解决了音响。后来,县里批了部分补足经费,父亲逐一统计队员服装、鞋子型号,收齐个人应出费用,统一购置队服、太极剑,把老年太极拳队带得有模有样,多次在县里有关活动中进行表演。因表现突出,2012年父亲还被县里评为老年体育工作先进个人。
父亲爱动,进入晚年,特别喜爱旅游,他说服喜静的母亲,与之相携登武当、游三峡、去张家界、上武夷山,还去香港、澳门、深圳观光。八十岁那年,竟说动母亲,连续五年去往海南过冬。2017年,在外甥天添的带领下,二老游苏杭、逛上海外滩直至东渡日本,次年再游北京、重庆等地。耄耋之年,他携母亲把游轮、飞机、高铁坐了个遍,也品尝到了各地美食。
父亲说,旅游不仅仅是看风景、品美食,还能亲身体验国家实实在在的变化,使精神更加愉悦。为此,他的意愿非常坚定——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每年都要往外走走。母亲对我讲,父亲原本打算,只要腿脚力量恢复,他仍是要携她去海南过冬的——因为,上年离开时,父亲已向疗养院预交了定金。
可是,父亲的意愿停止在了这个对于他的儿女而言而无比残酷的冬天,父亲勤勉善良的一生歇息在了这个对于他的儿女而言而无比悲痛的冬天……
亲爱的父亲,在您离开我们一周年之祭里,谨以此文感懷您绵绵的厚恩,寄托我们深深的哀思。
郝敬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让每一寸土地都美》(文汇出版社),《西路苍茫》(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