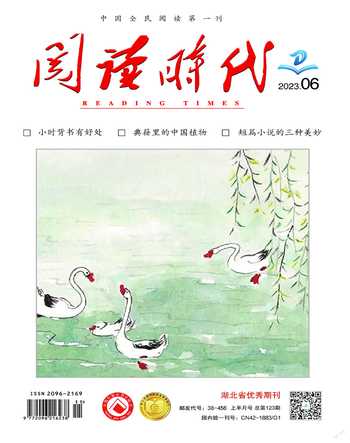他爱白云的飘浮 因为懂得漂泊的甘苦
李双志

德国西南部的小镇卡尔夫距离瑞士最南端的山村蒙塔尼奥拉约306公里。今天如果乘火车从卡尔夫前往蒙塔尼奥拉,大约需要六七个小时。
而从卡尔夫走到蒙塔尼奥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1877-1962)用了一生的时间,八十五年的岁月。如今,在他逝世六十年之后,他的文字依然召唤着全世界热爱文学的人,追随他的心灵漂泊,在如磐风雨中探寻人性的希望与美的光辉。
小镇的青春,成长的创痛
1877年7月2日,卡尔夫的一个新教虔敬派家庭中诞生了一个男孩,父母沿用孩子外祖父的名字,给他取名赫尔曼·黑塞。
十四岁时,黑塞在父母的期待中进入了卡尔夫附近的毛尔布伦修道院。但他的不羁天性和文学追求与修道院规训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他深陷苦闷,濒临绝望。第二年他逃出了修道院,并且在与家人的通信中流露出自杀的念头。家人将他送去了精神病疗养所,随后又让他去做钟表工厂的学徒工,放弃了让他继承家学、入职教会的愿望。黑塞自己则坚定地走上了文学道路。1895年他开始在图宾根一家书店里做学徒工和助手,1899年开始发表诗歌,1904年以一本《彼得·卡门青》一举成名,从此成为职业作家。
1906年,黑塞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贝诺利已定居于博登湖畔。面对着宁静的湖光山色,他以自己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那段艰难岁月为素材,写出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在轮下》,再次轰动文坛。封闭、压抑的学校生活,躁动不安的少年心灵,冷漠保守的成人世界,令人扼腕的夭亡结局,这是黑塞版的“残酷青春”,也连通着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文学中的青春书写。
不过,黑塞对青春的追怀不止于这一声哀叹。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还未散尽,身心俱疲而茫然失落的德国年轻读者,纷纷在一本名为《德米安》的小说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书中记述了作者埃米尔·辛克莱从十岁到二十多岁的成长历程,全书奔涌着一种探寻自我的真诚,一种渴望新生的热忱,让人很自然地认定是出自一个青年作家之手。
然而,辛克莱其实是黑塞的笔名,他有意让人误会这是一部作家自传,目的就是要让读者与自己一起沉浸式地体验特殊年代里的少年情怀。同时,他也将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精神分析方法融入到这部小说的写作中,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本能欲求与原型幻想一一剖析给读者。《德米安》由此一改《在轮下》的悲情格调,成为时代特色鲜明的一部成长发展小说。
对于黑塞来说,毛尔布伦修道院的创痛经历或许是他最希望告别的青春记忆。但在迈过五十岁门槛之后,他却让修道院连同其中的苦修生活再次进入自己的文學世界里。1930年出版的小说《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其故事发生的核心场所是历史悠久而戒律森严的玛利亚布隆修道院。不过,黑塞并没有重复二十年前那个自传色彩浓烈的悲伤故事。他将小说叙事的时间设置调回到中世纪,以丰沛的想象力构造出与自己生平截然不同的情节。
最重要的是,他塑造了德语文学史上最为闪耀夺目的双子星——纳尔奇思与歌尔得蒙。一个顺应经院教育,严守禁欲主义,智识天赋超群,象征了人的灵性追求;一个莽撞好动,离经叛道,纵情于感官享乐,生命活力饱满奔放,象征了人的肉体存在。而偏偏这两人成为了修道院里的同窗与挚友,彼此情深义重。歌尔得蒙从修道院出逃,辗转红尘,最终却因缘际会,经纳尔奇思搭救,重回修道院。然而他终究无法回归这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空间,再度流浪之后,最终病死在纳尔奇思怀抱中。这彼此吸引又永远分离的两极结构,无疑寄托了黑塞的人性思考与感悟。
醒世的呐喊,悟道的歌吟
真正让黑塞的声名跨越大西洋和欧亚大陆的,是两部堪称石破天惊的奇书——出版于1922年的《悉达多》和出版于1927年的《荒原狼》。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嬉皮士一度视这两本小说为反叛精神的“圣经”。其实对于黑塞自己来说,这两本风格内容迥异的作品是他的疗愈之书,是从他人生最严重的危机中孕育而成的果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黑塞和德奥大多数作家一样,还天真地期待一场战争能一扫颓靡与倦怠,让民族与国家振作一新。然而很快他就清醒过来,当年十一月就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了文章《啊,朋友,不要用这些声调》,反对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对战争、仇恨与屠杀。但是他的这声呼喊招致了德国媒体的大肆攻击和“叛国”污名,也让他在文学界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祸不单行,1916年黑塞的父亲去世,随后黑塞的妻子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接二连三的打击让黑塞再度坠入精神崩溃的深渊,他接受了荣格派心理分析师朗格博士的治疗。1919年他与妻子分手,移居瑞士提契诺州,最后落脚于蒙塔尼奥拉,在他一生挚爱的湖光山色中写诗、作画。虽然离世隐居,但黑塞却驱动创作之笔,造就了两则意象奇丽的心灵寓言。
1920年,《悉达多》发表,黑塞将其献给自己的法国朋友罗曼·罗兰。他强调这本书写作的背景是1914年之后令人窒息的灾厄,他要努力超越民族之间的分隔,向罗兰展示自己创造的爱与信仰的世界。黑塞说,《悉达多》披着印度的外衣,却更接近中国的智慧。当此之时,多少欧美文人,在世界大战之后对西方现代文明感到幻灭,急欲在古老的东方中寻得精神寄托。但唯有黑塞,真正努力在中印两家的思想源流中沉潜体味,成就了融合不同世界的文学奇迹。
与远赴印度的心灵漂泊之旅不同,五年后出版的《荒原狼》从一开始就将一个在欧洲市民文化边缘挣扎的中年男子形象推到了幕前。他痛斥市民道德的伪善,又贪恋市民生活的安稳,心中有狼嘶吼,眼前无家可归,流浪却又不满于流浪,不容于世俗却又无法与其彻底决裂。面对周围世界的庸俗和虚伪,荒原狼发出了惊世的呐喊;而面对自己内心的分裂和混乱,荒原狼又发现了莫扎特代表的古典理想与爵士乐代表的新世俗文化之间的和解可能。小说的开放式格局也暗示了现代人永远不会停止地自我探索。奇绝的形象,奇幻的情节,奇妙的布局,让托马斯·曼也不禁击节赞叹,说这是德语文学中可以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比肩的现代派杰作。
山中有隐者,云影共天光
对于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重来的噩梦。尤其对于德奥两国的人来说,噩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吞噬他们的“昨日世界”,纳粹势力迅速蔓延,希特勒掌权后变本加厉地迫害犹太人和一切不符合纳粹意识形态的作家、艺术家。德语作家开始大举流亡。
1931年的黑塞,与这阴云还相隔遥远。他在蒙塔尼奥拉搬进了新家,在静谧山林和新婚妻子的陪伴下,日子过得安宁而惬意。但他很快意识到了时局的变化,也很快就承担起了援助流亡作家的道义责任。从1933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黑塞在蒙塔尼奥拉的家接纳过不计其数的流亡者,在签证上帮他们与瑞士政府交涉,在情感和金钱上给予他们无私的帮助。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在流亡途中都曾到此做客。1939年起,黑塞自己的作品也被纳粹德国列为“不受欢迎的书”,禁止出版。然而这也没有阻挡黑塞继续向流亡作家伸出援手,并且继续写作。
从1932年开始,黑塞耗费十年心血,写完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玻璃珠游戏》。这是一部未来小说,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黑塞设计了一个学院系统卡斯塔里,将音乐、哲学、数学等人类精神领域都转化为抽象符号的游戏,也即所谓玻璃珠游戏。主人公克奈希特天资聪颖,在这个与俗世隔绝的卡斯塔里王国一步步晋升,最终成为了玻璃珠游戏大师。不满于这个空间的封闭,他走出了卡斯塔里,走向了普通人的世界,投身教育青年的事业,却不幸溺亡。这部小说1943年在瑞士出版,托马斯·曼对之赞誉有加,将其视为自己的《浮士德博士》的姊妹篇。
毫无疑问,卡斯塔里也有着毛尔布伦修道院的影子。这座未来学校寄托了纯粹的智识修养和心灵培育的乌托邦理想。也正因为此,1946年瑞典学院在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黑塞的时候,尤其提到了这部哲理小说在黑塞作品中的特殊地位。
有趣的是,黑塞并未出席这场颁奖仪式。此时的他,已安心做瑞士山中的隐士,俯仰天地草木,无心牵挂世间名望,继续写诗,作画,写短篇的散文,直至1962年8月9日因脑溢血在睡眠中与世长辞。
如果说写小说的黑塞从1943年开始就归于沉寂,画家和诗人黑塞却是一直创作到了生命尽头。黑塞的诗同样是德语文学中的瑰宝,继承了歌德与浪漫派诗人的自然诗歌传统,细腻而深情地描绘出山川万物,记载了静夜之思与田园之梦。他最爱在诗中描写云。苏尔坎普出版社专门出过一本诗集,收录了黑塞六十多首写云的诗。他写云的飄浮,写云的流散,写云的不羁,写的当然也都是他自己。
他在《白云》中写道:“一颗心灵若不曾/在漫漫旅途中/知晓漂泊者的所有甘苦/便不会理解云。”而他不正是在漫长人生旅途中尝尽甘苦的漂泊者吗?
这位如云的漂泊者,在浩渺无边的文学天空里给我们留下了绵延无尽的情思。而热爱李白诗歌的他,应该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源自《新京报》,有删节)
责编: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