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我在场,但不想腐烂

艺术家向京的工作室坐落在北京东六环外的宋庄艺术区,没有门牌号。
空无一人的街道旁,匍匐着一头巨型大象(向京代表作之一《异境——白银时代》的作品模具),像招牌一样醒目——就是這里了。
这座三层高的建筑采用了大量红砖漏砌的设计,营造出独特的光影氛围,向京和助手们常年工作、生活于此。
向京在会客厅的一面落地窗前就座,消瘦的面容和标志性的齐耳卷发。窗外庭院里,几件雕塑点缀在一棵150岁的老榆树与红木香、白玉兰、紫藤和银杏之间。东北角有一方池塘。2019年做完大章鱼(《降临》),向京再没有做过雕塑。
助手东东来工作室五年了,在她眼里,不做雕塑的向京依然保持着多年来自律的作息,生活非常简单——种花修枝、喂鱼撸狗、看书剪片,享受属于自己的乐趣。
家里的小动物都有自己的故事:两只跟回家的流浪狗已在工作室落户五年;一条全身溃烂的狗,靠五支人血白蛋白才从生死线上活过来;一只飞到院子里赖着不走的孔雀,头上的羽冠已经变成三根光杆儿,“老得不能再老了”。
向京把它们打点得健康、体面。对那只病狗下了很多功夫,虽然嘴上总说“破狗”,但雷打不动地天天上药,每周带去泡药浴,还凭借自己做雕塑对骨骼结构的了解,定期给它做按摩,进行行走训练。
2023年4月,向京新书 《行走在无形无垠的宇宙》 面世。书中汇集了二十年来她与作家林白、哲学家陈嘉映、电影学者戴锦华、诗人朱朱等不同领域朋友的对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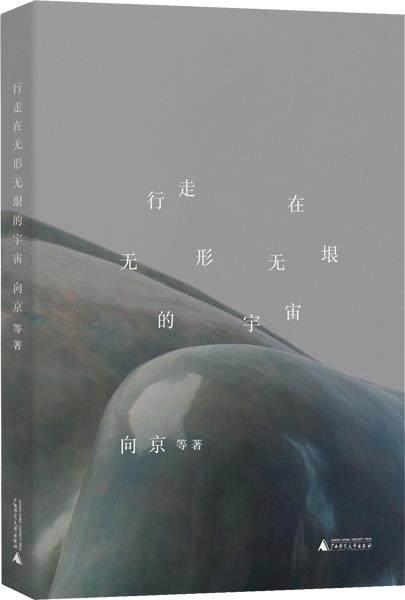
编辑周昀之前曾担任向京画册中文版编辑,这次他把谈话的时间顺序打乱,将不同时间谈论同一话题的片段用蒙太奇方式剪辑到一起,形成一篇长谈。
这是一本打破常规的访谈录,周昀去掉了各章节的标题和作品配图,营造出一群人围坐聊天的效果,类似一幕舞台剧。
向京对是否出版这样一本书犹豫了很久。她在跨度长达二十年的这些对话中表达的观点如今已成为过去时,她很难从“我曾经作为一个这么愚蠢的谈话者,贡献这些愚蠢的观点”的羞耻感中抽离出来。最终她被周昀的创新思路和满腔热情所感染,决定支持这个年轻编辑做一次大胆的尝试。
看到成书后,向京觉得文本呈现了自己思想的变化,有些甚至前后矛盾,也挺有意思。“这本书其实也是一个创作,把我曾经的素材转化为新作品的素材,只不过作者署名应该是周昀,而不是我。”
停止雕塑
二十年的艺术家生涯中,向京整个人被绑定在工作室。做雕塑是漫长的过程——泥塑、翻模、打磨、上色,天天要干活。“劳模”向京以平均三年一个系列(十余件作品)的速度稳定产出。这些玻璃钢作品大多是女性身体,表达着关于疼痛、困扰、忧伤和安慰等等内心深处的感受。
夏天开空调会把雕塑吹干,向京常常不开空调,在摄氏四十多度的工作室汗流浃背地工作。做大型雕塑站得高,上面的空气更热,有时她感到自己的脸胀得都要爆炸了。
当时的邻居是位老同学,特别会享受生活——吹着空调,抽着雪茄,喝着小酒。向京被邀请去吃现烤的面包,当她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踏进门,不禁感叹:“哇噻,真凉爽!”就像肉身又恢复了知觉,很快又自责:“我怎么都不知道怎么做人?”
工作室的阿姨照顾向京多年。做雕塑的时候她完全是“被饲养”的状态,阿姨给什么她吃什么,给多少吃多少。
向京意识到了问题——“当你如此无体感,甚至对正常人的生活都没什么需求了,这也许是个优点,但当你的生命慢慢趋向枯萎,你其实并不能真正去体验,也不能真的发现问题。”
问题先行是她的工作方法。这些问题大多来自她的阅读经验,特别是古典主义哲学理论:“敞开者”(The Open)借用了里尔克诗句里的意象;“保持沉默”来自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应该保持沉默”;“这个世界会好吗”则是新儒学大师梁漱溟面对的诘问。
向京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感到”,而不仅是被“看到”。比如刻画手——有些人看着很温和,但手是很神经质的,会暴露人性的一种内在的感觉。长期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德国学者阿克曼说“向京的作品是有灵魂的”。

向京工作室门前摆放着雕塑《 异境——白银时代》 的作品模具。图/本刊记者 梁辰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对人、对人性那么感兴趣的人,但后来觉得自己并不了解真实是什么。当你慢慢进入到一个你长期努力搭建起来的城堡,你已经跟这个世界很隔离了。你只能在书本里寻找你的命题。你认为这种命题是终极性的,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虚妄。”
她决定停一停。
客观原因则与互联网带来的巨大改变有关。向京看到网络上的话语形态是人人都在发言,都在表态,也都在表演,但已没有了倾听。“信息爆炸,很多东西我还没完全消化过来,所以不想贸然发言。”
当世界进入到一种混沌和不确定性,向京感到迷惑,继而失语。
2017年,上海龙美术馆举办了向京最大规模的作品回顾展,那段时间她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各阶段的艺术创作,“肉身”、“内在性”这样的词语啪啪啪往外蹦。与此同时,另一个向京跳脱出来,在一旁嘲讽:“你可真熟练。”
向京对这种熟练深恶痛绝,“这完全是被所谓成功裹挟的惯性表达,我下决心不做雕塑也是因为要给自己一个绝对的净化,除掉所有夹杂在工作思考之外的干扰,避免再次坠入陈词滥调之中。”

作品《 降临》 。图/向京工作室提供
透過DV投身火热的生活
不做雕塑后,有段时间向京拿着个DV满世界跑,试图投入到“沸腾的生活”中。
之前长时间关着门工作,与外界形成某种疏离,已经无法自如地与人打交道。拍DV让她从工作室走出去,获得具体的感知,同时又是一种很好的掩护——为介入到他人生活提供合理的借口。
做雕塑要经过漫长的工序,影像则转瞬即逝,需要快速反应,让身体和感知更加敏锐。
她拍居住地宋庄的变迁。几天没出门,周围就空了,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拆的痕迹。“宋庄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微缩景观,几乎没有一天是固定不变的。”
跟弟弟回老家福建泉州,向京被呈现着时间叠加痕迹的不同建筑风格吸引,看到什么都“哇噻”,一路狂拍。她意识到自己的大惊小怪,问弟弟,“我是不是像个外地人?”弟弟答,“你像个外国人。”
“可能是长期沉浸在外国理论这种知识层面里,我对文化的眼光已经改变了,很多切入点其实是很滑稽的。”向京说,“拍的素材越多就越发现,你能抵达的地方非常有限,你能看到的非常有限,透过这种‘看到,你能理解到的东西更有限,就像一个不断被震惊的傻帽一样。”
向京用自己拍的素材配上音乐,剪过一个类似MV的短片。为此她去“胶囊日记”(注:一个记录生活的网络日记本)寻找年轻人描述生活的金句——“美好的一天从卸载微博开始”、“我太平庸了,所以我想活一万年”、“闭嘴真的是一种智慧啊”、“我想要快速快乐”……片子呈现着当代生活的混沌,同时也掺杂了当代人的情绪。这种生活是向京不曾经历的,但作为社会的一员,她特别能共情。
向京原本计划带着这支作品参加展览,但当她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一个博主用类似的方法(视频素材+配乐)制作的作品,“完全被震撼到了”。他是在网上找的视频,配上流行乐,剪得“波澜壮阔”,而且作品量很大。“一看他的作品,我就傻帽了,这才是牛逼的当代艺术,干嘛非要自己拍,从表达本身来说,这样的作品更当代。”
关门做雕塑的时候,向京常年用一款不能上网的老式手机,现在可以熟练地操作智能手机刷抖音和小红书,什么都好奇:脱口秀表演、哲学类科普短视频、社会事件......
“像‘铁链女这种,站在基本的人性立场和社会价值层面,我肯定会同情她,但我确实不能想象她每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无法感同身受。但首先你得了解这种时代的疼痛感,才不至于变得更迟钝、更无情、更愿意悦己。”
做完《降临》后,向京特别想到处走走,但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中断了这个计划。
后面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让她陷入了沉思,“你发现所谓的现实,不用你走来走去地去采集,它就这么赤裸裸摆在你面前。”
疫情期间,只要还能走动,向京每天都要上街去拍,记录下这座城市呈现的异样感——曾经的车水马龙、人潮滚滚一下子变成万人空巷。再上网一看,发现更“精彩”,相比之下自己的东西“弱爆了”。
疫情之前,她和几个艺术家朋友每个月都会到画家张晓刚家里,举办沙龙式接力展览和交流。大家边吃饭边就一件作品展开讨论甚至争论。
向京每次都拿着DV 记录下这“迷人氛围下”的欢聚时刻。现在回看,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朋友们感慨那时是“浸在蜜里,而不自知”。疫情过后,他们又恢复了聚会,也会讨论艺术,但是明显能感觉到一种消沉的气息在弥散。

工作室的展厅内陈列着向京各个时期的雕塑作品,正中的作品为《你的身体》 。图/本刊记者 梁辰
跟自己的工作告别
戴锦华看向京的作品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都非常强烈。一种是强烈的个性化和风格化的东西;另外一种感觉是,作者是完全抽离的,不能从作品里看到任何关于作者个人生命的印记或者情感性、记忆性的东西。
纵观自己的创作生涯,向京把《你的身体》视为一座里程碑。人物从之前那种小女孩的视角——对外界的抗拒和排斥,一下子转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抛开外衣和社会身份,向你敞开。
作品像一个个物证,见证着艺术家的心路历程。借由《你的身体》,向京意识到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质的改变。
直到最后一个系列“S”之前,向京的创作焦点都在问题本身——挖掘和剖析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再用作品去建构它。向京反思自己做了这么多年雕塑,其实从没认真思考过雕塑到底是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发展这样一种介质的语言。
“S系列”是向京特别喜欢,但最不被外界理解的一组作品。无论是可拆分重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是无臂、可切分的女性人体《S》,向京试图用具象的雕塑语言去组织一个可以延展出去的意象。
一直以来,女性、女性艺术家、女性主义艺术家是向京绕不开的话题,在其官网的个人简介里,有批评家的意见:与其说向京是个“女性主义”艺术家,不如说她是个带着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的艺术家。
戴锦华认为向京的艺术是女性的,也是关于女性的。“但这里的‘女性,不囿于任何规范惯例,也非刻意源自任何立场或主义……向京的创作自发轫到极盛期,几乎持续奔涌为一个个作品系列。其起始点,与其说是面对父权社会的挑衅或嘶喊,不如说是一部昔日私藏的日记:关于个人的生命,关于成长、变形中的身体,关于私密的、不曾付诸语言的也没有语言可托付的体验。”
在龙美术馆的大型回顾展上,三千多平米的空间摆满了向京的作品,像一首终曲,很有隐喻性。她在里面流连忘返,一方面是跟自己的工作来一个隆重的告别,另一方面,也在跟对自己的创作来说特别美好的一个时代作别。
在新书《后记》中,向京说道:“在做展览的时候,我已经非常鲜明、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特别坚信的、恨不能当成我一生艺术观的这种东西,其实在这样一个时代挺失效的。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完全习惯浅消费了……不是艺术变得肤浅,而是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逻辑里面,一切都被肤浅化、庸俗化。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你所想要研究的命题和方向也不被真正关心。”
时代红利
2010年,向京的作品《一百个人演奏你?还是一个人》以627万元的成交价刷新了中国雕塑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她没怎么激动,那时她已经“不那么愁钱了”。

作品《 一江春水向东流》 。图/向京工作室提供
反倒是之前在上海师范大学雕塑工作室当老师时,自己的一件作品拍到5万元,向京当时正在给学生布展,听到消息后兴奋得直跳脚,因为这笔钱能解决实际的生存问题。
英国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从草根走向主流,“从2000年开始,尤其是到了2006年,当代艺术真是卖得太好了!”凯伦注意到,许多热钱开始流向艺术领域,所有美术学院都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院系,艺术学生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人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家也从千禧年开始纷纷归国发展,许多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名利双收,成为时代的宠儿。
向京享用着当代艺术井喷期的红利,从雕塑里“很早就收获了功名利禄”,这让她可以专注地工作,不必再去考虑生计。金钱首先带给她宽敞的工作环境,让她可以自由地做大型雕塑,不用发愁卖不出去,因为工作室都能放得下。
她的作品被大众喜爱,她本人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化着精致妆容,穿着高档服装的精修照片频频出现在时尚杂志。虽然向京很排斥这种矫揉造作,但借由出名,自己的艺术似乎就能被更多的人知晓和关注。
在生活上,向京一直很低欲。吃还稍微讲究一点(多年素食),但对首饰和华服她毫无兴趣。
挑选衣服的条件只有一个——穿着舒服。从高中到现在向京一直瘦,身材没走样,所以现在还偶尔穿上学时的衣服。
以前有很多裙子,现在岁数大了,不穿裙子了,每天基本上就是运动鞋配裤子。衣服穿到破为止,特别喜欢的衣服穿破了还会补,妈妈和家里的阿姨都精通针线活。
规律作息、清淡饮食、保持运动,这么做不是为了长寿,而是为避免最后的时刻一身病,“死得难看”。
经营“稀奇艺术”
向京出生于1968年,母亲是一位文学编辑,父亲在电影业工作,她从小在文化圈子里长大。那时最时髦的就是读书,家里各式各样的文学杂志以及难啃的西方哲学,都在向京的阅读范围,潜移默化形成了她日后艺术创作的思考模式。
向京在中央美院附中度过了美妙的青春期。附中是寄宿制学校,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美术馆都很近,她常跟同学们去看话剧和展览。
学校旁边的隆福寺是北京最早的商业街,那里出售跟流行文化相关的商品,比如音乐磁带。上课的时候,如果窗户开着,经常能听到外面商店传来的张行、张蔷以及刘文正等港台流行乐的声音。校园广播室播放的是The Beatles、Michael Jackson、David Bowie……
学校里开始有舞会,她经常整夜跳舞,过了宿舍熄灯的时间,就从墙上爬进校园。
当时轰动艺术界的星星画会、现代艺术大展都发生在隔壁的中国美术馆,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能看到这一切,向京已经感到幸运。
她曾经想做一个关于80年代的片子,看过一些书,还找了很多跟80年代一些大事件有关的人聊了一圈,之后就放弃了这个项目。
“我觉得真实的80年代什么样,不完全在这些讲述里面,因为当时的媒体形态、话语权基本掌握在这些文化精英手里。那种80年代是黄金年代的说法,包含一种典型的文艺精英对于自己曾经的青春经历的描述。宏觀的对于80年代的讲述还是太大的命题,我hold不住,我也可以说80年代是我的黄金时代,但这仅限于我个人的记忆,而记忆是一个多么主观的东西。”
最近,向京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对品牌“稀奇艺术”的经营上。
过多的浸入商业逻辑,是否会影响今后可能的艺术表达?影响肯定是有的,但向京认为它并非完全负面,“如果不是接触商业,我没有机会如此具体地去面对赤裸裸的、甚至带一点残酷的现实,这是躲在艺术的象牙塔里永远看不到的。”
采访的四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转眼已是黄昏。我为计划外的拖延表示歉意,向京低头快速翻看手机,“一堆事让我处理。”她安排助手带我参观楼上的展厅,自己奔向办公室,一场电话会议正等着她。
对话向京
人:人物周刊 向:向京
人:一个雕塑家不做雕塑了,或者说一个创作者停止了创作,究竟是什么原因?
向:雕塑这种介质对我而言是一种限制,它是一种非常封闭的媒介和语言,放弃雕塑是我早就有的想法。
我从雕塑中获得了所谓的成功——世俗上的财富和充分的名声。当我抛开这种对成功的渴望的时候,确实会想,“到底是什么驱动着我工作?雕塑还能够燃起我这么强烈的表达热情吗?”我必须确认工作的动机。
由于互联网的影响,世界早已进入一种不确定性中,当你把眼光放到很具体的现实世界,就会发现其实这根本不是艺术所能承载的。所有言辞凿凿的人都可疑,不管是假装深刻地说一些文本性的东西,还是为这个所谓的现实去呐喊和愤怒,都显得肤浅和滑稽。
人:2017年的回顾展后,你在2019年又做了《降临》,是手痒痒了吗?
向:那段时间就像被点燃了一样,一直有一只章鱼在脑海里盘旋,而且它是360度立体的不停地转。我觉得太折磨了,不做出来特难受。确实就是被这个东西追赶得走投无路,只好去干活了。
人:章鱼有什么隐喻吗?
向:章鱼是一个意象化的东西,它没带什么暗示,就是一个形态总在脑海里。我认同戴锦华老师对它的解读,她认为今天这个世界的失序,各种力量在不断制造更大的撕裂,章鱼身上那种柔软的力量在这样的时代是非常值得期许的。
人:现在还拍DV吗?今后会考虑用视频这种介质进行创作吗?
向:拍DV对我来说是个过渡阶段,我不觉得最终会拿影像去做作品,或者说希望未来的工作至少从介质上呈现一种开放性。我一直比较排斥把个人经验作为素材直接转换成作品。
拍DV的过程主要是推动我到处看看,这跟之前在工作室做雕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太多东西是在文本阅读的背景下建构起来的。有一段时间我就完全不看书了,还大放厥词:“反知识”。我觉得很多时候知识对人的感知力和直觉力是一种伤害,或者说是捆绑。我自己曾经长时间浸泡在所谓的文本习惯里,其实挺有问题的。
人:今后会考虑时下热门的人工智能作为介质进行创作吗?
向:我肯定会好奇,也会去了解AI包括Chat GPT这样的技术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关心这些热门话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不会立马拿这些东西开始干活,我还真不是那么快手。为什么要选这个介质,我要先说服自己。
人:跟着时代的脉搏?
向:我为什么要跟着时代的脉搏?我又不是弄潮儿。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弄潮儿的性格,很多问题要明白了、消化掉,才会去做。
AI、泥巴或者油画,对我而言它们只是介质的区别,而不是工作本质的区别,不是说你用AI就比较先进。我从一开始用雕塑做作品,就是为了反对这种以“先进”为标准的进化论——工具越先进,创作越先进。如果你的观点落后而腐朽,介质语法再“先进”也是腐朽。当代不当代不是以工具先进不先进来区分,关键还是: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自己要表达什么?
人:新冠疫情对你有哪些影响?
向:新冠疫情这么一个重大突发事件,确实改变了太多东西,其实这种改变在疫情前就开始了,只不过疫情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把一些问题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互联网带来的颠覆性变革类似于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知识精英话语体系的崩塌:我们曾经坚信的、牢牢掌握的一种知识体系以及对世界的一种确凿认知,特别是一种普世的理想,在某种巨大的现实面前变得不再坚固。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重回一种混沌,而这种混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它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改变,我们也很难预测。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始终强调建构的重要性,还是要在这种混沌当中去建构。
人:如何重拾信心?
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是有心理阴影的,但我觉得人没有那么脆弱,也不应该就此消沉。我们很幸运经历了相对漫长的和平时期,都以为太平盛世是一个正常和自然的现象。但你从人类史的角度看,它是不正常、是异常的一个阶段对吧?只是我们很幸运赶上了而已。
就我个人而言,我要保证自己在场,同时保证自己还对很多问题保持敏感,我要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因为对我来说,自我的处境是问题生成的一个基本前提。
人:现在每天都在忙什么?
向:现在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具体化到身边的人和具体的事上,具体也一样可以生成问题。开始接触并关注很“日常”的生活,也能怀着八卦心去听别人扯闲篇,听着还挺带劲,这在以前是我很排斥的。
我还是想说首先是去做人,真实地活着,真实地拥抱一切——好的、坏的、温暖的、冷酷的、美好的、肮脏的。这个过程中,理清自己的价值观,再去观看这个时代,看它一步一步怎样变化。
人:你曾经用“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著名的诘问为自己的作品命名,现在你对这个世界怎么看?
向:我觉得你始终关心,始终参与,它才会有变好的可能。要去做事,不要天天抱怨。我是个悲观的人,但不消极。我对很多事情忧心忡忡,但恰恰是因为悲观,所以我不消极,否则就会陷入黑暗的泥沼。

向京工作室外观。图/本刊记者 梁辰
人:最近有去看什么展览吗?
向:我现在很少去看展览了,最近去798看了耿建翌的展览,看完特别激动。我被当代艺术早期这种纯粹的艺术探索深深打动,这种探索在今天已经非常缺失。那时候艺术还没有那么多的资本推动,也没有利益,大家做艺术纯粹是为了思考,艺术是思考之后表达的工具,所以它很纯粹。
好比文艺复兴正好在人类文明的年轻时代,1980年代也像是当代艺术的年轻时代。初生的状态充满了朝气,一切都是空白,所以第一代的这些艺术家感觉一切都可能,一切都可以做,一切都有待发现,就是那样的一种精气神。
看老耿的作品,有几件我觉得特别棒,它们确实是不同方法论的尝试,背后又能建构起观念和意识形态,现在看着还很洋气,一点也不过时。
你能看到他不断地去寻找一个路径,留下一个线头,然后唰地跳到另外一个路径上去。如果他是以成功为目标的话,会在每一个路径里积攒更多的作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符号,可能会成为他成功的一个条件,但是他没有,而是留下很多线头,没有去深挖,这是他的局限,但也是他的可贵和可爱之处。
人:无论如何,接下來你还是会有新的创作的吧?
向:我既不想给自己制定一个所谓的计划,也不想做任何许诺。理由很简单,比方说我此刻突然死了,有什么遗憾吗?我没有任何遗憾,我的人生已经非常满意了。如果我还能做点什么,首先要能说服自己——我真的特别想要做这个东西,特别想要做一个表达,才能驱动自己去做。肯定要摸索着做一段时间,感觉这个东西特别有说服力,我才会分享给别人。不然的话,向京这人从此就不见了。无所谓。这世界缺谁吗?不缺谁。
(参考资料:《行走在无形无垠的宇宙》,向京等著;《语言之内,历史之外》,作者戴锦华;《一天零一页》视频访谈《向京|走出城堡》;《耿建翌 摘掉艺术家的帽子》,作者蒯乐昊。)

